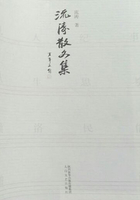
第13章 两个好人
那一年,我在西安上大学,放寒假后和一个同学结伴去广州看望一个朋友。出发的那天下午,天上飘洒着雪粒,寒风蛮横地往脖子里灌,旅客们匆匆忙忙地上车。我们座位对面坐着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年龄,女的身着大红色羽绒服、羽绒裤,配一双红皮靴,圆脸,说话笑眯眯,很开朗。男的国字脸,穿一件当时很流行的黑呢子大衣,话不多,微笑着听我们说话,偶尔插一两句,很友好,温暖人。黑衣大哥和红衣大姐也是偶遇,我们四人一路聊得很投机,渐渐熟络,爽朗的笑声,温馨的气氛一直伴随着我们。火车奔跑着,窗外渐渐暗下来,几点亮光一闪而过。交谈中得知,红衣大姐在兰州某医院工作,是位医生。黑衣大哥在铜川某矿务部门工作。大哥和大姐都是去广州探亲。
晚上,当火车进入湖北境内时,我的同学突然喊肚子疼,趴在桌子上痛苦地呻吟,额头上沁出一层细汗,我一时慌得手足无措。那位红衣大姐细心察看,根据病痛情况,判定大概是急性阑尾炎。到湖北孝感时,同学软成了一滩泥,我想马上下车送同学去医院,红衣大姐和乘务员商量后建议让我们最好在武汉下车,因为武汉医院医疗设备齐全。当时,我心急如焚,六神无主,外面风雪正急,寒风呼呼地吹打着车窗,透过灯光,清晰可见满天飞舞的雪花。大姐和大哥不停地安慰我和我的同学。我同学尽管脸色发黄,人蔫蔫的,但情绪已安静下来。
火车终于停顿在武汉。我和同学急忙在汉口火车站下车,我背着同学撒腿就跑。因为是半夜又下雪,挡不到出租车,跑了几条街道敲了三家医院的门,都因半夜不做手术拒绝了我们。我既着急又愤慨。北风吹,雪花飘,我在风雪中不停地奔跑,几次险些滑倒,终于在汉口港务医院找到了答应给做手术的医生。我放下同学后,一下瘫坐在凳子上,大口喘气。可屋漏偏遇连阴雨,事不凑巧,突然停了电,当晚做不成手术,只有先打了止疼药挂上吊针等电来。我的同学躺在病床上发出了轻微的鼾声,他逐渐进入了梦乡。我却无论如何睡不着,我怎么能睡着?我趴在椅背上,忧虑、伤感、无助。我点着蜡,看吊针一点一滴地下落,数一二三,时间仿佛和屋外房檐上挂的冰锥一样凝固了静止不动。蓦然,我想起了随身携带的衣物和同学的照相机,下火车时由于太匆忙,一着急竟忘了带。回想一路的艰辛,一时大恸。“滴答滴答”,夜深人静的冬夜,我充分感受到了吊针冰冷的节奏感,还有远离家乡无尽的无奈与无助。就在这时,蜡上的火苗蹿着跳跃了一下,门开了,红衣大姐和黑衣大哥又出现在我面前,我一下子愣住了,拿着我和同学失而复得的物品,一时竟然说不出话。我那不争气的眼泪悄悄滑落下来。这怎么可能?我揉了揉眼睛,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的。原来,我们下车后,他们才发现我俩忘了拿行李,也立即下车,但已找不到了我俩。那时还没有手机,不好联系,半夜里,风雪中,只有在火车站附近,一家接一家的找医院,素昧平生、非亲非故的人,一夜折腾,一夜未眠,做了本不该他们做的事,而且还白白耽误了去广州的车票,我一时激动得脑瓜迟钝、嘴巴麻木,拙于言辞。生活冷得太久,一股暖流涌来竟有点不知所措。
天亮了,电来了。同学的病正如红衣大姐说的是急性阑尾炎,上了手术台。大哥、大姐忙前忙后的张罗,一切安排妥当后,还买来许多吃的东西安慰我,那时,我还是个穷学生,羞惭于用物质的东西表达谢意,他们千叮咛、万嘱咐,在我的一再催促下才恋恋不舍的去了火车站。
那年冬天,我在武汉待了十一天,直到同学痊愈。那段日子,雪花飘飘,大街小巷正流行费玉清唱的《一剪梅》:“真情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总有云开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这首歌唱出了我的心声。兰州大姐和铜川大哥两个好人的沉稳、仗义和热情深深地感动了我和我的同学。
二十多年过去了。二十多年风雨沧桑,我和我的同学几次找那两位好心人也没有找到,不知大哥、大姐现在在哪?是他们拨动了我心底那根最柔软的弦,使我坚信人间自有真情在。每年冬天,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次邂逅,那次感动,那个让我温暖,给我无限慰藉的冬天。
201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