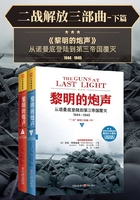
“漫长的海岸线”
6月7日星期三,朴茨茅斯细雨蒙蒙。艾森豪威尔阔步走过一处石隘口,来到位于布罗德街下方的造船厂。英国皇家海军快速布雷舰“阿波罗”号就在金斯泰尔斯对面的锚地等候。几个世纪以来,无数英国水兵都是从这里出击、奔赴战场的。快速布雷舰上,一面绘有4颗白星的红色信号旗已经升起,3根巨大的烟囱冒出滚滚蒸汽。上午8点整,艾森豪威尔登上甲板,“阿波罗”号随即起航。对于登陆日的战况,作为盟军最高统帅的他并不比同处指挥舱的下士普雷斯顿知道更多,于是他决定于登陆日次日亲赴诺曼底沿岸察看。
“阿波罗”号从怀特岛向东,仅用3个小时就穿过了英吉利海峡。舰队在沿途来来往往,大量驳船、轮船和登陆艇被弃置海中、行将沉没。“眼前的景象乱作一团”,陪同艾森豪威尔奔赴前线的海军上将拉姆齐在日记中写道,“令人异常不安。”
由于沿岸仍然遍布水雷,当天上午,美军扫雷舰“潮汐”号在卡登奈河岸的一处险滩罹难。舰长当场阵亡,舰身被掀飞,腾空5英尺高后化成碎片,最终葬身海底。不远处,运输舰“苏珊·B.安东尼”号载着2 300名士兵刚刚抵达港口,4号舱下突然爆炸。“运输舰被掀到半空,爆炸的冲击力令舰身中部向上拱起,猛地跌回水面,沉了下去。”一名船员在报告中写道。由于舰身向右舷倾斜了8°,为保持平衡,舰长下令水兵向左舷栏杆处集中,但对引擎舱内熊熊燃烧的烈火和不断涌入船舱、瞬间就已深达10英尺的海水束手无策。

1944年6月7日,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从英国南部跨越英吉利海峡赶赴诺曼底。罗斯福总统选中艾森豪威尔指挥“霸王行动”,是因为“他是军人中最出色的政治家,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能说服其他人追随他”。
上午9点,当救援船扑灭大火,将惊魂未定的水兵们救下时,海浪立刻冲上了主甲板。1小时后,“苏珊·B.安东尼”号舰长翻身跃入大海,离开了这艘即将沉没的舰艇。10点10分,舰艇“船头朝上,悄无声息地沉了下去”,A.J.利布林写道,“就像一位女士缓缓躺倒在扶手椅上,20分钟后便消失不见了”。令人惊异的是,船上所有人员都幸免于难。
一艘艘无畏舰发出阵阵怒吼,炮口不时喷射出灰色的浓烟。时近正午,“阿波罗”号在奥马哈海滩赶上了“奥古斯塔”号,艾森豪威尔站在栏杆旁,看着一艘希金斯艇乘风破浪,停在了快速布雷舰旁的竖梯前。奥马尔·布拉德利的鼻梁上还贴着绷带,当他爬上甲板准备敬礼时,才发现最高指挥官面带愠色。
从滩头堡发回的只言片语让艾森豪威尔怒不可遏,“你究竟为什么不让我们了解战况?”他厉声诘问,“直到傍晚也没有任何消息,他妈的一个字都没有。我不清楚你们到底是怎么了。”布拉德利有些笨拙地辩解道:“我们已经把所掌握的每一条信息都通过无线电发给你了。”尽管艾森豪威尔的训斥让他十分窝火,但他还是跟随前者来到了拉姆齐舱内。直到这时,艾森豪威尔才得知,布拉德利每小时发来的急电在蒙哥马利的无线电室堆积如山,而译电员早已应接不暇。
布拉德利强压怒火,向艾森豪威尔详细叙述了他所了解的情况。“霸王行动”已经“在法国站稳了脚跟”,当天清晨他亲赴“深红”海滩察看,甚至还踩着卡车的侧踏板登上了悬崖。海滩的火势已经减弱。被俘的敌军,尤其是波兰人和苏联人,协助盟军建起了牢房。傍晚时分,沿岸超过1/3的障碍物将被落潮清除。一天以后,所有屏障都将不复存在。援军也正陆续抵达:星期二晚间,在烟幕和电子干扰的掩护下,9艘运兵舰从泰晤士河出发,这是4年来第一批横渡多佛尔海峡的盟军船只。此外,盟军在一名被俘德军炮兵观测员身上发现了一张地图,上面标明了登陆海滩附近敌军所有炮台以及师、团和营指挥所的准确位置。上述地点立即遭到了盟军轰炸机、舰炮和大炮的连续猛攻。
但是,第一集团军大部分登陆目标仍未实现,他们只卸下了不到原计划1/4的给养和7 000辆汽车。第5军正从奥马哈海滩艰难地向前推进,第29师却困在距奥尔河6英里的内陆,而布拉德利本希望该师能在星期二抵达。第1师也未能深入腹地。在奥克角,不到100名突击队员仍在距离悬崖边缘近200码的范围内奋战。唯一能够牵制敌军的是驱逐舰的火力与游骑兵的士气。
犹他海滩前方的情况同样混乱。第101空降师正向南边的多佛尔河和重镇卡伦坦挺进。第82空降师在失踪24小时后,于星期三清晨派出一名注射了大量苯丙胺的军官,试图与正向内陆地区逼近的第4师取得联络。盟军已经出动了轻型坦克和坦克歼击车,以掩护伞兵降落。随后,罗斯福将军开进了作为第82空降师战地指挥所的苹果园。他把钢盔推到脑后,站在印有“莽骑兵”标志的吉普车上挥舞手杖,“仿佛刀枪不入一样”,一名当事人在报告中写道。“伙计们”,罗斯福吼道,“什么时候开饭?”
第82空降师占领了科唐坦半岛一块边长平均约为6英里的三角形地带。两个营控制了圣梅尔埃格利斯镇,从南北两面抵抗德国的反击。但其他数千名伞兵仍然极为分散,盟军甚至没有在梅德列河以西建立任何桥头堡。当天上午,第7军军长柯林斯将军弃船登岸,控制了一片纵深7英里的滩头阵地。在奥马哈海滩,第7军与第5军之间形成了一个宽10英里的缺口,美军与英军之间也出现了一段5英里的空白。因此,盟军的当务之急就是在隆美尔展开进攻之前,尽快填补这些防御缺口。
艾森豪威尔对布拉德利的汇报不置一词,他看着地图,陷入了思考。“布拉德利与我讨论了当前的局势,但丝毫未能减轻我的忧虑”,拉姆齐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桥头堡的数量非常稀少,防线仍然十分狭窄,陆上力量根本不值一提。”甲板上,与众人匆忙地行过礼后,布拉德利爬下竖梯,如释重负地返回了“奥古斯塔”号。他认为,这纯粹是“一次毫无意义的干扰和令人恼火的经历”,并为此闷闷不乐。
时至下午,天色转晴。“阿波罗”号向东疾驰,船身突然猛地一晃,艾森豪威尔等人重重摔倒在甲板上,经查看,原来是撞上了沙洲。“桅杆剧烈摇摆,布雷舰猝然向前冲去,发出轰隆隆的声响,上下晃动,逐渐停了下来……最终,我们挣脱了沙洲,浮上了海面。”哈里·布彻写道。但这次事故对船体造成了损坏,螺旋桨和传动轴严重变形,整整4个月,这艘快速布雷舰都不得不停在干船坞里进行修理。
1898年,年仅15岁的拉姆齐首次出海,以“精力充沛”名闻遐迩。对于这次事故,艾森豪威尔难辞其咎,因为他一再催促,要求加快速度,实在有失谨慎。但作为皇家海军总指挥,拉姆齐感到颜面尽失。“阿波罗”号以每小时6海里的速度踉踉跄跄地驶过海湾。随后,一艘英国驱逐舰接走了艾森豪威尔,匆匆返回朴茨茅斯。
“我们已经开战”,艾森豪威尔心烦意乱,在匆匆留给妻子玛米的便条上写道,“唯有时间能证明,我们必将大获全胜。”
★★★
即使是战争的阴霾也挡不住诺曼底6月清晨明媚的阳光。英军找到几个在街头贩卖香烟的法国男孩,在他们的带领下,第50师的两个营于星期三攻克了巴约。果园里盛开着白色的花朵,鲜红的天竺葵仿佛要从窗台的花盆里流淌出来。在一堵高墙后,篱笆上爬满了玫瑰。墙上还有一则用油漆绘制的杜本内葡萄酒广告。一头头奶牛在牲口棚里哞哞直叫,等着人们来挤奶。穿着蓝色罩衫和木底鞋的农夫站在路旁,对英军的到来表示欢迎,一些人甚至还行起了纳粹的军礼。
几辆运酒车正驶向圣约翰大街,那里的商店出售的货物在当时都很稀有,人们很难在伦敦看得到:有瓷器、塑料餐具、新式家具和多达4万个品种的卡芒贝尔奶酪。此外,巴约的一家店里还有一幅价值连城的挂毯,上面绣着11世纪英军横渡英吉利海峡登陆法国的事迹。但出于安全上的考虑,这幅挂毯早已被转移到勒芒。据传,在这座只有7 000人的小镇上,最后一个德国人举枪自尽。住在他家附近的一名寡妇在日记中写道,其他德国士兵纷纷穿过油菜田,仓皇逃窜,甚至“来不及带走他们的内衣、外套和剃须刀”。
谢尔曼坦克发出隆隆巨响,开进镇子,车身上还带着用于水中行驶的气囊。它们身上“系着巨大的浮板,仿佛一个个风尘仆仆的庞然大物”,一名目击者写道。随后,士兵们陆续走下坦克,开始烹煮名为“炮火”的浓茶。民事特遣队抵达后,在当地实施了宵禁,并逮捕了许多通敌分子。“乍看之下”,一名愤怒的军官感叹道,“你根本分辨不出谁是纳粹党徒,谁是维希分子,谁是法国的爱国民众。”另一份报告也承认:“军队掠夺财物的现象十分普遍。”
记者们用彩色的帆布帐篷在摇摇欲坠的金狮酒店里搭建了一处临时营地。这座酒店不仅供应煨羊肉和黑麦面包,正如艾伦·穆尔黑德所言,还有“每瓶15先令的干白葡萄酒……楼上妓院的老鸨经常带着姑娘们下来用餐”。然而,还有3.6万座法国市镇等着盟军解放,尽管巴约环境宜人,但几乎没人放松心情。
当然,一枚迫击炮弹就能将这里变成废墟。在亲眼目睹附近的别墅和农宅都“只剩下炸开了花的炮弹”后,穆尔黑德写道:“人们会以为战斗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譬如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在距离卡昂较近的地方,枪战始终持续不断。6月7日,英军第50师的一名少校在日记中写道:“哦,上帝,别再开炮了。如果你能让他们停下来,我愿永远做个好人。”
面对德军机枪的疯狂扫射,一名士兵瑟瑟发抖地抱怨道:“我他妈的就是不明白,这些兔崽子的子弹怎么总也用不完。”当炮弹落下来时,他接着说:“你要像胎儿般蜷起身来,同时用双手护住裆部,保护你的生殖器,以免绝种,这可是人类的本能。”他还表示:“蒙哥马利不用保护他的私处,但老天爷,我可得看好我的裆部。”在位于剑滩和卡昂之间的佩里耶尔,一名法国妇女写道:“头顶到处都是嘶嘶声和呜呜声,你只能把身子伏得更低……哪里才是安全的地方?或许哪里都不安全,只有等待发生奇迹。”
距此25英里以西,记者厄尼·派尔也在思索同样的问题。派尔来自印第安纳州,自称是一名“悲情的战士”。星期三一早,他于“奥马哈”登上了诺曼的海岸。布拉德利手下一名副官写道:“他看起来无助而渺小……但就像平时一样,竭力掩饰着自己的感情。”整整几个小时,他沿着涨潮线仔细搜寻,并列出了一份长长的清单:
这里有袜子、鞋油、针线包、日记本、《圣经》和手榴弹,还有刚刚寄来的家书,信封上的地址都被人用剃刀整齐地裁掉,这是战士们在登陆前要采取的安全措施之一。这里有牙刷和剃须刀,战士们家人的照片散落在沙滩上,照片里的他们正凝视着你。这里有口袋书、金属镜子和裤子,还有血迹斑斑的鞋子……我捡起一本袖珍《圣经》,上面写有一个战士的名字,我把它装进我的上衣口袋。走了大约半英里后,我又轻轻地把它放回到海滩上。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
这里有手枪带和帆布水桶,还有洁白的信笺,但再也不会有人在上面书写绵绵情话。一副网球拍仍然装在球拍袋里,看起来“完好无损”。这所有的一切正如派尔所说:“漫长的海岸线,承载着每一个人的痛苦。”当天晚上,他返回了第353号坦克登陆艇,整夜都辗转反侧、噩梦不断,看起来“异常憔悴和悲痛”,一名军官注意到。派尔对另一名记者坦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于这些已经越来越习以为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