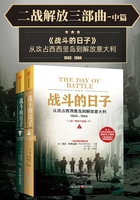
腐蚀英雄的灵魂
他们沿着100英里的战线向前推进,沿途的西西里人欢呼着“贝比·鲁斯万岁(贝比·鲁斯是美国棒球史上最有名的球员,号称“棒球之神”。——译者注)”“乔治国王万岁”并挥舞着自制的美国国旗。这些国旗上的条纹太多,星星太少。7月的炎热已经到来,他们将头巾绕过鼻子扎紧。一路上尘土飞扬,行进队伍中的士兵甚至看不见自己腰部以下的部位,仿佛行走在面粉中。
“刚走了一英里,我们便疲惫不堪,连发牢骚的力气都没有了,”一名迫击炮手回忆道,“但我们继续前进。”咸咸的汗水浸透了衬衫,靴子咯吱作响,他们将钢盔称作“脑炉”。他们吃着葡萄、青西红柿和安非他明(安非他明是一种兴奋剂,能够缓解疲劳。——译者注),或是以货易货,用一根香烟能换八个橘子。中午,记者艾伦·穆尔黑德写道,“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刺眼的颜色——红色的岩石、绿色的葡萄园、耀眼的深蓝色天空。”士兵们则没这么鲜艳,汗水和尘埃在他们的皮肤上混合成了一层灰色的糊状物。偶尔有炮弹落下,他们便扑入沟渠和地面上的浅凹地。“我把脸埋在尘土中,”一名士兵说道,“并试着用双膝将坑弄深些。”一些吉普车从前线返回,引擎盖上绑缚着阵亡的士兵,穿过奋力向前的队伍。“让开!”司机吼叫着,“快让开!”活着的人闪到一旁,仿佛他们是避开恶毒之眼的西西里人。
许多士兵戴着护身符,要么是一枚圣克里斯托弗纪念章,要么是一块光滑的石头,每当有曳光弹嗖嗖掠过,他们便会轻轻抚摩。一名士兵带着个小小的木雕猪,炮火密集时,他便喃喃说道,“小猪啊,这发炮弹不是射向我们的”,或是“小猪啊,你知道,这发炮弹会要了你和我的小命”。加入记者团采访入侵行动的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指出,信念“这种魔力不能太过频繁地使用,其功效并非用之不竭”。他得出结论,这种返祖现象在部队中反映出一种合理的信念,即“黑暗世界离我们并不远”。
他们踏过一片与北非同样具有异国情调的土地,一片女巫和驱魔师盛行的土地,在这里,病人们吞咽着碾成粉的琥珀,或是喝下圣丽达骨灰泡的水。圈在手推车硕大轮子上的钢轮圈轧过鹅卵石地面,叮当作响。两侧的墙壁上画着基督殉难图,旁边张贴着20年代电影明星的海报。戴着眼罩的挽马拖着“左右两侧分别描述一位圣人的生与死”的马车,嘚嘚作响地从那些在孩子的头发里挑虱子的妇女以及捧着五角形、沾有紫色污渍的酒瓶畅饮的老人们身边经过。
墙壁和公共建筑上涂写着法西斯口号:“少说多干”“墨索里尼永远正确”……这些口号“看多了甚至不再显得荒谬可笑”,穆尔黑德写道。有些墙壁刚刚用石灰水刷白,或是被覆盖上诸如“贝托尼完蛋了”这样的新标语。宪兵们仔细检查穿着从商店里买来的鞋子或干净长裤的当地人,以抓捕法西斯官员。告发和出卖很快成为当地的主要营生。蓝色蝴蝶、戴胜鸟和食蜂鸟飞来飞去,金银花和茉莉的香气夹杂着粪便和人类内脏的恶臭,产生了一种“贫困的气味”。“一条烟能让你在这里买下整个省,”一位美军军官叙述道,“一套衣服能让你得到全岛。”
敌军士兵的尸体倒在路边,他们张着双臂,仿佛在扮演雪地天使。他们被草草埋葬于标有“E.D”(敌军死者)字样的墓穴中。死去的平民也躺在路上,有些人倒在倾覆的彩绘大车旁,被掏去内脏的驴子仍套着挽具,形成一幅妖冶的死亡画面。在某些省份,掘墓工人罢工,使环境卫生变得更加糟糕,制造棺材的木料短缺,棺材不得不被反复使用。
“埋葬死者,喂饱活着的人。”第1步兵师的一位民事官员建议道,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争夺食物引发了骚乱,其中一起就发生在卡尼卡蒂,派去弹压的宪兵向骚乱者头顶上方开枪,却毫无效果。“他们渐渐压低火力时,”一名AMGOT(盟国占领区军政府)成员的报告补充道,“暴徒们趴在街道上,继续尖叫。”特拉斯科特将军下令处决劫掠者,一帮平民从一间仓库盗窃了肥皂并企图逃跑时,一名军官“朝人群开枪射击,士兵们一边开枪,一边抓捕其他人,6个人被打死”。还有7个被指控涉嫌破坏军用通讯设备的人被枪毙。
有些时候,活着的人只是需要些安慰。海军一等兵弗朗西斯·卡彭特,这位前百老汇演员被派去担任滩头侦察兵,因为他曾两次去西西里岛度假,在一片玉米地里,他遇到8个吓坏了的当地农民。卡彭特曾出演过奥森·威尔斯于1938年重新改编的《鞋匠的假日》,他掏出自己的烟盒,发了一圈香烟,然后清清嗓子,唱起了歌剧《弄臣》中迷人的咏叹调:“善变的女人”。
★★★
没有谁比这位目前在西西里岛指挥着大部分美军部队的中将更急于向内陆挺进。排名仅次于巴顿的第2军军长奥马尔·纳尔逊·布拉德利曾与逆境和困苦搏斗了50年:父亲早逝;滑雪事故造成的牙齿缺失;一场致命的流感;儿子胎死腹中。展开“爱斯基摩人行动”最初的36个小时内,布拉德利就在不停地经受考验。“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刻,”通过急诊手术切除痔疮(在陆军中被称为“骑兵扁桃体”)后,他被迫待在“安肯”号上,饱受疼痛和晕船的折磨。他最终搭乘自己的指挥车登上海滩,屁股下垫着个救生圈,这多少让人觉得有些可笑。7月12日周一早上,他在斯科利蒂以北3英里外一片闷热的树林中建起自己的指挥部。
还是一名军校学员时便已头发灰白的布拉德利穿着一件朴素的军用夹克,作为“一名勉强合格的年迈步兵”,他背着自己最喜爱的“斯普林菲尔德”1903式步枪。圆形的钢框军用眼镜彰显了他的“乡土气息”,历史学家马丁·布鲁门森写道,“他那种乡巴佬的腔调使他看上去相当质朴。”尽管在突尼斯战役,他指挥美军成功完成了致命的一击,但仍旧是默默无闻。近期,记者和公众的目光终于集中到了布拉德利身上,他的举止格外引人关注——“在风平浪静的日子,他就像奥索卡湖那样平静”。
《生活》杂志对布拉德利赞不绝口——他的个人经历深具吸引力:少年时代在密苏里的农田中劳作,根本没有自来水;他的寡母是一位裁缝,年轻的奥马尔靠打猎养活家人,松鼠、鹌鹑、野兔和大绿蛙是他们仅有的伙食;在西点棒球队,他保持了0.383的击球率,还是一位致命的投球手;同时他还是个神枪手,能用点22口径的步枪射中飞起的野鸡,他盯着空中的德国飞机,仿佛是在“双向飞碟比赛中的8号射位准备射击”。在艾森豪威尔的催促下,厄尼·派尔将在西西里岛跟布拉德利待上几天,写一篇偶像化的六段式文章,这将把布拉德利神话为一名士兵将军。“他太过普通,”派尔写道,“没有个性,没有迷信,甚至没有兴趣爱好。”
也许事实就是这样,但他的城府甚至超出了派尔的探究。“面具下是一颗冷漠无情的心。”马丁·布鲁门森作出结论。他“工于心计”(这个形容词出现在他的高中年鉴里),心胸有些狭窄。他对特里·艾伦这位“海盗”的厌恶越来越深(而后者认为布拉德利是“假冒的亚伯拉罕·林肯”),一直在找机会解除这位大红一师师长的职务。布拉德利对巴顿爱炫耀的性格、一根筋的战术,以及其忽略自己对各师的直接命令这一做法同样感到不满。“他太鲁莽了,”布拉德利后来写道,“我不喜欢他的指挥方式……我认为他是个相当浅薄的指挥官。”
第2军所面临最紧迫的问题是潮水般涌来的意大利战俘:在西西里,一周内抓获的敌军俘虏已超过美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抓获的战俘总数。他们三五成群地走出村子,走下偷来的卡车,或是排着长长的队伍,叽叽喳喳地从山里出来,边走边紧张地回望着不同意投降的“赫尔曼·戈林”师掷弹兵们的枪口。他们戴着长檐军帽,穿着被德国人称为“石棉布”的粗布军装,“兴高采烈地举手投降……把个人财物斜背在身上,空气中弥漫着他们的笑声和歌声”。一名士兵这样写道。一些美军部队实在不堪重负,用意大利语写了个标牌:“这里不收留战俘。”或建议敌军士兵改日再来投降。“对这些投降得如此之快,甚至不得不采用预约方式收留的敌军士兵,你真的对他们仇恨不起来。”比尔·莫尔丁评论道。
随后,他们像牲畜那样被赶上坦克登陆舰,但仍在唱歌,就像被关入笼中的鸟儿。负责审问一个意大利机枪组的OSS(战略情报局)官员报告,为防止士兵们倒戈归降,轴心国的军官们捏造并散布了一些盟军对战俘施暴的谎言。
“你们打算何时动手?”一名俘虏问道。
“动什么手?”
这名俘虏畏畏缩缩地说道:“割掉我们的卵蛋啊。”
被告知他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后,俘虏们放心地啜泣起来。
“意大利人真是个奇怪的民族,”一名中尉写信告诉他的母亲,“你或许会觉得我们只是他们的护送员,而不是押送者。”
但是,黑暗世界并未远去。
它已经开始蔓延。
★★★
“爱斯基摩人行动”令第180步兵团付出了尤为沉重的代价,他们是俄克拉荷马州的骄傲,也是第45步兵师麾下三个国民警卫队团之一。巴顿曾在该师从诺福克赶往西西里的途中,在奥兰短暂停留时,视察过这支部队,他督促军官们“尽情杀戮”,要警惕举着白旗的诈降,而且,就算敌人在几近崩溃时举手投降,也要“杀掉这些婊子养的”。第45步兵师应该被称为“杀手师”,因为巴顿告诉他们,“杀手将永生。”
尽管有这番谆谆告诫,但对第180团的杀手们来说,战斗进展得并非一帆风顺。登陆当天,该团团长福里斯特·E.库克森上校便被一位迷失方向的艇长丢在大红一师的登陆滩头,30个小时后才与自己的部下会合。库克森“焦虑而又彷徨,”——他经常摇着头嘟囔“不太妙”——似乎太容易陷入沮丧,以至于巴顿曾想让比尔·达比接替他出任团长,但达比选择和他的游骑兵们待在一起。
在没有适当人选接替的情况下,库克森的职务被暂时保留了下来,但很快便失去了手下最能干的营长威廉·H.谢弗中校。这位前西点军校的橄榄球选手被称为“金刚”,是“美国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中相貌最丑的人”,一名中尉这样说道。他曾多次告诫他第1营里的军官,千万不要冒被俘虏的危险,因为“被俘就无法作战了”。登陆后没几个小时,谢弗便被德军掷弹兵团团围住,关在了一座葡萄园里。“亲爱的将军,”他在一张牛皮纸上,给他的师长特罗伊·米德尔顿草草写了一封信,“很抱歉,我被俘了。”
第180团自我救赎的机会出现在偏远、贫困的比斯卡里,7月11日周日下午晚些时候,该团发起了进攻。“赫尔曼·戈林”师的士兵退至镇公墓高高的黄色墙壁后,隐蔽在山坡上的雪松和大理石墓碑后。美国人的迫击炮弹把他们轰了出来,棕色的硝烟弥漫在墓地上方,机枪子弹将六翼天使的雕塑打得碎屑飞溅。德国人再次后撤,向北逃过阿卡泰河,朝比斯卡里镇北面5英里处的一座机场而去。在这片岗峦起伏的地面上,双方的交火一直持续至7月13日。
周三清晨,美国人终于夺下了机场。跑道上留下了200多个弹坑,尸体像血淋淋的小块地毯那样铺在上面。被烧焦战机的十字形残骸在机库附近闷燃,敌狙击手躲在驾驶舱内肆意射击,直到一个“谢尔曼”坦克排赶来,排查每一架飞机机身,将他们全部消灭。在机场东面和西面的麦地里,火焰劈啪作响。透过滚滚浓烟,可以看见美军士兵犹如草绿色的幽灵,将受伤的战友拖至安全处,或是从被丢弃的背包上取下急救包和弹药。
在比斯卡里尘土飞扬的土路上,狙击火力仍然密集,不断有子弹从洼地射来。第180步兵团第1营的A连和C连在5天前发起登陆行动时,每个连有近200名士兵,可现在只剩下150人。“金刚”的接替者负伤,A连连长被俘。“我们有一种杀戮欲,”一名中士后来说道。另一名士兵写信告诉父亲,夏季的灰尘“尝起来像是粉状的血”,他又补充道,“我现在知道当兵的为何老得快了。”
周三上午前,第1营已穿过硝烟和舞动的火焰,沿着细窄的菲库扎河,将德国和意大利的散兵游勇从洞穴中逐出。很快,A连便俘虏了46人,其中有3个德国人。这群惊恐而又疲惫的俘虏只穿着长裤,赤裸着上身坐在菲库扎河上方一道干涸的斜坡上,他们的衬衫和靴子已被没收,防止他们逃跑。一名美军少校将9个战俘分开审讯(战俘中最年轻的几个被认为有可能如实交代情况),随后,这些人和其他俘虏被交给霍勒斯·T.韦斯特中士率领的一支小分队,押往后方。
然而,让韦斯特率队被证明是个糟糕的决定。他出生于俄克拉荷马州的巴伦堡,1929年加入美国陆军,后又调至国民警卫队。他只在周末参加训练,在平日的平民生活中,他是一名厨师。33岁的韦斯特有两个年幼的孩子,每个月的军饷是101美元,在部队中很有些声誉,一位上司曾说他是“我在陆军中见过的最认真的军士”。但过去几天的战斗令韦斯特中士身心俱疲。“某些东西沉甸甸地压在我心里,”他后来说道,“只想杀戮、破坏,并看着他们血流不止而死。”
战俘们排成两列,在道路上行进了400码,朝河岸上的一片橄榄树林走去。韦斯特让战俘们停下(他们毫不知情,参差不齐地执行了向左转的命令),并挑出一小群上级要审问的人,转身向连里的二级军士长哈斯克尔·布朗借用汤普森冲锋枪。布朗将冲锋枪和一个备用弹匣递给韦斯特。只听他说:“毙掉这些婊子养的。要是你不想看见这一幕,就转过身去。”韦斯特随即扣动了扳机。
战俘们倒下了,在尘土中扭动、抽搐着,然后用双膝蹒跚而行,苦苦哀求,但回复他们的仍旧只是子弹。惨叫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不!不!”混杂在枪声的轰鸣和无烟火药的刺鼻气味中。3名战俘朝树林跑去,其中两人得以逃脱。韦斯特停止射击,换上弹匣,走到倒在血泊中的俘虏身边,朝仍在蠕动者的心窝开枪射击。干完这一切,他将冲锋枪还给布朗。“这是命令。”说罢,他赶着9个大睁着双眼、浑身颤抖、被挑选出来要加以审问的俘虏继续上路,去找师里的G-2(负责情报的副参谋长)。37具尸体倒在路边,随着太阳升起,他们的影子越来越小,仿佛身体内的某些东西被掏空了似的。
5个小时后,就在韦斯特中士赶着他的战俘向后方走去时,德国人的坦克和半履带装甲车发动反击,重新夺回了比斯卡里机场,并将第180团赶过跑道南面的一条峡谷。激战持续了整个下午,直到敌人被再次击溃,这次他们永远地离开了。战斗中,第1营C连冲入一条深深的峡谷,敌人的机枪火力造成12名美军士兵伤亡,随后,一座嵌入山坡的巨大碉堡飘起白旗。下午1点,30余名意大利士兵走了出来,高举双手,其中5个身穿便衣。弹药箱、肮脏的被褥和行李箱散落在碉堡内。
指挥C连的是约翰·特拉弗斯·康普顿上尉。现年25岁的他,于1934年加入俄克拉荷马州国民警卫队。康普顿已婚,有一个孩子,月饷230美元(扣除6.60元政府保险后),对他的表现评判一直是“优秀”或“出众”。疲惫不堪的康普顿站在山坡上,命令一名中尉组织了一支行刑队,“毙掉这些狙击手”。行刑队很快便被组织起来了(有几人是自告奋勇加入),意大利人哀求他手下留情时,康普顿大声喊出了命令:“准备,瞄准,开火!”汤普森冲锋枪和勃朗宁自动步枪朝着沟壑中猛烈扫射,又有36名战俘被击毙。
第二天上午10点30分,威廉·E.金中校驾驶着吉普车,沿比斯卡里公路朝现已安全的机场驶去。据说金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患过暂时性失明,这番折磨促使他投身于教会,成了一名浸信会牧师。现在的他,作为第45师随军牧师服务于上帝和国家,宽宏大度的品质和简洁的布道使他深受尊敬。橄榄树林旁的一个黑色土堆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停下车,被惊得目瞪口呆,随即开始了调查。
“大多数人面朝下倒在地上,”金后来回忆道,“除此之外,每个面朝上的人,脊柱左侧和心窝部位都有弹孔。”大多数人头部也有伤,烧焦的头发和火药灼伤都表明这是近距离枪击。几个在附近游荡的美军士兵也来到牧师身边,抗议说“他们投身这场战争就是为了反对这种事情”,金说道,“他们为同胞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牧师匆匆返回师部,去报告这起屠杀事件。
奥马尔·布拉德利已获知战俘被屠杀的消息,他驱车赶至杰拉,告诉巴顿,50至70名战俘遭到“冷血、批量的”屠杀,巴顿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对此的反应:
我告诉布拉德利,这可能有点夸大其词,但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告诉有关人员,这些死者生前要么是狙击手,要么曾企图逃跑,否则这将在舆论界引发轩然大波,使平民们为之动怒。总之,他们都死了,对此我们已无能为力。
两名亲眼目睹了尸体的战地记者也出现在巴顿的司令部,对屠杀俘虏事件提出抗议。巴顿承诺要制止这些暴行,而记者们显然也未将这起事件公之于众。在7月18日给乔治·马歇尔的信中,巴顿写道,敌人用他们的尸体充当诡雷,还“经常在防线后展开狙击”。这种“穷凶极恶的行径”造成“不少意大利人意外死亡,但在我看来,这些杀戮完全是有道理的”。
布拉德利对此并不赞同,巴顿又在日记中写道,“我认为我们应该找两个人对屠杀俘虏事件负责。”第45步兵师的督察长通过调查发现,“战俘们并没有挑衅行为……他们遭到了屠杀。”巴顿心软下来:“审判那些王八蛋。”
比斯卡里屠杀发生后不久,康普顿上尉便身染疟疾,直到10月下旬康复后,他才接受了军事法庭的秘密审判。辩方认为,巴顿在奥兰的动员性讲话无异于“下达了一道消灭这些狙击手的命令”。康普顿证实:“我命令他们开枪是因为我认为这符合将军的直接命令。”军事检察官没有对他进行任何盘问,便表示:“我相信了他的话。”康普顿无罪释放,并回到第45师继续服役。
巴顿曾宣称,杀手将永生,这句话同样是错的:1943年11月8日,康普顿在意大利战役中阵亡。第45步兵师的一名同僚说了一句话,恰巧成为了他的墓志铭:“总算解脱了。”
韦斯特中士的案子更为复杂。与康普顿一样,他接受了精神病医生的检查,结果显示其神智正常。他同样声称,巴顿的煽动是造成他屠杀行径的直接原因,但同时也承认自己“也许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告诉军事法庭,自己的行为“超越了我对人类尊严的概念”。法庭宣判,韦斯特中士“蓄意、故意、刻意、残忍、非法,并有预谋地杀害了37名战俘,这些人的名字完全不为人知,但每一个都是活生生的人”。
韦斯特被判处终身监禁,在纽约一所监狱内服刑。但他在战争期间从未离开过地中海,也没被不光彩地开除军籍,继续拿着每个月101美元的军饷,外加各种家庭津贴。第180步兵团团长库克森上校后来说:“处理类似事件,就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尽可能漂亮地平息下去。”韦斯特被定罪几周后,艾森豪威尔审查了这起案件。如果将韦斯特送至美国国内的联邦监狱,比斯卡里事件很可能会被公之于众。如果将他留在北非,敌人也许会继续被蒙在鼓里,依然对这起屠杀事件一无所知。艾森豪威尔“担心盟军战俘遭到报复,并决定再给这个家伙一次机会”,哈里·布彻在日记中写道,“(韦斯特)将被处以军事监禁……一段足够长的时间,以确定他是否可以重新服役。”

1943年7月,跨越西西里岛的进攻
1 XX 第1步兵师
3 Rgr 第3步兵团
3 XX 第3步兵师
45 XX 第45步兵师
MONTGOMERY 8th Army 蒙哥马利,第八集团军
PATTON 7th Army 巴顿,第七集团军
TF X 游骑兵特遣队
XIII Corps 第13军
XXX Corps 第30军
ALB. 阿尔巴尼亚
ALG. 阿尔及利亚
AUSTRIA 奥地利
FRANCE 法国
GREECE 希腊
ITALY 意大利
SWITZ. 瑞士
TUNISIA 突尼斯
YUGOSLAVIA 南斯拉夫
Adriatic Sea 亚得里亚海
Agira 安吉拉
Agrigento 阿格利真托
Augusta 奥古斯塔
Belice R. 贝利切河
Biscari Airfield 比斯卡里机场
Biscari 比斯卡里
Bologna 博洛尼亚
Brolo 布罗洛
Caltanissetta 卡尔塔尼塞塔
Canicatti 卡尼卡蒂
CAPE PASSERO 帕塞罗角
CARONIE MOUNTAINS 卡罗涅山
Cassibile 卡西比莱
Castelvetrano 卡斯泰尔韦特拉诺
Catania 卡塔尼亚
Centuripe 琴图里佩
Cerami 切拉米
Cesaro 切萨罗
Corleone 科尔莱奥内
CORSICA 科西嘉岛
Enna 恩纳
Etna Line 埃特纳防线
Gangi 甘吉
Gela 杰拉
Genoa 热那亚
Gornalunga R. 戈尔纳伦加河
Gulf of Gela 杰拉湾
Gulf of Noto 诺托湾
Ionian Sea 伊奥尼亚海
Lentini 伦蒂尼
Leonforte 莱翁福尔泰
Licata 利卡塔
M. ETNA 埃特纳火山
Marsala 玛莎拉
Mediterranean Sea 地中海
Menfi 门菲
Messina 墨西拿
Milan 米兰
Naples 那不勒斯
Nicosia 尼科西亚
Pachino 帕基诺
Palermo 巴勒莫
Platani R. 普拉塔尼河
Ponte Olivo Airfield 蓬泰奥利沃机场
Porto Empedocle 恩佩多克莱港
Primosole Bridge 普里马索莱桥
Prizzi 普里齐
Randazzo 兰达佐
Regalbuto 雷加尔布托
Reggio di Calabria 雷焦卡拉布里亚
Rome 罗马
Salso R. 萨尔索河
San Fratello 圣夫拉泰洛
Santo Stefano 圣斯特凡诺
SARDINIA 萨拉丁岛
Sciacca 夏卡
Scoglitti 斯科利蒂
SICILY(ITALY) 西西里(意大利)
Simeto R. 锡梅托河
Sperlinga 斯佩尔林加
Strait of Messina 墨西拿海峡
Syracuse 锡拉库扎
Trapani 特拉帕尼
Troina 特罗伊纳
Tunis 突尼斯
Tyrrhenian Sea 第勒尼安海
Tyrrhenian Sea 第勒尼安海
Vizzini 维齐尼
这段时间长达一年多。韦斯特的家人和一名同情他的国会议员开始为了美国陆军中“最认真的军士”纠缠陆军部。1944年11月23日,以临时精神错乱为理由,他获得赦免并继续服役,尽管中士军衔被撤销。战后,军事法庭的记录作为绝密文件被锁在军方保险箱内长达数年,以免它们“激怒那些远离战争、不明白战争残酷性的公民”。
而那些知道这些屠杀事件的人则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对此加以分析。第45步兵师的炮兵指挥官雷蒙德·S.麦克莱恩准将得出结论,在西西里岛,“似乎出现了一种邪性,开始挑衅我们”。巴顿写信告诉比阿特丽斯,“一些金发小伙说我杀了太多战俘。但他们疏忽了一点,我杀的人越多,我损失的部下就越少。”第45步兵师的一名参谋军官写道,“是何种力量让一个正常人变成了杀手,这一点无从确定。但一场世界大战与我们的个人选择是不同的。”
在跟随第180步兵团投身战斗的第一周,比尔·莫尔丁中士曾写道,没人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但从利卡塔至奥古斯塔,另一些经验教训也值得借鉴。因为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行动,也是一个寓言。这些经验教训中包括战友之情、职责和无法预测的命运,也包括荣誉、勇气、同情和牺牲。另外,在接下来的几周,他们将穿越西西里岛,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将设法帮助这个世界走向和平,在这一过程中,有些最为悲惨的教训值得为人们所铭记:战争具有腐蚀性,能锈蚀灵魂,玷污精神,甚至连优秀和杰出者也会被腐蚀,没有谁能保证一尘不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