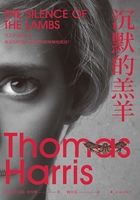
4
克拉丽丝·史达琳很激动,她精疲力竭,只是凭着意志力在奔跑着。莱克特评价她的话有的是对的,有的只是听起来接近真实。一瞬间她觉得有一种陌生感在脑海中散开去,好似一头熊闯进了野营车,将架子上的东西哗啦一下全都拉了下来。
他说她母亲的那番话令她愤怒,而她又必须驱除这愤怒。这可是在干工作。
她坐在精神病院对面街上自己那辆旧平托车里喘着粗气。车窗被雾糊住了,人行道上的人看不进来,她获得了一丝幽静。
拉斯培尔。她记住了这个名字。他是莱克特的一个病人,也是其受害者之一。莱克特的背景材料她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来了解。档案材料数量巨大,拉斯培尔只是众多被害人中的一个,她需要阅读其中的细节。
史达琳想赶紧了了这事儿,可她知道,进度由她自己掌握。拉斯培尔一案多年前就结案了,没人再会有危险。她有的是时间。最好是多掌握点情况多听点建议,然后再走下一步。
克劳福德可能会不让她干,将事情交给别的人去做。她得抓住这个机会。
她在一间电话亭里试着给他打电话,但发现对方正在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上为司法部讨专款呢。
本来她可以从巴尔的摩警察局的凶杀组获取该案的详细情况的,可是谋杀罪不归联邦调查局管,她知道他们会即刻将这事儿从她这儿抢走的,毫无疑问。
她驾车回到昆蒂科,回到行为科学部。部里挂着那亲切的印有格子图案的褐色窗帘,还有就是那满装着邪恶与罪孽的灰色卷宗。她在那儿一直坐到晚上,直到最后一位秘书走了,她还坐在那儿,摇着那架旧观片机的曲柄把手,一张张地过有关莱克特的微缩胶卷。那不听使唤的机器闪着光,仿佛黑暗房间里的一盏鬼火。照片上的文字与底片影像,密密层层地从她神情专注的脸上移过。
本杰明·雷内·拉斯培尔,白种男人,四十六岁,巴尔的摩爱乐乐团首席长笛手。他是汉尼拔·莱克特医生的一个精神病患者。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在巴尔的摩的一次演出他没有到场。三月二十五日,他的尸体被发现,是坐在一所乡村小教堂的一张长椅上;那地方离弗吉尼亚的福尔斯教堂不远。他身上只系着根白领带,穿着件燕尾服。尸体解剖发现,拉斯培尔的心脏已被刺穿,同时胸腺和胰脏也不见了。
克拉丽丝·史达琳从小就对肉类加工方面的事了解得很多——虽然她不希望了解得这么多,但是她依旧能辨认出那失踪的器官就是胸腺和胰脏。
巴尔的摩凶杀组认为,这两件东西曾出现在拉斯培尔失踪的第二天晚上莱克特为巴尔的摩爱乐乐团团长和指挥所设的晚宴的菜单上。
汉尼拔·莱克特医生声称对这些事一无所知。爱乐乐团的团长和指挥则表示,他们已想不起来莱克特医生的晚宴上有些什么菜,可是莱克特餐桌上菜肴的精美是出了名的,他也曾给美食家杂志撰写过大量文章。
后来,爱乐乐团的团长因为厌食以及酒精依赖,到巴塞尔[11]的一家整体神经疗养院去接受治疗了。
据巴尔的摩警方说,拉斯培尔是莱克特已知被害人中的第九个。
拉斯培尔死时没有留下遗嘱,在遗产问题上,他的亲属互相诉讼打官司,报纸对此都关注了几个月,后来是公众渐渐失去了兴趣。
拉斯培尔的亲属还和其他受害者家属联手打赢了一场官司,即销毁这个步入歧途的精神病专家的案卷及录音带。他们的理由是,说不准他会吐露什么令人尴尬的秘密来,而案卷却是提供证据的文件。
法庭指定拉斯培尔的律师埃弗雷特·尤为其遗产处置的执行人。
史达琳要想去接近那辆车,必须向这位律师提出申请。律师可能会保护拉斯培尔的名声,所以,事先通知他给他足够的时间,他也许就会销毁证据以遮护其已故的委托人。
史达琳喜欢想到一个点子就立即抓住不放并且利用。她需要听听别人的意见,也需要得到上面的批准。她独自一人在行为科学部,可以随便使用这个地方。在通讯簿里,她找到了克劳福德家的电话号码。
她根本就没听到电话响,而他的声音突然就出现了,很低,很平静。
“杰克·克劳福德。”
“我是克拉丽丝·史达琳。但愿你不在用餐。……”对方没有声音,她只得继续往下说,“莱克特今天跟我说了拉斯培尔案子的一些事儿,我正在办公室对此进行追查呢。他告诉我拉斯培尔的车里有什么东西,要查看那车我得通过他的律师。明天是星期六,没有课,我就想问问你是否——”
“史达琳,怎么处理莱克特的消息我是怎么跟你说的还记得吗?”克劳福德的声音低得要命。
“星期天九点给你报告。”
“执行,史达琳。就那么办,别的不要管。”
“是,长官。”
拨号音刺痛着她的耳朵。这痛又传到了她脸上,使她的双眼喷出怒火。
“他妈的臭狗屎!”她说,“你这个老东西!狗娘养的讨厌家伙!让密格斯来对着你喷,看看你喜不喜欢!”
史达琳梳洗得鲜鲜亮亮,身着联邦调查局的学员睡衣,正在写着她那份报告的第二稿。这时,她的室友阿黛莉亚·马普从图书馆回来了。马普的脸呈褐色,粗线条,看上去很健康,她这模样在她这个年纪更招人喜欢。
阿黛莉亚·马普看出了她脸上的疲惫。
“你今天干什么啦,姑娘?”马普总是问一些有没有答案都好像无关紧要的问题。
“用甜言蜜语哄了一个疯子,搞了我一身的精液。”
“我倒希望我也有时间去参加社交生活——不知你怎么安排得过来的,又要读书。”
史达琳发觉自己在笑。阿黛莉亚·马普因为这小小的玩笑也跟着笑了起来。史达琳没有停止笑,她听到自己在很远的地方笑着,笑着。透过眼泪,史达琳看到马普显得异常的老,笑容里还带着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