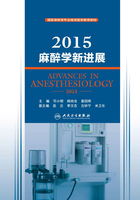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12 吗啡耐受的发生及其机制的研究进展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把一个国家的吗啡消耗量作为衡量该国疼痛控制水平的标志。因此吗啡是全球应用最广泛的阿片类镇痛药物,尤其用于中到重度的疼痛患者 [1]。但吗啡长期使用可产生镇痛耐受(不考虑疾病进展的情况下,吗啡镇痛作用逐渐降低,同时发生耐受相关的痛觉过敏),慢性疼痛患者需要不断增加吗啡的用量以达到同样的镇痛强度,而吗啡剂量的增加可导致恶心、呕吐、便秘等不良反应的增加,甚至出现呼吸抑制等严重不良反应,由此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2,3]。因此,吗啡镇痛耐受的发生极大的限制了吗啡在临床安全有效的使用。现将吗啡耐受的发生、机制及其预防的研究进展作以下综述。
一、吗啡耐受的发生
吗啡耐受是指长期反复使用吗啡后,需要不断增加吗啡的剂量或缩短给药间隔时间,才能达到原来的镇痛效果 [2,3]。吗啡耐受是一种药理学现象。不仅是吗啡的镇痛作用,吗啡的不良反应(除便秘外)包括镇静、呼吸抑制、恶心呕吐、瘙痒、焦虑以及欣快感等均可出现耐受现象 [3]。动物研究表明吗啡镇痛耐受具有时间和剂量依赖性以及受体特异性的特点 [4],并且可以预防和逆转 [2,5]。
在动物实验研究中,吗啡耐受所表现的行为学改变是:长期反复使用吗啡后,动物出现痛觉敏化(痛觉过敏) [6]和吗啡镇痛作用的剂量-反应曲线右移 [5]。目前关于吗啡耐受发生机制的大量研究是在无痛的生理状态下,因此研究的结果并不能反映临床实际情况。而对于疼痛状态下是否发生吗啡耐受,目前尚存有争议。神经病理性疼痛和烧伤痛的大鼠,慢性吗啡暴露后,吗啡镇痛作用的剂量-反应曲线右移,与Sham大鼠相比发生了吗啡耐受 [4,5,7]。Wang的研究显示:烧伤痛的大鼠即使在没有慢性吗啡暴露的情况下,单次注射吗啡也会出现吗啡镇痛作用的降低 [7]。也有学者认为在癌痛状态下不会发生吗啡耐受 [8]。以上不同的研究结论可能与不同的动物模型、行为学测试方法以及不同的药物处理方式有关。
二、吗啡耐受的分子机制
发生吗啡耐受的分子机制目前尚不清楚,这是一个涉及多因素多系统多种神经递质的极其复杂的病理过程 [4]。吗啡的长期使用可导致细胞发生适应性的改变、神经元发生可塑性变化而产生耐受。研究发现:中枢μ-阿片受体(mu-opioid receptor,MOR)表达及功能的降低 [9,10,11],兴奋性氨基酸受体及神经胶质细胞的激活 [2,4,5,7,12],中枢促炎性细胞因子(IL-1、IL-6、TNF-α)的释放 [4,13,14]以及抑制性神经递质的减少 [4,6]等均参与了吗啡耐受的发生。
(一)MOR表达的降低与吗啡耐受
吗啡主要作用于MOR。MOR在大脑皮质、尾状壳核、杏仁核中外侧、海马、伏核、丘脑核中央、松果体、脚间核、黑质、上下丘脑、臂旁核、孤束核、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Periaqueductal Gray,PAG)及脊髓背角表面均有分布 [4]。其中PAG和脊髓背角的MOR的分布密度最高,并与吗啡耐受的发生密切相关 [4]。
目前认为吗啡耐受发生的主要机制是神经元胞膜上MOR的受体数量和功能的下调 [7,9,10,11]。研究显示:大鼠鞘内或全身反复给予吗啡后发生吗啡耐受相关的痛觉过敏,并伴有脊髓背角Ⅰ-Ⅱ层的MOR表达下降 [10,11]。即使没有慢性吗啡的暴露,在疼痛状态下的大鼠脊髓背角的MOR表达也会降低,而导致大鼠吗啡镇痛作用剂量-反应曲线右移 [7]。动物研究显示:脊髓背角MOR的降低的原因可能为两方面:①MOR基因表达的降低 [4];②MOR脱敏(desensitization)和内化(endocytosis) [9,10,11]。对于MOR内化的机制目前尚不清楚,近来认为,调节蛋白β-arrestin介导的MOR的脱敏、内化在吗啡镇痛耐受的发生中具有关键性作用 [10]。当外源性的阿片类药物(如吗啡),与MOR结合后,MOR被激活,与arrestins结合引起受体的内化,导致细胞膜表面可以被阿片类药物激活的具有功能的MOR减少,从而导致吗啡镇痛耐受的发生 [10]。敲除小鼠的β-arrestin2基因后,吗啡的镇痛作用明显增强而且镇痛耐受被抑制 [10]。
(二)兴奋性氨基酸受体激活与吗啡耐受
兴奋性氨基酸(ecitatory amino acid systems,EAAs)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一类重要的神经递质,广泛分布在脊髓尤其是背角浅层。研究发现EAAs参与了阿片耐受的发生。中枢神经系统(CNS)的兴奋性氨基酸受体分为:离子型和代谢型。其中离子型受体包括:N-甲基-D-天冬氨酸(N-Methyl-D-aspartate,NMDA)受体、红藻氨酸盐受体和α-氨基-3-羟基-5-甲基-4-异  唑丙酸(AMPA)受体。其中NMDA受体激活在吗啡镇痛耐受的发生中具有重要作用。鞘内联合注射吗啡和MK-801(一种NMDA受体非选择性的拮抗剂)可以有效抑制脊髓背角星形胶质细胞的激活而预防Sham大鼠吗啡耐受的发生 [4,15]。此外,非NMDA的兴奋性氨基酸受体-AMPA受体的激活和表达在吗啡耐受的发生中也产生了一定作用 [4,16]。
唑丙酸(AMPA)受体。其中NMDA受体激活在吗啡镇痛耐受的发生中具有重要作用。鞘内联合注射吗啡和MK-801(一种NMDA受体非选择性的拮抗剂)可以有效抑制脊髓背角星形胶质细胞的激活而预防Sham大鼠吗啡耐受的发生 [4,15]。此外,非NMDA的兴奋性氨基酸受体-AMPA受体的激活和表达在吗啡耐受的发生中也产生了一定作用 [4,16]。
 唑丙酸(AMPA)受体。其中NMDA受体激活在吗啡镇痛耐受的发生中具有重要作用。鞘内联合注射吗啡和MK-801(一种NMDA受体非选择性的拮抗剂)可以有效抑制脊髓背角星形胶质细胞的激活而预防Sham大鼠吗啡耐受的发生 [4,15]。此外,非NMDA的兴奋性氨基酸受体-AMPA受体的激活和表达在吗啡耐受的发生中也产生了一定作用 [4,16]。
唑丙酸(AMPA)受体。其中NMDA受体激活在吗啡镇痛耐受的发生中具有重要作用。鞘内联合注射吗啡和MK-801(一种NMDA受体非选择性的拮抗剂)可以有效抑制脊髓背角星形胶质细胞的激活而预防Sham大鼠吗啡耐受的发生 [4,15]。此外,非NMDA的兴奋性氨基酸受体-AMPA受体的激活和表达在吗啡耐受的发生中也产生了一定作用 [4,16]。
吗啡作用于神经元上的MOR(G-蛋白偶联受体)后,MOR被激活,并通过磷脂酶A途径使蛋白激酶A活性增强,门控的Ca 2+离子通道开放,Ca 2+内流增加,细胞内Ca 2+离子浓度增加,神经元兴奋性增加,同时Ca 2+离子作用于突触前膜促进谷氨酸释放,进而激活NMDA受体 [4,17]。NMDA受体的激活促使G蛋白介导的肌醇磷脂水解作用,并激活磷脂酶C,之后细胞内1,4,5三磷酸肌醇(IP 3)诱导细胞内Ca 2+离子游离,Ca 2+离子浓度进一步升高;Ca 2+离子协同甘油二醇(DAG)的产物以及肌醇磷脂水解后的产物共同激活细胞内蛋白激酶C(PKC) [4,17]。由此可见,NMDA受体激活在吗啡镇痛耐受的发生中具有重要作用。电生理研究也显示,MOR激活后可增强NMDA介导的电流 [18],同时在烧伤大鼠吗啡镇痛效果的研究中也发现,大鼠脊髓背角NMDA受体激活可导致MOR表达降低 [7]。
此外,NMDA受体激活所介导的PKC激活也参与了吗啡镇痛耐受的发生。在烧伤大鼠吗啡镇痛效果的研究中,发现除了大鼠脊髓背角NMDA受体表达增加以外,PKCγ表达的升高也导致了MOR表达的降低 [5,7]。鞘内联合注射吗啡和双吲哚基顺丁烯二酰亚胺(一种特异性的PKC抑制剂)或氯化白屈菜赤碱(一种非特异性的PKC抑制剂)可有效抑制大鼠吗啡耐受的发生 [5,17]。
(三)γ-氨基丁酸(GABA)的降低与吗啡耐受
GABA作为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广泛分布于脊髓,当谷氨酸介导的神经元兴奋时,GABA可拮抗增强的突触传递,以平衡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和抑制 [19]。GABA是在谷氨酸脱羧酶(GAD)的作用下由L-谷氨酸脱羧基形成,GAD分布于GABA中间神经元和胶质细胞 [19]。其中GAD65是分布于神经元的膜相关蛋白,促进GABA囊泡的产生,GABA囊泡以胞吐的方式进入细胞间隙后,GAD65同时介导GABA快速区域化与神经元突触后位点结合 [19]。研究显示幼年大鼠慢性吗啡暴露后,出现吗啡耐受所致的痛觉过敏,其脊髓背角GAD65的表达明显降低,说明GABA的降低参与了吗啡耐受的发生 [6]。
(四)中枢促炎性细胞因子表达增加与吗啡耐受
已有动物研究证实:当发生吗啡耐受时,脊髓背角除了神经元发生可塑性改变以外,星形胶质细胞和小角质细胞也同时被激活,并释放促炎性细胞因子(IL-1、IL-6、TNF-α等) [2,4,13],鞘内给予非甾体类抗炎药(non-steriod anti-inflammation drugs,NSAIDs),可降低脊髓水平炎性细胞因子的表达,从而抑制吗啡耐受的发生 [13]。
三、吗啡耐受的预防
发生吗啡耐受后,将导致吗啡的使用剂量不断增加,这一恶性循环又导致了吗啡耐受及其相关的痛觉过敏现象进一步恶化,而大剂量的吗啡使用又可导致严重不良反应的发生。因此,在临床治疗慢性疼痛时,不恰当的使用阿片类药物将会导致无法预测的痛觉过敏的发生(与治疗前的疼痛情况截然不同),并使得临床疼痛情况更加复杂和棘手。
临床上,当吗啡的剂量逐渐增加时,可考虑阿片类药物替换(opioid rotation)来预防吗啡耐受的发生。进行阿片类药物替换之后可能只需要之前一半剂量的吗啡或者更少的剂量就能够达到相同的镇痛效果,因此阿片类药物替换应该是预防吗啡剂量逐渐增加的切实可行并有效的方法 [3]。
此外,联合用药的方式也可以预防吗啡耐受的发生。动物研究显示:NSAIDs与吗啡联合使用,可改善慢性吗啡暴露大鼠的痛觉过敏现象 [13]。抗癫痫药物加巴喷丁与吗啡联合使用,也可抑制大鼠吗啡耐受的发生 [20]。MK-801和氯胺酮(均为非选择性的NMDA受体拮抗剂)均可通过抑制脊髓背角NMDA受体的激活抑制吗啡耐受的发生 [15,21]。
四、展望
吗啡是临床治疗急慢性疼痛的最主要的阿片类药物,随着舒适医疗需求的增加,吗啡的消耗量将逐年增加,吗啡耐受的发生已成为临床亟待解决的问题,采用各种有效的药物或方法抑制吗啡耐受的发生具有极大的意义。对于吗啡耐受的发生及其机制的研究促进了阿片类药物在慢性疼痛治疗中的有效应用,并对临床阿片类药物耐受的预防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有助于提出新的镇痛方式和方法,以改善阿片类药物镇痛时所带来的其他的神经病理性疼痛综合征。今后,尚需大量开展关于吗啡和辅助镇痛药物联合应用以及其他镇痛方式(如神经阻滞)联合应用抑制吗啡耐受的临床研究。
(宋莉 左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