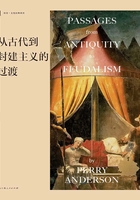
第一章 奴隶制生产方式
18
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许多篇幅论述资本主义的缘起时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这个问题就成为众多研究者研究的主题。对封建主义起源的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内还没有进行多少:作为新生产方式的一种不同的转化形式,它从来没有被列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它对于整体历史形态研究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向资本主义转化。吉本(Gibbon)对于罗马的衰落和古典时代终结的结论是严谨的,其中也许是自相矛盾地第一次提出了这个今天才被充分认识的真理:“这是一场将被永远记住的并且至今仍然影响世界各国的革命。”[1]与资本主义初期出现的原始积累的特点相反,欧洲封建主义的缘起是“灾难性的”,先前的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同时衰落,衰落中不可融合的因素的重组削弱了正常的封建生产方式的综合,因此始终保持着混合的特点。封建生产方式的双重的祖先自然是:曾经是罗马帝国基石的奴隶制生产方式的瓦解,以及蛮族入侵后日耳曼人的入侵,他们在新家园站稳脚跟,他们原始的生产方式出现扩张和转型。这两个根本不同的世界在古典时代的后几个世纪中缓慢地瓦解,并互相渗透。
19
要了解它是怎样发生的,首先必须追溯整个古典世界文明发生的最初发源地。希腊罗马文明一直是各个城市的组成中心。早期希腊城市和后期罗马共和国的自信与辉煌,其耀眼的光芒照耀了以后的多少个世纪,它的城市政体和文化所达到的鼎盛程度是其他任何时代都无可比拟的。哲学、科学、诗歌、历史、建筑、雕塑、法律、行政、流通、税收、选举、辩论、征募——所有这些都出现并发展到了一种无可比拟的成熟和强大的地步,虽然同时在城市文明的边缘总留给后人一些假象(trompe l'oeil)。在类似的城市文明之后再没有出现过与之相称的城市经济类型,相反,支撑着其知识分子和市民活力的物质资源却被来自农村的占压倒优势地位的冲击所牵制。古典世界的绝大部分基础是庞大的、无所改变的农村。农业经济是全部历史长河中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恒久地支撑着城市文明本身的繁荣。希腊罗马的城市,从来没有手工业者、商人和生产者所控制的社团,它们最初是而且通常是土地占有者聚集的城市。无论是实行民主制的雅典(Athens),还是实行寡头制的斯巴达(Sparta)或元老院制的罗马,其行政规则必定是被农业占有者控制的。他们的收入来源于在城市周围的农庄中生产的谷物、油、葡萄酒——古代社会的三种主要作物。城市中从事制造业的人是少数的、原始的:一般城市产品不外乎织物、陶器、家具和玻璃制品。技术是简单的、受限制的,运输费用极高。古典时代生产的结果不像后期那样集中发展,而是压缩和分散,因为距离决定着相关的生产费用,而不是劳动分工。有关古典时代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所占比重的图示说明,公元4世纪来自罗马帝国各城市的财政收入最终首次归入君士坦丁(Constantine)“五年期纳税”(collatio lustralis)所规定的帝国税收体系,即城市财政收入总额不得超过土地税的5%。[2]
20
当然,两种经济产量的统计并不足以削弱古典时代城市经济的重要性。因为在一个正规的农业社会中,城市交换的毛利是极小的,但是它从根本上超过任何农业经济的优越性仍然是决定性的。造成古典文明的这一与众不同的形式的前提是其海洋文明特点[3]。希腊罗马文明本质上是地中海文明的精华,因为内陆贸易只能通过水路连接,海上中途和长途运输是实现物物交换的唯一可行的方法。海洋对于贸易的巨大重要性可以从这样一个简单事实看出: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时代,在地中海两岸的叙利亚和西班牙之间运输大麦,海上运输距离比陆路运输短75英里[4]。因此,拥有曲折的岛屿、港口和岬角的爱琴海地区成为最早的城邦发源地,并不是偶然的;雅典作为城邦的典范,其建立应得益于它的海上商业运输的优势;当希腊化时代希腊殖民运动向近东地区扩张时,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成了埃及的主要城市,它也是埃及历史上第一个港口首都;位于台伯河上游的罗马成为水边大都市。水是贸易和交往中不可替代的中介,它使城市有可能向更集中和更成熟的方向发展,并远远超过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海洋是古典时代奇异光辉的向导。古典时代城市和乡村的特定结合是可能使用的最后一步,因为这在中心地区是不存在的。地中海是地球上面积最大的内陆海,它拥有最快捷的海上运输速度和抵抗最大风浪的陆地避风港。古典时代在全球历史中独一无二的地位是与它的地理优势密不可分的。
21
换言之,地中海为古代文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地理环境,其历史内涵和新意却是其中的城市联系的社会基础。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就是希腊罗马世界的重要发明,它是希腊罗马兴旺和衰亡的决定性特点。对这种生产方式的起源必须加以说明。奴隶本身在整个近东文明中以各种形式存在(其后亚洲其他地区也是如此),但是它一直是一种不纯正的司法形式——经常采取债务奴隶和刑事劳役的形式——在其他混合的劳役形式中,它只是向前发展的社会等级中带有依附和不自由特点的不定型的社会统一体中的低级形式[5]。它也从来不是希腊化时代以前的各君主政体中残余的血统论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它是主要的乡村劳动力的边缘存在的一种残余形式。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和埃及人的帝国——与后来地中海世界稀疏的、旱地农业形式相对立的,建筑在集中的、灌溉农业基础上的大河国家——并不是奴隶制经济,而且它们的司法体系也缺乏鲜明的单独的奴隶制的观念。是希腊城邦最早在形式上确立了绝对的奴隶制度并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并由此从一种从属的设施发展成为一套系统的生产方式。古典希腊化世界当然从来没有停留在完全使用奴隶劳动上,自由农民、依附民和城市工匠一直在不同的希腊城邦中以不同的形式结合,而且与奴隶制并存。此外,他们自身在从一个世纪到下一个世纪的内部和外部发展过程中,两者的比例都会有明显改变:每一个具体的社会组织都是不同的生产方式的特定组合,古典时代的那些国家也不例外[6]。但是,古希腊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是奴隶制,它控制着各类地方经济之间繁杂的关系,它给整个城邦文明留下深刻印记。罗马也一样。在古典文明的鼎盛时期——希腊从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罗马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奴隶制在劳动体系中是庞大的和普遍存在的。古典城市文化的顶点以奴隶制的鼎盛为标志;它在希腊化时代的希腊和基督教的罗马的衰落同样以另外一种生产方式的确立为标志。
22
古风时代之后的希腊作为奴隶生产方式的发源地,其占有的奴隶人口的总数,由于缺乏任何可信的统计,还无法准确地计算出来。那些被认可的数字之间差距很大,但是近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在伯利克里(Pericles)时代,雅典的奴隶与自由民比率大约是3比2[7]。在开俄斯(Chios)、艾吉纳(Aegina)或科林斯(Corinth),奴隶人口在不同时代可能更多;同时在斯巴达,农奴人口要远远多于公民人数。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很自然地注意到“城邦中必定有大量奴隶”,同时色诺芬(Xenophon)在描述雅典的兴旺景象时写道:“该城邦应当拥有公共奴隶,而每个雅典公民都能拥有3个奴隶。”[8]在古典时代的希腊,奴隶第一次超越了家务劳动的界限而被用于手工业、工业和农业生产中。同时,当奴隶劳动普遍使用时,它的内涵相应地变得绝对了:它不再是多种劳役中的一种可有可无的形式,而逐渐发展到了一个完全失去自由的极端,与一种新的不受束缚的自由矛盾地并存着。因为它确实是一种完全独立于奴隶人口之外的形式,所以它相应地提高了希腊城市中公民的地位,并使司法意义上有意识的自由达到了一种迄今未知的高度。希腊化的解放制度和奴隶制度是不可分的:一种是另一种的构成条件,这是一种双重系统。在近东诸帝国中,还没有先例和相应的社会等级制度,也没听说过自由公民权的概念或奴隶财产[9]。这种深刻的司法变化本身是在社会上和观念上与由于奴隶生产方式的发展所创造的经济奇迹相关联的。
23
我们注意到,古典时代的文明体现了在占绝对优势的农村经济中城市高高凌驾于农村之上的特点,与后来的早期封建世界形成了对照。这种没有地方性工业的繁华的大城市出现的前提是在农村有奴隶劳动的存在:因为它可以使土地所有者阶层从土地中脱离出来,使他们从土地中获取基本财富而转化成为一个实际的城市公民。亚里士多德运用因果关系表达了希腊古典时代后期社会观念的结果:“那些耕种土地的人在观念上应是奴隶,他们不是全部从一个民族中召集来的,他们在气质上也没有活力(因此能长年不息地工作也不会造反),他们的特性,往好的方面说,类似于次一等的蛮族农奴。”[10]罗马农村的高度发达的奴隶制生产方式是最具特色的,在那里甚至管理工作也授权给奴隶的监管人和管事官,安排各个组织的奴隶下田耕作[11]。奴隶大地产与封建庄园不同,允许居住地与收入永久分离;提供给富裕的有产者阶层的富余产品可以在不居住于该土地的情况下领取。直接的农业生产者与城市的占有者之间的联系不是固定的,也不以土地所在地为中介(如后来的附属于土地的农奴制)。相反,它是城市典型的货物买卖的普遍的商业行为,在那里,是典型的奴隶买卖市场。古典时代奴隶劳动由此体现出两种互相矛盾的特性,在各个统一体中隐含了希腊罗马世界的城市自相矛盾地早熟的秘密。一方面,奴隶制反映了最基本的农村可想象的劳动的堕落——人自身由于丧失了各种社会权利及法律权利而转化为无生命的生产工具,与驮兽无异:根据罗马理论,农业奴隶被认为是“会说话的工具”(instrumentum vocale),与“半会发声的工具”(instrumentum semi-vocale)家畜处于同等地位,这两种都是可买卖的动产(instrumentum mutum);另一方面,奴隶制同时也是迄今所知的最严厉的商业化劳动形式:在大城市的商品交换市场,劳动力整个下降为被买卖的物品。古典时代大量奴隶的特色在于农业劳动(这一点不是任何地方一直这样,而是总量上的情况):他们日常的组合、分配和派遣受城市市场的影响,在城市中很多奴隶当然也是受雇用的。奴隶制因此把城市和农村连接在一起,成为转向城市过分的利益的经济转折点。在城市和农村,战俘农业依然存在,它造成城市统治阶级与农村统治阶级的巨大差别,并作为地中海地区这种农业的补充,促进了城市间贸易的发展。在交通枢纽就是整个经济结构的中心的世界里,奴隶的优势之一是,它是一种卓越的可移动的商品[12]。他们可以毫不困难地从一个地区被运到另一个地区,可以被训练成具有各种技能;另外,在供给富庶的时代,在使用雇佣劳动或自由手工业者的地方,奴隶价格是低廉的,因为他们的劳动是灵活的。古典时代特别是雅典和罗马鼎盛时期,城市有产阶级极尽奢华和享乐——由于这种劳动体系的普遍存在而造成大量剩余产品,留给了其他不从事劳动者。
24-25
但是,这种野蛮的、有利可图的赚钱方式所需要的费用是高昂的。在古典时代,奴隶制生产关系决定了它与古代生产力具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它最终导致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瘫痪。这期间古典文明的经济技术自然有所进步。没有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在其上升时不伴随着物质进步,奴隶制生产方式在新的社会劳动分工结构确立的过程中使经济取得了重大进步。其中,被认为比较有利可图的可能是酒文化和油文化的扩展,旋转碾磨机碾磨谷物的引进以及面包质量的改良。螺旋压榨机设计出来了,吹玻璃技术发展了,供暖系统更加完善了,使用联合收割的方式收割谷物,植物学知识和土地灌溉技术也有可能有所发展[13]。因此,在古典世界,技术并没有完全停滞不前。但是同时,也没有产生出能够推动古代经济向新的大规模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重要的发明。历史上再没有比古典时代全方位的技术停滞更令人震惊的了[14]。将从雅典兴起到罗马覆亡的8个世纪的文献与其后兴起的、时间跨度同样长的封建生产方式相比,足可以理解静态经济与相对的动态经济的差别。当然给人以更深刻印象的是古典世界自身文化和上层建筑的生命力与迟钝的经济基础的差距:古典时代的手工技术不仅相对于后世的外部标准,而且相对于它本身的知识基础来讲,也是微小的和原始的——但毕竟在它自身的知识水平的高度上,在最关键的方面比随后的中世纪的水平要高得多。很少有人怀疑奴隶制经济结构从根本上要为这种不正常的不成比例的现象负责。亚里士多德用一句话言简意赅地总结了这种社会准则:“最杰出的城邦不会使手工工人成为公民,因为今天手工劳动的主体是奴隶或外国人。”[15]这类城邦反映了奴隶制生产方式的观念,而在古代世界的实际的社会结构中没有成为现实,但其逻辑一直是古代经济实质所固有的。
26
27
一旦手工劳动与失去自由紧密结合在一起,也就失去了自由发明的社会基础。奴隶制对于技术的消极影响不仅单纯造成奴隶劳动本身平均生产率的低下,而且造成奴隶使用总量的低下,他们逐渐地影响到所有的劳动方式。马克思曾试图表达过他们所致力的一种著名的甚或是隐晦的理论模式的行为类型:“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6]农业奴隶本身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旦监督放松,就几乎没有动力去称职认真地完成他们的经济任务;他们最合适的工作是在集约化的葡萄园和橄榄林中。另一方面,许多手工业奴隶和一些耕作奴隶,在有限的流行的技术领域是有很高技术能力的,因此,奴隶制对技术来说并不是基础性限制的直接原因,虽然这对于它自身的权利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在包围着古典世界全部手工劳动的社会观念的媒介中,奴隶制以降低身份的耻辱玷污了雇佣劳动甚至是独立劳动[17]。奴隶劳动一般来说不比自由劳动生产率低,特别在某些领域中更是这样;但是它确立了两种劳动的步调,因此在一个排除了文化和发明技术的普遍应用的经济空间中,两种劳动之间并没有产生较大的区别。物质工作与自由环境的脱离是如此严格,以致在希腊语中没有一个词表达劳动的概念,无论它是作为社会功能还是作为个人行为。农业和手工业基本都相信要“适应”自然,而不是改变自然,它们是服务方式。柏拉图(Plato)也绝对地将工匠排除在城市整体之外,对他来说,“劳动处于人类价值之外,在某些方面似乎甚至与人的本质对立”[18]。预先计划的技术,人所创造的对自然界的先进手段,与整体的人被吸收为自然界的“会说话的工具”是不相容的。生产力是根据“会说话的工具”的长年不懈的工作确定的,它阻碍了对于节省劳力的任何设计的持久的关心,从而降低了所有劳动的价值。对于任何一个曾经存在的城邦来说,古典时代典型的横向的扩张之路是地理上的征服,而非经济上的扩展。古典文明因而在本质上具有殖民的特点:通过定居和战争,在上升势头中的城邦细胞一成不变地繁殖它自己。掠夺、贡赋和奴隶是扩张的中心目标,这些就是殖民扩张的方式及结果。军事力量也许比在其他生产方式中都更加紧密地与经济发展相关,因为此前或此后奴隶主要的唯一的正常来源是战争中的俘虏,供养自由的城市作战军队也有赖于奴隶在家坚持生产;战场提供了在农田的劳动力,而反过来,被俘的劳动者则导致了从军公民的产生。帝国主义扩张的三个高潮可追溯至古典时代,它们依次以各不相同的特点构成了希腊罗马世界的总体模式:雅典的、马其顿的和罗马的。每一种模式都反映了一种海外征服的政治和组织问题的解决方法,每一种模式都被后一种模式所吸收和超越,但都没有逾越共同的城市文明的基础。
28
注释
18
[1] 《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第1卷,1896年[伯里(Bury)主编],1页。吉本在有关他的著作修订本的计划中,曾经对这句话作过修改,将范围局限在欧洲国家,而不是全世界的国家。他问道:“难道亚洲和非洲,从日本到摩洛哥,都曾经对罗马帝国有所了解或记忆吗?”(同上书,XXXV页)他很快又进一步阐述了世界其他地区怎样“感受”到欧洲的冲击以及他所记载的“革命”的基本秩序;但无论是遥远的日本,还是紧邻的摩洛哥,都不可能受到他所论述的地区历史的影响。
20
[2] 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1卷,465页。税款由negotiatores,即城市中从事各种商业活动的人,如商人或手工业者缴纳。尽管回报极少,它对城市人口来说是强制性的、不得人心的,因而正常的城市经济是脆弱的。
[3]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他的两部伟大的、但被忘却的研究著作《古代农业状况》(Agrarverhältnisse im Altertum)和《古典文化衰落的社会基础》(Die Sozialen Gründe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Kultur)中,第一个着重强调了这个基本事实。见《社会经济史论文集》(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图宾根,1924年,4页以下,292页以下。
[4] 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2卷,841—842页。
21
[5] 芬利(M.I.Finley),《奴役和自由之间》(Between Slavery and Freedom),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第6卷,1963—1964年,237—238页。
22
[6] 通篇文献中,“社会形态”一般应指“社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形态观念的意义就是强调,在已知的任何历史社会整体中可能产生的生产方式的多种多样(heterogeneity)性。相反,“社会”一词不加评论地反复出现,常常充分反映一个历史整体中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内在统一的假设,实际上,这种单纯的统一特性并不存在。而社会形态,除非在特殊情况下,通常指各种不同生产方式在一种占统治地位(dominance)的生产方式的组织下的结合。这个差别,参见波朗查斯(Nicos Poulantzas),《政治权力和社会等级》(Pouvoir Politique et Classes Sociales),巴黎,1968年,10—12页。清楚这一点后,就可以避免在使用“社会”一词时有所局限,在此不赘述。
[7] 安德鲁斯(A.Andrewes),《希腊社会》(Greek Society),伦敦,1967年,135页。他指出,在公元前5世纪,当公民人数大约在4.5万人时,全体奴隶的人数在8万—10万之间。这种提出量值的方式,可能比确定比例高低的方式会得到更广泛的支持。但是,所有现代的、有关古典时代的史书,都缺乏关于人口数量和社会等级的可靠信息。根据公元前4世纪雅典人口下降时城市谷物的进口数量,琼斯确定,奴隶与公民的比率为1比1,见《雅典民主》(Athenian Democracy),牛津,1957年,76—79页。而芬利认为,在前5世纪和前4世纪的鼎盛时期,比率应为3比1或4比1,见《希腊文明是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吗?》(Was Greek Civilization Based on Slave Labour?),载《历史》(Historia),第8期,1959年,58—59页。韦斯特曼(W.L.Westermann)的《希腊和罗马古典时代的奴隶制体系》(The Slave Systems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y),费城,1955年,9页,是以古代奴隶制为主题的现代论著中最通俗易懂的一部,他所确定的比率为安德鲁斯和芬利所接受,即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奴隶数量约为6万—8万人。
23
[8]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7,iv,4;色诺芬,《方法论》(Waysand Means),IV ,17。
[9] 韦斯特曼,《希腊和罗马古典时代的奴隶制体系》,42—43页;芬利,《奴役和自由之间》,236—239页。
24
[10] 《政治学》,7,ix,9。
[11] 在罗马共和国和元首制发展的鼎盛时期,奴隶劳动存在的普遍矛盾性的影响是,某些类别的奴隶地位上升,占据了内政和职业的地位,又有利于解放有技术的自由人之子,并随之将其提升至公民阶层。这个过程并不是为古典奴隶制的人道主义辩护,而是罗马统治阶级从任何一种劳动形式——哪怕是行政领域中——完全解脱的另一个标志。
25
[12] 韦伯,《古代农业状况》,5—6页。
26
[13] 见基希勒(F.Kiechle),《罗马帝国奴隶劳动和技术进步》(Slavenarbeit und Technischer Fortschritt im römischen Reich),威斯巴登,1969年,12—114页。莫里茨(L.A.Moritz),《古典时代的谷物碾磨和面粉》(Grain-Mills and Flour in Classical Antiquity),牛津,1958年;怀特(K.D.White),《罗马农业》(Roman Farming),伦敦,1970年,123—124、147—172、188—191、260—261、452页。
[14] 如往常一样,芬利很有说服力地提出了普遍问题,见《古代世界的技术革新和经济进步》(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Progress in the Ancient World),载《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第18期,第1号,1955年,29—45页。关于罗马帝国的专门记载,见沃尔班克(F.W.Walbank),《恐怖的革命》(The Awful Revolution),利物浦,1969年,40—41、46—47、108—110页。
[15] 《政治学》,3,iv, 2。
27
[16]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柏林,1953年,27页(此处译文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757页。——译者)。
[17] 芬利指出,希腊语中penia一词的意思,传统上与ploutos意思相反,即“贫穷”与“富裕”,事实上,它还有更广泛的贬低的意义,指“苦工”或“强制的苦工”,甚至包括富裕的小土地所有者,他们的劳动处在同样的文化阴影的笼罩之下。芬利,《古代经济》(Ancient Economy),伦敦,1973年,41页。
28
[18] 韦尔南(J.P.Vernant),《希腊神话和思想》(Mythe et Pensée chez les Grecs),巴黎,1965年,192、197—199、217页。韦尔南的两篇短文《普罗米修斯及技术职能》(Prométhée et la Fonction Technique)和《古希腊的劳动及其性质》(Travail et Nature dans la Grèce Ancienne)中对“创造性实践”(poiesis)和“一般性实践”(praxis)的区别,以及耕作者、手工业者和放债人与城邦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亚力山大·哥瑞(Alexandre Koyré)曾经致力于讨论希腊文明技术停滞的原因,认为,原因不在于奴隶制的存在和劳动的贬值,而是因为物理学没有发展,使数学计算方法无法用于现实世界,见《精密宇宙中大概的世界》(Du Monde de l'À Peu Près à l'Univers de la Précision),载《评论》(Critique),1948年9月,806—808页。他坦言,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这种现象的社会学解释。但是在别的场合,他本人承认,中世纪同样没有物理学,虽然产生了有活力的技术,但这不是科学的进展,而是生产关系的进程造成技术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