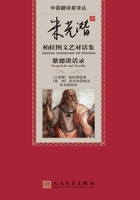
第5章 理想国(卷十)[97]
——诗人的罪状
对话人:苏格拉底
格罗康
苏 我有许多理由相信,我们所建立的城邦是最理想的,尤其是从关于诗的规定来看[98],我敢说。
格 你指的是哪一项规定呢?
苏 我指的是禁止一切摹仿性的诗进来。我们既然分清心灵的各种因素[99]了,更足见诗的禁令必须严格执行。
格 这话怎样说?
苏 说句知心话,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悲剧诗人和其他摹仿者们,在我看,凡是这类诗对于听众的心灵是一种毒素,除非他们有消毒剂,这就是说,除非他们知道这类诗的本质真相。
格 你为什么这样说?
苏 我的话不能不说,虽然我从小就对于荷马养成了一种敬爱,说出来倒有些于心不安。荷马的确是悲剧诗人的领袖。不过尊重人不应该胜于尊重真理,我要说的话还是不能不说。
格 当然。
苏 那么,就请听我说,或是说得更恰当一点,请听我发问。
格 你问吧。
苏 请问你,摹仿的一般性质怎样?我自己实在不知道它的目标是什么。
格 你都不知道,难道我还能知道吗?
苏 那并不足为奇,眼睛迟钝的人有时反比眼睛尖锐的人见事快。
格 这话倒不错。不过当你的面前,我不敢冒昧说我的意见,尽管它像是很明显的;还是请你说吧。
苏 我们好不好按照我们经常用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呢?我们经常用一个理式[100]来统摄杂多的同名的个别事物,每一类杂多的个别事物各有一个理式。你明白吧?
格 我明白。
苏 我们可以任意举那一类杂多事物为例来说,床也好,桌子也好,都各有许多个例,是不是?
格 不错。
苏 这许多个别家具都由两个理式统摄,一个是床的理式,一个是桌的理式,是不是?
格 不错。
苏 我们不也常说,工匠制造每一件用具,床,桌,或是其他东西,都各按照那件用具的理式来制造么?至于那理式本身,它并不由工匠制造吧?
格 当然不能。
苏 制造理式的那种工匠应该怎样称呼呢?
格 你指的是谁?
苏 我指的是各行工匠所制造出的一切东西,其实都是由他一个人制造出来的那种工匠。
格 他倒是一个绝顶聪明人!
苏 等一会儿,你会更有理由这样赞扬他。因为这位工匠不仅有本领造出一切器具,而且造出一切从大地生长出来的,造出一切有生命的,连他自己在内;他还不以此为满足,还造出地和天,各种神,以及天上和地下阴间所存在的一切。[101]
格 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咧!
苏 你不相信吗?你是否以为绝对没有这样一个工匠呢?你是否承认一个人在某个意义上能制造一切事物,在另一意义上却不能呢?在某个意义上你自己也就可以制造这一切事物,你不觉得么?
格 用什么方法呢?
苏 那并不是难事,而是一种常用的而且容易办到的制造方法。你马上就可以试一试,拿一面镜子四方八面地旋转,你就会马上造出太阳,星辰,大地,你自己,其他动物,器具,草木,以及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切东西。
格 不错,在外形上可以制造它们,但不是实体。
苏 你说得顶好,恰合我们讨论的思路,我想画家也是这样一个制造外形者,是不是?
格 当然是。
苏 但是我想你会这样说,一个画家在一种意义上虽然也是在制造床,却不是真正在制造床的实体,是不是?
格 是,像旋转镜子的人一样,他也只是在外形上制造床。
苏 木匠怎样?你不是说过他只制造个别的床,不能制造“床之所以为床”那个理式吗?
格 不错,我说过这样话。
苏 他既然不能制造理式,他所制造的就不是真实体,只是近似真实体的东西。如果有人说木匠或其他工匠的作品完全是真实的,他的话就不是真理了。
格 至少是研究这类问题的哲学家们不承认他说的是真理。
苏 那么,如果这样制造的器具比真实体要模糊些,那就不足为奇了。
格 当然。
苏 我们好不好就根据这些实例,来研究摹仿的本质?
格 随便你。
苏 那么,床不是有三种吗?第一种是在自然中本有的,我想无妨说是神制造的,因为没有旁人能制造它;第二种是木匠制造的;第三种是画家制造的。
格 的确。
苏 因此,神,木匠,画家是这三种床的制造者。
格 不错,制造者也分这三种。
苏 就神那方面说,或是由于他自己的意志,或是由于某种必需,他只制造出一个本然的床,就是“床之所以为床”那个理式,也就是床的真实体。他只造了这一个床,没有造过,而且永远也不会造出,两个或两个以上这样的床。
格 什么缘故呢?
苏 因为他若是造出两个,这两个后面就会有一个公共的理式,这才是床的真实体,而原来那两个就不是了。
格 你说得对。
苏 我想神明白这个道理,他不愿造某某个别的床,而要造一切床的理式,所以他只造了这样一个床,这床在本质上就只能是一个。
格 理应如此。
苏 我们好不好把他叫做床的“自然创造者”[102],或是用其他类似的称呼?
格 这称呼很恰当,因为他在制造这床和一切其他事物时,就是自然在制造它们。
苏 怎样称呼木匠呢?他是不是床的制造者?
格 他是床的制造者。
苏 画家呢?他可否叫做床的制造者或创造者?
格 当然不能。
苏 那么,画家是床的什么呢?
格 我想最好叫他做摹仿者,摹仿神和木匠所制造的。
苏 那么,摹仿者的产品不是和自然隔着三层吗[103]?
格 不错。
苏 悲剧家既然也是一个摹仿者,他是不是在本质上和国王[104]和真理也隔着三层吗?并且一切摹仿者不都是和他一样吗?
格 照理说,应该是一样。
苏 我们对于摹仿者算是得到一致的意见了。现在再来说画家,他所要摹仿的是自然中的真实体呢?还是工匠的作品呢?
格 他只摹仿工匠的作品。
苏 他摹仿工匠作品的本质,还是摹仿它们的外形呢?这是应该分清的。
格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苏 我的意思是这样:比如说床,可以直看,可以横看,可以从许多观点看。观点不同,它所现的外形也就不同,你以为这种不同是在床的本质,还在床的外形呢?现形不同的床是否真正与床本身不同呢?其他一切事物也可由此类推。
格 外形虽不同,本质还是一样。
苏 想一想图画所要摹仿的是实质呢,还是外形呢?
格 图画只是外形的摹仿。
苏 所以摹仿和真实体隔得很远,它在表面上像能制造一切事物,是因为它只取每件事物的一小部分,而那一小部分还只是一种影像。比如说画家,他能画出鞋匠木匠之类工匠,尽管他对于这些手艺毫无知识。可是他如果有本领,他就可以画出一个木匠的像,把它放在某种距离以外去看,可以欺哄小孩子和愚笨人们,以为它真正是一个木匠。
格 确实如此。
苏 那么,好朋友,依我想,关于画家的这番话可以应用到一切与他类似的人们。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他遇见过一个人,精通一切手艺,而且对于一切事物精通的程度还要超过当行的人,我们就应该向他说,他是一个傻瓜,显然受了一个魔术家或摹仿者的欺哄,他以为那人有全知全能,是因为他分不清有知,无知,和摹仿三件事。
格 的确。
苏 现在我们就要检讨悲剧和悲剧大师荷马了。因为许多人都说悲剧家无所不通,无论什么技艺,无论什么善恶的人事,乃至于神们的事,他都样样通晓。他们说,一个有本领的诗人如果要取某项事物为题材来做一首好诗,他必须先对那项事物有知识,否则就不会成功。我们对于这些人们必须检查一下,看他们是否也碰到了摹仿者们,受了欺哄,看不出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对真实体不用有知识就可轻易地做成呢?还是他们说的果然不错,有本领的诗人们对于他们因描绘而博得赞赏的那些事物真正有知识呢?
格 是的,这倒是必须检查的。
苏 你想一想,如果一个人既能摹仿一件事物,同时又能制造那件事物,他会不会专在摹仿上下功夫,而且把摹仿的本领看作他平生最宝贵的东西呢?
格 我想他不致如此。
苏 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摹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摹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
格 我也是这样看,那样做,他可以得到更大的荣誉,产生更大的效益。
苏 关于许多问题,我们倒不必追问荷马或其他诗人,不必问他们对医学有没有知识,是否只在摹仿医学的话语;不必追问他们古今有没有过一个诗人,像埃斯库勒普医神一样,医好过一些病人,留传下一派医学。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技艺,我们也不必去追问诗人们。但是荷马还要谈些最伟大最高尚的事业,如战争,将略,政治,教育之类,我们就理应这样质问他:“亲爱的荷马,如果像你所说的,谈到品德,你并不是和真理隔着三层,不仅是影像制造者,不仅是我们所谓摹仿者,如果你和真理只隔着两层,知道人在公私两方面用什么方法可以变好或变坏,我们就要请问你,你曾经替哪一国建立过一个较好的政府,像莱科勾对于斯巴达,许多其他政治家对于许多大小国家那样呢?世间有哪一国称呼你是它的立法者和恩人,像意大利和西西里称呼卡雍达斯,我们雅典人称呼梭伦那样呢?[105]谁这样称呼你呢?”格罗康,你想荷马能举出这样一个国名来么?
格 我想他不能,就连崇拜荷马的人们也不这样说。
苏 有没有人提起当时有哪一次战争打得好,是由荷马指挥或参谋呢?
格 没有。
苏 有没有人提起他对各种技艺或事业有很多发明和贡献,像密勒图人泰利斯,或是西徐亚人阿那卡什斯那样呢?[106]
格 也没有。
苏 荷马对于国家既然没有建立功劳,我们是否听说过他生平做过哪些私人的导师,这些人因为得到他的教益而爱戴他,把他的生活方式留传到后世,像毕达哥拉斯那样呢[107]?据说毕达哥拉斯由于这个缘故很受人爱戴,一直到现在,他的门徒还在奉行他的生活方式,显得与众不同。荷马是否也能这样呢?
格 更没有这样事。如果传说可靠,他的门徒克瑞俄斐罗在教育上比在名字上显得更滑稽[108]。传说荷马在世时就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身后的事更不用说了。
苏 不错,他们是那么说。格罗康,你想一想,如果荷马真正能给人教育,使人得益,如果他对于这类事情有真知识,而不是只在摹仿,他不会有许多敬爱他的门徒追随他的左右吗?阿布德拉人普罗塔哥拉以及克奥斯人普若第库斯[109]之流,都能在私人谈论中使当时人相信,不从他们受教,就不能处理家务和国政;他们的智慧大受爱戴,所以门徒们几乎要把他高举到头上游行。如果荷马也能增长人的品德,当时人会让他和赫西俄德到处奔走行吟吗?人们不会把他们当宝贝看待,抓住他们不放,强迫他留在家乡吗?若是留不住,人们不会跟他们到处走,等到教育受够了,才肯放手吗?
格 在我看,你的话一点也不错,苏格拉底。
苏 所以我们可以说,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只是摹仿者,无论是摹仿德行,或是摹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像,并不曾抓住真理。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画家尽管不懂鞋匠的手艺,还是可以画鞋匠,观众也不懂这种手艺,只凭画的颜色和形状来判断,就信以为真。
格 完全是这样。
苏 我想我们也可以说,诗人也只知道摹仿,借文字的帮助,绘出各种技艺的颜色;而他的听众也只凭文字来判断,无论诗人所描绘的是鞋匠的手艺,将略,还是其他题材,因为文字有了韵律,有了节奏和乐调,听众也就信以为真。诗中这些成分本来有很大的迷惑力。假如从诗人作品中把音乐所生的颜色一齐洗刷去,只剩下它们原来的简单躯壳,看起来会像什样,我敢说你注意过的。
格 我确是注意过。
苏 它们像不像一个面孔,还有点新鲜气色,却说不上美,因为像花一样,青春的芳艳已经枯萎了?
格 这比喻很恰当。
苏 再想一想,影像的制造者,就是我们所说的摹仿者,只知道外形,并不知道实体,是不是?
格 对。
苏 可是我们对于这问题不应半途而废,应该研究到彻底。
格 请你说下去。
苏 画家能不能画缰辔?
格 能。
苏 但是制造缰辔的却是鞍匠和铁匠?
格 当然。
苏 缰辔应该像什样,画家知道不?还是连制造它们的鞍匠和铁匠也不能知道,只有用它们的马夫才知道呢?
格 只有马夫才知道。
苏 我们可否由此例推一切,得到一个结论呢?
格 什么结论?
苏 我说关于每件东西都有三种技艺:应用,制造,摹仿。
格 对的。
苏 那么,我们怎样判定一个器具,动物,或行为是否妥当,美,完善呢?是否要看自然或技艺所指定它应有的用途?
格 这是要看它的用途来判定。
苏 那么,每件东西的应用者对于那件东西的知识就必然比旁人的可靠,也就必然能告诉制造者说他自己应用这件东西时,哪样才好,哪样才坏。比如说,吹笛者才能告诉制笛者,笛子要像啥样,吹起来才顶好,应该怎样做才好,而制笛者就要照他的话去做。
格 当然。
苏 所以吹笛者才知道笛的好坏,把他的知识告诉制笛者,制笛者就照他的话去做。
格 不错。
苏 所以每件器具的制造者之所以对于它的好坏有正确见解,是由于他请教于有知识者[110],不得不听那位有知识者的话,而那位有知识者正是那件器具的应用者。
格 当然。
苏 现在谈到摹仿者,他对于他所描写的题材是否美好的问题,是从应用方面得到知识呢?还是由于不得不请教于有知识者,听他说过应该怎样描写才好,而后得到正确见解呢?
格 都不是。
苏 那么,摹仿者对于摹仿题材的美丑,不是既没有知识,又没有正确见解吗?
格 显然如此。
苏 摹仿者对于他所摹仿的东西,就理解来说,可就很了不起啦!
格 不见得是了不起。
苏 话虽如此说,尽管他对于每件东西的美丑没有知识,他还是摹仿;很显然地,他只能根据普通无知群众所认为美的来摹仿。
格 当然。
苏 那么,我们现在显然可以得到这两个结论:头一层,摹仿者对于摹仿题材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知识;摹仿只是一种玩艺,并不是什么正经事;其次,从事于悲剧的诗人们,无论是用短长格还是用英雄格[111],都不过是高度的摹仿者。
格 的确如此。
苏 老天爷!摹仿的对象不是和真理隔着三层吗?
格 是的。
苏 再说摹仿的效果,它可以影响哪一种心理作用呢?
格 我不懂你的意思。
苏 这话可以这样解释:同一量积,近看和远看是不是像不同?
格 是不同。
苏 同一件东西插在水里看起来是弯的,从水里抽出来看起来是直的;凸的有时看成凹的,由于颜色对于视官所生的错觉。很显然地,这种错觉在我们的心里常造成很大的混乱。使用远近光影的图画就利用人心的这个弱点,来产生它的魔力,幻术之类玩艺也是如此。
格 的确。
苏 要防止这种错觉,最好的方法是使用度量衡。人心只能就形似上揣测大小多寡轻重,使用计算,测量,或衡度,才可以准确。
格 当然。
苏 这种计算衡量的工作是否要靠心的理智部分?
格 当然要靠理智。
苏 经过衡量之后,理智判定两件东西哪个大,哪个小,或是相等[112],我们对于同一事物不就有两种相反的判断么?
格 是那样。
苏 我们从前不是说过:同一心理作用对于同一事物不可能同时得到两个相反的结论吗?
格 我们说过这样话,而且说得不错。
苏 那么,信赖衡量的那种心理作用,和不信赖衡量的那种心理作用就不相同了?
格 当然不同。
苏 信赖衡量的那种心理作用是不是人心中最好的部分?
格 那是无可辩驳的。
苏 和它相反的那种心理作用就是人心中低劣的部分了。
格 那是毫无疑问的。
苏 原先我说图画和一切摹仿的产品都和真理相隔甚远,和它们打交道的那种心理作用也和理智相隔甚远,而它们的目的也不是健康的或真实的,我的意思就是要你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格 你说得对。
苏 那么,摹仿不是低劣者和低劣者配合,生出的儿女也就只能是低劣者吗?[113]
格 显然是那样。
苏 这番话是否只能应用到视觉方面的摹仿,还是也可以应用到我们所称为诗的声音摹仿呢?
格 诗自然也是一样。
苏 我们不能单凭诗画类比的一些貌似的地方,还要研究诗的摹仿所关涉到的那种心理作用,看它是好还是坏。
格 我们的确应该这样办。
苏 我们姑且这样来看它。诗的摹仿对象是在行动中的人,这行动或是由于强迫,或是由于自愿,人看到这些行动的结果是好还是坏,因而感到欢喜或悲哀。此外还有什么呢?
格 诗的摹仿尽于此了。
苏 在这整个过程之中,一个人是否始终和他自己一致呢?是否像在视觉中一样,自相冲突,对于同一事物同时有相反的见解,而在行为上也自相冲突,自己和自己斗争呢?我想我们用不着对这问题再找答案,因为你应该记得,我们从前讨论这类问题时,已经得到一个一致的意见了,就是人心同时充满着这类的冲突。[114]
格 我们所得到的意见是对的。
苏 当然是对的,不过我以为还应该讨论我们从前所忽略掉的。
格 忽略掉什么?
苏 我们从前说过,一个有理性的人若是遭到灾祸,比如死了儿子,或是丧失了他所看重的东西,他忍受这种灾祸,要比旁人镇静些,你还记得么?
格 记得。
苏 想一想,他还是简直不觉哀恸呢?还是哀恸既不可免,他就使它有节制呢?
格 他会使哀恸有节制。
苏 请再想一想,他要控制哀恸,在什样场合比较容易,在许多人看着他的时候?还是在他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呢?
格 在许多人看着他的时候,他比较容易控制哀恸。
苏 若是单独一个人,他会发出本来怕人听见的呼号,做出许多本来怕人看见的事情。
格 的确如此。
苏 鼓励他抵抗哀恸的不是理性和道理吗?反之,怂恿他尽量哀恸的不是那哀恸的情感本身吗?
格 是的。
苏 一个人对于同一事物,同时被拖着向两个相反的方向走,又要趋就,又要避免,这不就足以证明人心中本来就有两种相反的动机么?
格 的确。
苏 其中一个动机常愿服从道理,一切听它指导。
格 这话怎样说?
苏 依理说,遇到灾祸,最好尽量镇静,不用伤心,因为这类事变是祸是福还不可知,悲哀并无补于事,尘世的人事也值不得看得太严重,而且悲哀对于当前情境迫切需要做的事是有妨碍的。
格 迫切需要做的事是什么?
苏 要考虑事件发生的原委,随机应变,凭理性的指导去作安排。我们不能像小孩们,跌了一个跤,就用手扪着创伤哭哭啼啼的;我们应该赶快地考虑怎样去医疗,使损失弥补起来,让医药把啼哭赶走。
格 这倒是处逆境的最好的方法。
苏 人性中最好的部分让我们服从这种理性的指导。
格 显然如此。
苏 然则人性中另外那一部分,使我们回想灾祸,哀不自禁的那个部分,不就是无理性,无用而且怯懦吗?
格 不错。
苏 最便于各种各样摹仿的就是这个无理性的部分,而达观镇静的性格常和它自己调协一致,却不易摹仿,纵然摹仿出来,也不易欣赏,尤其是对于挤在戏院里那些嘈杂的听众,因为所摹仿的性情对他们是陌生的。
格 的确。
苏 总之,摹仿诗人既然要讨好群众,显然就不会费心思来摹仿人性中理性的部分,他的艺术也就不求满足这个理性的部分了;他会看重容易激动情感的和容易变动的性格,因为它最便于摹仿。
格 显然如此。
苏 那么,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摹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像。
格 的确。
苏 我们还没有数出摹仿的最大的罪状咧。连好人们,除掉少数例外,也受它的坏影响,这不是最严重的吗?
格 的确,如果摹仿真有那种坏影响,如你所说的。
苏 想一想这个事实:听到荷马或其他悲剧诗人摹仿一个英雄遇到灾祸,说出一大段伤心话,捶着胸膛痛哭,我们中间最好的人也会感到快感,忘其所以地表同情,并且赞赏诗人有本领,能这样感动我们。
格 我懂得,我们确实有这样感觉。
苏 但是临到悲伤的实境,我们却以能忍耐能镇静自豪,以为这才是男子气概,而我们听诗时所赞赏的那种痛哭倒是女子气,你注意到没有?
格 我注意到,你说得一点不错。
苏 看见旁人在做我们自己所引为耻辱而不肯做的事,不但不讨厌,反而感到快活,大加赞赏,这是正当的么?
格 这自然不很合理。
苏 不错,尤其是你从另一个观点来看。
格 从哪个观点看?
苏 你可以这样来看:我们亲临灾祸时,心中有一种自然倾向,要尽量哭一场,哀诉一番,可是理智把这种自然倾向镇压下去了。诗人要想餍足的正是这种自然倾向,这种感伤癖。同时,我们人性中最好的部分,由于没有让理智或习惯培养好,对于这感伤癖就放松了防闲,我们于是就拿旁人的痛苦来让自己取乐。我们心里这样想:看到的悲伤既不是自己的,那人本自命为好人,既这样过分悲伤,我们赞赏他,和他表同情,也不算是什么可耻的事,而且这实在还有一点益处,它可以引起快感,我们又何必把那篇诗一笔抹煞,因而失去这种快感呢?很少有人能想到,旁人的悲伤可以酿成自己的悲伤。因为我们如果拿旁人的灾祸来滋养自己的哀怜癖,等到亲临灾祸时,这种哀怜癖就不易控制了。
格 你说得很对。
苏 这番话是否也可以应用到诙谐?你看喜剧表演或是听朋友们说笑话,可以感到很大的快感。你平时所引为羞耻而不肯说的话,不肯做的事,在这时候你就不嫌它粗鄙,反而感到愉快,这情形不是恰和你看悲剧表演一样吗?你平时也是让理性压制住你本性中诙谐的欲念,因为怕人说你是小丑;现在逢场作戏,你却尽量让这种欲念得到满足,结果就不免于无意中染到小丑的习气。你看是不是这样?
格 是这样。
苏 再如性欲,忿恨,以及跟我们行动走的一切欲念,快感的或痛感的,你可以看出诗的摹仿对它们也发生同样的影响。它们都理应枯萎,而诗却灌溉它们,滋养它们。如果我们不想做坏人,过苦痛生活,而想做好人,过快乐生活,这些欲念都应受我们支配,诗却让它们支配着我们了。
格 我不能不赞成你的话。
苏 那么,你如果遇到崇拜荷马的人们说,荷马教育了希腊人,一个人应该研读荷马,去找做人处世的道理,终身都要按照他的教训去做,你对说这种话的人们最好是恭而且敬的——他们在他们的见识范围以内本来都是些好人——你最好赞同他们,说荷马是首屈一指的悲剧诗人;可是千万记着,你心里要有把握,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格 你的话对极了。
苏 我们既然又回到诗的问题[115],我们就可以辩护我们为什么要把诗驱逐出理想国了;因为诗的本质既如我们所说的,理性使我们不得不驱逐她。如果诗要怪我们粗暴无礼,我们也可以告诉她说,哲学和诗的官司已打得很久了。像“恶犬吠主”,“蠢人队伍里昂首称霸”,“一批把自己抬得比宙斯还高的圣贤”,“思想刁巧的人们毕竟是些穷乞丐”,以及许多类似的谩骂都可以证明这场老官司的存在[116],话虽如此说,我们还可以告诉逢迎快感的摹仿为业的诗,如果她能找到理由,证明她在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有合法的地位,我们还是很乐意欢迎她回来,因为我们也很感觉到她的魔力。但是违背真理是在所不许的。格罗康,你是否也感觉到诗的魔力,尤其是她出于荷马的时候?
格 她的魔力对我可不小!
苏 那么,我们无妨定一个准她回来的条件,就是先让她自己做一篇辩护诗,用抒情的或其他的韵律都可以。
格 这是应该的。
苏 我们也可以准许她的卫护者,就是自己不做诗而爱好诗的人们,用散文替她作一篇辩护,证明她不仅能引起快感,而且对于国家和人生都有效用。我们很愿意听一听。因为如果证明了诗不但是愉快的而且是有用的,我们也就可以得到益处了。
格 那对我们确是有益。
苏 但是如果证明不出她有用,好朋友,我们就该像情人发见爱人无益有害一样,就要忍痛和她脱离关系了。我们受了良好政府的教育影响,自幼就和诗发生了爱情,当然希望她显出很好,很爱真理。可是在她还不能替自己作辩护以前,我们就不能随便听她,就要把我们的论证当作避邪的符咒来反复唪诵,免得童年的爱情又被她的魔力煽动起来,像许多人被她煽动那样。我们应该像唪诵符咒一样来唪诵这几句话:这种诗用不着认真理睬,本来她和真理隔开;听她的人须警惕提防,怕他心灵中的城邦被她毁坏;我们要定下法律,不轻易放她进来。
格 我完全赞成你的话。
苏 一个人变好还是变坏,这关系是非常重大的,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还更重大,所以一个人不应该受名誉,金钱和地位的诱惑,乃至于受诗的诱惑,去忽视正义和其他德行。
格 我和你同意,把这作为我们讨论的总结,我想一切人都会和我一样同意。
根据Lindsay参照Jowett和Emile Chambry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