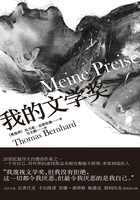
自由汉莎城市不来梅文学奖
长达五年之久没有动笔写什么之后,我在1962年一年里写出了《严寒》这本书,那时我对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茫然。我把《严寒》寄给了一位朋友,他是岛屿出版社的编辑,没过三天,手稿就被出版社采用了。这时我认识到,手稿并不完整,不能就这样发表。于是我来到法兰克福,住进一家小旅店,位于埃申海姆塔附近一条交通繁忙的大街,是我可以接受的最便宜的旅店之一,在那里我要彻底修改我的小说,书中所有带标题的章节都是我在那里写的。每天我五点钟就起床,坐到靠窗户的小桌子旁,每逢到了中午能写出五页或者八页甚至于十页,我就去岛屿出版社把稿子给负责该书的女编辑看,与她商量把这几页放到书稿的什么地方。在法兰克福逗留的几个星期里,全书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删掉了许多篇幅,可能将近一百页,这样修改之后,我觉得书稿可以认可了,能够付排了。校样印出来之后,我带着它去华沙旅行,我一个女友在那里的艺术学院读书。当时那里正值一年最冷的季节,我住宿在人们称作Dziekanka的大学生宿舍里,离政府宫不远,好几个星期在这座美丽的、令人新奇而又陌生的城市里到处跑,同时读着书稿校样。中午我在作家俱乐部用餐,晚饭同演员在一起,那里的饭菜相对更好一些。在华沙的这些日子是我生活中最幸福的岁月之一,我大衣兜里总揣着校样,我的对话者是讽刺作家莱茨,他那些著名的格言警句都首先记在他妻子的厨房记事簿上,他经常邀请我去他家,有时也请我到新世界大道喝咖啡。我很幸运,这本书在1963年春天出版,《时代周报》同时发表了楚克迈尔(1)的占据整版的长篇评论。于是对这本书的论战就开始了,言辞激烈,硝烟弥漫,从令人窘迫的称赞到恶意的贬损,应有尽有,我被完全击垮了,仿佛掉进了可怕的无底深渊。我误以为文学是我的希望,这个错误会让我窒息。我不想再理会什么文学了。它没有使我幸福,而是将我踹进了臭气熏天的沟壑,我想,没救了,没有逃生的希望了。我诅咒文学,诅咒我与其勾搭连环的淫乱行为,毅然去了一处建筑工地,受雇当了卡车司机,为位于修道院新城堡街的克里斯托福洛斯公司干活。有好几个月我为著名的格斯勒酿酒厂运送啤酒。我不仅熟练了我开卡车的技术,而且比先前更熟悉了维也纳这座城市。我住在姑姑家里,开卡车养活自己。再也不想去碰什么文学,我把我拥有的一切都投入了进去。可它怎样对待我呢?把我扔进了深渊。我厌恶文学,憎恨所有的出版商、所有的出版社和所有的书籍。我觉得仿佛我写了《严寒》这本书是受骗上当倒了大霉。现在多好呀,我身穿皮夹克坐在驾驶室里,开着一辆斯太尔牌旧卡车颠簸在维也纳的街道上。现在看来几年前我学习开卡车多么有预见性啊,当时之所以学习开卡车是因为我想去非洲闯荡,报了名接受那儿的一份工作,前提是必须学会开卡车,这事后来没有成功,今天看,这样的结果是幸运的。但是,自然好景也不长,为格斯勒酿酒厂当卡车司机这项工作没过多久就结束了。我忽然憎恨起这份工作,很快便辞职不干了,整天躺在姑姑家小房间的床上用被蒙着头。她理解我的心境,有一天,她说邀我与她一起去山区待几个月。把大城市的残酷和伤害撇到一边,投身到大自然里去,这对我们俩都有好处。她的目的地是萨尔茨堡地区的圣·魏特,距离我住过多年的肺结核医院不远,也就八百米吧,位置极为理想,会让我们的身心得到很好的休息。一天清晨,我们从维也纳西站乘火车踏上去山区的旅程,我姑姑和我,她的免付膳宿费的旅伴。但是我得说,火车刚开出西站我就开始诅咒乡村,就在渴望返回维也纳了,不是吗?火车离维也纳越远,我就越难过,我想,背离维也纳和我姑姑一起到乡下去,我这是在犯错误,但是为时已晚,我无法纠正这个错误了。我对自己说,我不是农村人,我是城里人,但事情已无可挽回了。自然我在乡村找不到我的幸福,那里的人让我感到无聊,我讨厌他们,大自然也乏味得很,我讨厌它,我开始憎恨这里的人和自然。我成了一个意志消沉的、愁眉苦脸的人,耷拉着脑袋走在草地上和在村子里转悠,最后,无精打采的我连一口东西都不想吃了。我私下里与农村和山区生活的对立,将我推向灾难,我只不过是一个极其让人惋惜的滑稽可笑的人,与我那可怕的不幸生存结下了不解之缘。就在这种时刻传来了我获得自由汉莎城市不来梅文学奖的消息。不是这个奖本身把我从生存灾难和精神危机中解救出来,而是因为由此想到,用一万马克奖金拦截住我那摇摇欲坠的生活,让它来个彻底的转变,使它重新恢复正常。文学奖宣布了,奖金的数目也知道了,我现在能够而且必须用这笔钱做点最理智的事情。我一向希望有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房子,如果不能有像样的,至少有四面墙,在那里我自作主张做什么,不做什么,随心所欲,我可以把自己关在里边。我想,我要用这笔款子给自己弄来四面墙,于是我便立即与一位房地产商取得联系,他也马上到圣·魏特来与我会面,并向我推荐了几处房产。当然对我来说所有这些都太贵了,我将拿到的这笔奖金也只能是这些房产价格的很小一部分。但是为什么不接受呢?我想,我当即与他约好一月初在上奥地利见面,他的家在那里,那些地产也在那里,大部分都是年久的,多半已经败落的农家庄户院,他提供我选择的这些地产价格都在十万到二十万先令之间。但我奖金的数目只有七万。也许我可以找到七万上下适合于我的房产,可以把自己关在里边安静地生活,在我心目中,我想要购置的地产,不是一幢房子,而是墙,是可以把我关在里边的四面墙。我乘车到上奥地利,姑姑与我同行,我们去拜访那位房地产商。他给我的印象很好,我立刻就对他产生了好感,他做事精明干练,为人我觉得也无可挑剔。我们来到一个地方,地上是一米厚的积雪,我们踩着雪到了房地产商的家。他让我们坐到他的汽车里,指着一张纸条告诉我们要去看的那些房产的位置,想走什么路线去一个个地观看。纸条上记载了一共十一处或十二处待出售的农家院落。然后他把汽车门关上,我们便出发了。当天这个地区大雾弥漫,我们什么都瞧不见,甚至于去第一处房产的道路也看不清。他的眼前也是一片雾蒙蒙,但是他熟悉这条路,我们全依靠他了。我的姑姑像我一样感到新鲜,我们都不言语,我不知道她这会儿在想什么,她也不知道我这会儿在想什么,房地产商不知道我们俩在想什么,他也沉默不语,忽然车子停了下来,他说我们该下车了。的确我透过大雾看到一面高大的墙,是用大块石头砌的那种墙。房地产商为我们打开门轴已易位了的大木门,我们走进一个很大的院子。这里也是一米多厚的积雪,看样子房产主人是仓皇地逃离了这里,将一切都弃之不顾,我想,房主一定遭遇了巨大的不幸。房地产商说,这房子空置了一年了,边说边带我们往里边走。在我们走进的每一个房间里他总是说“这是一个很漂亮的房间”,还总是把“比例特别合适”这句话挂在嘴边,他随时都会因某处地板腐烂而把脚陷进去,不得不通过灵巧的蹦跳从烂泥坑拔出脚来,房地产商在前面走,我跟在他后边,我的后边是我姑姑。我们一个个房间看着,好像走在长条木板上,越过满是污水的臭烘烘的蛤蟆坑,有时我转头去看我姑姑,她动作很灵巧,比我和房地产商都强。要看的房间有十一个或十二个,所有这些房间都异常败落,空气中弥漫着已经干瘪了的死耗子散发出来的气味,这样的动物尸体随处可见,我想如果没有几千,至少也有数百只。所有的地板都腐朽破烂了,大部分窗框经过风吹雨打已残缺不全。下头的厨房里,有一个很大的锈迹斑斑的搪瓷灶台,肮脏得已经面目皆非了。自来水龙头没有拧紧,水哗哗地流着,地板上下到处积着水,房地产商说,房主是一年前走的,忘记了关水龙头,他走过去把龙头关上。他本人也没有来看过这房子,他说,我们是他第一批带到这里看房子的人,他说他非常喜欢这房间的比例,如此合适的比例实在罕见。我的姑姑一直用手帕堵着鼻子和嘴,这房子里的气味让人难以忍受,不仅是东西和畜类腐烂的味道,在牲口圈里到处都是房子主人没有清理运走的大堆牲畜粪便。房地产商一再说这些房间的比例多么不同寻常,他越是这样说,越让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最后不再是他说了,而是我在说这句话,而且说起来没完。我简直像着了魔一样,越来越频繁地说这些房间的比例多么不同寻常,最终我深信不疑,整个这处地产房间的比例确实异乎寻常的好。我立刻就迷上了这处地产。我们又来到大门前,准备去参观另一处地产,房地产商希望马上离开这里,因为还有十处或者十二处房产要看,这时我说,我对所有其他要看的地产不感兴趣了,我已经找到了我所需要的,就是这一处,因为房间的比例特别合适,简直可以说不能再这么理想了,我愿意立刻就与房地产商签订购买合同。从开始参观到我做出决定只过了不到一刻钟的时间。我姑姑大吃一惊,她说,别做蠢事,她觉得这些大墙太可怕了,毫无疑问,当我们又坐在汽车里准备返回房地产商家签订合同时,她坐在我身后总是说,这是件大事,要我深思熟虑地考虑一下,她说,让这事情过个夜,第二天再说。但我决心已定。我找到了我要的四面墙。我向房地产商建议,首付七万先令,一月末支付,就是说在不来梅颁奖之后,余下的款子在一年内付清。无论如何剩下的也有十五万多先令。虽然我还不知道从哪里弄到这笔钱,但我并不担心。房地产商已经在起草合同了,我姑姑还一再劝我再考虑一番,睡一晚上第二天再说。我喜欢这位房地产商起草合同的样子,喜欢听他说的话和他周围的一切。我本人的样子仿佛我不在乎钱,这一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时他妻子在厨房忙活着做可口的炒鸡蛋。我第一次看见了纳塔尔,我的四面墙所在的地方叫这个名称,应该说甚至于没有看得很清楚,上面已说过,那天大雾弥漫,更不用说我根本就没有去看这处房产周围,也就是说周遭的景观如何,只有估计和猜想,总而言之,到那里只待了半个钟头,我就草签了所谓购买意向书。我们吃了炒鸡蛋,又闲聊了一会儿便离开了房地产商家。他把我们送到火车站,我们乘车返回山区。旅途中我姑姑因心里有种可怕的预感一言不发,我得承认,这会儿我的头脑里也产生了恐惧,我一下子感到发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放任自己干了些什么,当然是做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度过了一些不眠之夜,自然仍然弄不明白,我到底干了些什么,签了什么合同,让我从哪里弄来余下的十五万先令。但是不来梅文学奖一定会拿到的,首付的七万先令也就不成问题了,我想,没有理由着急上火。我姑姑仍然对这件事情不做任何评论。与她在一起办事,我还是第一次没有听从她的劝告。我乘车去不来梅,它对我来说是座陌生的城市。我熟悉汉堡,我爱汉堡这座城市直至今天,我从一开始就讨厌不来梅,这是一座充满小资产阶级习气的、索然寡味的城市。给我订的房间就在火车站对面一座新建的宾馆里,我记不得它的名称了。为了不去观看这座城市,我躲进给我安排的房间,等待着明天上午的颁奖。颁奖典礼将在不来梅古老的市政厅大楼里举行,实际上的确在那里举行了。我最大的难题是要我在颁奖典礼上发言,虽然说几周前我就知道要我在典礼上讲话,现在我人已经到了不来梅,却总是还不知道要说什么,到了夜里仍然如此,第二天早晨心里依然一点儿谱也没有。现在可到了关键时刻了。吃早点时,我忽然想到与不来梅有关的不来梅乐师,脑子里出现了一个方案,我的发言可以把不来梅乐师作为中心。我喝完茶,迅即返回房间,坐到床上起草讲话稿。我的草稿写了两个、三个都不满意。这时我明白了,我的方案很糟糕,我得改变思路。但时间紧迫。这期间已经有电话打过来,问我讲话需要多少时间,我在电话里说,很简短,虽然我讲什么还八字没一撇呢。离颁奖典礼开始只还有半个小时了,我又坐到床上,写下了“随着寒冷清晰度在增强”这句话,我想,现在我有主意了,知道该在颁奖会上讲些什么了。以这句话为中心,很快又写了些句子,无论如何在十分或者二十分钟里我还是写满了半张纸。当有人来宾馆接我去市政厅时,讲话稿刚好完成。“随着寒冷清晰度在增强”,我边想边跟随着几位先生往市政厅走,感觉仿佛他们是带我去法庭受审。他们把我,他们的犯人,夹在中间,带着我从宾馆向市政厅走去。市政厅里已经人头攒动,主要是学校的学生。不来梅这座市政厅也是一座著名的建筑,这座建筑也如同一切其他著名的市政厅建筑一样使我感到压抑。在这里也是勋章耀眼,市长礼服上的绶带闪亮。我被堂而皇之地引到礼堂第一排,在市长身旁就座。一位男士走上讲台谈起了我。此人专程从法兰克福赶来,为的就是对我第一本小说做半个小时的演讲。据我记忆,他当时讲得很透彻,讲了许多称赞的话,但老实说,我根本听不懂他讲的是什么。我坐在那里,眼前呈现的只是我在纳塔尔的四面墙,想着如何能弄到购买它的钱款。我想,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拖延,直到筹措到足够的钱。当致颂词者结束演讲时,礼堂里响起了掌声,看上去主要是学生们在热情洋溢地鼓掌。这时主持人示意我上台讲话。在台上我接受了获奖证书,我今天记不得它的样子了,我没有保留它,所有其他的获奖证书我一概都不保留,随着岁月的流逝它们也都散失了。现在我已经把证书和奖金拿到手了,我走向讲桌去读我的讲稿,讲在寒冷中增强的清晰度。正当听众开始弄清我要讲的是什么时,讲话已经结束了。我想这是不来梅文学奖获得者最简短的讲话,在典礼结束后我的判断得到了证实。我站在讲台上,为让照相师拍照,再次与市长握手。在外边走道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看见了我的朋友,那位三天之内就决定接受小说《严寒》的编辑,当他确信就剩下我们俩时,颇为私密地对我说:喂,借我五千马克,我急需这笔钱。好,当然可以,我说,并不清楚这样做会有怎样的后果,我说,待下午两点钟不来梅银行上班后,我立即和他去那里兑现支票,给他五千马克。我想,他经常不断地借钱给我,不久前他还帮我度过了一场严重的债务危机!典礼后还有一顿午餐,在不来梅一家颇为高雅的餐馆,我两点钟准时离开了这家餐馆,与我的朋友一道去银行兑现我因《严寒》一书获得的支票。我想到我还要从不来梅到吉森,在那里的基督教文化教育中心朗读我的作品,报酬为两千马克。这样我总算又有七千马克了。想到这里就又觉得很幸运了。次日,在不来梅我还看望了另一位朋友,他住在一间阁楼里,我与他品着香茶,放眼朝铅灰色的威悉河望着,我们谈戏剧谈得很投机,主要的话题是关于安托南·阿尔托(2)。与他告别后我立即返回维也纳。自然,我已迫不及待想搬进新购置的房产,我那位于纳塔尔的四面墙。我如何主持装修它,自己动手改造它、扩建它,在某种程度上说,活儿干得还算不错,最终收拾得有模有样,可以安适地在里边生活,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在资金上满足它的需要等,这是后话就不在这里讲了。总而言之,不来梅文学奖对购置我的家园是很大的推动,没有它我的一切很可能就另是一样了,就是另一种方向和另一种发展了。不管怎么说,我后来又去了一次不来梅,也是与不来梅文学奖有关。对于这第二次去不来梅的经历我不想闭口不谈。我这次去是作为不来梅文学奖的评委会成员,评选下一次获奖者,我的主意已定,要去不来梅投卡内蒂(3)一票,据我所知,迄今为止他还没有获得过任何一种文学奖。为什么一定是他,理由并不重要,我当时就是觉得只有他才合适,其他人都是可笑的。正如我的想像,评委开会的地方设在不来梅一家餐厅的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张长条桌子,坐着许多拥有表决权的先生,其中有著名的州政府委员哈姆森,我和他很有共同语言。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大家都提出了各自的候选人,都不是卡内蒂,轮到我了,我说出了卡内蒂这个名字。我主张把这个奖颁给卡内蒂,因为他的作品《迷惘》,是这位青年作家才华横溢的体现,一年前刚好再版一次。我多次提到卡内蒂这个名字,每次坐在长条桌旁的人都愁苦地拉长了脸。许多人根本就不知卡内蒂何许人也,但是少数知道卡内蒂的人中,有一位在我又提及卡内蒂的名字后,突然说:“但他可是个犹太人呐。”然后只听见一片含糊不清的咕哝声,卡内蒂就没有人再理会了。直到今天我耳朵里仍然响着这句“但他可是个犹太人呐”,我无法说出桌旁的哪一位说了这句话。可是至今我仍经常听见这句话,从一个阴森的角落发出来,尽管我并不知道是谁说的。这句话就那么几个字,就将我把文学奖颁给卡内蒂的提议扼杀在萌芽中,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争论了。我当时立即选定了一种态度,即绝对不参加接下来的讨论,三缄其口地坐在桌旁。时间又过去了不少,虽然这期间又有不少可怕的名字被提出来,对其我只能用“胡诌八扯”和“过于业余”来评价,最终还是没有把获奖者选定。诸位先生们已经在看表了,从旋转门飘过来烤肉的味道。在座的必须作出决定了。使我颇为惊讶的是,有人这时突然,我不知道是在座的哪一位,从桌上堆的一些书中,我觉得是非常盲目地,抽出一本希尔德斯海姆的书,边站立起来准备去吃午餐,边以极其幼稚的语调说:“让我们就选希尔德斯海姆吧,让我们就选希尔德斯海姆吧。”而希尔德斯海姆这个名字,正是几个小时争论中根本就没有提到过的那一个。现在突然有人提出这个名字,大家在座位上立刻活动起来,感到如释重负的轻松,一致表示同意,于是几分钟内希尔德斯海姆就成为新的不来梅奖获得者了。谁是希尔德斯海姆,他们大家很可能一无所知。这时也已经把结果通知了媒体,希尔德斯海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讨论成为新当选的获奖者。先生们立即起立走进了餐厅。犹太人希尔德斯海姆获得了不来梅文学奖。对于我来说,这的确是这次评奖的噱头。我不能隐瞒不说。
(1) Carl Zuckmayer(1896—1977),德国作家、戏剧家。代表作为话剧《克彭尼克上尉》。
(2) Antonin Artaud(1896—1948),法国戏剧家、诗人、超现实主义理论家。
(3) Elias Canetti(1905—1994),德语小说家,代表作为《迷惘》。曾获毕希纳奖(1972)、诺贝尔文学奖(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