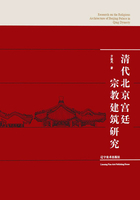
第一节
明代之前的宫廷宗教建筑
一、帝王与宗教的发展
宗教的发展需要一定的外部环境,从心理上分析,人只要有未知的领域,就很容易产生神秘思想,进而为宗教的发展打下基础。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科学如此昌明的今天,宗教仍然是许多人的信仰,甚至一些科学家也抱有宗教观念[1]的原因。宗教的起源可以说明人类对未知的自然的畏惧和崇拜。
帝王与宗教的关系不外乎以下几条线索。其一是同国家政治的关系,在这一线索中作谶语、假天意谋取权利者有之,收人心、崇信仰治理天下者有之,甚而借教生威以御外敌者也有之;与上述情况对应的是一旦宗教在这些方面产生了反作用,那么限制宗教甚至灭教者同样有之。其二是帝王个人的需求,长生成仙、满足私欲无不同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宗法性传统宗教为帝王所重视是极其自然和不言而喻的事实,因为帝王本身就扮演了大祭司的角色,并垄断了最高级别的祭祀权,宗教本身就是其统治的基础。同时,帝王虽然自称“天子”,有通神的能力,但实际上也有许多作为人所不可避免的烦恼和疑惑,甚至有比常人更为强烈的欲望。中国古代的帝王普遍追求长生不老,尽管他们垄断了对天地山川的祭祀权,但显然这样的宗教活动有其局限性,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他们也寄希望于流传民间的巫术方技,秦始皇与徐福、汉武帝与李少君、栾大、公孙卿等莫不如此,这一现象的存在也就为宗教的传播创造了条件。首先,得到了帝王的信任,无疑就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其次,也使进一步的传教、吸收信徒有了很好的例证。因此,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可谓一针见血。而从《高僧传》等一些文献中也不难看出,传教活动首先是通过显示神迹来获得认可和信任的。
帝王同宗教的结合是以他们之间有所契合为现实基础的,但当宗教的发展达到相当程度以至与国争利的地步时,帝王也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措施断然灭法,中国佛教史上有著名的三武灭佛为明证。这两个方面形成的一对矛盾构成了中国封建帝王同宗教相互关系的主旋律,这在清代的宫廷宗教生活中也有反映,将在后文论及。同时也要看到,宗教活动在许多情形下也是一种奢侈品,比如外丹一道和寻访仙迹等,所费昂贵,非权贵和帝王所不能。
二、早期宫廷中的宗教建筑
从上面的概述中可以知道,中国的三大宗教基本形成于汉末,因此汉以前的宗教都处于宗教理论不完备的状态。三代至秦都是宗法性宗教占据主导地位,宗庙、祭台等祭祀建筑早已有之;道教保留着其神仙传说和一些宗教实践,而佛教还没有传入。从文献记载看,秦汉之际的宫廷中有祠祀类的建筑,有观天象察人事的灵台,也有望仙楼、望仙台之类的体现神仙思想的建筑类型。
秦历二世而亡,宫廷的建设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但秦代的兰池宫开创了宫苑中模仿海上神山的传统。汉代的情况就大不相同,有大规模的议礼活动,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礼崩乐坏”的局面,封建宗法制度开始成熟,祠祀建筑的类型也丰富起来,原庙之制的源头即在汉代。汉代别宫御苑的建设规模惊人,数量众多,其中受神仙思想影响的建筑引人注目,《郊祀志》中屡见记载。甘泉宫为秦故旧,汉初被废,它的修复和扩建即始于汉武帝听信了方士少翁的进言:“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2]于是宫中“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3]……(元封二年夏)“作甘泉通天台、长安飞廉馆。”[4]……“公孙卿曰:‘仙人可见,上往常遽,以故不见。今陛下可为馆如缑氏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且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则作飞廉、桂馆,甘泉则作益寿、延寿馆,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神仙之属。于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广诸宫室。”[5]汉武帝的殷切之情诚可感人,而方士的言辞也的确巧妙,引得帝王亦步亦趋。“其后又作柏梁、铜柱、承天露仙人掌之属矣。”仙人承露自此开始成为皇家园林中的经典,后世多有模仿,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饮之。”[6]乾隆帝曾出言讥讽为承露荷叶足矣,但这已是一千多年后的认识,而且北海、圆明园中也都有仙人承露之设,不过此时确如乾隆帝所言,装点的意味是主要的。
后来柏梁殿遭火灾被毁,根据公孙卿的厌胜之术,以大压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商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立神明台、井干楼,高五十丈,辇道相属焉。”[7]一池三山的模式已经成型,其他的建筑也都同同一主题配套,这点同后世的园林有所区别,关键在于当时园林的一个主要功能不是游观而是求仙,因此主题立意影响到设计经营,此时不难判断方士在建筑经营上有重要的作用,以建筑附会神仙传说,并且神仙建筑应体现出一些迥异于常规的形态,高是一个主要特征。
汉宣帝即位后继续了祠祀方面的活动,注重祥瑞,据记载白虎的皮、牙、爪者即立祠,“又以方士言,为随侯、剑宝、玉宝璧、周康宝鼎立四祠于未央宫中。……又立岁星、辰星、太白、荧惑、南斗祠于长安城旁。”[8]宫廷中的宗教建筑进一步丰富,宗教功能也细化、深入地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普遍信仰。王莽篡位后也大兴神仙之事,“以方士苏乐言,起八风台于宫中。台成万金,作乐其上,顺风作液汤。又种五梁禾于殿中,各顺色置其方面,先鬻鹤髓、毒冒、犀玉二十余物渍种,计粟斛成一金”。[9]王莽后来沉溺于神仙故事之中,祭祀的内容也十分庞杂,祭祀场所达一千七百处,供品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最后“以鸡当鹜雁,犬当麋鹿”[10],显然是祭祀太滥,供品不敷应用了,宗教行为的严肃性受到影响,走向极端了,王莽后期多次自以为成仙,结合他的行为观察,确已有迷乱的迹象。
汉代还有众多的行宫,有的是后世尊崇先帝,有的是汉武帝遗留下来的专为祭祀祈祷成仙所用,“集灵宫、集仙宫、存仙殿、存神殿、望仙台、望仙观俱在华阴县界,皆武帝宫观名也。《华山记》及《三辅旧事》云:‘昔有《太元真人茅盈内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蒙,于华山乘云驾龙,白日升天’。……武帝即其地造宫殿,岁时祈祷焉。”[11]总之,汉代的神仙思想在历史中占据了一个显著的位置,留下了大量的印迹。汉末社会动乱至魏晋南北朝,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局面之后的历史最长的分裂时期,此时的帝王同宗教之间的关系密切,但宫廷宗教建筑的状况目前尚难核实。
隋历两代而亡,统治时间非常短,但开国之初正是大兴土木之时。新建大兴城和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等,都是十分庞大的工程。所谓百废待兴,宫苑的建设肯定是首要的,但宫苑之中的宗教建筑却非必需,很可能修之不及。隋文帝生长于尼庵,对佛教有特殊的感情,在全国广建寺庙、兴修佛塔,其于佛教的发展可谓功莫大焉,他的宗教活动屡见之于文字,但史籍之中却无宫中有宗教建筑的记载。完全可能因为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公共性的宗教建筑的建设上,而无暇顾及宫廷之中个人化的宗教生活。这本身也是一种宗教态度。唐代继承了隋的都城和其中的建筑,改称长安城,当然也有新的兴建,如大明宫的建设等,但一方面工程的摊子铺得要较隋小(实际上大明宫是唐代唯一创建的正式宫廷[12]),另一方面,唐王朝延续的时间较长,经济和时间上都具备了宫廷建筑的建设向更丰富的方向发展的条件,则内苑之中的宗教建筑才有可能得到兴建。
三、唐代的宫廷宗教建筑
唐朝的皇室奉老子为祖先,崇信道教,宫廷之中也不乏其例,主要的有太清宫(又名太上玄元皇帝宫)、三清殿、望仙台等道教建筑。文献之中早就发现了相关记载,更为可贵的是近年来进行的大明宫遗址的考古发掘,不仅证实了文献中的情况,而且提供了文献中所没有介绍的情况,使我们对于当时的宗教建筑有更为深入的了解。除了道教建筑之外,宫中也有佛教建筑,甚而直接冠以某寺之名,体现了唐王朝佛道并重的宗教政策在实际宫廷生活中的情况。
唐王朝崇奉道教,也有民族性的考虑,因为唐皇室实际上是胡人,并非汉族,通过奉老子为祖先这一行为模糊了这一问题,夷夏之防得以突破,道教作为汉族的本生宗教在文化上有很强的生命力,在政治上也多有所用。唐代宫殿在建筑的命名上也多取道教用字,玄元、太极、太清、三清、通天、九仙、望仙等不一而足,究其用途倒未必真是宗教建筑,清朝宫殿的命名则多取自儒家经典,不同的文化趣向和政治理想在这方面也可窥其一斑。
在唐代政治生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有太清宫,在长安大宁坊,位于长安城东北隅,离大内宫苑较近(老子故乡也有太清宫,洛阳太微宫在昭宗迁洛后曾改名太清宫,代替原太清宫的位置)。《新唐书》卷二十一载,龙首渠流于宫前,宫内有殿有廷,廷中置乐悬,殿上列有老子及时君、时相雕像。宰相兼任宫使,管理宫事,也住有道士。《旧唐书》记玄宗、代宗、德宗、宪宗、穆宗诸帝在祭祀郊庙之前,必先朝献太清宫。《资治通鉴》等书记载,国有大事亦必上告太清宫。就连黄巢即位,也先斋于太清宫[13]。太清宫之名起于天宝二年,唐玄宗早年由于政治上的考虑崇奉道教,不断给老子加封号,提升玄元庙为宫,祭献老子的礼仪与祭献太庙同。道教具有了类似国家宗教的地位。“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14]而《霓裳羽衣曲》等也是在玄宗的授意下创作,为太清宫祭献老子时演奏。此时道教艺术得到大发展。
启圣宫为玄宗故居,所谓潜邸是也,开元十一年,改为飞龙宫,后又更名为启圣宫,潜邸而改宫观这一做法在清代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比如福佑寺、雍和宫等,不能确定最早的源头是否就在此地。《册府元龟》中记,曾于宫中琢玉造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及玄宗像,可以肯定此处确为皇家道教宫观。与启圣宫可以对照的是,也有改道观为行宫的例子,奉天宫原为嵩阳观,在嵩山之南,高宗永淳元年改为奉天宫,作为行宫,曾在此召见大臣,商讨国事。永淳二年,高宗崩,据遗诏复改为观。同样的,唐僖宗在中和年间改元中观为青羊宫,改宫后仍行道教活动。这些宫都是大内之外的别宫,内苑之中还有不少殿堂也是为举行宗教活动而兴建的。
太极宫是唐代正宫,见诸文字的有两处佛教建筑。一是佛堂,在太极宫东北隅;二是佛光寺,在两仪殿东北,神龙殿西南。《文献通考》提到,东都洛阳的宫中也有佛光寺。但这些建筑的始建年代无考证,唐长安太极宫应是因循隋代故旧,那么佛堂与佛光寺是否也是隋代就有呢?目前尚无法解答。这些建筑的规模和具体形制也是无从考证,但既见之于《长安宫城图》,那么应当是独立的建筑,甚至是规模可观的建筑。
大明宫是唐代初年兴建的,其紫宸殿东有望仙台,台东远处近东城折角处有昭德寺,太液池以北宗教建筑渐多,东有大角观,玄元皇帝庙(供奉老子);西有三清殿,东北角有护国天王寺,其寺南有墙与宫廷相隔(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有所记述,他曾居于该寺)。望仙台是武宗时修建,最近于紫宸殿。武宗是相当虔诚的道教徒,渴望服药成仙,在位仅五年,但做了一件影响历史的大事就是“会昌灭法”,望仙台的营造似乎表明了他的宗教立场和对神仙的向往。沿用、保留固有的宗教建筑往往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兴建建筑必定有其原因,尤其武宗时已是唐中后期了,建设活动肯定不是出于生活的需要或迫切的功能要求,而反映的是帝王个人的宗教思想和热诚。武宗在道士们的怂恿下灭法,却很快死于丹药,继位的唐宣宗马上宣布恢复佛教,但佛教的元气已伤。宫中还有咸泰殿,具体位置不详,有记载文宗时在此与太后及诸公主筵宴作乐,正月望夜观灯,也应是内宫之中的建筑。到唐懿宗时,由于懿宗好佛太过,在殿内筑坛,为内寺尼受戒。这种做法,几近儿戏,不过从中可知宫中别有尼庵,《旧唐书》记肃宗韦妃为太子妃时,肃宗为自保同其离婚,无奈削发为尼,于宫中佛庵度日[15]。

图2 唐大明宫遗址实测图(引自《唐代长安宫廷史话》)
从现有资料看,大明宫中规模最大的宗教建筑是三清殿,位于大明宫城的西北隅。三清殿据文献记载有两处,一在大明宫,一在太极宫。《册府元龟》卷五十四记,宝历二年曾命道士于三清殿修道场,而唐自肃宗后诸帝都定居大明宫,道场往往近便,所以修道场的三清殿当在大明宫。考古发掘证实了这一点,挖出了一高台建筑的遗址,规模宏大,台高出当时的地面有14米之多,南北长73米,东西宽47米,有收分,顶部面积约3000平方米,具体建筑形制已不可考,但其为宫中唯一在平地上起如此规模高台的建筑。有云“仙人好楼居”,起高台筑殿堂是符合道教的审美要求的。高台东侧还有一组庭院式建筑的遗址,为三清殿的附属部分,面积亦在5000平方米以上,而如此规模也可想见唐代帝王对道教的崇奉程度。
三清殿台基为夯土,周围包砌砖壁,砖壁厚达1米多,且磨砖对缝,工艺考究。另外从出土的大量砖瓦、石栏构件和琉璃瓦等来看,当时的三清殿必定金碧辉煌、美轮美奂。宗教建筑的装饰是冠于各类建筑之首的,朝寝空间的建筑或壮丽重威或茅茨土阶,囿于儒家教条,庄重素朴,虽等级较高,但装饰却相当节制,只有在宗教建筑上可以无所顾忌地进行铺张,因为这些都不是为了帝王个人,而是为神,并且也通过铺张最为直观地表达了虔诚。此处出土的琉璃瓦最多,很可能三清殿就是宫中最为华丽的建筑。
四、宋元之际的概况
唐之后,中国再次进入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这一时间不算太久,分裂之后,宋太祖完成统一,但国势积弱,至南宋偏安,辽、金占据北方。宋辽金时期,宗教的发展逐渐呈现颓势,但仍然有自己的特点,帝王同宗教的关系依然密切。
宋朝宫室不以壮美见称,同国力有关,宫廷之中有无宗教建筑,难以稽考。辽的宫廷之中是否有宗教建筑,目前也不清楚。金灭辽后,在其宫廷之中已有史书所记载的宗教建筑。《金史》记述了宫廷中拜日、拜天的情形:“天会四年正月,始朝日于乾元殿……天眷二年,定朔望朝日仪。”帝南向拜。大定十五年,有司上言:宜遵古制东向拜。十八年,帝“拜日于仁政殿,始行东向之礼。”[16]又拜天礼如下:“金因辽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礼。重五于鞠场,中元于内殿,重九于都城外。其制刳木为盘,如舟状,赤为质,画云鹤文,为架高五六尺,置盘其上,荐食物其中,聚宗族拜之。若至尊则于常武殿筑台为拜天所。”[17]金代统治者是满族的前身,是同一种族,从这段文字可知,这种方式同后来满族萨满祭天基本相同,属于萨满世界,并且也是通过拜天来维系整个宗族。不过这些建筑并非专门为拜天而建,显然其时典制化的程度不高。金代统治者对佛教也是十分崇信,屡有记载“御宣华门观迎佛”[18]
之语,想必宫中应有供佛之所。
元结束了南北对峙的局面,首次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了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统一的帝国,宗教方面则有帝师制度,成为一大特色,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元代帝王崇佛,入关之前已然成风,元世祖忽必烈“万机之暇,自持数珠,课诵、施食”[19],以此判断宫廷之中的宗教建筑当有无疑,《元史·释老传》也有内廷做佛事的耗费记载[20]。宫中建有五福太乙畤[21]、祭紫微星的云仙台[22]等宗教建筑,位于后宫的徽音亭中有玛哈噶拉佛像[23]。后宫之中僧尼来做佛事,大殿之中设佛像,都有明文[24]。寝殿之中也是“中位佛像,旁设御榻”,又香殿内藏“西番波若经”[25],可知生活空间中有宗教内容非只一处,但宫中含宗法性宗教内容的建筑似乎未见记载,可能这方面确实没有引起元代帝王的足够重视[26]。
元代御苑之中的宗教活动更见频繁,宗教建筑也有不少。方壶殿后有吕公洞[27],万寿山前立法轮竿[28],不一而足。禅师入觐,于后宫大殿说法,不同的建筑中都举办过佛事活动,帝师为帝后受戒等[29],正史之中有如此之多的宗教活动记载,在历朝之中也是罕见。万寿山更有规模宏大的佛事,用人至千数,游行线路不限于一地,时人称之“游皇城”。元顺帝荒于游宴,以宫女扮天魔舞,“以宦者察罕岱布哈管领,遇宫中赞佛,则按舞奏乐。宫官受秘密戒者得入,余不得预”。而天魔舞与佛事游行并举,盛况自是空前,有诗为证:
西天法曲曼声长,
璎珞垂衣称艳妆。
大宴殿中歌舞上,
华严海会庆君王。
西方舞女最娉婷,
玉手昙花满把青。
舞唱天魔供奉曲,
君王常在月宫听。
炉香夹道涌祥风,
梵辇游城女乐从,
望拜彩楼呼万岁,
柘黄袍在半天中。[30]
元代崇佛的另一大特色是帝后影堂设于佛寺之中,可知元代统治者始终没有彻底汉化,宗法性宗教对他们的影响远未达到使他们全心敬奉的地步,这也是元朝迅速败亡的原因之一[31]。全真教同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关系非同寻常,但至元辩论失败,其势大挫,至元之后已不见宠。
从某些方面看,元朝统治者同清朝统治者有许多相像之处,他们都是少数民族政权,原本信奉原始巫教——萨满教,在北方地区纵横驰骋之时,接触到了藏传佛教(喇嘛教),然后深受其影响,并多有崇奉。只是元朝帝王对宗教的热诚过高,危及了统治,这也成为清朝统治者的前车之鉴、后世之师,清朝统治者制定了较为稳健的宗教政策,有所抑,有所扬。而萨满教同中国传统的宗法性宗教之间也有颇多类似之处,其源相近,由彼及此,非为难也。萨满教缺少的是宗教理论,因此无论从统治的角度还是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接受中原文化都是很自然的选择,利用儒家经学现成的理论体系来维护宗法性家族制度或以血缘维系的氏族制度都是可以行之有效的。
[1] 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在2001年5月参加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活动期间,于理学院前广场发表演讲《美与物理学》,其中提到物理学家面对宇宙奥秘时的心情是“一种庄严感,一种神圣感,一种初窥宇宙奥秘的畏惧感”。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2001年第8期上第18-19页有缩写的署名文章。
[2]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中华书局,北京,1982年第2版,第1388页。
[3] 《汉书》卷二十五上,《郊祀志第五上》,中华书局,北京,1962年,第1219页。
[4]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中华书局,北京,1962年,第193页。
[5] 《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第五下》,中华书局,北京,1962年,第1241-1242页。
[6] [明]顾炎武著,《历代宅京记》卷三,中华书局,1984年,第46-47页。
[7] 《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第五下》,中华书局,北京,1962年,第1244-1245页。
[8] 《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第五下》,中华书局,北京,1962年,第1249-1250页。
[9] 《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第五下》,中华书局,北京,1962年,第127页。
[10] 《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第五下》,中华书局,北京,1962年,第1270页。
[11] 《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陈直校证,1980年。
[12] 郭湖生著,《唐大明宫建筑形制初探》,刘先觉主编、张十庆副主编,《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文集》(1927—1997),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年。
[13] “巢斋太清宫,卜日舍含元殿,僭即位,号大齐。”引自《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下,《列传第一百五十下》,《逆臣传下·黄巢传》,第6458页。
[14] 《旧唐书·礼仪志四》,页681。《二十五史》,北京电子出版物出版中心,2000年,第681页。
[15] “妃兄坚为李林甫构死,太子惧,请与妃绝,毁服幽禁中。”引自《新唐书》卷七十七,《列传第二·后妃下·张皇后传》,中华书局,北京,1975年,第3498页。
[16] 《金史》卷二十九,《志第十·礼二·朝日·夕月仪条》,中华书局,北京,1975年,第722页。
[17] [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第一册,卷二十九,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16页。此前尚有拜天射柳之说,狩猎之习仍存于礼中,而拜天之常武殿即为宫中习射之所。《金图经》一书言,“金本无宗庙,不修祭祀。自平辽后,所用执政大臣多汉人,往往说天子之孝在尊祖,尊祖在建宗庙,金主方开悟。遂筑室于内之东南隅,庙貌虽具,制极简略。迨亮徙燕,乃筑巨阙于南城之南,千步廊之东,曰太庙。标名曰衍庆之宫。”可知金人汉化在掌握政权之后,而大内之中曾有过祭祖建筑。满族在未入关之前也无宗庙。
[18] 《金史》卷五,《本纪第五·海陵纪》卷十一,海陵、章宗都有此举。本纪中载正隆元年、承安四年等此条,宣华门为一重宫门。中华书局,北京,1975年,分别第106页,第173页。
[19] 语出《佛祖统记》卷四十八,转引自牟钟鉴、张践著,《中国宗教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701页。
[20] “延祐四年,宣徽使会每岁内廷佛事所供,其费以斤数者,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油七万九千、酥二万一千八百七十、蜜二万七千三百。……僧徒贪利无已,营结近侍,欺昧奏请,布施莽斋,所需非一,岁费千万……”《元史》卷二百二,《列传八十九·释老传·八思巴传附必兰纳识里传》,中华书局,北京,1976年,第4523页。
[21] “五福太乙有坛畤,以道流主之”。《元史》卷七十二,《志第二十三·祭祀志一·序》,中华书局,北京,1976年,第1780页。
[22] 至元三十一年五月,“太白犯舆鬼。壬子,始开醮祠于寿宁宫。祭太阳、太岁、火、土等星于司天台。……庚申,祭紫微星于云仙台。”《元史》卷十八,《本纪第十八·成宗纪一》,中华书局,北京,1976年,第383页。
[23] 至治三年十二月,“塑马哈吃剌佛像于延春阁之徽清亭。”《元史》卷二十九,《本纪第二十九·泰定帝纪一》,中华书局,北京,1976年,第642页。
[24] 《元史》卷一百七十八,《列传第六十五·王结传》,第4145页:元统元年,王结召拜翰林学士,“中宫命僧尼于慈福殿作佛事,已而殿灾,结言僧尼亵渎,当坐罪。”延祐七年十二月,“庚戌,铸铜为佛像,置玉德殿。”《元史》卷二十七,《本纪第二十七·英宗纪一》,中华书局,北京,1976年,第608页。
[25] [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三十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51页。《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一:“嘉禧殿又曰西暖殿,在寝殿西,制度如寿昌。中位佛像,傍设御榻”。第453页,“宝集寺金书西番波若经成,置大内香殿”。殿在宫垣西北隅。
[26] 元代统治者也有兴学之举,但对孔子未加尊崇,官学中行礼未立孔子牌位。
[27] “方壶殿右为吕公洞,洞上数十步为金露殿”语出《大都宫殿考》,转引自[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三十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72页。
[28] 二十一年二月,“立法轮竿于大内万寿山,高百尺”。《元史》卷十三,《本纪第十三·世祖纪十》,中华书局,北京,1976年,第265页。
[29] [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三十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77-482页。
[30] “张昱辇下曲”,《张光弼诗集》,转引自[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三十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78-479页。
[31] 《元史》卷七十五,《志第二十六·祭祀志四·神御殿条》,第1875页载:“世祖帝后大圣寿万安寺,裕宗帝后亦在焉;顺宗帝后大普庆寺,仁宗帝后亦在焉;成宗帝后大天寿万宁寺;武宗及二后大崇恩福源寺,为东西二殿;明宗帝后大天源延圣寺;英圣帝后大永福寺;也可皇后大护国仁王寺。”中华书局,北京,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