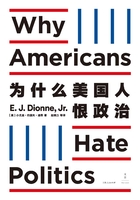
第2章 德性的优点:新保守主义的反叛【55】
一
当新左派在自由主义的左侧造反时,一群和新左派持同样的怀疑论的知识分子在自由主义的右侧开始发起叛乱。新保守主义的反叛更为成功,他们持续地对美国的政治造成强有力的冲击。
新保守派们最初反对新保守派的标签。他们甚至没有发明这个词,已故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迈克尔·哈林顿发明了这个词。哈林顿想要澄清,这群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人,事实上属于一个新近变得保守的前自由主义者的运动。[1]这个标签最后还是贴牢了,因为它是如此恰当——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新保守主义者开始接受他们毕竟是保守主义者的事实。无论如何,到了1980年代,术语保守主义就不是一种侮辱了。通常被描述为这场运动“教父”的欧文·克里斯托尔,是最早接受这个标签的人之一。他把他自己描述为“唯一还在世的、自认的新保守主义者,逍遥法外和蹲大狱的都算上”。克里斯托尔承认,贴政治标签更像是左派而不是保守派干的事情,但是,他说,【56】保守主义者们有时候不得不忍受对手造的孽。克里斯托尔宣称:“明智的做法是接受你的标签,承认是自己的,带着它到处跑。”[2]他和他的同志就是这么做的。
新保守主义受到如此多的关注,是因为它是美国政治重组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新保守主义代表着脱离举足轻重、能说会道的自由主义团体,走到另一边。正好因为他们从内部懂得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在解释自由主义信条的错误上,通常比老的保守主义更加有效。在很多议题上,新保守主义属于“右派”或部分属于“右派”;当他们犯错时,他们的错误通常也很有趣。
新保守主义的第一个成就,是在知识界、艺术界、新闻界这些保守主义长期被质疑的领域,使得从右派角度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变得可以接受。对于这些精英的经典观点,莱昂内尔·特里林在1954年做了权威表述。特里林写道:“在当今美国,自由主义不仅仅是占支配地位的,它甚至是唯一的知识传统。因为,很清楚,今天没有任何保守的或者反动的思想在传播流行。”[3]特里林承认,确实不乏保守主义的冲动,但是这种冲动很少表达为“理念,而是表达为行动,或者是竭力模仿理念的易怒的精神姿态”。我们将看到,特里林的这种观点对于在世纪中叶处于地下状态的强大的保守主义知识传统是不公平的。但是正因为特里林的观点精确地反映了在知识精英中占统治地位的偏好,所以在废黜自由主义王位的过程中,新保守主义的传教工作才显得如此重要。
特里林在另一方面是正确的:自由主义是如此宽广和全面的信条,对于美国理解自身是如此关键,在它的行列里包含着一系列极其广泛的人物和观念。假如知识界是个自由主义一党专制的国家,那么事实上所有的政治斗争都是在一个党内进行的。共产主义者就是这样通过其同路人,在这个被当作自由主义的世界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华尔街对外政策体制集团也是这样,他们的敏感和忠诚几乎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相去不远了。很多反共的左翼人士与左派分道扬镳之后,从中产生了很多新保守派,情况也是如此。自由主义一统天下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内部冲突,就像后来里根广泛的联合阵线里的冲突也是不可遏制的一样。
新保守主义的根源存在于这些自由主义的内讧中。大部分后来【57】创造新保守主义的人来自“冷战自由主义”联盟中最好战的成员,这些人把阻止苏联1940年代后期的扩张看作是美国的头等大事。排队反对他们的人称自己是“进步主义者”,并且将冷战看作是对国内新一轮新政改革的阻碍。进步主义者和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站在一起,他们都主张对苏联采取更加友好的态度,对美国采取更加批判的态度。共产党公开地支持华莱士运动是所有冷战自由主义者需要知道的,就像乔治·麦戈文在1948年出席华莱士的进步党大会是二十四年后所有新保守主义者都需要知道的一样(麦戈文,像冷战自由主义者一样,最终是反对华莱士而支持亨利·杜鲁门的再次当选)。
新保守主义的冷战自由主义根源的重要性不能被夸大。在1960年代,新保守主义者感到最惊骇的,是如此众多的自由主义者自愿地放弃杜鲁门和艾奇逊的强硬反共路线。新保守主义者认为,强有力的反共主义是战后美国自由主义非常重要的一块,这个论点毫无争议——新左派和新保守主义都同意这一点,虽然他们由此得出了不同的政治结论。因而,虽然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包括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和内森·格拉泽反对越南战争,认为那是轻率的,但是在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是支持这场战争的。更重要的是,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新保守主义者都带着怀疑和不信任的眼光看待反战运动。在这方面,和很多其他方面一样,新左派的崛起在新保守主义的成长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新左派攻击的“体制的”反共自由主义,正是后来的新保守主义信仰的那种自由主义。
二
如果说新保守主义冲动的最早表述是围绕着对外政策议题的,那么它第一次变成看得见的运动则是在国内政治上。新保守主义者第一个独特的标志,就是批评那些他们认为建立在僵化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自由主义项目。
在彼得·斯坦菲尔斯对新保守主义杰出的批评性的研究中,他确定了一些1950年代出现的对未来新保守主义者很重要的一些关键词,[4]那时新保守主义者仍然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害怕大众社会【58】的成长会导致大众政治,他们将其视为向暴民统治的倒退。他们认为大众政治会合乎逻辑地蜕变为极权主义——希特勒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解决大众政治的答案是多元主义,这是一种建立在主要社会团体的领袖之间的谈判上的政治理念。对新保守主义者来说,多元主义是美国解决大众政治之危险的答案,是麦迪逊的制约与平衡体系的现代政治社会学版本。新保守主义中的多元主义者认为,选举应该关乎有形的经济利益。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说西方的选举是“阶级斗争的民主”表达。在新保守主义者的眼里,被激情和道德主义支配的选举——新政治的自由派似乎很喜欢的那种选举——是危险的。正是那些在1950年代称赞“利益集团多元主义”的人变成了对民主党的尖锐批评者,认为民主党给太多的“特殊利益群体”以声音和权力,这是自由主义瓦解过程中诸多反讽中的一个。当越来越多和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在谈判桌边找到自己的座位时,新保守主义者(以及大多数其他保守主义者)对利益集团政治越来越感到不安。
在这个阶段的知识界骚动中,最高的概念是“意识形态的终结”。[5]意识形态终结的主题先是漂浮在文化自由大会的会议上,[6]文化自由大会是由中央情报局资助的(虽然当时它的成员很少有人知道)反共知识分子的国际性组织。意识形态终结是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它反对共产主义的信条,支持民主主义的宽容。“对于激进的知识界,旧有的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它们的‘真理性’和说服力”,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里写道。“没有几个严肃的头脑还相信人能制定‘蓝图’并通过‘社会工程’造就一个社会和谐的新乌托邦。”贝尔敏锐地意识到“意识形态终结”这个主题对年轻的新左派没有多少吸引力。在其他政治评论家开始关注之前很久,贝尔就注意到了新左派的崛起。“年轻的知识分子不高兴,因为‘中间道路’属于中年人,不属于他;中间道路缺乏激情,没有活力。”贝尔写道,新左派“不能确定他们追求的‘事业’的内容,但是那种向往是清晰可见的。”[7]“意识形态的终结”有很多作用,赞扬美国这个对各种意识形态都过敏的国家,并非其中最小的一个作用。在李普塞特的表述里,意识形态终结也和一些社会中暴力的阶级斗争的衰落有关,在这些社会中,经济的增长已经满足了工人阶级的需要,并且福利国家已经约束了资本主【59】义的漫无节制。[8]
从1990年代的观点去看,意识形态终结的主题看上去比它在1970年代或1980年代要好得多。贝尔的不幸是,《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出版后,紧接着就是一个激烈的意识形态化阶段,尤其是在美国。首先是新左派登场,然后是新右派。新时代似乎标志着意识形态的开始而不是结束。贝尔的批评者很少注意到,甚至当他预言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时候,他已经发现了新左派的崛起;但根据随后发生的事情,很容易就能彻底地驳斥贝尔的分析。
而现在清楚的是,贝尔、李普塞特和其他一些意识形态终结论者预见到的,正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弱点。尤其在当代,当“左”和“右”的概念似乎不如以前有用的时候,贝尔“政治思想的枯竭”的说法似乎比以往都更加中肯。传统的工人阶级的衰落严重伤害了西方的左翼政党。作为回应,很多在西欧的社会主义党和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在英国也越来越如此——已经抛弃了老社会主义的大部分内容。民主社会主义者现在视自己为现代化论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东欧,从只是不信任社会主义的人到憎恨社会主义的人,什么样的都有。在东方受到真心支持的那种社会主义是贝尔自己也支持的极其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即使是苏联也包含一些市场机制,贝尔和他的同事看上去很有预见性——虽然那些现在宣称“历史终结”的人走得太远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世界上最大的驱动力,那些激发了革命的力量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当然也不是基于阶级的,而是种族的和宗教的(奇怪的是,只有在波兰的反对共产党统治的革命才能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革命)。这些天,报纸的大字标题主要是关于伊斯兰的复兴,以及在苏联一些共和国和前卫星国里民族主义的增长。这些发展也被新保守主义预见到了。内森·格拉泽是其中之一,很早以前就预言了他所谓的“族群的普遍化”[9],他并且声称关于现代政治,族群比阶级告诉我们更多。
但是,不管意识形态终结的预言价值几何,事实证明,它就是即将诞生的新保守主义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运动。它最初只是对马【60】克思主义信条的反对,后来却变成了批判自由主义的乐观主义和自由主义项目的背后驱动力。它是第一份新保守主义刊物《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背后的精神所在。
1965年《公共利益》的创刊被看成在关键十年里的关键事件。在创刊号里,编辑们宣称影响有效的公共政策的主要障碍是“意识形态先行”导致的盲目,“不论这种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的”。
“因为意识形态的本性,”编辑们继续写道,“就是去预设事实;并且就是这种预设严重妨碍了对一个人所谈的东西的理解。”[10]
如果从1990年代早期看,这样的观点可能被解读为自由主义对罗纳德·里根所塑造的、在华盛顿处于优势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回应。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又回归自由主义和民主党人——特别是莫伊尼汉和贝尔——他们对保守主义搞过头也是这种批评。但是当《公共利益》的编辑们写下那些话时,“伟大社会”在华盛顿如日中天,年轻的新左派正在举起激进主义的大旗,保守主义看起来一溃千里。
在现实主义的旗号下,新保守主义发展出来的一些主题被证明对自由主义者具有毁灭性。最重要的就是意外后果定律。从进步时代开始,美国自由主义的一个核心信条,是相信政治家和规划者能够理性地分析社会问题,并提出科学的解决方案。讽刺的是,《公共利益》自己的信条里就有一条认为社会问题应当理性地分析。在第一卷里,莫伊尼汉谈到“专业化的改革”。[11]然而刊物的编辑和作者们却一直怀疑改革者清楚地看待事物的能力。他们怀疑不完美和不可预测的人类仅仅能够在“科学的”知识的基础上被社会性地组织起来。格拉泽的一篇重要论文的标题“社会政策的局限”[12]就抓住了这个意思。
就这样,《公共利益》用一篇接一篇的文章记载了一个又一个意图良好的项目的失败,经常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创造了一个新的。这份杂志成了“地毯里凸起的大包”的社会政策理论的主要解释者。推平了一个“大包”的结果仅仅是产生了另外一个,并且经常是在别处的更大的“大包”。这个观点的逻辑导致了这样一种感觉:或许那第【61】一个“凸起的大包”就应该被留在那里。现代保守主义杰出的历史学家乔治·H.纳什引用麻省理工学院的杰伊·W.福里斯特发现的一个“定律”,即“在复杂情况下,改进某事的努力通常趋向于使它们更坏,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13]
认为自由主义者已经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这种观念成为新保守主义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说,自由主义者将不得不接受,某些问题“我们不能完全理解,并且确实不知道怎么解决”。[14]他在批评“向贫穷宣战”的社区行动项目的文章《最大可能的误解》中,大量使用斜体字责备自由主义的盲目性。“项目发起了,但没有理解,没有解释,并且这带来了本来不会发生的社会损失……政府不知道它在做什么。它有一个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有一套理论。除此之外就没别的了。”[15]
失败的例子众多,情况各不相同。为平衡黑白学童比例,强制用校车接送学生上学驱使很多白人离开公立学校,从而使得种族隔离变得更严重,而不是更好。无论如何,校车接送并没有对那些被接送的学生起到真正的帮助作用。反贫穷项目中“最大可能的参与”,创造了莫伊尼汉的“最大可能的误解”,并且战胜贫穷的目标经常迷失在尖酸刻薄的政治争论中。高福利可能鼓励穷人完全不去工作。积极行动的负担沉重地落在了贫穷白人男子身上,而不是那些已经富裕起来的人,这在某种意义上又增加了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双语教育项目使得说西班牙语的孩子更加没有能力在一个主要说英语的国家里竞争。
新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项目的批评是强有力的,因为他们几乎总是包含一些事实,在社会政策领域,意外后果变成了生活的定律。作为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新保守主义者也比旧时代的保守主义者更值得信赖。毕竟,新保守主义者是彬彬有礼的知识分子,而不是种族主义者或者小气的生意人。在理论上,新保守主义者是真的信任政府项目的。只是这个项目、那个项目或者其他的项目都失败了而已。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新保守主义者开始怀疑所有的社会改革努力,认为其患了“地毯里凸起的大包”综合征,并且日益对改革者本身产生怀疑。不久,政府项目的主要结果对他们来说似乎都是那些预想不到的结果。在一个层面上,新保守主义者给未来的改革者的信【62】息无疑是有价值的:要谦逊,不要不懂装懂,要意识到你造成的损害可能比好处多。但是当这个信息开始渗透政治文化,并且被强硬派保守主义利用时,情况是非常不同的:如果你改变什么,很可能只是使它变得更差,为什么还多此一举?很多《公共利益》的编辑乐于承认,他们的理念在他们自己的分析的影响下,的确在向“右”漂流。《公共利益》的助理编辑马克·里拉写道,结果“一个新的更具有侵略性的论点被拿出来”。新智慧?“不论善意与否,扩张政府行动的尝试,在很多社会领域同时事与愿违,犯了错误。”[16]里拉在1985年提出这个观点。二十年后,新保守主义对待社会改革的态度已经从带着怀疑的支持变成了原则上一律反对。
事实上,新保守主义逐渐地转向接受保守主义的核心信念:人本身存在深深的缺陷,需要通过传统的约束来防止他们胡作非为。“传统行为模式的崩溃是我们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格拉泽写道。他说,解决很多社会问题的关键是“传统约束”的重建。[17]主流保守主义对新保守主义者不断增长的吸引力,能够很清楚地从列奥·施特劳斯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中看到。施特劳斯是一个寻求重建“古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影响力、以战胜现代政治哲学的政治理论家。施特劳斯强调(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部分新保守主义者也都开始强调),国家在提升一个有德性的公民体中的作用。这一观点里暗藏的主张是,如果权威统治能产生“更好的”公民的话,某种权威统治的形式要优于民主的形式。虽然新保守主义的历史学家费尽心机想说明这个观点正是我们的国父持有的观点,但是在民主的美国,这样一种观点还是个异端。新保守主义对新左派和反传统文化产生的敌意,很多应归功于施特劳斯的这一倾向。克里斯托尔受到施特劳斯很大的影响,他对那些放弃了“自我约束”而投身于个人和集体自我的“解放”的人不屑一顾。克里斯托尔说,这些解放论者对人性持一个太仁慈的态度,并且不能理解一个民主政体的命运“最终是由它的公民控制自己的激情,并且因此正确地理解其持久的公共利益的能力来决定的”。“觉得好,就去干”,这样的事现在太多了。[18]
在后来的年代里,新保守主义者由于担心自由主义的福利项目【63】会妨碍穷人的自律和“德性”,对查尔斯·默里的激进反国家观点予以严肃的关注,因为所有的福利项目都提升了依赖性,所以它们差不多都应该废除——为了穷人的利益。
意外后果的讨论再往前走一小步,就是新保守主义的另外一个主题,即:对民主最严重的威胁是权威的危机。[19]新保守主义者认为,太多的人对政府要求太多的东西,造成了“超负荷”。塞缪尔·P.亨廷顿警告说,“民主的过度”会毁了民主本身,他把艾尔·史密斯的著名的格言——没有什么民主的错误是更多的民主不能治愈的——彻底翻了个个儿。这个信息似乎是说,那些被剥夺应有权利的人对政府的要求太多。
除了一些例外情况,新保守主义并不把国家的问题怪罪到穷人头上。他们宁可去攻击“新阶级”,即一脑门子改革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官僚,据说他们对权力的欲望是没有限制的。他们指控新阶级的成员扩张国家的权力不是想去帮助穷人,而是帮助他们自己。迈克尔·诺瓦克写道,向贫穷宣战将为那些“心里渴望去做好事并且渴望有意义地使用他们的才能、技巧和时间”的人制造“无数工作和机会”。[20]“新阶级”作为一个种类包含了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者和左派对手——马克思主义教授、高中教师、社会工作者和无数各种各样的为监管委员会、法律援助机构以及拉尔夫·纳德工作的律师。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我们现代官僚社会的专业阶级正在与商人群体为了身份和权力展开阶级斗争。”克里斯托尔在1972年尼克松改选前夕写道。“不可避免地,这场斗争是在‘平等的’旗帜下进行的——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曾经高举过这面旗帜”。克里斯托尔写道,但是当新阶级“用意识形态的大词”表达它对商人群体的敌意时,它的基本动力是它相信自己“能更好地运作社会,并且感觉有权得到这个机会”。他补充说:“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平等’。”[21]
对“新阶级”的攻击给了新保守主义真实的政治影响。如果为了平等的战斗并非为了弱势群体,而只是有野心的知识分子和改革者夺取权力的方式,那它就可以取消了。没有什么国家对精英的不信任会比在美国还广泛,所以有一批精英敌人是一笔巨大的政治资本。正【64】当主流保守主义意识到它需要成为“民粹主义”时,绝对不民粹的新保守主义者送给右派一份大礼:一个完美的精英敌人。事实上,戈德华特(1)保守主义长久以来一直怀疑知识阶级。参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2)的主要辩护者小威廉·F.巴克利在1951年写道,国家被分成了“‘大学’的一群和‘非大学’的一群”。[22]他说,麦卡锡对非大学那群人非常有吸引力——巴克利肯定不是要恭维那些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在主流保守主义中对新左派的典型看法来自杰弗里·哈特,他是达特茅斯学院的文学教授。哈特在1970年的《国家评论》上写道,知识分子“对周围的社会”是“习惯性的反对,有时甚至是一种叛逆的关系”。[23]新保守主义者带着他们从其马克思主义根源那里继承来的阶级分析的天赋,将这种保守主义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合法化了。由于新保守主义的存在,右派的曾经被谴责为“反智”的观点,从而获得了一个高度可敬的知识谱系。
新保守主义的思想漂流最终将会使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全心全意的保守主义者。新左派的崛起和它逐渐地拥抱国际革命左派的举动,大大加速了这个进程。所有那些献给胡志明的赞美诗不仅警告了新保守主义者,也警告了民主派的社会主义者,像迈克尔·哈林顿、欧文·豪以及迈克尔·沃尔泽[24]。哈林顿、豪、沃尔泽和新保守主义都有反斯大林主义政治的共同背景,并且同样担心新形式的左派集权者崇拜的兴起。假如胡志明、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毛泽东,甚至金日成都成为左派合适的崇拜对象,那左派可真就出问题了。但是与哈林顿这样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不同,新保守主义者在很多其他的问题上已经漂移到右派那边了。反战运动中很多激进因素使得向保守主义的转变成为全面的转变。有人提出了一个算数规则:反战集会上每出现一面越共旗帜,十个新保守主义的同情者就诞生了,十个已经信奉新保守主义的人就更右了。因为很多新保守主义者是犹太人,随着很多新左派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加入值得左派尊敬的革命组织的行列中,他们的恐惧就更深了。
新左派点燃大学,让新保守主义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尽管很【65】多新保守主义者不信任新阶级的成员,他们却深深地信任培育这些新阶级的大学。很多新保守主义者是穷人家的儿女,发现在学院里有他们晋升的机会。对于新保守主义者来说,大学远不止一个获得身份和权力的路径。它本身就是良好社会的模范。大学既是富于权威的地方,也是自由统治着的地方。对于很多新保守主义者来说,把占据学校行政楼的新左派和当年烧书的小纳粹画等号,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新保守主义坚定不移地向右前进,既是它自身逻辑发展的结果,也是一些事件的结果,这些事件看似证实了它的逻辑。经常被忽视的是新保守主义所走的路,和那些大城市老社区的不那么有知识的前自由主义者和前民主党人是如此接近。假如新保守主义对拥有特权的大学生的行为感到愤怒的话,那么建筑工人和警察也会感到愤怒。如果新保守主义说在大城市里,控制犯罪率比控制贫困对于城市的生存问题更重要,那么很多白人以及为数不少的黑人也是这么认为。如果新保守主义担心太多的社会开销用于事实上不起作用的项目,那么这种情绪在很多不那么富裕的中产阶级纳税人中间会有很多共鸣。因而,欧文·克里斯托尔宣布了一个观点:“这是新保守主义者自己给自己的任务,向美国人民解释为什么他们是对的,向知识分子解释为什么他们是错的。”[25]
在新保守主义的主要成员中,詹姆斯·Q.威尔逊可能是和城市里愤怒的白人感受最接近的人。1968年夏天发表在《公共利益》上的一篇重要文章《城市的不安》中,威尔逊针对种族主义的指控为内城区的白人激烈地辩护。他争论说,这些人对黑人穷人的不满很少是基于种族主义的,而更多的是因为这样一种感觉,即,黑人穷人拒绝按照普通白人视为合理正派的标准来生活。威尔逊坚持认为,这样的白人对于黑人工人阶级中遵循这些标准的成员没有意见。在和马里奥·库默这样的自由主义者辩论的过程中,威尔逊宣称:“在种族被作为一个粗糙的社会阶级的指示器的情况下,很多被当作‘种族偏见’的东西不过是阶级偏见。”[26]这个论点在后来的年代变得更为流行。黑人有理由拒绝这样的辩论,因为用种族当作“一个粗糙的社会阶级的指示器”听起来脱不了种族主义的嫌疑。这种“粗糙的指示器”经常【66】被当作种族歧视的根据。但是威尔逊的分析对于大多数反叛的城市白人的真实情感而言,比起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些白人就是十足的种族主义者的观点,更真实。像新保守主义者喜欢指出的那样,现实是复杂的。
保守主义的政治家注意到这些观点,并且积极地向白人工人阶级以及他们在新保守主义者中的知识分子辩护人献殷勤。理查德·M.尼克松在1968年说:“曾经有一段时间,国家的焦点在失业者、穷人、破产者身上,工作的美国人变成了被遗忘的美国人”。这些被遗忘的美国人,尼克松说:“有合理的冤情需要平反,正当的事业应当获得胜利。”[27]威尔逊和其他半打的新保守主义者能很容易地写出尼克松的演讲稿。1968年,大部分新保守主义者还固守他们的自由主义,反对尼克松,支持休伯特·汉弗莱(3)。[28]但是到了1972年,相当多的人走到了另一边。他们开始把尼克松当作正义的应当获胜的目标,尤其是战胜乔治·麦戈文这样的反对者。
新保守主义者在民主党内的最后一次得意之作是1976年亨利·杰克逊获得总统候选资格。当杰克逊在候选人资格上败给吉米·卡特后,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开始支持非常温和的民主党候选人,这些候选人似乎上过很多新保守主义的课。但是他们对于卡特的任命非常失望——他们认为太多任命给了自由派,更让他们失望的是他们看到了卡特“第三世界主义”对外政策的软弱。到1980年,他们中的大部分成员,国家中最老到的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准备好了迎接一个名叫罗纳德·里根的演员和前棒球节目广播员。
三
很多有新保守主义倾向的民主党人如此轻易地从1976年的斯库普·杰克逊(4)转换到1980年的罗纳德·里根,以至于现在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最自然的政治转向。我们用的政治语言有意让这些转向看上去显得很正常。亨利·杰克逊变成了一个“保守主义”民主党人,所有跟随他的人在“麦戈文分子”接管民主党后,合乎逻辑地变成了“保守主义”共和党人,这大概可以从吉米·卡特的政策中反映出来。但是这里出了一些问题。斯库普·杰克逊在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里,都【67】被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吉米·卡特身上带有很多东西,但是他和乔治·麦戈文却没有什么共同点。并且罗纳德·里根绝不是新保守主义的“自然”选择。
很少有什么事态比如此众多的新保守主义者选择罗纳德·里根更能说明我们政治上的深刻转变。想知道为什么这代表了如此深远的变化,只需看看1964年,未来的新保守主义者对罗纳德·里根的政治化身巴里·M.戈德华特的回应。对于大部分新保守主义者来说,巴里·M.戈德华特是一个威胁,他代表的运动不过是一群偏执狂的集合。一些未来的新保守主义者在丹尼尔·贝尔编辑、1955年出版的重要著作《新美国右派》(The New American Right),以及在1963年戈德华特竞选前夕出版的该书扩充版《激进右派》[29]中为其观点给出了论据。他们的态度在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也得到很好的表达。虽然霍夫施塔特不能被完全归类为新保守主义者(或其他什么),但他也是丹尼尔·贝尔编辑的著作的重要作者,并且他对戈德华特运动的观点,公平地看,反映了那些将成为新保守主义者的群体的感受。
《新美国右派》的作者们担心,被戈德华特吸引的激进右派根本不是保守主义者,而是“假保守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贝尔写道:“激进右派在心理上惯用的手段就是如下一个三重的吁叹:美国道德勇气的崩溃;‘控制政府机器’一直在卖国的阴谋论;共产主义者将‘接管’国家的详细预言。”[30]对于激进右派的批评者来说,约瑟夫·麦卡锡的反共圣战不是传统的共和党精英对在新政时期多年政治失败的反应,而是一种民粹主义者反对国务院和华尔街精英的反叛。“激进右派”有时候被定义为只包括怪癖的边缘人,另外一些时候似乎想包括大部分被认为是现代保守主义者的人。在《激进右派》作者的眼里,激进右派与其说是被政治激发的,还不如说是被各种各样的病态人格所激发——特别是“身份焦虑”,以及右派的追随者无力面向现代世界作出调整。保守主义的历史学家乔治·纳什说,《新美国右派》的作者往往是“把保守主义看作是异常心理问题,而不是理性的政治”。[31]
戈德华特本人也被认为是一路货色。霍夫施塔特认为戈德华特成为候选人代表了对美国政治健康一面——“在竞选过程中分别吸引【68】不同的特殊利益群体,然后在现实的政府过程中努力像他们的经纪人那样行事的可敬传统”——的危险背离的趋势。霍夫施塔特写道,戈德华特却把这看作是“不光彩的政治,与这样一种政治,即致力于实现公共的宗教和道德价值并且处理‘我们时代的道德危机’比起来,相差不知有多远。简单说,他想把政治赶出政治领域。”[32]事实上,要说1980年罗纳德·里根信奉的或说过的东西就是这样,也不赖。尽管如此,还是有这么多的新保守主义者,在戈德华特是戈德华特主义的倡导者的时候,鼓吹反对戈德华特主义,到头来却拥护罗纳德·里根的戈德华特主义。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保守主义从一种病态人格,变成新保守主义者认可的理性的政治反应?
在后面的章节中可以看到,一些变化根本不是发生在新保守主义者当中,而是发生在美国右派当中。特别地,到了罗纳德·里根成为总统候选人的时代,大部分老保守主义者最终接受(至少作为一种政治上的必要),福利国家的很多方面不能简单地废止。乔治·纳什在1970年代早期就指出,老的保守主义者也走到了外交政策的中间路线,特别是,他们不再大胆谈论在不久的将来埋葬苏联共产主义。“现在已经很少有关‘解放’或者‘回滚’[33]的严肃讨论了”,他写道。
现在罗纳德·里根来了。他的全部思想充满了闪亮的乐观主义光芒,和右翼中那伙经常发出大灾难即将来临的阴郁预言的人相比,似乎没有多少共同点(新保守主义者对这些人非常讨厌)。欧文·克里斯托尔准确地抓住了这种不同,他在1983年这样写里根:“他的姿态是向前看的,他的重点是经济发展,而不是节制。所有的那些长着一颗会计师的心脏和灵魂的共和党人——这是共和党传统意识形态的核心——紧张起来了,甚至是惊慌起来了。”[34]
然而里根和戈德华特的差别并没有那么大。像戈德华特一样,里根把累进所得税看作是共产主义理论的产物,并且偶尔会很轻率地说到核战争的危险。里根也公开抨击利益集团政治。并且里根像戈德华特一样清楚地谈及“我们时代的道德危机”,从而赢得了数百万张选票。在此过程中,他协助一些名为“道德多数派”之类的组织大量繁殖,竭力推进选区里的福音传道。
促使新保守主义者拥护里根后期的戈德华特主义的,是他们自【69】己的思想转变,以及优先考虑的对象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知道,新保守主义者对特定的自由主义项目的批评逐渐变成了全盘批评,最后开始质疑自由主义计划本身。特别地,新保守主义越来越怀疑政府。悖谬的是,反而是丹尼尔·P.莫伊尼汉对自由主义计划比他的新保守主义同伴保持了更多的信任,他对政府的有限性有平实的看法。在1967年他宣称“自由主义者们必须放弃他们自己的这个想法,即认为国家——尤其是在这个国家里的城市——能够靠华盛顿的政府机构来运行”。[35]在196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里,莫伊尼汉强调了这个主题。“不知何故,自由主义者不能从生活中学习,”他说,“新保守主义者似乎生来就被赋予了一种东西,那就是,对政府机构做好事的能力的健康怀疑。”[36]
另外,新保守主义者对于他们曾经称赞是政治的稳定力量的利益集团多元主义,变得越来越怀疑。当利益集团的数量变多,黑人、女权主义者、同性恋、美洲原住民、西班牙裔和其他也包括进来后,利益集团之间的讨价还价突然不再是稳定的力量而是混乱的渊薮了。新保守主义认为,自由主义者对这些新利益集团的回应,从鼓吹“机会平等”转变为通过积极行动达到“结果平等”。莫伊尼汉准确地抓住了新保守主义者的担心,即“平等的革命”[37]和利益集团政治扩张失去控制。“一旦这个进程变得合法,将很难停下来,”莫伊尼汉在1968年写道,“如果不打算停下来,我担心它会对目前已经很火爆的趋势火上浇油:使现代生活越来越多的方面变得政治化(以及种族化)。”[38]
莫伊尼汉的论点有一些讽刺意味,因为林登·约翰逊对他引以为傲,认为他是自己最好的民权演说的合著者。1965年6月在霍华德大学作的演讲中,约翰逊坦率地宣称:“我们追求的不只是自由,还有机会——不仅是法律上的平等,而是人的能力上的平等——不仅是在权利上和理论上的平等,而是作为事实和结果的平等。”[39](强调为引者加)积极行动对新保守主义者造成很大的困扰,因为它打破了他们认为大体正义的奖赏结构。尽管新保守主义者也接受市场的结果并不总是公平、需要通过福利国家的收入再分配的观点,但是他们相信上大学和进入职业领域这种利益大体上还是要基于能力。新保守主义者【70】对他们在其中取得成功的那些机构是极其保守的,新保守主义的评论家身上也没有丢掉这一点。但对于正在上升的集团,尤其是对黑人来说,通过积极行动挑战老的精英统治和通过福利政策进行收入再分配同样合理。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一个直截了当的利益冲突却膨胀为一场关于价值的愤怒争论。对于寻求积极行动的黑人,新保守主义者和实行种族隔离的餐厅老板一样把自己的机构看得牢牢的,前者身上的种族主义不比后者少多少。对于新保守主义来说,这种比较是一种诽谤。他们反对种族隔离,并且信仰机会平等。但他们在配额上画了一条线。随着积极行动超过结束种族隔离变成民权争论的中心,新保守主义者在争论中站在了保守主义的一边。
在道德和传统上向右漂移也是值得注意的。很多曾经嘲笑过戈德华特的“道德危机”谈话的新保守主义者开始相信,国家正面临这个问题。在1964年,谈论“放纵”似乎主要是文化上的粗人和学究的专利,他们轻视现代性,偏爱纯朴的生活。但是新保守主义者被反传统吓着了,以至于他们感觉要被迫去维护他们明确地称为“资产阶级道德”的东西。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不是没有疑虑。“新保守主义者对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的精神气质的态度是拥护,但保持距离。”克里斯托尔在1979年写道:“这种适度的热情将新保守主义同旧右派和新右派区别开来——新老右派都极度怀疑资产阶级。”[40]但是新保守主义者完全同意右派两翼的观点:国家需要比现在更多的资产阶级道德。一个人不必非要成为保守主义者才同意丹尼尔·贝尔的说法:“现代资本主义已被一种广泛的享乐主义所改变,这种享乐主义将世俗关注而不是先验纽带作为人生活的中心。”贝尔担心资本主义可能会被它的“文化矛盾”[41]所摧毁。资本主义提倡的消费主义和“放纵”将破坏努力工作、纪律、延迟满足这些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美德。老保守主义者一直怀疑这一点。
尽管一个丹尼尔·贝尔(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制新保守主义标签的人)可以怀疑资本主义的运作,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新保守主义作为一个团体却对资本主义体系变得越来越印象深刻。一群思想家,包括很多前托洛茨基分子、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却越来越赞赏现代商业体系。1988年,当保守主义刊物《政策【71】评论》(Policy Review)问珍妮·柯克帕特里克(5),她在国内政策上的观点是怎样转变的,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的回答也代表很多参与运动的人:“我要说,在过去十年里我观点的最重要的转变是对市场经济有了更大的赞赏。我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有关经济问题的东西。”[42]克里斯托尔总结了新保守主义者新近在经济问题上获得的智慧,在1980年《公共利益》“经济理论的危机”特刊的一篇总结论文中,他列举了关于经济的五个“基本真理”:
(1)绝大多数的男人和女人自然地和不可救药地对提高他们的物质条件感兴趣;(2)压制这种自然愿望的努力将导致强制的和贫乏的政治;(3)当这种自然愿望被给予充分的自由,商业交易不受阻碍,经济增长就发生了;(4)作为经济增长的结果,每个人最后的确改善了自己的状况,尽管在程度上或者是时间上是不平等的;(5)这种经济增长导致了拥有财产的中产阶级巨大增长——对于人权受尊重的自由社会来说这是一个必要的(虽然不是充分的)条件。[43]
就连小威廉·F.巴克利或米尔顿·弗里德曼,也不能为戈德华特——里根保守主义始终鼓吹的东西提供一个比这更简洁的概要了。
最后,新保守主义被1970年代的对外政策推向右派一边。很多新保守主义者都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和共产主义者的斗争历史已经使得他们比一般的保守主义者更加反共。不仅是吉米·卡特,还有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德·福特,都对苏联采取缓和的政策,新保守主义者被迫空前地向“右”看寻找一位领头者。1960年,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国防上花费太少的冷战战士成群结队奔赴约翰·F.肯尼迪的竞选,并被称为“自由主义者”。到1980年,在总统政治上力持这种立场,是共和党人右派的专利。保守主义者比如罗纳德·里根和杰克·坎普如此急切地援引约翰·肯尼迪的话推行他们自己的对外政策就不足为奇了。
吉米·卡特向新保守主义者提出了一个独特的问题。卡特几乎【72】很难被看作是自由主义者——大部分热情的自由主义者也不用那样的方式看待他。事实上,正是卡特开始增加军备,罗纳德·里根却为此得到了好评。新保守主义者在白宫再也找不到一个比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更亲近的朋友了。
但是对于新保守主义者来说,卡特的政策最终奠基于一种不连贯的道德主义上,并且他们不能忍受他的人权政策。这是很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正是新保守主义自己最先举起“人权”的旗帜来攻击在苏维埃帝国内部对异议者和少数派的虐待。谈论人权,成了新保守主义者批评尼克松–基辛格“无道德”的缓和政策的一种方式。但是当吉米·卡特把人权作为他的政策的基石时,他削弱了美国对右翼独裁者的支持,而这些右翼独裁者是美国的盟友。这不是新保守主义者想要的东西。因此,欧文·克里斯托尔攻击卡特持有“双重标准:关于任何涉及人权的怀疑,左翼的政府被给予利益,而右翼的政府总是不断地被谴责”。[44]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对“权威主义”和“极权主义”的著名区别就是要给新保守主义者一个自己的标准。在柯克帕特里克看来,美国应该对反共主义的“权威主义”政体更加温和,不仅仅因为他们是美国的盟友,而且是因为他们比共产主义国家更有可能转向自由放任主义的方向。对柯克帕特里克的批评者来说,她的双重标准已经被最近东欧各国的事件证明是错误的。但是,不论将卡特看作是削弱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的“道德主义者”价值何在,它有一个优点,就是澄清了新保守主义者必须做的政治选择。它使得罗纳德·里根更加具有吸引力。
因此,大部分新保守主义者放弃了对抗迈克尔·哈林顿的标签并且欣然接受了他们的保守主义的事实。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继续坚持他们的自由主义性质(并且因此被一些新保守主义者的老同志放弃,比如莫伊尼汉就是如此),更多的新保守主义者掉头朝右,经常发现他们站在里根阵营的远端。对于诺曼·波德霍雷茨这个新保守主义的先锋来说,里根早期对苏联的开放背叛了他曾一度支持的原则,并且代表了一种“绥靖主义”的形式。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在共和党人中变成了英雄,但不是在温和派中(这些人可能曾经受到过她维护福利国家的吸引),而是在强硬派中(这些人认为他们【73】在对外政策观点上与她有很多共同基础)。威廉·贝内特可能是新保守主义者变成右翼的英雄的最成功案例。他对教育体制(一个“新阶级”的要塞,如果真有的话)以及1960年代的放任的攻击,得到了右派的大声喝彩。
新保守主义家族内最显著的转变标志是欧文·克里斯托尔的儿子威廉·克里斯托尔的角色,他变成了里根和布什政府保守主义事业最能干的代言人。比尔·克里斯托尔欣然拥抱右派;他的保守主义不需要任何前缀。他甚至愿意接受一项大多数热情的共和党人和保守主义者都反对他接受的工作:他做了副总统丹·奎尔的高级政策顾问和幕僚长。就这样,美国中西部的保守主义最终和东海岸的知识分子讲和了。
四
新保守主义者破坏自由主义的可行方案众多并且众所周知。讨论最多的是新保守主义者帮助右派创立的大量机构。欧文·克里斯托尔比大部分人更明白金钱可以购买的知识影响力,他呼吁商人资助他们在新阶级中的朋友,而不是他们的敌人。“你只能用一种理念击败另一种理念,理念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将会在‘新阶级’中间而不是之外决出输赢。”克里斯托尔写道。“商业在这场斗争中也有利害关系,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无忧无虑不知道这一点。”商人们突然变得意识清醒,并且真的帮助创立了许多保守主义研究机构、法律中心和刊物。并非所有的这些机构都是新保守主义倾向的,但是新保守主义者(尤其是欧文·克里斯托尔)在创立这些机构的时候都露面了。[45]
但是新保守主义者对自由主义造成的知识上的伤害远比他们有组织地做的任何事情都更加深刻。简单说,他们使得对国家的保守主义战争合法化了。在一本为自由主义项目辩护的书中,政治科学家约翰·E.施瓦茨准确地抓住了新保守主义花费了很大精力创造的一种流行感觉。“在迷惑和沮丧中,美国人进入了1980年代,感觉国家过去的二十年被大大浪费了,他们被这种感觉所困扰。”他写道,“在那【74】些年中,一点一点地,我们走上了错误的道路”。罗纳德·里根用一句精炼的话成功地总结了所有问题:“在向贫穷发动的战争中”,“贫穷赢了”。
新保守主义的成就中有很多具有讽刺意味的东西。毕竟,最初他们的计划是净化政策,使之摆脱意识形态的无理性。最后,他们对美国历史上一个最意识形态化的政府赋予了合法性。新保守主义者曾经是公共政策领域的专家。他们曾经相信政府,相信政府能够做到一些事情,只要它愿意被证据引导。到最后,他们的计划越来越多地被愤怒而不是证据引导——愤怒于新阶级问题,积极行动的号召者问题,反文化问题,对外政策的道德主义者问题。
也包括在政府问题上。在寻找让他们十分苦恼的“权威的危机”问题的答案时,新保守主义者和他们新左派的敌人一样,都转向了反国家主义的自由放任主义。这种立场当然有一个逻辑。“废除政治是自由放任主义对公共权威危机的解决方案,”斯蒂芬·L.纽曼写道,他是一位评论家,自由放任主义思想敏锐的研究者。“他们的想法是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用市场取代政府。”[46]这逐渐成为新保守主义者选择的解决方案。
然而,新保守主义者不相信市场或者其他包治百病的万灵药,能解决难于处理的社会问题。1960年代到底发生了什么,对此有一种完全误导的观点,而我们目前政治的虚伪的花言巧语,正是建立在这种观点之上。这种观点极大地夸大了“伟大社会”到底做了什么,以及它实际上花费了什么。与此同时,它忽视了“伟大社会”事实上的成就。在这些问题上,没有人比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说得更好,因为他曾经抱怨过“伟大社会”时代的政府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莫伊尼汉争辩说,断言政府在“伟大社会”上花费了巨资是荒谬可笑的。莫伊尼汉指出,在最好的年份,经济机会办公室的预算是17亿美元。如果所有这些钱直接分配给穷人,莫伊尼汉指出每个穷人将会收到慷慨的50—70美元。[47]那个时期花费增幅最大的是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障/医疗补助项目。在社会保障上增加的经费做了本来就要做的事情【75】:全面消灭老年人中的穷人。医疗保障项目为数百万没有健康保险的人提供了保障。这些项目的得失可以争论。如果说有什么项目为解决问题上“投下”了巨资,这些就是,但这些项目如此受欢迎,以至于没有哪个保守主义者会废除它们。说到预计将会失败的“实验性”的伟大社会项目,“领先一步”(6)是如此成功,甚至成为保守主义者最喜欢的项目——乔治·布什就想花更多的钱在上面。像莫伊尼汉总结的:“出现的成就比我们想知道的还要多。”[48]
这里的要点不是说1960年代在社会改革上做出的努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而是说,正是新保守主义者正确地评价的社会政策的进路——以冷静的意愿检查证据——表明了“伟大社会”是一个成功和失败的复杂混合。另外一个新保守主义的教导是,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是很困难的。一些“伟大社会”的项目悲惨的失败不应该看作是什么稀罕事。然而把社会政策上的争论简缩为一句套话“自由主义的项目失败了”(一个新保守主义者无意中鼓励的观点),我们就只是让什么都不做变成合法的。这同样并不解决社会问题。
新保守主义的力量之一是它从对政治和其他人类努力的反讽中得到了乐趣。新保守主义很中意这样的反讽:和新左派结伙击败自由主义。如果说新左派反对自由主义国家是因为他们反独裁,那么新保守主义者则证明自由主义国家如何破坏了权威。在理论上,新保守主义者是冷静的、“专业化的”改革的捍卫者,而新左派却以这种改革为敌。然而两者最终都破坏和击败了专业的改革者。
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悲剧在于他们需要向新保守主义者学习很多东西,正如他们本来可以从新左派那里学到一些有关民主与参与的东西。尤其是,新保守主义者把德性视为政府政策的合法目标,这是正确的——即使他们经常错把德性当作反对民主的攻城武器。新保守主义者坚持认为民主体制取决于自律和自制的公民,这是正确的——即使他们过于担心新左派和反文化者攻击这些价值。
到1960年代末期,非常清楚的是,自由主义需要注意新保守主【76】义者的警告。那时,自由主义者不再有足够的自信去探究他们想要国家来促进哪些价值(如果还有的话)。利用国家执行一种刚性的道德准则(一种既不可行也没有什么吸引力的努力),和坚持自由主义项目要促进一些使社会和执行这些项目的个人都受益的价值,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而自由主义者却日益忘记这种区别。随着时间过去,自由主义者也不再确定哪种家庭是值得鼓励的;他们担心福利项目要求接受福利者去工作;他们几乎总是把对法律和秩序可理解的忧虑看作一种隐蔽的种族主义;他们开始相信,所有强调本地社区价值的学说与种族隔离分子使用过的假冒“州权”论点是一回事。
正如我们在下两章将要看到的,自由主义者为他们没有接受这些教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注释
[1]哈林顿和他的同伴,民主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欧文·豪,是最早理解新保守主义中间诞生了一种新的哲学的人。见Lewis A. Coser and Irving Howe, eds., The New Conservatives: A Critique from the Left (New York: Quadrangle, 1974),特别是哈林顿的文章, “The Welfare State and Its Neoconservative Critics,” pp.29–63。
[2]Irving Kristol, Reflections of a Neoconserva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pp.74, ix.
[3]Lionel Trilling, The Liberal Imaginat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54),pp.5–6.
[4]斯坦菲尔斯对关键概念的分析,见Peter Steinfels, The Neoconservative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9), pp.32–41。
[5]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5), p.402.
[6]关于文化自由大会在支持意识形态终结论中所起的作用,见Peter Coleman, The Liberal Conspiracy(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9), pp.108–13。
[7]Bell, p.404.
[8]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63),pp.442–44。又见李普塞特后来的文章“A Concept and Its History: The End of Ideology,” in Seymour Martin Lipset, Consensus and Conflict: Essay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5), pp.81–109。
[9]Nathan Glazer, “The Universalization of Ethnicity,” Encounter (February 1975), pp.8–17.
[10]Daniel Bell and Irving Kristol, “What Is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Public Interest 1: 1 (Fall 1965), pp.3–5.
[11]Daniel P. Moynihan,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Reform,” The Public Interest 1: 1 (Fall 1965),pp.6–16.
[12]Nathan Glazer, The Limits of Social Poli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pp.1–17.格拉泽最初的同名文章发表于《评论》(Commentary)1971年9月号。
[13]George H. 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1979), p.325.
[14]转引自Nash, p.325。
[15]Daniel Patrick Moynihan, Maximum Feasible Misunderstanding (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70), pp.xiii–xiv, 170.
[16]Mark Lilla, “What Is the Civic Interest?” The Public Interest 81 (Fall 1985), p.71.
[17]Glazer, “The Limits of Social Policy,” p.8.
[18]Irving Kristol, On the Democratic Idea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73),pp.vii–viii.
[19]见Steinfels, pp.55–69。又见Michel Crozier, Samuel P. Huntington, and Joji Watanuki,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A Report on the Govemability of Democracies to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5)。
[20]诺瓦克在成为新保守主义者之前就批判新阶级了。见Novak, Choosing Our King (New York:Macmillan, 1974),特别是pp.63–92。
[21]Irving Kristol, “About Equality,” reprinted from Commentary (November 1972) in Irving Kristol,Two Cheers for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 p.177.
[22]见Nash, p.119。
[23]见Nash, p.299。
[24]沃尔泽是新左派的系统的、极其强硬的批评者。他论新左派的文章见Walzer, Radical Principles:Reflections of an Unreconstructed Democra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0), pp.109–85。
[25]Kristol, Reflections of a Neoconservative, pp.xiv–xv.
[26]威尔逊关于种族偏见的论述,见James Q. Wilson, “The Urban Unease,” The Public Interest 12(Summer 1968), pp.25–39。
[27]尼克松对“被遗忘的美国人”这一主题的最好陈述是他接受提名的演说。见Nixon Speaks Out: Major Speeches and Statements by Richard M. Nixon in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Nixon-Agnew Campaign, 1968), pp.277–91。
[28]关于新保守主义者支持汉弗莱,全年中为汉弗莱所做的最精彩的论辩来自克里斯托尔,见Irving Kristol, “Why I Am for Humphrey,” The New Republic (June 8, 1968)。
[29]Daniel Bell, ed., The Radical Right (Garden City: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64).
[30]Daniel Bell, ed., The Radical Right (Garden City: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64),p.8。
[31]Daniel Bell, ed., The Radical Right (Garden City: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64),p.138。
[32]Richard Hofstadter,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Vintage, 1967), p.121.
[33]关于“回滚”(rollback),见Nash, pp.322–23。
[34]Kristol, Reflections of a Neoconservative, p.112.
[35]Daniel P. Moynihan, “The Politics of Stability,” New Leader 50 (October 9, 1967), pp.6–10.
[36]Daniel P. Moynihan, “Where Liberals Went Wrong,” in Melvin Laird, ed., Republican Papers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68), p.138.
[37]“平等的革命”这句话,Herbert Gans在More Equality (New York: Vintage, 1974)一书中从头到尾都在用,特别是第7–35页。
[38]Daniel P. Moynihan, “The New Racialism,” in Coping: On the Practice of Governmen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5), p.204.
[39]对约翰逊在霍华德大学演讲的一个有益的讨论,见Richard N. Goodwin, Remembering America:A Voice from the Sixties (Boston: Little, Brown, 1988), pp.342–48,以及Daniel P. Moynihan, Family and Na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6), pp.30–34。古德温和莫伊尼汉是演说稿的主要创作者。
[40]Kristol, Reflections of a Neoconservative, p.76.
[41]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paperback ed.
[42]Jeane Kirkpatrick, “Welfare State Conservatism,” Policy Review 44 (Spring 1988), pp.2–6.引语见第5页。
[43]Irving Kristol, “Rationalism in Economics,” The Public Interest (special issue 1980), p.218.
[44]Kristol, Reflections of a Neoconser-vative, p.269.又见Jeane J. Kirkpatrick, Dictatorships and Double Standards (New York: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Simon and Schuster, 1982), pp.23–52。
[45]关于保守主义不断蔓延的知识帝国的产生,一个批判性的详细研究,见Sidney Blumenthal,The Rise of the Counter-Establishment: From Conservative Ideology to Political Power (New York:Perennial Library, 1988,特别是pp.147–60。
[46]Stephen L. Newman, Liberalism at Wits’ End: The Libertarian Revolt Against the Modern Stat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42.
[47]Daniel P. Moynihan, Family and Nation, p.133.
[48]Moynihan, Family and Nation, p.87.
(1) 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1909—1998):美国政治家,先后五次当选共和党参议员,并于1964年成为共和党提名的总统选举候选人。他被视为1960年代起美国保守主义运动复兴的主要精神领袖。——译者注
(2) 约瑟夫·雷蒙德·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1908—1957):曾任美国共和党参议员,1950年代初在他的煽动下,美国兴起了全国性的反共“十字军运动”,涉及美国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各个层面。——译者注
(3) 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1911—1978):两度当选民主党参议员,代表明尼苏达州,并任民主党党鞭。曾任林登·约翰逊的副总统。1968年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败给了尼克松。——译者注
(4) 斯库普·杰克逊(Scoop Jackson,1912—1983):1941年起任国会众议院议员和参议员,1972年、1976年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均未成功。——译者注
(5) 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nae Kirkpatrick, 1926—2006):1980年里根竞选总统时的外交政策顾问。1985年,她从一位资深的民主党人转变为了共和党人。她还是首位女性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译者注
(6) “领先一步”(Head Start):美国健康与公共服务部为低收入儿童及其家庭提供的一项全面的教育、医疗、营养服务,始于1965年。——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