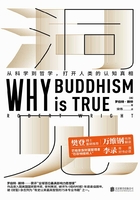
第5章 感觉何时为幻觉
围绕本章标题的是一个更宏大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到底要谈些什么?幻觉看似真实,其实不真实,那么说感觉是“真”是“假”到底是什么意思?感觉就是感觉。你感觉到的,就是你的感觉——真实的感觉,并非想象的感觉。没有什么可多说的。
针对这种观点,有些事情要先说清楚。其实,佛教哲学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感觉即感觉。如果我们接受感觉的起落,认为它就是生命的一部分,而不是认为它有别的深意才去孜孜追求,结果往往会更好。学习这样做是正念冥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多从中得到满足的受众可以证明这样的做法是有效的。
不过,说它有效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具有智识合理性。这仅仅是因为,你看淡某些个人感觉而感到快乐,并不意味着你对世界的理解更真实了。或许这种看淡个人感觉的状态就像麻醉一样:屏蔽了现实世界对你的感觉提供的反馈,使你的痛感变得迟钝。或许使你陷入梦境的是冥想,而不是正常意识。
如果你想知道冥想到底能不能帮你接近真相,探寻这个问题应该会有所帮助:冥想使我们摆脱的那些感觉是否会带我们偏离真相?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方法,来解答这个艰深的问题:我们的感觉在某种意义上是“假”的,还是“真”的?还是有些是“假”的,有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是“真”的?
想要解答这些问题,可以回溯到生物体的进化过程。回到很久以前,回到“感觉”第一次出现的时候。遗憾的是,谁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时候,甚至连大概的时间段都难以推测。是哺乳动物出现的时候吗?爬行动物出现的时候?黏糊糊的一团漂在海上的时候?细菌之类的单细胞生物出现的时候?
难有定论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感觉”有一个怪异的特性:永远也不可能完全确认除你之外的其他人或其他事物到底有没有感觉。“感觉”的定义中有一点就说明了,它是私密的,不显于外的。举个例子,我也不敢说我家的狗弗雷泽到底有没有感觉。或许摇尾巴仅仅是摇尾巴而已!
但是,恰如我认为我不会是唯一具备感觉的人,我所归属的物种也不会是唯一具备感觉的物种。我注意到,我们的近亲黑猩猩痛得打滚的时候,是真的因为痛才打滚的。如果从黑猩猩开始,循着行为复杂性的阶梯向下看,到狼、蜥蜴,甚至水母,还有细菌,我也无法找到一个确定的位置,认定从这里开始往后更简单的生物就没有感觉。
总之,不管感觉最初在何时出现,行为科学家对于“好感觉和坏感觉的最初作用”已经基本达成一致:使生物体接近对其有益的事物,躲避对其有害的事物。比如,养分可以保证生物体的生存,所以自然选择偏爱的基因就会使生物体产生某种感觉,引导它们去追寻含有养分的东西,也就是食物。你或许对这类感觉很熟悉。相反,对危害生物体或导致生物体死亡的东西则最好躲开,所以自然选择就给了生物体厌恶的感觉,让它们倾向于躲避这类东西。接近和躲避是最基本的行为决定,感觉则像自然选择的工具,用于引导生物体从自然选择的角度做出正确的决定。
毕竟,普通动物还没有聪明到可以思考:“嗯,那种物质富含碳水化合物,能给我能量,所以我要养成习惯,摄取、消化它。”事实上,普通动物甚至没有聪明到去思考:“食物对我好,所以要吃。”感觉的出现,替代了所有此类思考。寒冷冬夜里,温暖的营火对我们有吸引力,这意味着,对我们而言,温暖比严寒更好。直接接触火焰会痛,意味着暖过了头。此类感觉和其他感觉的作用就是向生物体转达哪些对它们好、哪些对它们不好。正如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二十五年后的1884年,生物学家乔治·罗曼斯George Romanes)所说:“快感和痛感一定是伴随着对生物体有益或有害的过程而进化出来的主观产物,进化而来的目的或根源在于驱使生物体追寻一种,躲避另一种。”[13]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种辨别感觉真假的方法。生物体的感觉旨在针对我们所处环境中的事物所作的评价进行编码。此类评价通常关乎这些事物对于产生感觉的生物体的存亡是好还是坏(有些时候关乎这些事物对于生物体的近亲,特别是后代是好还是坏,因为近亲之间有很多共同基因)。[14]因此,如果编码的这些评价是准确的,我们就可以说感觉是“真实的”——吸引生物体的东西确实对生物体来说是好的,或者,鼓励生物体躲避的东西确实是对生物体不好的。如果感觉引导生物体走入歧途,生物体跟随感觉会走向对其不利的事物,那么就可以说这种感觉是“假的”,或者说是“幻觉”。[15]
上述并非从生物学角度判定“真”和“假”的唯一方法,但也是方法之一,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种方法有多管用。
滞后性
以甜甜圈为例。我个人热衷于吃甜甜圈,如果依从个人感觉的引导,早饭、午饭、晚饭和餐间茶点,我都要吃甜甜圈。但是我被告知,其实每天吃太多甜甜圈对我不好。所以我觉得个人被甜甜圈吸引的感觉可以称作“假的”:这些甜甜圈给我的感觉很好,但却是一种幻觉,因为它们其实对我并没有好处。这一点当然很难让人接受,使人脑中不禁回荡起老卢瑟·英格拉姆(Luther Ingram)的苦情歌:“如果爱你是错,我不想正确。”
“这也不禁让人有所疑惑:为什么自然选择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的感觉难道不应该引导我们趋向对生物体有利的东西吗?确实应该。但事情是这样的:自然选择是在特定的环境下设计出我们的感觉的,在当时的环境中没有垃圾食品,能获取的食物中最甜的就是水果了。因此喜好甜食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它给我们的感觉引导我们追求对我们有利的东西,从这层意义上来讲,这些感觉是真的”。但是在现代环境下,以实现“零卡路里”的科学烹饪为重要目标,这些感觉就变成了“假的”,至少是不那么可靠的,有时这些感觉会告诉我们某样东西对我们是好的,但其实不然。
很多这样的感觉被嵌入我们的血统,它们能够很好地服务我们的祖先,却不一定总能符合我们当下的利益。比如路怒症。惩罚对自己不公或不敬的人,是深植于人类内心的一种欲望。承认吧,虽然被激怒会令人不悦,但恰如其分的愤怒感觉能令人感到愉悦。佛陀说,愤怒有“毒根和蜜端”[16]。
你大致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自然选择要把恰如其分的愤怒设计得如此诱人:在狩猎—采集者的小村庄里,如果有人占了你的便宜——偷了你的食物,偷了你的伴侣,或者只是看不起你——你就需要给他一点教训。毕竟,如果他认为欺负你之后没有任何后果,就很可能会不停地这样做。更糟糕的是,你所处社交圈的其他人会认为可以压榨你,于是也开始欺负你。在这样一个一成不变的狭小社会环境中,对压迫者表现出极度的愤怒,直面压迫者,敢于反抗,对你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即使打输了,甚至被揍得特别狠,你也传递出了对你不敬必有后果这一信息,长远来看,这种信息会给你带来好处。
你或许已经开始思量,这种感觉,放在现代的高速路上会带来怎样的荒诞结果。你想要惩罚的那个无礼的司机,你可能再也不会见到,见证你实施报复的其他司机也一样。所以此处放纵发怒不会带来任何益处。至于代价?我想,以将近一百三十公里的时速驾车追逐他人,肯定比在狩猎—采集社会中拳脚相向更容易害死你。
所以你可以说路怒是“假的”。路怒给人好的感觉,但是这种好是幻觉,因为屈从于它而导致的行为往往是对生物体不利的。
还有很多路怒之外的愤怒也同样是“假的”——突然爆发的怒气,往好里说是徒劳的,往坏里说可能会造成恶果。因此,如果冥想真的能使你从这些感觉中解放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就能驱散幻觉——你跟随感觉走而无意间认同的幻觉,认为愤怒以及由愤怒激起的复仇欲望在本质上是“好”的幻觉。从结果来看,从最基本的利己主义角度来看,这些感觉都算不上好的。
因此,在定义感觉的“真”或“假”时有这样一种方法:如果它们给我们的感觉很好,却引导我们做出不利于自身的事情,那么它们就是“假的”感觉。但是还可以从另外一个层面来判定感觉的“真”或“假”。毕竟,有些感觉并不仅仅是感觉。它们不仅仅判断做某些事对生物体到底有没有好处,也是一种真切、明确的信念,评判环境中的事物及其与生物体福祉间的关系。显然,我们可以相对直截了当地判断这类信念的“真”或“假”。
误报
假设你在一个响尾蛇出没的区域徒步旅行,你知道,就在一年前,某个独自徒步旅行的人在附近被响尾蛇咬了之后身亡。再假设,你脚旁的草丛里有异动,这种异动不仅会使你感到一阵恐惧,你甚至会感觉到响尾蛇就在身边一样的恐惧。其实,等你转身看向异动的方向时,恐惧感会达到顶峰,你甚至会清晰地想象出一条响尾蛇。如果发出异动的是一只蜥蜴,在那短暂的瞬间,这只蜥蜴也会看起来像一条蛇。这就是真实的幻觉:你真的相信本来没有的东西存在;事实上,你真的“看见”它了。
这种错觉被称作“误报”。从自然选择的角度来看,这属于一种特性,而非故障。尽管在99%的情况下,你以为看到了响尾蛇这个念头是错的,但是在1%的情况下,这个念头可能会救你的命。从自然选择的角度测算,在关乎生死的问题上,1%的正确率值得以99%的错误为代价,即使在那99%的情况下你会感到短暂的恐惧。
一方面是响尾蛇幻觉,另一方面是甜甜圈和路怒症幻觉,二者之间存在这两点不同:(1)在响尾蛇的例子中,幻觉是明确的,是真的对物质世界产生了错误的感知,在那短暂的瞬间产生了错误的信念;(2)在响尾蛇的例子中,你的情绪机器完全按照设计的方式运转。换言之,响尾蛇幻觉并非“环境错位”造成的,在这个例子中,自然选择设计的感觉,在狩猎—采集环境下为“真的”,而转换到现代生活环境中就变成了“假的”。其实,自然选择设计这种感觉,原本几乎总是幻觉,这种感觉给你的信念(对即时环境中存在事物的判断)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假的。这也提醒了我们,自然选择设计大脑的初衷并非要我们看清世界,自然选择设计的大脑会产生有利于基因延续的感知和信念。
这也引出了甜甜圈、路怒症幻觉与响尾蛇幻觉之间的第三点不同:从长远来看,响尾蛇幻觉对你很可能是有好处的,这种幻觉能帮助你躲开可能降临的伤害。根据你生活的不同环境,可能更容易出现类似于响尾蛇幻觉的别的情况,这类幻觉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走夜路回家时,听到身后的脚步声,或许会害怕那是行凶抢劫的人发出的。尽管你的感知很可能是错的,但是考虑到个人生命安全,跑到马路对面很可能会防止一次致使你遇害的犯罪行为。
我怕这样讲或许会把现实说得过于清晰。看似好像有两种不同的错误感觉——非自然的“环境错位”类和自然的“误报”类。我们应该忽略第一种,同时遵从第二种。其实,在现实世界中,两者的分界线很模糊。
比如,你是否会担忧自己的话冒犯了某人?而且你很可能很久也不会再见这个人?还有,因为你和这个人不是很熟,那么如果专门给她打电话或发邮件,确认她有没有受到冒犯或澄清你并无恶意,是否会显得很尴尬?
“担忧自己冒犯了某人”这种感觉本身是很自然的,与人保持良好关系,能大幅提升我们祖先生存和繁衍后代的概率。另外,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过分夸大了自己冒犯他人的概率,甚至一度坚信自己确实犯了错,这也很自然。这或许也算是一种自然的“误报”——认为自己犯错的感觉,或许被“设计”得太过强烈,使你做出很多不必要的补救行动。
不自然的是,补救行动太难实施。在狩猎—采集时代,你担忧会冒犯的人可能就住在十几米之外,或许二十分钟左右就会再见到他。到时你可以权衡他的举止动作,或许就能确定自己并没有冒犯对方,或者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对方真的生气了,然后尝试扭转局面。
换言之,最初的感觉,即使是幻觉,也很可能是自然的,被设计成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那些不自然的是现代社会的特点,因而令人难以确定这种感觉到底是不是幻觉。所以,这种感觉持续的时间过长,很可能已经不再有实际价值。而且不幸的是,这种感觉令人不悦。
“环境错位”还带来了另外一种令人不悦的产物,即痛苦的自我意识。我们经由自然选择设计,会在意——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待我们。在进化过程中,受人喜爱、钦佩和尊重的人能够更有效地实现基因传播。但是在狩猎—采集时代的村落里,邻居对你的行为特点非常熟悉,你不太可能突然做出某件事情,大幅改变他们对你的认识,不管那种认识是好还是坏。人际接触(social encounters)通常不是高压活动。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经常身处不自然的境地,会见不太了解或根本不了解我们的人,这样的场合就会带来一些压力。如果你的母亲说:“你只有一次给人留下好的第一印象的机会!”你的压力可能就会更大。你可能会急切地去确认对方对你的态度,从而看到一些本不存在的东西。
20世纪80年代的一项社会心理学实验正好阐明了这个观点。一位化妆师在实验对象脸上画出逼真的“伤疤”,并告知实验对象,实验的目的是观察伤疤会如何影响人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实验对象被要求去和其他人对话,实验者会观察他们的反应。实验对象在镜子里见过自己脸上的伤疤,但是在接触他人之前被告知伤疤需要一点修饰,需要涂一点润肤膏,以免伤疤皲裂。其实,这时伤疤被擦掉了。然后实验对象开始了人际接触,心中怀着对自身样貌的错误印象。
在与他人接触之后,实验对象们接受问询:有没有注意到对话伙伴对伤疤有特别的反应?“噢,有”,他们中很多人都这么说。而且在播放对话对象的录像时,他们还能指出对方做出反应的具体地方。比如,实验对象觉得有时谈话对象会看向别处,目光显然是在躲避伤疤。[17]由此,一种感觉——一种不自在的自我意识——再次造成了感知错觉,误解了他人的行为。
现代生活充满了各种说不通的情绪反应,只有放到物种进化的环境中才能解释通。你可能会因为在公共汽车或飞机上发生的某件尴尬事情而不安数小时,尽管你知道可能再也不会遇见那些目击者,他们对你的评价也不会产生任何后果,但是心底还是难以释怀。为什么自然选择会这样设计,使生物体产生这种看似毫无意义的不适感?或许在我们祖先所处的环境中,这并非毫无意义,因为在狩猎—采集社会中,见识过你的某些表现的人,几乎都会再见,因此他们对你的评价也是重要的。
我母亲以前经常说:“我们如果意识到他人很少会在心里评价我们,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担忧别人对我们的评价了。”她是对的。我们假想他人会以某种方式评价我们,这种假想往往都是幻觉。同样,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他人对我们的评价很重要,这也是幻觉。但是在人类进化的环境中,这些直觉大多不是幻觉,这也是它们如今仍然如此执着存在的原因之一。
公开演讲和其他令人恐惧的事情
如果要说有什么事情比站在一群素未谋面的人面前更不自然的话,那就是在他们面前演讲。想到这样的情景,我们就会对未来产生恐怖的幻觉。假设你明天要做一个展示,或许是幻灯片展示,或许是更开放的展示。现在再做一个假设:你和我一样。如果你和我一样,随着展示的时间临近,你可能会感到焦虑。而且,这种焦虑可能会使你坚信事情将进展得不顺利,你甚至会想象出一些特定的灾难场景,而这些想象往往都不会发生。回想起来,这些因焦虑而起的末世念头都属于“误报”。
当然,有可能这种焦虑正是事情最终进展顺利的原因之一,或许焦虑激励你做出了一次很好的演讲。如果是这样的话,“幻灯片灾难的误报”就和“响尾蛇误报”有所不同。毕竟,你对响尾蛇就在身边的瞬间恐惧与响尾蛇到底在不在身边无关。相反,你的幻灯片灾难焦虑真有可能导致一场幻灯片灾难。
这真的有可能。但是说实话,尽管这样来讲,焦虑有时会提高效率,但是更多的时候,人们心怀很多无谓的焦虑,这是有害无益的。有些人会想象自己对一群人讲话时发生喷射性呕吐并因此饱受困扰,尽管回想起来,他们在对一群人讲话的时候,从未发生过喷射性呕吐的情况。
我也经历过很不合常理的幻灯片灾难焦虑,我曾在一次重要演讲的头天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担心“如果睡不着,第二天就会搞砸”。其实,这是一种过度简单的描述。我不仅担心睡不着,间或还会产生自我厌恶感,厌恶自己会那么担心睡不着。等怒气消退之后,我又会回归正题,继续担心自己睡不着,结果就真的睡不着了。
我可以自豪地说,我在大多数公开演讲之前都不会这样,但偶尔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人或许会辩称,这是自然选择为了增加我的存活或繁衍概率而设计的,我坚决不同意这种观点。同样,还有很多与人类社交相关的焦虑:参加一场鸡尾酒晚宴前的恐惧,其实不太可能导致任何值得恐惧的事情;担心“孩子在第一次睡衣晚会上的表现”,而这是一件你根本无法控制的事情;或是在幻灯片展示完成之后还要担忧,就好像“担心人们是否喜欢自己的演讲”可以改变别人的想法一样。
我想,上述三个例子都与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生存环境变化有或多或少的关系。我们祖先的生存环境中没有鸡尾酒晚宴、睡衣晚会,也没有幻灯片。狩猎—采集时代的祖先不需要面对一屋子的陌生人,不用送孩子去一个素未谋面的家庭过夜,也不用向一群根本不认识或大部分都不熟悉的人做演讲。
顺便提一句,这种进化而来的特性与环境之间的错位,并非现代现象。数千年来,人类的社会环境与人性定型时的社会环境相比,发生了很多变化。佛陀生在一个贵族家庭,也就意味着他生活的社会中有大量居民,人口数量远高于狩猎—采集时代的村落。尽管当时幻灯片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但是也有证据显示,人们会被要求在大庭广众之下演说,与幻灯片灾难焦虑类似的情绪也逐渐成形。在一次讲经时,佛陀把“当众出丑的恐惧”[18]列为“五惧”之一。这种恐惧如今仍然位列前五,甚至,有些调查显示,当众演说是最令人畏惧的事情。
需要再说明一点:我并不是说,社交恐惧在任何层面上都不能算作自然选择的产物。在我们祖先的生存环境——我们进化的环境——中,也有很多的社会交流,这类交流对我们的基因有很大影响。如果你的社会地位低下,朋友很少,那么你传播基因的机会就会大大降低,所以,即使不是通过幻灯片赢得他人的赞许,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很重要。同样,如果你的后代不善交际,那么就预示着繁衍后代的前景不乐观,你的基因也就难以继续传播。因此,使我们对个人社会地位前景以及后代社会地位前景产生焦虑的基因似乎已经被纳入人类基因库了。
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的社交焦虑可以被看作“自然的”。但是其运转的环境已经与其最初被“设计”时的运转环境发生了很大的不同,这或许就能解释为什么它们经常徒劳无果,还带来毫无价值的幻觉。因此我们会产生一些在本义和实用层面都错误的信念,比如笃信灾难将近,这些信念既不是真的,对我们也没有好处。
很多困扰我们的感觉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幻觉,如果你认同这种观点,那么冥想就可以被看作一种驱散幻觉的过程。
下面举一个例子。
2003年,第一次冥想静修之后几个月,我出差来到缅因州卡姆登,在一次流行科技年会上做演讲。演讲的前一天晚上,我凌晨两三点钟醒来,感到一丝焦虑。我醒着,思索“醒着思索坏影响”的坏影响,过了几分钟,我决定起身,坐在床上,开始冥想。我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但同时特别注意了自身的焦虑:腹部绷紧的感觉。我试着像在冥想静修时学习的那样审视这种焦虑,不做任何判断。焦虑本身不一定是坏事,也没有理由逃避。焦虑不过是一种感觉,于是我坐在那里,感受着它,审视着它。我不能说那种感觉很好,但是我越接纳这种感觉,越是不加判断地观察它,它带来的不悦就越弱。
随后发生的事情就和我在冥想静修时那次对咖啡因摄入过量的突破一样。焦虑好似从我身上剥离了,它就像我的心灵之眼所看到的一样东西,看它就像我在博物馆看一件抽象雕塑一样。它看起来好像一条由紧绷感编成的粗结绳,占据着腹部感觉焦虑的位置,但是感觉已经不再紧绷。几分钟前,焦虑还令我痛苦不堪,现在我却感觉它既不好也不坏。焦虑转化成这种中性状态之后不久就彻底消散了。享受了几分钟从痛苦中解脱的愉悦,我便躺下睡着了。第二天,我的演讲很顺利。
从理论上讲,我们有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克服焦虑。就像我那天晚上所做的一样,不要将注意力放在感觉本身上,而是审视与之相关的思虑。这正是认知行为疗法的作用方式:理疗师问你一些问题,比如:“根据你以往做展示的经历,搞砸这次展示的可能性大吗?”“如果你搞砸了,会立刻断送掉职业生涯吗?”如果你能看出自己的思虑缺乏逻辑,伴随思虑而出现的感觉就会随之弱化。
所以,认知行为疗法和正念冥想非常相似。二者都是在某种程度上质疑感觉的真实性。只不过认知行为疗法中问的问题更直白一些。顺便说一句,如果你想结合二者,成为新的理疗方式的奠基人,闻名世界,那么我只能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以正念为基础的认知行为疗法(MBCT)已经存在了。
幻觉的类型:扼要重述
如果我讲得够清楚,你应该会感觉受到了欺骗,不是被我欺骗,而是被你的感觉欺骗。我甚至没有谈及你的感觉所带来的最深、最微妙的幻象,这一点我会在本书后文中详述。与此同时,我们来回顾一下感觉可能产生误导的几个类型:
1.即使在“自然”环境中,我们的感觉原本也并非为准确描述现实而存在的。感觉出现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狩猎—采集时代的祖先将基因传递给下一代。如果实现这一目的需要我们的祖先陷入幻觉,比如使他们感到恐惧、“看见”并不存在的蛇,自然就会这样设计。这种“自然的”幻觉有助于解释我们对世界,尤其是对社交世界各种扭曲认知的理解:对自己、朋友、亲戚、敌人、点头之交甚至陌生人的扭曲认识。(差不多说全了吧?)
2.我们并没有生活在“自然的”环境中,这使得我们的感觉在引导现实时更不可靠。旨在制造幻觉的感觉,比如看到本不存在的蛇,或许至少有利于生物体的生存和繁衍。但在现代环境中,很多从达尔文主义层面对我们的祖先有利的感觉,如今却起到了反作用,它们可能会降低一个人的生存预期,暴怒、贪恋甜食都是很好的例子。曾经,这些感觉至少在实用角度上是“真的”,可以引导生物体趋向一定程度上对其有益的行为。但是现在,这些感觉更多的是误导。
3.所有这一切的根本都是幸福的幻觉。正如佛陀所强调的,我们不断努力追求更好的感觉,一定程度上是对“更好”所能持续时间的过高估计。而且,一旦“更好”结束,伴随而来的可能是“更糟”——一种不安的感觉,一种更深的渴求。早在心理学家描述“享乐跑步机”之前很久,佛陀就已看穿了。
他看不穿的是其本源。我们由自然选择塑造,自然选择的目标是实现基因增殖的最大化,别无他求。自然选择不仅不关心真相,也不关心我们的长期幸福。如果一种幻觉有利于我们祖先的基因传播,自然选择会毫不犹豫地迷惑我们,使我们分不清什么能够带来持久的幸福、什么不能。其实,自然选择甚至不关心我们的短期幸福。看看那些误报的代价就够了:被一条连续误报九十九次都不会出现的蛇吓到,可能会对人的心理健康造成极大的伤害。当然,好消息是,第一百次时,这种恐惧可能会帮助我们的祖先活下去,并最终令现在的我们可以有机会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继承了这种误报的倾向,不仅仅表现在躲避蛇这方面,还表现为其他恐惧和日常焦虑。正如亚伦·贝克(Aaron Beck)——有时被称为认知行为疗法的创始人——所写的那样:“血统存续的代价或许就是一生的不适。”[19]或者,可以用佛陀的说法,是一生的“苦”dukkha)。而且佛陀可能还会补充说,如果你能够直面“苦”的心理原因,这种代价就是可以避免的。
当然,本章并非对人类感觉的控诉。我们的感觉终归有一部分,或许大部分都能合理地为我们服务,它们不会过分扭曲我们眼中的现实,可以助力我们的生存、兴旺。我喜欢苹果,我厌恶抓刀刃、攀爬摩天大楼,这些都是对人有利的感觉。尽管如此,我希望你能看到“审视感觉”的好处,查验哪些值得遵从、哪些不值得遵从,尝试摆脱那些不值得遵从的感觉的束缚。
与此同时,也要认识到其中的困难。感觉从本质上会刻意制造困难,使我们难以辨别它们是有价值的还是有害的、是可靠的还是误导性的。所有的感觉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最初被“设计”出来,就是为了说服你遵从它们。一看它们的设定就感觉它们应该是对的,是“真”的。它们会努力阻挠你去客观地审视。
或许这也可以解释我为什么用了这么长时间才了解正念冥想的窍门——采用完全沉浸的方式,做一周冥想静修,而在此之前,冥想从来没有“奏效”过。但这并非唯一的原因。感觉还会通过其他一些方面影响我们,使我们难以转劣势为优势,改变与它们的主仆关系。另外,头脑运转的方式会使我们从一开始就难以进入冥想状态。其实,直到经历了第一次静修,我才开始意识到,想要达到正念冥想真正起作用的那个点是多么难,也知道了为什么会这么难。
另外,有益的事情总是需要耗费心力才能实现。经过那一次静修,我还认识到正念冥想的益处是多么大。其实,正念冥想的益处远不止前面提到的那些,我甚至有些担心自己会不会把冥想的体验说得太平凡了。当然,逐步掌控一些特别困扰你的感觉是很好的,如果认清这些感觉在某种意义上是“假的”对你有所助益,那就再好不过了。但是驯服令人困扰的感觉可能只是个开始。正念还有其他的维度,除了认识到“屈从于路怒症并非好主意”,还有很多更深刻、更精妙的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