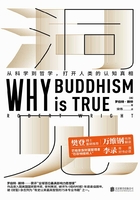
第3章 选择红色药丸
我要冒着过于戏剧化人类境况的风险,问一个问题:“你看过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吗?”
电影主人公叫尼奥(Neo,基努·里维斯饰),他发现自己住在一个梦境里。他的生活其实是精心打造的幻境。他深陷幻境,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躯体被装在一个黏糊糊的棺材大小的吊舱里——很多吊舱中的一个,一排又一排的吊舱,每个舱内都是一个沉入梦境的人。这些人被机器大帝(robot overlord)放入吊舱,在梦境中沉睡。
电影里有一个关于“红色药丸”的片段,很好地阐释了尼奥所面临的选择——要么继续生活在幻境中,要么醒来,回归现实。反叛军进入尼奥的梦境(或者严格来讲,他们的化身进入了尼奥的梦境),联络到了尼奥。反叛军首领墨菲斯(Morpheus,劳伦斯·菲什伯恩饰)向尼奥解释了当时的状况:“你是个奴隶,尼奥。同其他人一样,每个人呱呱坠地之后,就活在一个没有知觉的牢狱,当一辈子囚犯——一个思想被禁锢的囚犯。”他们把牢笼称作“母体”Matrix),但没法向尼奥解释“母体”到底是什么。墨菲斯说,想要了解全貌,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去看”。他给了尼奥两颗药丸,一颗红色,另一颗蓝色。尼奥可以吃下蓝色药丸,回到梦境世界;也可以吃下红色药丸,打破幻境的束缚。尼奥选择了红色药丸。
这是一个很严酷的选择:是选择被束缚的幻境人生,还是选择自由的充满真相的人生。说实话,这个选择太戏剧化,你也许会认为只有好莱坞电影里才会出现这样的情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做的人生选择远没有这样重大,而是要平凡很多。然而,电影上映时,很多人认为,这个故事反映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要做的选择。
我所想到的这类人,就是所谓的西方佛教徒,他们中的大多数生活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并非生来即佛教徒,而是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选择了佛教,或者至少是选择了某种佛教,这种佛教剥离了轮回和神明等亚洲佛教特有的各种超自然元素。这种西方佛教引领下的佛学实践在亚洲的僧侣中比较常见,但在普通人中并不盛行:冥想,同时沉浸于佛教哲学。(西方对佛教最普遍的两种理解——无神论、以冥想为核心——是错误的;大多数亚洲佛教徒信仰神明,但不信唯一的创世神,而且他们也不冥想。)
这些西方佛教徒,在看到《黑客帝国》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坚信眼中的世界是一种幻觉——即使并非完全是幻觉,也是极度扭曲的现实,使他们的人生扭曲,对他们和周围的人都造成了不良影响。他们觉得,幸亏有冥想和佛学,他们才能更清晰地看待事物。在他们眼中,《黑客帝国》就好似自身经历的一种寓言,因而这部电影也被称作“达摩电影”。“达摩”(dharma)一词有几层意思,包括“佛法”以及“佛教徒修行佛法应走的路”。随着《黑客帝国》的上映,“一心向佛”又有了一种简单易记的说法:“我选择红色药丸。”
1999年,《黑客帝国》刚上映时我就看了,几个月之后,我发现自己和这部电影之间有些关联。基努·里维斯为出演尼奥做准备的时候,导演沃卓斯基兄弟给了他三本书,其中一本就是我早几年写的《道德动物》。
我也不确定导演在我的书和电影《黑客帝国》之间看到了什么联系。但是我可以讲讲在我眼中二者的联系。对进化心理学可以有多种描述方式,下面是我在书中的一种讲述:进化心理学研究的是大脑如何由自然选择设计来误导我们,甚至奴役我们的。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自然选择有其优点,而且比起根本未曾出生,我还是愿意被自然选择创造出来(据我目前所知,宇宙也只给了我们这两种选择)。从任何意义上讲,成为进化的产物都不能完全算作被奴役,也不能算是彻底的幻觉。进化过的大脑赋予了我们很多能力,往往也赋予我们对现实基本准确的认识。
不过,自然选择最终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或者说,只“关心”一件事,因为自然选择只是一个盲目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设计师)。这件事就是把基因传递给下一代。过往有利于基因传播的基因特性兴盛繁荣,而不利的基因特性则被遗忘在角落里。在这些试炼中保留下来的基因特性里,有一些是精神特性——在头脑中固化的结构和算法,决定着我们的日常行为。所以,如果你问“是怎样的感知、思想和情感引导我们度过生命中的每一天”,从最基本的层面讲,答案不是“帮我们准确描绘现实的那些思想、情感和感知”。不管这些思想、情感和感知向我们展现的现实世界是怎样的,其实都无关紧要。这样说来,有时它们向我们展示的并非真实世界。我们的大脑有很多特性,其中一个就是欺骗我们。
也不是说这样有什么问题!我最幸福的一些时刻,有的就是来自幻觉。比如,相信掉了一颗牙之后,牙仙子就会来访。但是幻觉也可能带来糟糕的经历。我指的不只是噩梦这种回想时显然是幻觉的经历,还指那些你可能认为挺真实的经历,比如夜里躺着睡不着,焦躁不安;或连日感到无望,甚至沮丧;或对他人不可遏制的仇恨,这类情绪可能只是让你短暂地快慰,长久下去会腐蚀你的性格;或对自己不可遏制的恨意;或贪婪,有要买东西、吃东西或者喝东西的冲动,这种冲动的程度远超自己的实际需求。
焦躁、绝望、仇恨、贪婪……尽管这些情绪和噩梦这种毋庸置疑的幻觉不一样,但是如果你细细观察就会发现,它们都具备幻觉的构成要素。如果能摒弃这些要素,你就会拥有更好的生活。
想想看,如果你的生活变得更好,那么整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毕竟,绝望、仇恨和贪婪的情绪会催生战争和暴行。所以,如果我说的是真的(从基本源头来看,人类的痛苦心境和残暴本性很大程度上真的是幻觉的产物),那么将这些幻觉曝光就是有价值的。
听起来逻辑清晰,对吧?但是写完一本关于进化心理学的书[2]之后不久,我就开始认同一个问题:幻觉曝光的价值,取决于我们所说的到底是曝于怎样的光。有时,认识到痛苦的根源本身并不能带来太大的帮助。
日常幻觉
我们举一个简单也很基本的例子:吃垃圾食品会使我们得到短暂的满足感,但是几分钟之后,它就会使我们产生急切渴望更多垃圾食品的感觉。作为开头,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原因为以下两个。第一个原因是,这个例子证明了我们的幻觉是多么微妙。你在吃六个一盒的砂糖小甜甜圈时,根本不会想到自己是救世主,也不会担心外国特工要蓄谋暗害你。我在本书中要探讨的很多幻觉源头也有类似的特点:它们更多的不是关乎幻觉本身(眼见并非事物真相),而是“幻觉”一词更夸张的那层含义。不过,我在本书末尾还是辩称,这些幻觉会对现实造成极大的扭曲,使人迷失其中,就像彻彻底底的幻觉一样。
以垃圾食品的例子开头很好,第二个原因在于它是佛陀训诫的核心。好吧,仅从字面上来看它不可能是佛陀训诫的核心,因为两千五百年前佛陀讲经的时候,我们所知道的“垃圾食品”的概念还不存在。佛陀训诫的核心是一种普遍的动态:深深迷恋感官愉悦,这种快感充其量只是稍纵即逝的享受。佛陀传达的重要信息之一就是,我们寻求的快感会迅速消失,然后令我们渴求更多。我们花时间追求下一件令人满足的事物:下一个砂糖甜甜圈,下一次性接触,下一次职位的提升,下一次网上购物……但兴奋感总会退去,而且总会使我们渴求更多。滚石乐队的一首老歌里唱到的“我无法得到满足”,就是佛教所谓的人类境况。确实,尽管众所周知,佛陀宣称人生充满无尽的苦,但还是有些学者称这样的解读不够客观、准确,而且“dukkha”这个词虽然译作“苦”,但在某些语境下也可以翻译成“不满足”。
那么,对甜甜圈、性、购物或升职的渴求中,到底哪些算幻觉呢?不同的追求与不同的幻觉相连,不过眼下我们可以关注这些事物所共有的一种幻觉:对它们所带来的幸福感的过高预期。再次强调,这种幻觉本身是很微妙的。如果我问你,下一次升职,或者下一次考试得到优秀,或者再吃一个甜甜圈,是否能给你带来永恒的幸福,你肯定说“不能”,当然不能。另一方面,在我们追求此类事物的时候,也会出现对未来认知失衡的状况。我们更多是在预想升职带来的额外收入,却很少考虑随之而来的棘手责任。可能我们还经常抱有一种从未说出的潜意识,认为一旦达成某个长久追求的目标,一旦我们取得可能范围内的最高成就,就可以放松了,或者至少事情会一直变得更好。与之类似,看到甜甜圈时,我们立刻想到的是它多么美味,而不会想到吃下它几分钟之后就会更想吃下一个,也不会想到糖分刺激消失之后,人会感到疲倦和焦躁。
为什么快感会消失
关于人类为什么会持有这种失真的预期,我们不需要找火箭科学家来解释。只要找一位进化生物学研究者(甚至任何一个愿意花时间思考进化的人)就可以了。
下面讲讲其中的基本逻辑。人类在自然选择的“设计”之下去做某些事情,以帮助我们的祖先将基因传递给下一代,比如,吃饭、做爱、赢得他人尊重和超越对手等。我给“设计”一词加了引号,原因是自然选择并非有意识、有智慧的设计师,而是一种无意识的过程。但是,自然选择所创造的生物体又确实好似有意识的设计师之作,这个设计师不断修缮生物体,使他们成为高效的基因传播者。因此,从思维实验的角度出发,有理由将自然选择看作“设计师”,你们可以设身处地地从它的立场来思考:如果由你来设计善于传播基因的生物体,使生物体去追寻这些目标,延续这项事业,你会怎么做?换言之,假定进食、做爱、令同伴钦佩、战胜对手等行为能够帮助我们的祖先传播基因,那么你会怎样设计大脑,使他们能够追求这些目标?我认为,合理的做法是在设计中至少遵循下述三个基本原则:
1.实现这些目标应该能够带来快感,因为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都愿意追求能带来快感的事情。
2.快感不应该长时间持续。毕竟,如果快感不消退,我们就再也不用去追寻。我们的第一餐将成为最后一餐,因为根本不会再有饥饿感。同样道理的还有性爱:交配一次,余生都将沐浴在欢愉的回味中。这样根本不可能将大量的基因传递到下一代。
3.动物大脑应该更多地关注1(快感会伴随着目标的实现到来),而不是2(随后快感会迅速消退)。毕竟,如果你更关注1,就会纯粹由衷地追求食物、性爱和社会地位等,然而,如果你更关注2,就会产生矛盾心理。你或许会问,既然快感在得到之后不久就会消退,害你不断渴求更多,那么为什么还要如此积极地追求快感呢?找到答案之前,你就会感到厌倦,并开始后悔自己没有主修哲学。
将这三种设计原则结合起来,就能相对合理地解释佛陀诊断下的人类窘境。正如他所说,快乐易逝,这将使我们陷入周而复始的不满足。原因正是自然选择的“设计”:使快感易于消退,从而带来不满足,驱使我们追求更多快感。毕竟,自然选择并不“想要”我们快乐,它只是“想要”我们多产——从它的角度来看的多产,很狭隘的多产。使我们多产的方法就是使得对快感的预期非常强烈,但是快感的持续时间又不长。
科学家可以从生化层面观察多巴胺(与快感和快感预期相关的一种神经传导物质)的分泌来研究这种逻辑。在一项开创性研究中,他们以猴子为实验对象,将甜果汁滴到猴子的舌头上,同时监测猴子产生多巴胺的神经元。恰如预测的一样,果汁沾到舌头之后,多巴胺立刻就分泌出来。随后猴子受了训练,了解到灯亮起之后就能喝到果汁。随着实验的推进,灯亮使猴子们分泌的多巴胺越来越多,而“果汁真正沾到舌头”让它们分泌的多巴胺则越来越少。[3]
我们无法肯定那些猴子的感受,但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甜味的期待所带来的快感越来越强烈,真正从甜味中体会到的快感反而越来越少。[4]用日常语言解释这个推测是这样的:
如果你体验到一种新的快感——假设你一生从未吃过砂糖甜甜圈,别人给了你一个,让你尝尝——甜甜圈的味道刺激味蕾之后,你会分泌大量多巴胺。但接下来,你已经尝过砂糖甜甜圈的美味,下次再吃,多巴胺分泌量的峰值就会出现在你吃下甜甜圈之前,在你充满渴望地盯着甜甜圈看的时候(并且此时吃下一口甜甜圈所分泌的多巴胺量远远小于你第一次充满喜悦地吃甜甜圈时的分泌量)。吃之前多巴胺大量分泌是因为对更多快感的期许,而吃过之后多巴胺分泌量降低,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因为期许的破灭,或者是对过分期许的某种生化响应。如果你心怀这种期许——期待的快感比实际吃下所带来的快感更强——那么就是陷入了幻觉,或者换个不那么激进的说法,至少是被误导了。
听起来多少有些残酷,但如果不是这样,又能是怎样呢?自然选择的职责是制造机器来传播基因。如果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将某种幻觉植入机器,它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做。
无用的洞见
上文所述是从科学角度来解释幻觉。我们称之为“达尔文之光”。从自然选择的角度看待事物,我们就能看清幻觉被植入人类头脑的原因,也更有理由清晰地认识到这是一种幻觉。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切实地从幻觉中得到解放,那么这种解释的价值就很有限——这也是此处偏离主线所要探讨的核心观点。
不信?试试下面这个简单的实验:(1)思考,其实我们对甜甜圈和其他甜食的欲望是一种幻觉——欲望假意允诺给我们比实际上欲望得到满足所得更大的快感,而且蒙蔽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看不到伴随而来的失望;(2)在你做这样的思考时,拿起一个砂糖甜甜圈,放在面前十五厘米左右的地方。你会不会感觉到欲望神奇地变弱了?如果你和我是一样的,欲望就不会变弱。
这是我深入研究进化心理学之后的发现:了解你所处情境的真相(至少是进化心理学所揭示的真相),并不一定会使你的生活变得更好,事实上反而可能使你的生活变得更糟糕。你仍然会陷入这种出于本能的自然怪圈而难以自拔,徒劳地追寻快感——心理学家有时将之称作“享乐跑步机”(the hedonic treadmill)——但是现在你有了新的理由,去审视其中的荒诞。换言之,你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跑步机,是特意设计出来让你不停奔跑的,而且你通常到达不了任何终点。然而你还是不停地奔跑。
砂糖甜甜圈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我想说,了解你缺少控制饮食的自律性背后的进化论逻辑,其实也不完全是令人不悦的事。从这个逻辑中,你还能找到一些自我安慰的借口:对抗大自然母亲太难了,对吧?但是,通过进化心理学,我还更多地注意到幻觉如何塑造了其他行为,比如我如何对待他人,还有从各种意义上如何对待自己。在这个层面上,进化论中所谓的自我意识,有时会令人极为不适。
藏传佛教的冥想老师咏给·明就仁波切(Yongey Mingyur Rinpoche)曾经说过:“归根结底,幸福就是在因意识到精神痛苦而不适和被这种痛苦控制而不适之间做出选择。”[5]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想得到解放,摆脱那些阻碍你认识真正的幸福的思维,那么首先就要了解这些思维,而这个过程可能会令人不悦。
好吧,这是一种令人痛苦的自我意识,但也是有价值的——最终可以引导我们走向深层的幸福。但是我从进化心理学中得到的是两个世界中最糟糕的部分:令人痛苦的自我意识,却带不来深层的幸福。我既要忍受意识到精神痛苦的不适,还要面对受其控制的不适。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6]嗯,通过研究进化心理学,我感觉自己已经找到了真理。但是显然,我并没有找到道路。这也让我想起耶稣说过的另一句话:“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7]我觉得自己已经看清了人类本性的基本真理,也比以前更清晰地看透了各种幻觉是如何奴役我们的,但是了解这些真理并不等同于拿到了“赦免令”。
那么是不是有另外一种真理,可以给我自由?不,我认为没有。我认为,至少科学上并没有提供其他选择,不管人类喜欢与否,都是自然选择的进程创造了人类。但是写完《道德动物》之后几年,我开始思考:是否有一种方式能使这种真理在现实中得以操作——可以将人类本性和人类境况的真实、科学的真相转换成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不仅能够辨别、解释使我们受困的幻觉,还能帮助我们从幻觉中解放出来?我开始思考,一直听闻的西方佛学是否可以成为这样一条路。或许佛学教义里有很多东西与现代心理学理论不谋而合。又或许,冥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些真相的不同解读,也是针对这些真相采取的切实对策。
于是,我在2003年8月去马萨诸塞州乡下,开始了第一次冥想静修——整整一周的冥想,摒弃了电子邮件和外界消息等一切干扰,不与他人交谈。
“正念”的真相
你可以质疑:这样的静修能得到激动人心而影响深远的成果吗?那一次静修从广义上讲采用的是“正念冥想”,这种冥想方式近些年开始在西方流行并逐渐成为主流。通常描述中的“正念”——正念冥想要实现的目标——并非深奥、奇异的概念。所谓“正念生活”就是留心、注意当下发生的事情,用清晰、直接的方式体验,不要被各种精神困惑蒙蔽。停下来,闻闻玫瑰花香。
目前来讲,这样描述“正念”,虽准确,但不够深刻。这种普遍认知中的“正念”,其实只是正念的开端。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误导性的开端。你如果钻研过古代佛学著作,就会发现,那里面其实没有太多让世人停下来闻玫瑰花香的劝诫,即使你钻研的是以“sati”(正是这个词被翻译成“正念”)为主题的著作,也同样如此。事实上,有时这些著作似乎还传递出很不同于当前流行说法的信息。作为正念圈里最接近《圣经》的一本佛经,古代佛经《四念处经》(The Four Foundations of Mindfulness)提醒我们,人类的身体里“种种不净充满”,指导我们冥想身体的各种组成成分,即“屎、胆汁、痰、脓、血、汗、脂肪、泪、淋巴、唾、涕、滑液、尿”。经文还要求我们想象身体“或死一日,或死二日,或死三日,膨胀瘀黑,脓烂充满”。
我没听说过哪本关于正念冥想的畅销书用过“停下来,闻闻粪”之类的书名,也从没有听过哪位冥想老师建议冥想胆汁、痰、脓,或者我们终将成为的腐尸。如今我们接触到的所谓冥想传统,其实是对古代冥想传统有选择的继承,甚至是经过精心修饰的。
其中也没什么可谴责的。现代解读者对佛教的选择性甚至创造性的呈现,也没有任何问题。所有的精神传统都在随时代和空间发生演化,做着调整,佛教教义能在当今美国和欧洲拥有信众,也是这种演化的功劳。
从本书的角度来看,关键点在于这种演化(演化出了独具一格的21世纪西方佛教)并没有切断现行方法和古代思想之间的联系。现代正念冥想和古代正念冥想并非完全相同,但二者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如果你深究二者的内在逻辑,就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打个比方来讲就是,我们都生活在“母体”中。[8]虽然有时正念冥想听起来很平常,但是在现实中,如果孜孜不倦地探寻,你将看到墨菲斯口中红色药丸带你见识的世界,也就是看到“兔子洞到底有多深”[9]。
在第一次冥想静修期间,我有过一些震撼的体验。它们真的足够震撼,使我想要看看兔子洞到底有多深。于是我阅读了更多关于佛教哲学的书籍,跟佛学专家交流,最终又参与了更多的冥想静修,养成了每日冥想的习惯。
所有这些经历,使我更清晰地理解了《黑客帝国》被看作“达摩电影”的原因。尽管我已经通过进化心理学认识到,人类生来便陷入了很深的幻觉,岂知佛教描绘的图景反而更加夸张。佛教认为,幻觉以微妙、更为普遍的方式渗透到日常的感知和思考中,其发挥影响力的方式远超我们的想象,且看起来合情合理。换言之,在我看来,这种幻觉可以解释为,在自然选择设计下的大脑的自然产物。我越深入研究佛学,就越觉得它激进;但是当我越多地以现代心理学视角审视佛学,又越觉得它合情合理。现实生活中的“母体”,也就是我们生活着的这个真实世界,看起来越发像电影里的“母体”——或许没有电影中的那么离奇古怪,但也充满误导性,令人极度压抑,是人类迫切需要逃离的。
好消息恰是我相信的另外一件事:如果你想逃离“母体”,佛法修行和佛教哲学给了我们巨大的希望。给人期许的并非只有佛教。其他信仰系统的传统也有解决人类苦难的洞见和智慧。但是佛教冥想及其暗含的哲学思想,以一种惊人的直接且全面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佛学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直白无误的诊断,并给出了疗法。这种疗法一旦生效,不仅能带来幸福,还能带来清晰的远见:关于事物的切实真相,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比我们日常的观察更接近事物本质。
近年来开始冥想的人,主要以精神治疗为目的。他们修习正念,以此减压或专注于某个特定的个人问题。他们或许根本不曾意识到,自己所修习的冥想其实可以是一种深刻的精神修行,可以革新他们的世界观。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接近了一种基本选择的门槛——一种只有他们可以做的选择。正如墨菲斯对尼奥所说的:“我只能给你指出门的所在。真正跨过那扇门的是你自己。”
本书旨在为人们指出那扇门的所在,概要讲述了门的另一侧是怎样的世界,从科学的角度解释为什么门另一侧的世界比我们熟悉的世界更为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