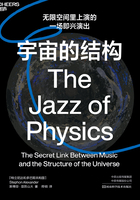
前言
以爵士之眼,透视物理学之奥秘
正是直觉告诉我,音乐是直觉的原动力。我的这项发现源自乐感。
——爱因斯坦
(当他被问到有关相对论的问题时)
我最为珍视类比法,它是我最信赖的导师。它们洞悉了自然界中的一切奥秘,但在几何学等领域中被忽视了。
——开普勒
人类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在宇宙诞生110亿年之后,在被我们称为“地球”的这颗行星上,富含矿物质的海洋充满生机,这种条件刚好适合孕育生命——不断发展、进化的艰难求存者。在宇宙演化的最后一段时期,人类已经成长起来,一边辛勤地耕作,一边大胆地仰视天穹,以探究“我们从哪里来”的大问题。
每一文化背景下的人都曾沉思:人类是如何诞生的?宇宙又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周围的空间是什么?人类来自哪里?无疑,这些我们在孩提时代就问过的问题,在科学界依然是最难回答的。这类问题既出于我们与生俱来的对自我起源的好奇,又出于我们自身知识的局限性。几千年来,我们只能用神话来作答。而从科学革命开始,我们一直在试图抛开神话,让科学家及其所应用的唯实的方法论来回答人类与宇宙的起源问题。虽然现代宇宙学家用复杂的方程和高科技的实验来佐证自己的理论,但他们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制造者”。虽然我们进行了精确的数学计算与实验,但现代物理学和宇宙学中还是不断出现新的问题,这迫使一些杰出的物理学家制造出某些神话,以解释人类在探索宇宙本质的过程中所发现的令人费解的现象。
科学家曾竭尽全力向普通读者解释那些构成现代宇宙学基础的概念,但在书中解释这些概念并非易事,因为用通俗的语言来阐释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这些通常用数学语言来描述的学科,实在是困难重重。那些复杂的方程甚至会蒙蔽物理学家的眼睛,以至于想完全理解或是设想出这些公式到底意味着什么,于他们自身而言都是一项艰巨的挑战。这一事实表明,我们需要另辟蹊径,以清晰的物理图像或类比法来呈现宇宙的结构。我发现,在思想交流方面,最成功的书籍必然都找到了最合适的类比法来映现物理学。实际上,类比推理法也是本书阐释的关键。
《宇宙的结构》这本书将带你进入理论物理研究进程之旅的最前沿。你将看到,与物理定律中固有的逻辑结构相反,在试图展示我们理解中的新远景时,我们通常必须接受一些荒诞且不合逻辑的演示过程,有时这些过程中还充满了缺乏深思熟虑的错误想法。对爵士乐手与物理学家来说,在各自的领域内努力掌握技术和理论固然十分重要,但若是想创新,他们就必须超越自身已经精通的技能。于理论物理而言,创新的关键是类比推理法。正确的类比是一门艺术,在本书中,我将向读者展示它是如何帮助我们开辟新天地,并横贯隐藏的量子世界,直抵宇宙广袤的超结构的。
在本书中,我将以音乐作为类比,它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现代物理学和宇宙学中的许多知识,还有助于揭开物理学家面对的一系列最新的谜团。在撰写本书时,通过这种类比思维,我甚至发现了解决早期宇宙学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的新方法。理解这一点的关键是“最初的结构是如何从空无一物、毫无特征的婴儿宇宙中产生的”,这也是宇宙学中一个重大的开放性问题。那些基本的物理定律以错综复杂的方式一起运作,从而创造并维持了宇宙那包罗万象的结构,而宇宙的结构则可以解释我们的存在,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正如乐理的框架催生了从《一闪一闪亮晶晶》到爵士乐萨克斯演奏家约翰·柯川(John Coltrane)的《星际空间》(Interstellar Space)的一切一样。在三位伟人(柯川、爱因斯坦和毕达哥拉斯)的启发下,通过跨学科研究,我终于发现,“绽放”的宇宙那“魔法般的”行为正是建立在音乐的基础之上。
大约10年前的一天,我独自坐在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镇(Amherst)主街上一家灯光昏暗的餐厅里,正为一份物理学报告做准备。突然之间,我产生了一种冲动。我找到了一台投币电话和一本本地的电话簿,并鼓起勇气给尤瑟夫·拉蒂夫(Yusef Lateef)打了个电话。拉蒂夫是一位传奇爵士乐音乐家,刚从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音乐系退休。但是那个时刻,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他。
怀着激动的心情,我的手指颤抖着在电话簿的条目之间划过,紧张地寻找着拉蒂夫教授的电话号码。终于,我找到了!当我拨出那个号码时,新英格兰轻快的秋风吹拂着我的面庞。冒着给对方留下粗鲁印象的风险,我一直在等他接听。
“你好?”终于,一道男性的声音从电话那端传来。
“你好,请问拉蒂夫教授在吗?”我问道。
“拉蒂夫教授不在。”那个声音直截了当地说。
“我可以给他留言吗?是有关1961年柯川作为生日礼物赠送给他的一幅图,我认为我找到了它潜藏的意义。”
电话那端的人沉默起来,良久之后说道:“我就是拉蒂夫。”
关于那张出现在拉蒂夫教授广受好评的《音阶与旋律图谱大成》(Repository of Scales and Melodic Patterns)一书中的图,我们聊了将近两个小时,这本书是对来自欧洲、亚洲、非洲,乃至全世界的音阶的汇编 。我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那张图是如何与另一个看起来毫不相关的领域——量子引力联系在一起的。量子引力是一个宏伟的理论,它试图将量子力学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统一起来。我告诉拉蒂夫教授,推动爱因斯坦的理论的几何原理也出现在柯川的图中。实际上,爱因斯坦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柯川与拉蒂夫也是。
。我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那张图是如何与另一个看起来毫不相关的领域——量子引力联系在一起的。量子引力是一个宏伟的理论,它试图将量子力学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统一起来。我告诉拉蒂夫教授,推动爱因斯坦的理论的几何原理也出现在柯川的图中。实际上,爱因斯坦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柯川与拉蒂夫也是。
拉蒂夫教授告诉了我一些重要的信息,即那张图与四度圈和五度圈很相似。他对哲学和物理学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向我讲授了他的“自动灵魂治疗” 音乐的概念,这是一种来自人类身体、精神以及灵魂的音乐。
音乐的概念,这是一种来自人类身体、精神以及灵魂的音乐。 在我将宇宙与音乐建立起联系的后续研究中,这个概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拉蒂夫鼓励了我,并且肯定了我的想法,即音乐与宇宙结构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那一天就像一幅立体图画般逐渐清晰起来,我在物理学与音乐两个领域中的平行生活在我眼前慢慢融合,最终创造了一个新的图景。
在我将宇宙与音乐建立起联系的后续研究中,这个概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拉蒂夫鼓励了我,并且肯定了我的想法,即音乐与宇宙结构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那一天就像一幅立体图画般逐渐清晰起来,我在物理学与音乐两个领域中的平行生活在我眼前慢慢融合,最终创造了一个新的图景。
柯川深深地痴迷于爱因斯坦及其理论。爱因斯坦因其对物理学的直觉超越数学局限的能力而出名,这可能是他最大的天赋。他总是通过“思想实验”(gedankenexperiments,德文)来进行即兴推演,从而想象出那些无人能完成的实验的结果。例如,爱因斯坦曾想象:如果乘着一束光旅行,会是什么感觉呢?成功地想象出结果是需要洞察力的。爱因斯坦拥有的另一项资源正是音乐。他会弹钢琴,虽然这一事实并不广为人知。他的第二任妻子埃尔莎曾说:“音乐有助于他思考自己的理论。工作时,爱因斯坦偶尔会走到钢琴前弹奏几个和弦,记下某些东西后,又回到研究之中。”一方面,爱因斯坦运用了数学的严谨性;另一方面,他又有着非凡的创造力与敏锐的直觉。本质上,他是一位即兴演奏者,正如他心中的英雄莫扎特一样。爱因斯坦曾表示:“莫扎特的音乐既纯粹又美丽,在我看来,它是宇宙内在美的一种映射。”
柯川的曼荼罗(图0-1)让我意识到,即兴演奏是音乐与物理学的一个共同特征。与爱因斯坦进行思想实验一样,某些爵士乐即兴演奏者在独奏时也会在脑海中构建一些图案和形状。我猜想,这正是柯川所绘图案的意义。

图0-1 柯川的曼荼罗
注:柯川于1961年作为生日礼物赠送给拉蒂夫的图。
图片提供者:艾莎·拉蒂夫(Ayesha Lateef)。
柯川于1967年逝世,仅在阿尔诺·彭齐亚斯(Arno Penzias)与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发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CMB),即宇宙大爆炸残留物两年之后。这项发现推翻了静态宇宙论,并且证实了宇宙膨胀理论,正如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所预示的那样。在柯川最后录制的唱片专辑中,有三张分别名为《恒星区域》(Stellar Regions)、《星际空间》和《宇宙之声》(Cosmic Sound)。柯川的音乐中包含着物理学,并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正确地意识到了宇宙膨胀是反引力的一种形式。在小型爵士乐团中,“引力”的拖曳来自节奏乐器中的贝斯和鼓。《星际空间》中的曲目就是柯川磅礴的独奏表演,它们不断膨胀,最终挣脱了节奏乐器的引力拖曳。柯川是一位音乐革新者,对物理学知识信手拈来。爱因斯坦是一位物理学的革新者,对音乐了如指掌。不过,他们之所为并不新奇。他们都是在重建音乐与物理学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几千年前毕达哥拉斯(那个时代的“柯川”)第一次提出音乐中的数学时建立的。由此,毕达哥拉斯的哲学变成了“万物皆数”,而音乐与宇宙都是这种哲学的表现形式。“天体之声”在行星轨道的数学模型中回响,以一根振动的弦演奏着和声。
追随着柯川和爱因斯坦的脚步,在《宇宙的结构》这本书中我们也会重游古老的王国,在那里,音乐、物理学与宇宙是一体的。我们将会看到毕达哥拉斯与其他人是如何理解声音的,以及他们的思想与实践是如何经开普勒和牛顿等伟大思想家的改造,最终发展成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弦与波的动力学的。2500年后,弦理论的发明者正忙于研究如何用基本弦来统一自然中的4种基本作用力,但他们中有多少人记得或者重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方程——波动方程,正是根植于对物理学和音乐之间的普遍联系的研究。
本书也是对类比法的力量的一次运用。通过类比法将物理学与音乐重新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借由声音来理解物理学。我们将会看到,和声与共振是一种普遍现象,可以用来解释早期宇宙的动力学。我们还将看到,大量有关宇宙的数据表明,在大约140亿年前,一系列相对较简单的声音模式发展成了诸如星系和星系团这样的结构,并最终使行星与居于其上的生命的形成成为可能。
我们还将讨论生命的量子起源。在大多数音乐中,一个音阶中的音调的范围受到离散振动的限制。亚原子领域也充斥着离散的波包,这些波包被称为量子(相关学科因此被称为量子力学)。大型强子对撞机证实了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的存在,在此基础上,我们验证了构成许多物理实在性的范式正是量子场论(Quantum Field Theory)。这是一个在数学上令人生畏的物理学领域。让我们感到幸运的是,这个领域中的许多知识都可以通过音乐元素来理解。例如,量子对称性破缺在产生基本作用力与基本粒子方面至关重要,而音乐结构(如大调音阶)上的对称性破缺则创造出一种合成的分解感。在我们的探索之路上,即兴演奏将会发挥重要作用,为我们提供一种工具以理解量子世界那奇异的动力学:它内在的不确定性,以及“每个结果实际上都是所有可能的结果的叠加”的理念。
我意识到,若想解开理论科学的奥秘,最重要的工具除了数学就是简化正在使用的系统,并借助某些乍看上去可能完全不相关的学科来做类比。这些类比有其局限性,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找到通向新发现的大道。这就像跨学科的“跨礁玩浪”(rock hopping),从无知之岸跳向知识彼岸,而生命的长河从两岸之间汹涌而过。
从我们所能想象到的最小尺度到最大尺度,物理学在揭开大自然的秘密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物理学界如今却陷入了困境。物理学家在一些基本问题上遇到了困难,比如宇宙的“微调”,这是自然中形成碳基生命的4种基本作用力相对强弱平衡的一个例子。但我认为,物理学会迎来一个兼容并包、多学科交融的新时代——这是一种即兴演奏式的物理学。这种物理学根植于交叉学科间的类比,将界限推向了类比法的极限。
这便是我的生命之旅。我是一个纽约出租车司机的儿子,我父亲来自特立尼达(Trinidad)。十几岁时,我便迷恋上了维克托·魏斯科普夫(Victor Weisskopf)的著作《有幸成为一位物理学家》(Privilege of Being a Physicist)。我的家人则希望我学习音乐。“只有两种事物能赋予生命价值,”诺贝尔奖得主、该书作者魏斯科普夫说,“那就是莫扎特和量子力学。”我热爱莫扎特,但在那时,我对量子力学所知不多。然而,这最终成为一段长久的“爱情”的开端。这段“爱情”成就了我的未来,并且包含了除量子力学与莫扎特之外的许多事物,而宇宙学与柯川将成为这种激情的核心部分。在成为一位物理学家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了一些那时预料之外的名字。我为自己铺设了一条融合爵士乐与物理学的非凡之路,最终我成了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我能取得这些成就,离不开过去的20年里老师和朋友的指导与认可,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超导理论的先驱、热爱音乐的利昂·库珀(Leon Cooper),以及奥尼特·科尔曼(Ornette Coleman)和布莱恩·伊诺(Brian Eno)等热爱物理学的音乐家。他们使我明白了跨学科思维的重要性,以及类比法是扩展知识边界的重要手段。
领略这些重要人物的思想是我们旅行的一部分;按照乐理的节奏轻叩节拍是我们旅行的一部分;追寻宇宙结构的演化是我们旅行的一部分;在物理学与音乐之间构建类比是我们旅行的一部分;不进行精确的类比,以及清晰地论证问题所需的严格计算,也是我们旅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