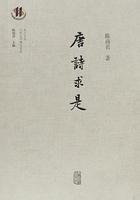
七 《全唐诗》拟题错误举例
拟题错误或不当者,前文已经分别有所论列。以下以《全唐诗》为例,指出一些拟题错误的典型例子。
(一)拟题过于宽泛而无助诗意理解。卷八〇八义净《西域寺》:“众美仍罗列,群英已古今。也知生死分,那得不伤心。”按此诗源出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为义净在王舍城观那烂陀寺,惊其规模之宏伟而所发感叹之数句。义净从广州渡南海到天竺求法,非如玄奘之取途西域,诗则在天竺所作。拟题《西域寺》,显然以为凡往印度者皆经西域,印度之佛寺可统称西域寺。
(二)以原文献中叙事原文为诗题。卷八〇八义净诗《玄逵律师言离广府还望桂林去留怆然自述赠怀》:“标心之梵宇,运想入仙洲。婴痼乖同好,沈情阻若抽。叶落乍难聚,情离不可收。何日乘杯至,详观演法流。”又《余以咸亨元年在西京寻听于时与并部处一法师莱州弘祎论师更有三二诸德同契鹫岭标心觉树然而一公属母亲之年老遂怀恋于并州祎师遇玄瞻于江宁乃叙情于安养玄逵既到广府复阻先期唯与晋州小僧善行同去神州故友索尔分飞印度新知冥焉未会此时踯躅难以为怀戏拟四愁聊题两绝》:“我行之数万,愁绪百重思。那教六尺影,独步五天陲。”“上将可陵师,匹夫志难移。如论惜短命,何得满长祇。”按三诗均见《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叙江宁僧玄逵欲往天竺求法,行至广州,因病而不行:
行至广州,遂染风疾,以斯婴带,弗遂远怀。于是怅恨而归,返锡吴楚。年二十五六,后僧哲师至西国,云其人已亡,有疚于怀。嗟乎不幸,胜途多难,验非虚矣!实冀还以法资,空有郁蓝之望;复欲旋归遗锷,徒怀陇树之心。乃叹曰:“淑人斯去,谁当继来?不幸短命,呜呼哀哉!”九仞希岳,一篑便摧。秀而不实,呜呼哀哉!解乎易得,行也难求。嗟尔幼年,业德俱修。传灯念往,婴痼情收。慨乎壮志,哀哉去留。庶传尔之令节,秉辉曜于长秋。于时逵师言离广府,还望桂林,去留怆然,自述赠怀云尔。五言(诗略)。净以咸亨元年在西京寻听,于时与并部处一法师、莱州弘祎论师,更有二三诸德,同契鹫峰,标心觉树。然而一公属母亲之年老,遂怀恋于并川;祎师遇玄瞻于江宁,乃敦情于安养。玄逵既到广府,复阻先心,唯与晋州小僧善行同去。神州故友,索尔分飞,印度新知,冥焉未会。此时踯躅,难以为怀,戏拟四愁,聊题两绝而已。五言(诗略)。
前半叙义净在西国闻玄逵已亡,寄言哀悼,并录玄逵在广州去留之际之自述诗。《全唐诗》在此误读原文,将玄逵诗误为义净诗。后半义净追述自己咸亨间与僧友欲往鹫峰求法,但处一、弘祎皆因故未能成行,玄逵行至广州而因病归死,仅能与小僧善行同往,因此而作两绝寄怀。《全唐诗》编者显然觉得此处文义很难概括,干脆将原文之一大段文字钞作题目,形成这样的奇观。
(三)因所见书文本有错误而致误读。《全唐诗》卷八〇八收慧宣《咏赐玄奘衲袈裟》:“如蒙一被服,方堪称福田。”又收道恭《出赐玄奘衲袈娑衣应制》:“福田资象德,圣种理幽薰。不持金作缕,还用彩成文。朱青自掩映,翠绮相氤氲。独有离离叶,恒向稻畦分。”二诗均源出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
〔贞观二十二年〕秋七月景申夏罢,又施法师衲袈裟一领,价直百金。观其制作,都不知针线出入所从,帝库内多有前代诸纳,咸无好者,故自教后宫造此,将为称意,营之数岁方成,乘舆四巡,恒将随逐。往十二年,驾幸洛阳宫,时苏州道恭法师、常州慧宣法师并有高行,学该内外,为朝野所称。帝召,既至,引入坐言讫,时二僧各披一纳,是梁武帝施其师,相承共宝。既来谒龙颜,故取披服,帝哂其不工,取衲令示,仍遣赋诗以咏。恭公诗曰(诗略)。宣公诗末云(诗略)。意欲之,帝并不与,各施绢五十匹。即此衲纲也,传其丽绝,岂常人所服用,唯法师盛德当之矣。
按“往十二年”,《慈恩传》各本多作“往二十二年”,近人校点本从宋本改。太宗于贞观十二年曾示二僧袈裟,二僧献诗欲得之,太宗并不予,至二十二年始赐玄奘。因传本一字之误,至《全唐诗》误拟诗题。
(四)拟题时并没有考虑应以作者当时的立场还是后代的立场来表达。如《太平广记》卷二四一引《王氏闻见录》:
蜀后主王衍(中略)至十月三日,发离成都。四日,到汉州。(中略)九日到凤州。(中略)上梓潼山,少主有诗云(诗略)。宣令从官继和。中书舍人王仁裕和曰:“彩仗拂寒烟,鸣驺在半天。黄云生马足,白日下松巅。盛德安疲俗,仁风扇极边。前程问成纪,此去尚三千。”成都尹韩昭、翰林学士李浩弼、徐光浦并继和,亡其本。至剑州西二十里已来,夜过一磎山,忽闻前后数十里军人行旅,振革鸣金,连山叫噪,声动溪谷。问人,云将过视人场,惧有鸷兽搏人,是以噪之。其乘马皆咆哮恐惧,棰之不肯前进。众中有人言曰:“适有大驾前鸷兽,自路左丛林间跃出,于万人中攫将一夫而去。其人衔到溪洞间,尚闻唱救命之声。况天色未晓,无人敢捕逐者。”路人罔不溜汗。迟明,有军人寻之,草上委其馀骸矣。少主至行宫,顾问臣僚,皆陈恐惧之事。寻命从臣令各赋诗。王仁裕诗曰:“剑牙钉舌血毛腥,窥算劳心岂暂停。不与大朝除患难,惟于当路食生灵。从来户口资嚵口,未委三丁税几丁。今日帝皇亲出狩,白云岩下好藏形。”(下略)至剑门,少主乃题曰(诗略)。后侍臣继,成都尹韩昭和曰(诗略)。王仁裕和曰:“孟阳曾有语,刊在白云棱。李杜常挨托,孙刘亦恃凭。庸才安可守,上德始堪矜。暗指长天路,浓峦蔽几层。”(下略)过白卫岭,大尹韩昭进诗曰(诗略)。少主和曰(诗略)。王仁裕和曰:“龙 飘飖指极边,到时犹更二三千。登高晓蹋巉岩石,冒冷朝冲断续烟。自学汉皇开土宇,不同周穆好神仙。秦民莫遣无恩及,大散关东别有天。”洎至利州,已闻东师下固镇矣。
飘飖指极边,到时犹更二三千。登高晓蹋巉岩石,冒冷朝冲断续烟。自学汉皇开土宇,不同周穆好神仙。秦民莫遣无恩及,大散关东别有天。”洎至利州,已闻东师下固镇矣。
《王氏闻见录》为王仁裕叙述平生见闻的著作,原书中谈到自己时应该作第一人称,《太平广记》引录时一律改作第三人称。引录的一段原文甚长,是叙述在前蜀灭亡前夕,前蜀主王衍率后妃、群臣北巡秦凤的经历。王仁裕追随后主一行,先后作诗四首。《唐音统签》卷七五五、《全唐诗》卷七三六分别拟题为《从蜀后主幸秦川上梓潼山》《奉诏赋剑州途中鸷兽》《和蜀后主题剑门》《和韩昭从驾过白卫岭》,史实并没有错误,但称“蜀后主”是前蜀亡后的口气,而“奉诏”“从驾”则为追随前蜀皇帝之口气。这组拟题,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五)多种拟题均因没有追究唱和始末而皆误。《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载:
周墀任华州刺史。武宗会昌三年,王起仆射再主文柄,墀以诗寄贺,并序曰:“仆射十一叔以文学德行,当代推高。在长庆之间,春闱主贡,采摭孤进,至今称之。近者,朝廷以文柄重难,将抑浮华,详明典实,由是复委前务,三领贡籍。迄今二十二年于兹,亦缙绅儒林罕有如此之盛。况新榜既至,众口称公。墀忝沐深恩,喜陪诸彦,因成七言四韵诗一首,辄敢寄献,用导下情,兼呈新及第进士。文场三化鲁儒生,二十馀年振重名。曾忝《木鸡》夸羽翼,又陪金马入蓬瀛。(原注:墀初年《木鸡赋》及第,尝陪仆射守职内廷。)虽欣月桂居先折,更羡春兰最后荣。欲到龙门看风水,关防不许暂离营。”时诸进士皆贺。起答曰:“贡院离来二十霜,谁知更忝主文场。杨叶纵能穿旧的,桂枝何必爱新香。九重每忆同仙禁,六义初吟得夜光。莫道相知不相见,莲峰之下欲征黄。”
以下在“王起门生一榜二十二人和周墀诗”的总题下,录二十二人诗,仅于诗下注姓名和表字。在后世著作的引录中,《唐诗纪事》卷五五未署题,但于诗末注云:“自肇至王甚夷,各和主司王起一章,多用起韵。”而《豫章丛书》本《文标集》卷下收卢肇诗《奉和主司王仆射答周侍郎贺放榜作》。《全唐诗》卷五五一收卢肇诗,卷五五二收丁稜等二十人诗,皆以《和主司王起》为题,卢肇下注“一作《奉和主司王仆射答周侍郎贺放榜作》”,丁稜下注“一作《和主司王仆射答华州周侍郎贺放榜作》”,高退之下注“一作《和主司王仆射酬周侍郎贺放榜》”,孟球等十八人下注“一作《和主司酬周侍郎》”。同书卷五五三姚鹄下所收,诗题作《及第后上主司王起》。罗列这些材料,是要指出同一史源(只有姚鹄一诗可能出自其诗集)的同一次唱和,题目居然有六种之多,而且除姚鹄一题稍近事实外,其他各题居然都错了。从前引《唐摭言》的事实是,会昌三年,王起在长庆间曾知贡举后的二十年,以八十五岁高龄再主文闱而放二十二人及第。长庆间及第的周墀时任华州刺史,驰诗寄贺。《唐摭言》既言“时诸进士皆贺”,又言“王起门生一榜二十二人和周墀诗”,是应为新及第进士分别和周墀诗而进贺。二十二人诗中,卢肇、裴翻、樊骧、崔轩、林滋、李仙古、丘上卿、王甚夷八人诗皆次周诗原韵,分别以生、名、瀛、荣、营五字押韵,如卢肇诗:“嵩高降德为时生,洪笔三题造化名。凤诏伫归专北极,骊珠搜得尽东瀛。褒衣已换金章贵,禁掖曾随玉树荣。明日定知同相印,青衿新列柳间营。”丁稜、高退之、孟球、张道符、石贯、李潜、唐思言、金厚载八人诗则同用清韵而非次韵。不用周诗韵部者仅姚鹄、刘耕、蒯希逸、黄颇、孟宁、左牢六人,但没有一人用王起的阳韵。《全唐诗》所收各诗之拟题,虽然逐一的来源似乎还难以完全理清,但显然都沿袭了《唐诗纪事》“各和主司王起一章”的误读,认为是诸人和王起答周墀诗之作。至于拟题中直呼王起之名,亦不妥当,但为另一问题。
其他问题尚多,容以后稍作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