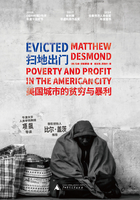
第1章 导读——家:占有与驱逐
项飙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谢伦娜·塔弗(Sherrena Tarver)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财良机。谢伦娜是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为数极少的黑人全职房东之一,靠出租房屋赚钱。次贷危机后,她以每月一套房的速度在贫民区置产。贫民区里大量家庭因为不能按期付按揭,被扫地出门,房价跌至低谷。被扫地出门的家庭不得不租房,所以房租不降反升。
谢伦娜买的这些房子特别便宜,因为它们没什么升值空间。但在黑人贫民区的房租又高得出奇。穷人买不起房,只好租;再者,他们(特别是黑人)在别处租不到房,只能在贫民区里租。贫民区因而成了租房生意的一脉金矿:不少在富人郊区赔了本的房东,都指望着在这里把钱捞回来。
然而,在贫民区出租房产也有它的问题:穷人没钱。很多穷人靠联邦政府发的救济金过活;有时候房租要吃掉家庭总收入的70%,所以他们不时拖欠房租,所以他们不断被逐出家门。
《扫地出门》一书解释了,强行驱逐是将一些人的贫困转化成另一些人的超额利润的关键环节。2009年至2011年间,密尔沃基市每8名房客中至少有1人经历过强制性搬迁。2012年,纽约市的法院每天都会判出将近80笔以未缴租为由的驱逐令。被驱逐过的房客因为有了这个记录,很难再租到好房子。他们只能住进条件更为恶劣的社区。贫穷、暴力、毒品进而聚集到了一起。为保证按时缴租、不再被驱逐,他们更要节衣缩食。这样,驱逐不仅是贫困的结果,还是致使贫困不断恶化的原因。贫穷能够成为利润的源泉,并不是因为穷人被剥削,而是因为他们不断突破自己生存条件的底线——吃本来不能吃的东西,住本来不适合住的地方——为没有价值的房子创造出不菲的租金收入。驱逐是不断突破底线的重要驱动力。
《扫地出门》是一部非常严肃的学术著作。除了历时一年多的实地调查、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大范围的档案检索,作者又在成书后专门聘请了一名校对人员,对他所有的田野笔记一一进行核对。但是,它又和通常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很不一样;这里没有理论假设、没有框架,甚至没有概念。学术作品中常见的内容,比如文献回顾和数据陈列,也都隐身于脚注间。整本书像是一部深度的纪录片,从一个场景推移至另一个场景。作者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直白而细致的描写有如特写镜头,把各个人物的表情语气、所感所思直接呈现给我们。诸多具体场景叠加在一起,逐渐呈现出强制驱逐这一现象的历史、制度和结构特征,及其后果。
最让我感叹的是,马修能从“看到的东西里看到东西”。我们时常无视眼前的事物,又经常看见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之所以对眼前的事物熟视无睹,是因为我们觉得它们不符合自己的理论视角(比如阶级、性别、自我意识),因而显得琐碎而无“意义”。与此同时,我们拿自己的框架去诠释世界,生造出“意义”,好像看见了一些似有若无的东西。当我们看不清眼前琐事对于受访人的意义、看不清受访人的真实感受时,我们只好灌入自己的想法,把不在眼前的东西拉扯进来。事实上,直观的感受才是生活实践的血液,观察者的臆想无非是窗外的雨点。当我为了写这篇导读和马修对谈时,他援引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话说,如果你在博物馆看到一幅画,说“它是新古典风格的”,这是一种肤浅无聊的“看法”。站在一幅画面前,为什么一定要下这样的定义?为什么不以自己的直觉进入画本身?
我问马修,他是如何与受访人建立起那种强烈直接的同理心的。他强调,这不是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而是你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方式的问题。对身边的事物予以高度的关注,是他一贯的生活方式。“你看坐在眼前的朋友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是蓝色。但那究竟是哪一种蓝色,它和通常说的蓝色可能又不一样。”只有深入到细节,才能看清生活的肌理。他很受几位被他称作是“观察天才”的小说家的启发。除了大家熟知的《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的作者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和《天堂》(Paradise)的作者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之外,他还提到了拉尔夫·艾里森,莱斯利·马蒙·西尔科,丹尼斯·约翰逊,以及杰斯米妮·瓦德。他们从大家都能看到的东西里,看到了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
我觉得马修还有一种能力,能在陌生的受访者身上看到他自己。因为在受访者身上看见了自己,受访者就是很具体真实的人,而不是被理论定义了的“角色”。调查者在受访者身上看到自己,也会让受访者在调查者身上看见自己,彼此都可以放松。调查者无需时刻惦记着那些事先准备好的问题,用不着为一问一答间可能出现的冷场担心。如果一时无话可说,就观察对方怎么自言自语,怎么在沙发上发愣打瞌。受访者对马修坐在身边埋头写笔记也毫不在意。
马修的这个能力和他自己的生活经历是离不开的。他出身贫寒,父母曾有过被驱逐的经历。后来他又认识了不少被驱逐的、不得不自己动手盖房的游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只能研究和自己生活经历相似的群体。人类学实地调查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通过长时间的亲密互动,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要达到这种状态,靠投入、靠执着、靠想象,归根到底靠对生活的关怀和热爱。能与街头小贩随意地聊天、和建筑工人轻松地玩笑,是一种相当重要的能力。如果不培养这种能力,那么方法和理论学得越多,你和这个世界的距离也许就会拉得越远。
马修能从受访者身上看到自己,在书写时却全然没有提到他自己。全书采用第三人称。这和80年代后期以来的民族志书写风格迥然不同。从影响深远的《写文化》(Writing Culture)一书出版后,把自己写入民族志几乎成了人类学家的一项义务。学者们强调,研究者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我们总是以某种具体身份、在某个具体位置上进行观察和思考的。所以需要阐明自己的立场,说明如何在互动中理解对方。几乎在同一时期,西方媒体写作也越来越多地引入作者本人的身影。这种情况在中国也相当明显。如果我们把上世纪30年代、80年代的报告文学,和2010年以来的非虚构写作做一个对比的话,“我”的介入是一个突出的变化。从“我替你看”到“我带你看”——作者的行踪构成报道的基本线索,报道者双目所及即报道的基本内容。
然而,由此带来的新问题同样不言而喻。读者固然清楚地知道你看到了什么、你怎么想,但是你的所见所想,和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些“看到什么就写什么”的写作方式蜕化成了一种自然主义,没有背景梳理、没有系统分析、尤其没有对信息的可靠性、代表性、局限性做检测。信息碎片化、感官化。调查者固然不是全知全能,但这并不意味这世界就无法被系统客观地分析;调查者不能被视为调查对象的代表,但是调查者不能就此推卸向公众提供可靠信息的责任。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仅仅是我们在后现代认识论的轨道上滑得太远吗?人们一般认为《写文化》代表了人类学学界内部的反思和转化。但是媒体、甚至文学界在同时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说明背后可能有更普遍也更深刻的原因。80年代后期的北美和当下的中国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具体矛盾复杂多样,个体焦虑凸现,但是社会却没有统一的“大问题”感。“大问题”感,在冷战初期、在民权运动、在反越战运动中是很明显的。身份政治的兴起,使得个体经验替代了公共问题,成为思考的引擎。
除了大问题感的消解,“公共感”的削弱也可能造成了“我文本”的兴起。原来现实主义作家和实证主义学者在描述世界时那么自信,完全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位置缺乏反思吗?不尽然。他们有那份自信,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代表一个“公共”:他们在代表公共观察问题,在向公共报告他们的发现,在推进公共改变。现在,对个体多样性的强调,替代了对公共的想象。这样,我碰到、我听到、我看到就成了最真实的内容。
马修这么写,我不觉得他是刻意要在文本形式上复古。他可能认为这是最自然、最经济的写法。马修不可能不了解80年代以来的反思性写作,但他没有在简单的客观主义的思维上,相信一个先验的公共、跟着预设的问题走。他的公共感和问题感是在和调查者深度互动中形成的,是具体的、扎根的。
中国近来的非虚构写作、私写作、自媒体的发展令人兴奋,但是如何在这些多样、分散的表达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大问题感和公共感,将是一个重要课题。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样本。
马修告诉我,他要把这本书写成一个道德批判。这个道德批判的主要基础,如书在结语部分中强调,是认为家居(home)是生活意义的载体。“家是我们生活的重心。家是避风港,是我们忙完学习工作之余、在街头历劫种种之后的去处。有人说在家里,我们可以‘做自己’。只要离开家,我们就会化身为另外一个人。只有回到家,我们才会褪下面具。”他还援引法国政治学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话:“要逼着一个人站出来关心整个国家的事务,谈何容易?但如果说到要在他家门前开一条路,他就会立刻感觉到这件公共意义上的小事会对他的切身利益产生巨大的影响。”
马修对家居的阐释,很多中国读者听来可能像丝竹入耳。而书中记录的被驱逐的悲惨故事,更让一些读者感到买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只有占有了房,才不会被驱逐。一张房产证,意味着安全、尊严、自我、意义,意味着可以放松地去参加同学会。中国的私人住宅拥有率领跑全世界(90%),要比典型的福利国家瑞士(43%)高出一倍左右,也远高于日本(62%)、韩国(57%)等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上较为超前的国家。
然而,家居是不是从来就是“人之为人的泉源”?游牧者,山民,水上民族居无定所,是不是就丧失了他们的人格(personhood)和自我身份意识(identity)?
我读大学前的十八年人生是在两个完全没有产权证的家度过的。一个是我外祖父所在工厂的宿舍,由码头边的仓库改建而成;另一个则在我母亲工作的中学,由教室改建的宿舍。虽然我们不必担心被驱逐,但要是单位要我们搬,我们也必须搬。我并不觉得,在仓库和教室改建而成的家中居住的我们,不算是完整的人。现在身边的“炒房团”,尤其是从我们这一代开始的“房奴”,过得也并不比我们舒心。
有人可能会说,“房奴”总比无家可归者好。如果人人都成为“房奴”,没有人被驱逐,岂不是很好?事实可能没那么简单。当作为基本生活资料的家成为被占有的资产,占有的逻辑可能会不断强化和扩张,不断产生新的排斥和驱逐。驱逐是占有的前提。驱逐也是占有者维持、提升占有物价值的手段。如果没有排斥和驱逐,就不会有额外的市场价值。倒过来,驱逐又成为占有的动力。我们渴望占有,是因为我们害怕被驱逐。历史上,对占有的渴望和面临的驱逐风险是成正比的。“家天堂”的意识比较盛行的年代,比如维多利亚的英国和现在的美国,也是无家可归者数量剧增的时期。在住房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的西欧,“家天堂”的意识则相对薄弱。上世纪60和70年代,“人人有房住”的公共政策在西欧取得长足发展;当地的年轻人很少会动买房的念头。
虽然中国没有像这本书里描述的驱逐,但那些在城里买不起房、落不了户、租不到合乎标准的房子、孩子因为不够条件上不了学的,常常有被劝退清理的可能。相反,被正式占有的房产进一步升值。这种情况刺激着更多的人去占有,以防再被“扫地出门”。在美国,认为占有房产是天经地义、提倡“人人成为业主”的意识形态,和大规模的驱逐现象是紧密相联的。《扫地出门》告诉我们:2008年,联邦政府花在直接租房补贴上的金额不足402亿,但业主拿到的税务优惠竟高达1710亿美元。这个数目相当于教育部、退伍军人事务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与农业部在当年的预算总和。美国每年在业主津贴上的投入,包括房贷利息扣抵与资本利得豁免,是全美租房券政策成本预估的三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人是业主”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占有者的利益远远压过了居住者的利益。如果“人人有房住”成了主流信条,那么政策可能就会向居住者倾斜,驱逐可能不会那么普遍。
占有者保护资产价值的动机,也在促进驱逐。美国大量的房客被扫地出门,原因不是房子不够。就密尔沃基而言,其人口在1960年是74万,现在却不到60万。驱逐数量的增加与房源的相对宽松是同时出现的。为什么空出来的房子不能成为被驱逐者的家园?占有者不愿意。我10万买下来的房子,白给别人住,岂不是降低了房子的价值?中国二线以下城市政府办公楼前和房产开发商公司门口时不时有业主静坐,对房子降价表示抗议。不许房产降价,直接动机是保护自己投资的价值。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不许那些比我穷的人拥有和我一样的房子。宁可让房子空着,也不能让别人便宜地住。业主当然不是坏人;然而,一旦必需品成为利润的源泉,对利润的追逐就难免沦为“要命”的肉搏。
“家天堂”意识的背后,也许是一个诡异的“双重异化”。这个过程首先把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和享受的东西——生命基本活动所需的起居空间——变成每个人要拼搏着去占有的资产。家在这种条件下有极高的价值,前提是把作为人类“诗意栖居”的家居工具化,把人和她/他的生活空间剥离开来。英国社会主义运动早期的发起者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可能是最重视家居的思想家之一。他设计的住宅、家具、(特别是)壁纸,至今受到很多人的喜爱,被奉为经典。莫里斯强调精心设计、手工制作、独一无二,从而让人彻底享受家居;他强调人和生产工具、物质产品、制作过程、物理环境的有机融合。在他眼里,这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今天的“家天堂”意识、对装潢(在高度程序化标准化的格式下展示所谓个性)的重视,显然大不一样。
当起居空间成为被占有的资产,本来自然的人际关系和不成问题的人的存在价值,也成了问题,被异化为要通过奋斗去“证明”、去追求的对象。房产证现在是你人之为人的一个基础。没有房产,年轻人找不到对象;不能帮子女买房,父母内疚自责,可能还会被自己的孩子埋怨。
而所谓双重异化,是指当家被异化成资产之后,它又重新在意识形态上被异化为人性的依托、终极价值的载体等等。“家是最后的圣土”、“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有恒产者有恒心”,这些说法将私有住宅的意义提高到了政治层面。但是,如果你买不起房、动不动被驱逐,国王进不进你的房又有什么意义?有产者确实可能趋于保守,但是说只有买了房的人才有公德心、原则心,这完全不能被历史经验证明。把对房产的占有理解为民主的条件,更是臆断。
我完全同意马修对居住权的强调。人人有房住,就是居住权。但是居住权之所以重要,无非是因为有个地方住和有碗饭吃、有口水喝一样,是人的基本需求。如果把家提到人性、意义、精神、民主的层次,在今天的语境下,就可能在为双重异化添油加醋了。人性、意义、精神、民主,只能靠人的普遍社会联系和社会交往实现,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把家神圣化,也是把家和社会分割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公共感,我们把家绝对化成为一个私人祭坛。如果家是我们“忙完学习工作之余、在街头历劫种种之后的去处”,那么,工作越折磨、学校越有压力,街头越危险,家就越显得温馨而珍贵。也许,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循环里:为了买房安家,我们承受更多的工作折磨;工作折磨又让家居这个避风港显得愈加宝贵。于是,人之为人的基本需求(住所)成了我们全力拼搏的目标,实现人之为人的基本手段(工作、学习、在街上和人相遇交流)成了折磨和负担。
占有者,是驱逐者,也是被驱逐者——从安详、得体、自洽的生存状态中被驱逐。
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看到这些问题。他们在疑问,他们在反思,他们在想象新的生活方式。敢于不占有,在不占有的前提下享受生活,精神昂扬地过好每一天,这也许会是这个时代的最大的革命。向成长中的勇敢的“我革命”者致敬。
2017年10月—2018年5月
牛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