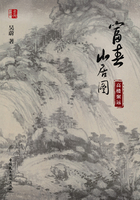
第二章 汴京梦华
桑哥执政后,为减少运输成本,积极寻求南粮北调的运输路线。朱清、张瑄主动上书,建议海运,被朝廷采纳。朱、张二人遂移居太仓,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自刘家港运粮四万石至京师,正式开创了元代海漕。之后,运粮数逐年增加,一度高达三百多万石。因为海运的开发,太仓发展成为东南沿海大港,号称“六国码头”,盛极一时,富庶繁华不亚于泉州,朱清和张瑄也因功被拔擢为都漕运万户。
霜水明秋,霞天送晚,画出江南江北。
满目山围故国,三阁余香,六朝陈迹。
有庭花遗谱,弄哀音、令人嗟惜。
想当时、天子无愁,自古佳人难得。
惆怅龙沉宫井,石上啼痕,犹点胭脂红湿。
去去天荒地老,流水无情,落花狼藉。
恨青溪留在,渺重城、烟波空碧。
对西风、谁与招魂,梦里行云消息。
——白朴《夺锦标·霞水明秋》
江浙行省官员马致远称待罪在家的僧官杨琏真迦将会出席聚远楼宴会,令黄公望大吃了一惊。
桑哥被逮以及清算杨琏真迦,是举国关注的大案。而今桑哥人在大都监狱,已然在审讯中服罪,翻身无望,世人遂将目光投向僧官杨琏真迦。
黄公望在浙西廉访使徐琰麾下任职已有两年,也不算初出茅庐,自问对时局判断素来准确,满心以为这次杨琏真迦一定难逃此劫:即便皇帝不在意杨氏罪行——毕竟杨琏真迦是藏传佛教 重要传人,取得藏地支持,能令忽必烈在与西北诸王对仗中取得一定优势——但为了拿到杨氏私财充作军费,也会痛下杀手,就跟当年对付阿里海牙一样。
重要传人,取得藏地支持,能令忽必烈在与西北诸王对仗中取得一定优势——但为了拿到杨氏私财充作军费,也会痛下杀手,就跟当年对付阿里海牙一样。
甚至黄公望的上司浙西廉访使徐琰及杨琏真迦心腹也是这样认为,杨氏铁杆党羽僧人允泽畏罪潜逃便是明证,却不想到了最后关头,朝廷又变了卦。黄公望一时瞠目结舌,不明所以,适才因登楼望远而滋生的豪气,尽数被失望替代。
倪昭奎又指了指聚远楼,迟疑着道:“会不会……”
黄公望这才会意过来:宴会地点是上头指派,或许上头选中聚远楼时,便知晓皇帝已经决意赦免杨琏真迦,所以才不避嫌疑,毫无顾忌。这般说来,诸多江南士民期盼的杨琏真迦倒台的那一刻,竟是始终不能到来了。
黄公望有些发蒙,怔怔地望向马致远。马致远摇了摇头,长叹一声。那是一声发自心底的叹息,夹杂着世间诸多复杂情感,有一些无可奈何,也有一些灰心丧气。
倪昭奎也跟着叹了一口气。马致远随即沉声吟道:“故宫思见旧冬青,一塔如山塞涕零。领访鱼影香骨案,更从何处哭哭灵。”
这是宋遗民所作吟诵杨琏真迦盗掘宋陵一事的《杂事诗》 。“冬青”指会稽义士唐珏手植冬青树。“一塔”指杨琏真迦在临安南宋旧宫中所修白塔。“鱼影”“香骨案”均为杨琏真迦盗自宋陵的稀世之珍。
。“冬青”指会稽义士唐珏手植冬青树。“一塔”指杨琏真迦在临安南宋旧宫中所修白塔。“鱼影”“香骨案”均为杨琏真迦盗自宋陵的稀世之珍。
说到底,马致远跟宋朝并无太大干系——其祖上早在宋室南渡后便已成为金朝子民。即便在更早的北宋,因为五代时期燕云十六州的割让,马氏也是契丹辽国人,并非宋人,但一句“故宫”,显然是以祖上仍为中原人而自居,且对杨琏真迦的倒行逆施极为不满了。
三人一时相对无语,正各有所思时,忽有大队蒙古军士涌将进来,却是阔阔真公主的侍卫长斡朵思不花率着侍卫先到了。
黄公望定了定神,急忙迎上前去。斡朵思不花先道:“阔阔真公主已经从行馆动身出发,聚远楼这边可有准备好?”
黄公望忙道:“一切均安排妥当,只待公主大驾光临。”
斡朵思不花问道:“戏班到了吗?”
黄公望道:“珠帘秀戏班早已经到了。不过按照惯例,没有官职者,得等主宾先入楼,所以他们目下正候在北边的宗阳宫中。”
斡朵思不花点了点头,又问道:“佩娘人呢?阔阔真公主对饮食有自己的要求,她不是先行过来这边做准备了吗?”
忽有人接口道:“我人在这里。”一名四旬妇人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正是阔阔真公主心腹女官汪小佩。
斡朵思不花忙招手将汪小佩叫到一旁,低声告道:“我适才在桥边看到了一位熟人,是乃颜旧部安心。我虽然很是意外,但还是下了马,走过去跟他打招呼。结果安心一认出我,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又不无忧虑地道:“聚远楼附近混杂有不少蒙古人,虽然服饰打扮与汉人无异,但举手投足一看就知道是蒙古人,应当就是之前皇帝陛下安置在江浙的乃颜旧部。”
汪小佩皱紧眉头,问道:“侍卫长怀疑安心这些人想对阔阔真公主不利吗?”
斡朵思不花点了点头,道:“听说乃颜被俘虏后,曾向皇帝陛下苦苦求饶,还提及当年塔察儿大王支持当今皇帝陛下坐上大汗之位一事,但仍然被以酷刑处死,其部属因而怀恨在心,也在情在理。”
斡朵思不花是卜鲁罕部人,该部落在蒙古族人中地位很高,承认大元的宗主权及统治权,但仍相对独立。而斡朵思不花只是阔阔真公主的私人护卫,并不在朝为官,因而不似一般大元大臣,对皇帝忽必烈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其言外之意,似对忽必烈杀俘颇不以为然。
斡朵思不花见汪小佩踌躇不语,续道:“阔阔真公主是未来的伊儿汗国王后,如果公主在杭州出事,伊儿汗国必然对大元不满,乃颜旧部,甚至西北海都大王等,不是可以趁机渔翁得利吗?”
顿了顿,又道:“不过甘麻剌大王是当今皇帝长孙,极可能是未来的皇位继承人,身份尊贵,安心那些人有心作乱的话,也有可能是针对他。”
汪小佩是果决之人,微一沉吟,即叫过黄公望,说了斡朵思不花的发现及顾虑。
黄公望忙道:“不错,叛王乃颜旧部是有不少被安置在江浙行省。不过聚远楼不比别处,这里戒备森严,寻常人难以进来。因为阔阔真公主及梁王殿下 驾临,又特意请杭州路达鲁花赤
驾临,又特意请杭州路达鲁花赤 调兵,增加了防卫,闲杂人等绝对不可能混进来滋事。”
调兵,增加了防卫,闲杂人等绝对不可能混进来滋事。”
斡朵思不花是蒙古卜鲁罕部最著名的勇士,生性警觉,蓦然有所感觉,仰起头来,喝问道:“谁在上面?”
黄公望闻声急忙抬头,却只见一条人影从楼顶缩了回去。他先是一怔,随即会意过来,忙告道:“那是江西行省贯平章的小公子。贯平章人到了,又出去办事了,只留下了贯公子一个人在这里。”
斡朵思不花转过头来,愕然道:“贯平章的小公子,那不是佩娘的小侄子吗?”
汪小佩点了点头,应道:“我上去看看。”
她人刚进楼,便有蒙古侍卫急奔而来,朝斡朵思不花行了一礼,禀报道:“出事了,阔阔真公主一出行馆,便遭遇了刺客。”
斡朵思不花大惊失色,急问道:“阔阔真公主受伤了吗?”
侍卫道:“公主没事。刺客下手的对象不是阔阔真公主,而是杨暗普。不过他人没大碍,刺客失了准头,只射中了他的肩头。”
斡朵思不花舒了一口气,又皱眉问道:“杨暗普是谁?”
侍卫道:“永福大师杨琏真迦之子。今日一早,杨暗普便来到行馆外,等着见阔阔真公主一面。说是感谢公主出面救了他父亲,还说他父亲心腹僧人允泽不是畏罪潜逃,而是遭人暗害。”
斡朵思不花显然不知原委,露出了浓重的惑色,只问道:“刺客可有抓获?”
侍卫道:“行馆一带,围观的人很多,刺客混在人群中,没有人看到他的面貌身形,只知道箭矢是从街对面射过来的。”
斡朵思不花道:“那阔阔真公主……”
侍卫忙道:“甘麻剌大王已经闻讯赶到,说会跟阔阔真公主一道过来。甘麻剌大王扈从极多,有他在阔阔真公主身边,刺客绝无下手机会。”
斡朵思不花这才放了心。他二人说的是蒙古语,也不避讳旁人在场。黄公望和倪昭奎既为廉访司书吏,平日要处理汉蒙两种文字的文书,亦是精通蒙古语,闻言均大为吃惊,面面相觑。听起来,竟是即将远嫁的阔阔真公主出面为杨琏真迦说了话,当今皇帝这才改变了主意。
阔阔真公主是未来的伊儿汗国王后,地位不比大元皇后差,自是有扭转乾坤的能力,却不知生长于北方草原的公主,与杨琏真迦又有何渊源?
一番忙乱后,定于正午时分的宴会终于如期开始了。金罍美酒,银盘靡肉,仍然盖不过荷香满楼。杂剧名角珠帘秀应邀而来,也在楼前戏台上使出了浑身解数,只为博楼上众宾客展颜一笑。
今日聚远楼酒宴的宾客,以护亲队伍为主,虽是浙西廉访使兼江浙行省代长官徐琰派人张罗,但徐琰等地方官员却均未参与。除了形势微妙、朝廷正派了钦差大臣严查江浙行省及杭州路官员外,还因为此次宴会最重要的宾客是一位女眷——她本人不喜欢人多,尤其是陌生人,事先一再声明不需要地方官员列席 。
。
主客自是即将远嫁伊儿汗国的十八岁蒙古阔阔真公主。她将先奔赴泉州,与等候在那里的伊儿汗国使者会合后,再正式登船出发,踏上漫长的西行旅程 。这次途经杭州,是她生平第一次,也极可能是最后一次来到江南。她在塞外时便听闻杭州有“地下天宫”之美景,又有“天堂之城”之繁华,倾慕已久,预备在本地多逗留几日。
。这次途经杭州,是她生平第一次,也极可能是最后一次来到江南。她在塞外时便听闻杭州有“地下天宫”之美景,又有“天堂之城”之繁华,倾慕已久,预备在本地多逗留几日。
其他宾客,身份贵重者有梁王甘麻剌,也就是当今大元皇帝忽必烈之孙、已故太子真金之长子。他新封了梁王,将赴云南任职,刚好有阔阔真公主远嫁之事,他便成了护嫁长官,将一路护送阔阔真公主到泉州登船后,再行前往封地云南。
梁王之女宝塔实怜也在座上。其实甘麻剌本人还未到三十岁,宝塔实怜也才十四岁。她是真正的金枝玉叶,遂以公主身份陪同阔阔真坐在首席。宝塔实怜活泼好动,比照于沉静的阔阔真公主,她的心思明显不在宴席上,不断东张西望,对台上的杂剧表演也没有任何兴趣,若非梁王甘麻剌多次以目光暗示,只怕她早已起身离开。
再则是高丽王世子 王璋注1。他是历史上第一位与蒙古人混血的高丽王子,父亲为高丽忠烈王王昛,生母则是元世祖忽必烈之女安平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是地地道道的大元皇帝外孙。
王璋注1。他是历史上第一位与蒙古人混血的高丽王子,父亲为高丽忠烈王王昛,生母则是元世祖忽必烈之女安平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是地地道道的大元皇帝外孙。
注1王璋初名王 ,字仲昂,号海印居士,蒙古名益智礼普化(意为小公牛,为真金太子妃伯蓝也怯赤亲自赐名),后来才改名王璋。本书为方便起见,一律以王璋称呼。同样,王璋生父王昛(高丽王朝第25任君主,1274—1298年、1298—1308年在位,无庙号,元朝赐谥号“忠烈”)初名谌(中国史书作愖),后改名昛,本书一律以王昛称呼。王璋祖父王禃(高丽王朝第24任君主,1260—1274年在位,庙号元宗,也是高丽王朝最后一位拥有庙号的国王)原名倎,即位后改名禃,一度改名为钊,本书一律取王禃。
,字仲昂,号海印居士,蒙古名益智礼普化(意为小公牛,为真金太子妃伯蓝也怯赤亲自赐名),后来才改名王璋。本书为方便起见,一律以王璋称呼。同样,王璋生父王昛(高丽王朝第25任君主,1274—1298年、1298—1308年在位,无庙号,元朝赐谥号“忠烈”)初名谌(中国史书作愖),后改名昛,本书一律以王昛称呼。王璋祖父王禃(高丽王朝第24任君主,1260—1274年在位,庙号元宗,也是高丽王朝最后一位拥有庙号的国王)原名倎,即位后改名禃,一度改名为钊,本书一律取王禃。
王璋虽为蒙古公主所生,却不喜狩猎饮酒,坚持汉学,熟读儒家经典,文化修养颇深。由于热爱中国文化,其人常年待在中国,名义上是在外祖父元世祖忽必烈身边充当怯薛,实则四下游山玩水。这次担任护卫长,护送阔阔真公主前往泉州,也是他自己主动请缨,大有假公济私之嫌。
当今皇帝忽必烈极其重视与伊儿汗国的邦交,而阔阔真公主是伊儿汗国未来的王后 ,是能够影响国中军政的关键人物,忽必烈特意做足排场,派出了规模庞大的护亲队伍,梁王甘麻剌和高丽王世子王璋只是一行人中最为显贵的二位,其下还有枢密副使囊加歹、江西行省平章政事贯只哥、都漕运万户朱清和张瑄等。
,是能够影响国中军政的关键人物,忽必烈特意做足排场,派出了规模庞大的护亲队伍,梁王甘麻剌和高丽王世子王璋只是一行人中最为显贵的二位,其下还有枢密副使囊加歹、江西行省平章政事贯只哥、都漕运万户朱清和张瑄等。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贯只哥是大元开国名将阿里海牙次子,这次刚好由湖广调任江西,由大都赴任,皇帝忽必烈便命他顺道加入护亲队伍,以壮声势。
都漕运万户朱清、张瑄身份相对特殊——二人原是海上巨盗,手下有五百艘海船,以及数千人组成的海盗武装队伍,势力很大,一度纵横于海上。除了抢劫商船外,朱清、张瑄也从事商业贸易,从南洋各国到日本、高丽等国,活动范围极广,因而熟悉南北海道、诸岛门户。
正因为朱清、张瑄名气太大,元军南下攻宋时,因兵船不足,部众大多不习水战,元廷遂打起了朱、张二人的主意,主动招降。朱清、张瑄均是苦孩子出身,受不了富户欺压凌辱才铤而走险,贩卖私盐时还被南宋官府逮住,险些丧命于刀下 。二人既对南宋小朝廷并无好感,见元廷来招,便顺势投靠,二人均被授予行军千户职,跟随元军主帅伯颜进攻南宋。
。二人既对南宋小朝廷并无好感,见元廷来招,便顺势投靠,二人均被授予行军千户职,跟随元军主帅伯颜进攻南宋。
南宋京师临安陷落后,伯颜一军劫掠了大量宫廷财物,及诸省、院、寺的乐器、祭器、郊天仪仗、宝册、图书等物。当时淮东地区仍有南宋军队驻守,元军所掠库藏图书诸物无法取道运河,伯颜遂命朱清、张瑄用海船载运,自崇明由海道运至渤海湾直沽 ,再由陆路转运到大都,此即为元代海运之始。
,再由陆路转运到大都,此即为元代海运之始。
宰相桑哥执政后,为减少运输成本,积极寻求南粮北调的运输路线。朱清、张瑄主动上书,建议海运,被朝廷采纳。朱、张二人遂移居太仓,调集军民,疏通娄江,“通海运,循娄江故道导由刘家港入海”。又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自刘家港出发,运粮四万石至京师,正式开创了元代海漕 。之后,运粮数逐年增加,一度高达三百多万石。
。之后,运粮数逐年增加,一度高达三百多万石。
太仓原是古娄县之惠安乡,“本田畴之村落”,为“人文罕著之斥堠之地”,甚至到宋朝时,还“田畴未辟”“居民尚不满百家”,然因为海运的开发,太仓一跃成为东南沿海大港——
“浚娄江达海,大通番舶,琉球、日本、高丽诸国咸集太仓,称天下第一都会”,海外诸番因得于此交通市易,是以四关居民闾阎相接,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辏而云集,号称“六国码头”,盛极一时,富庶繁华不亚于泉州。朱清和张瑄也因功被拔擢为都漕运万户。
而今宰相桑哥倒台,就连与之交好的僧官杨琏真迦也未能置身事外,而曾受桑哥鼎力支持的朱清、张瑄不但没有卷入其中,还被皇帝忽必烈亲自召见,指定二人负责组建船队,护送阔阔真公主前往伊儿汗国,盖因为忽必烈大大尝到了海运的甜头。
至于枢密副使囊加歹,其人也是大有来历,其生父即是灭宋功臣伯颜。这次囊加歹被选为护卫队长官,是因为其父伯颜生长于伊儿汗国,其家族尚有许多亲眷、包括囊加歹祖父等仍在伊儿汗国任职,他与伊儿汗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而与梁王甘麻剌、高丽王世子王璋等人只送到泉州不同的是,囊加歹将率军一路护送阔阔真到达最后的目的地——伊儿汗国。
坐在朱清、张瑄之下的,是一名高鼻碧眼的外国男子,他并非伊儿汗国使者,而是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名义上也是元朝大臣、护亲使者。
马可·波罗父亲尼科洛和叔叔马泰奥也是商人,早年到中国经商,曾朝见过忽必烈,还带回了忽必烈给罗马教皇的信。马可·波罗自小便对父亲、叔叔东方旅行的经历很是着迷,很想亲身去体验。十七岁时,马可·波罗终于美梦成真,他和父亲、叔叔带着教皇给忽必烈的复信及礼品,向东方进发。一行人先抵达上都,皇帝忽必烈接见后,很喜欢年轻机智的马可·波罗,携他同返大都,并留在朝中。而后马可·波罗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游历了中国的许多地方,还在扬州短暂担任过官职。
光阴荏苒,一晃十七年过去了。来中国时,还是朝气蓬勃的青葱少年,而今已过而立之年,马可·波罗开始思念家乡及亲人,遂上书请求回国。忽必烈虽然有些不舍,但还是同意了。刚好有阔阔真公主西嫁一事,忽必烈遂令马可·波罗加入护亲队伍,待护送阔阔真公主抵达伊儿汗国后,马可·波罗才算正式完成使命,然后可以转路回国 。
。
除了有职务在身的官方人员外,在座的还有几位平民宾客,如陈思恭、危碧崖。
陈思恭只是一名普通的泉州海商。他与都漕运万户朱清私交甚好,其人曾几次亲往东南亚、中亚贸易,熟悉海道。而今元廷积极发展海漕及海上贸易,朱清、张瑄主管其事,是朝中炙手可热的大红人,分身无术,难以亲自护送阔阔真公主的船队,故而朱清请陈思恭做本次旅途的航海向导。
坐于陈思恭身边的则是名医危碧崖及其孙危亦林。危氏祖籍抚州,后迁南丰 ,世代行医。危碧崖曾于泉州海商陈思恭有恩,治好了陈妻庄氏及其子陈彦廉的怪病。陈思恭为人缜密周全,思及此次航程路途漫漫,将会在海上漂泊数月,而阔阔真公主长于北方草原,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状况,所以极力举荐名医随行,阔阔真公主随身女官汪小佩也很是赞同,由此定下此事。
,世代行医。危碧崖曾于泉州海商陈思恭有恩,治好了陈妻庄氏及其子陈彦廉的怪病。陈思恭为人缜密周全,思及此次航程路途漫漫,将会在海上漂泊数月,而阔阔真公主长于北方草原,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状况,所以极力举荐名医随行,阔阔真公主随身女官汪小佩也很是赞同,由此定下此事。
不过将要跟随护亲队伍的不是危碧崖本人,而是其女危子美。危碧崖本人年事已高,怕是经不起风浪。退一步说,阔阔真公主是女儿身,女医随行,要方便许多。危子美人尚在家乡行医,将会直接到泉州与公主一行会合。危碧崖则刚好与故友关汉卿相约在杭州见面,护卫队长官枢密副使囊加歹听说后,便邀请危碧崖来参加宴会,也算是表达感谢之意。
危碧崖之孙危亦林才是一名十四五岁的少年,却是目不斜视,正襟危坐,神情严肃,看起来如同大人一般。与其年纪相仿的宝塔实怜公主不知道为何对他很感兴趣,目光一直在他身上溜来溜去,只可惜二人座位相隔甚远,交谈不便。
主要人物阔阔真公主、梁王甘麻剌都是率真少言之人,没太多的寒暄。尤其梁王甘麻剌略略有些口吃,不到万不得已,极少开口发言。阔阔真公主对杂剧很有兴趣,看到不解之处,便转头向坐在身后的女官汪小佩询问。席间最为健谈者,是马可·波罗和高丽王世子王璋。二人身份特殊,也无太多顾虑,便主动揽起了话题,以免宴会冷场。
马可·波罗因行将归国,心情激动,回顾了在中国十余年的见闻,对各地风俗人情赞不绝口。又盛赞杭州华美,是他生平所见最为壮丽的城市。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贯只哥笑着接口道:“波罗先生去过太仓吗?那里也很不错,号称六国码头,繁盛不在杭州之下,全靠朱、张二位万户一手经营。”
贯只哥其实也没有去过太仓,况且太仓是新兴港口,如何能与杭州相提并论?不过是随口一句,有意与朱清、张瑄两位朝中大红人结纳罢了。
马可·波罗却是不懂这套手段,信以为真,呆了一呆,叹道:“可惜,我竟是来不及去了。”
海漕万户朱清忙道:“贯平章开玩笑呢。太仓也就是这几年才兴旺了些,哪里比得过杭州!”
马可·波罗又兴奋起来,道:“只怕天下再没有一个城市,能够超过杭州了吧。”
名医危碧崖忍不住接口道:“汴京富丽,天下无双,若是波罗先生见过北宋时的汴梁,便不会再说这等话了。”
马可·波罗问道:“是开封汴梁吗?我有去过。”
危碧崖道:“波罗先生见到的只是大元汴梁,是金人留下来的,老夫说的,则是北宋东京开封府,‘琪树明霞五凤楼,夷门自古帝王州。'”
马可·波罗点头道:“这我知道啊,二者完全不同。我见到的汴梁,是经历了宋金两朝战火的汴梁,早已衰败,风貌不及昔日十之一二了。”
顿了顿,又道:“听说有一本汉文书,名叫《东京梦华录》 ,是专门追述北宋都城汴京风貌的。”
,是专门追述北宋都城汴京风貌的。”
高丽王世子王璋忙应道:“是有这样一本书。我还记得作者孟元老的自序。”
王璋汉学修养颇深,又一向以名士自居,也不待旁人反应,先自顾自地背了起来:“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琦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马可·波罗的汉文程度仅限于口头交流,对他而言,古文都是云山雾罩,看起来有朦胧之美,实际却不明真切。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一句,以数量词为主,他是听懂了,料想前面大段言辞都是在盛赞东京风貌,无与伦比,不由得极是神往。
高丽王世子王璋又告道:“记录描述昔日东京盛况的,不光有《东京梦华录》一书,还有一幅名为《清明上河图》 的画作。”
的画作。”
王璋虽然年轻,却对中国文化有着狂热的热情,不惜花费巨资搜罗各种名家字画,自是知悉北宋宫廷画家张择端所绘巨作《清明上河图》,一涉及热衷的领域,谈兴愈浓,又续道:“听说《清明上河图》中的东京——我是说画作中的东京,已经是天下数一数二的繁华城市,而那仅是画作所绘场景,不及原城十分之一。”
马可·波罗虽久在中国,却只是游历四方,兼之语言及文化修为原因,少与文人墨客交往,竟不知《清明上河图》,今日才第一次听闻,一时兴致勃勃,忙问道:“世子只是听说吗?莫非世子也没有见过那幅《清明上河图》?”
王璋摇头道:“我一直在打听这幅图的下落,始终没有消息。”
北宋末年,张择端完成《清明上河图》后,即被收入皇宫御府。当时在位的皇帝宋徽宗赵佶还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法在卷首题了五签,并加盖上皇帝自己最爱的双龙小印。而后靖康之变,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掳北上,皇宫府库所积尽为金人所夺,《清明上河图》当也在其中。据说金大臣张著、张公药、郦权、王磵、张世积等,均曾观赏过此画作,并题跋于图后。然在此之后,便再无《清明上河图》的确切消息。
金国最终亡于蒙古之手,金国财富、子民也尽为蒙古军所掠,马可·波罗自是知晓此节,忙道:“如此,那幅《清明上河图》肯定流入大都皇宫内府了。”一边说着,一边望向梁王甘麻剌,想从梁王口中得到验证。
梁王甘麻剌却只是一怔,露出了茫然的神情。
王璋忙告道:“我早设法确认过了,《清明上河图》并不在大都内府。”
北宋灭亡时,金人横行于中原,抢掠走大量字画珍宝,《清明上河图》也在其中,这是确认无疑的事,毕竟金国大臣观赏过此画,有诗文明确记录了此事。但后来南宋小朝廷成立,与金人议和,最终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彼时南方经济文化远远领先于北方,随着两国交流的加强,金人对南宋的物资依赖日益加重,现钱亦大量流出,用于交换茶叶等日常物资。也就是说,当年金人从北宋掠夺抢走的财富,大多数又重新回到了南宋的腰包。
马可·波罗听了王璋一番解释,这才恍然大悟,问道:“如此说来,《清明上河图》又重新流回南宋宫廷了?”
王璋道:“是,但并没有回到南宋皇室手中。”
他笑了一笑,转头看了对面的枢密副使囊加歹一眼,又看了海漕万户朱清一眼。这两眼,看似不经意,实则大有意味——
囊加歹生父伯颜是灭亡南宋的主帅,元军进入临安后,府库各种财物、秘籍等也是由伯颜本人清点封箱,而后又委托朱清用大船经海路运往大都。如若《清明上河图》之前流回了南宋宫廷,那么临安陷落之后,该图便该经由二人之手,流入了大都皇宫。
囊加歹没有会意过来,依旧只是肃着脸坐在那里。朱清本来一直垂首不语,这时候却忽而抬起头来,看了身边的泉州富商陈思恭一眼。陈思恭便有些惶然起来,嘴唇翕动,似想说些什么,却又没有开口。
马可·波罗却对《清明上河图》起了浓厚的兴趣,追问道:“那么那幅图到底流落在了何处?”
王璋道:“据我所知,是落在了大奸臣贾似道之手 。后来贾似道为舆论民情所逼而失势,又在流放途中意外被杀,《清明上河图》也就下落不明了。”
。后来贾似道为舆论民情所逼而失势,又在流放途中意外被杀,《清明上河图》也就下落不明了。”
说到“下落不明”一句时,王璋微有停顿。他虽以高丽王世子的身份依附元朝,但毕竟是一国储君,又是当今皇帝亲外孙,有钱又有势,既对《清明上河图》念念不忘,志在必得,便下了许多功夫,专门派了得力人手追查下落。得到的结果是——
《清明上河图》确实落入了南宋权相贾似道之手,但在贾氏失势之前,该图便已经下落不明,一说是被相士张锦堂盗取。
张锦堂年轻时曾向高人学习相人术,后成为著名相士。他视人形状气色,再参以所生年月,能准确预测来日境况,无不奇准,百无一谬。贾似道任宰相后,久仰张锦堂大名,便下令征其来为自己相面。
张锦堂到了后,只委婉告道:“公忧民忧国,颜色未知,请俟异日。”
起初贾似道听了还挺高兴,但后来张锦堂一再推托,贾似道便有些不高兴了。据说张锦堂已测算到贾似道日后必会身败名裂,且将死于非命。但张氏若说实话,必遭贾似道毒手,可他顾念名声,更不愿意当面撒谎,所以只能找理由拖延。到了最后,贾似道以武力威胁,张锦堂被逼无奈,才道:“一尘尚不容,安能治天下?”
贾似道大怒,准备杀死张锦堂泄愤。张锦堂这才勉强妥协,说将在当晚月明之夜为贾似道相面,并让对方沐浴更衣,做好准备。
当夜,张锦堂离奇失踪。同时消失不见的,还有贾似道最为珍爱的《清明上河图》。次日一早,临安大街小巷疯传相士张锦堂因说了实话而为贾似道暗害。贾似道吃了哑巴亏,不好公然令官府通缉张锦堂,只暗中派人追查,但始终未有下落。
王璋从贾府奴仆后人口中得知此段故事后,推测《清明上河图》必是为相士张锦堂所盗,但四下寻访,却没有张锦堂半分消息。料想其人当年得罪了宰相,必刻意避世,销声匿迹,即便后来将《清明上河图》传给了子嗣,怕也是无迹可寻。今日聚远楼宴会,王璋将《清明上河图》最终下落当面告知马可·波罗,有炫耀自身博闻之意,不提及相士张锦堂,则是存了一点私心。
马可·波罗自是猜不到内中关节,仍为不能一睹《清明上河图》而抱憾不已。又问道:“宋元之际,杭州多次大火,该不会《清明上河图》已经焚毁,消失于人世了吧?”
王璋道:“这个嘛,世事无定,也未可知。”
他二人将宋人画作《清明上河图》当作了中心谈资,你来我往,旁人不免很有些瞠目结舌——
元朝风气相对开放,但在宋室一事上,却是极为敏感,主要是民间反元力量仍在,元廷生怕宋室会死灰复燃。南宋宰相文天祥被俘后一直囚禁在大都,元世祖忽必烈爱惜其人才,虽招降不成,却也不忍加害,已有放还文天祥出家为道之意 。但京畿之地忽然冒出了一股武装力量,称要引兵起义,救出文天祥,奉文氏为主,反抗元廷。忽必烈闻讯后大为紧张,立即出动重兵镇压围剿,又下令公开将文天祥处死,以绝后患。
。但京畿之地忽然冒出了一股武装力量,称要引兵起义,救出文天祥,奉文氏为主,反抗元廷。忽必烈闻讯后大为紧张,立即出动重兵镇压围剿,又下令公开将文天祥处死,以绝后患。
《清明上河图》虽然只是一幅画,但毕竟是北宋宫廷画家所作,最早为宋徽宗赵佶收藏,所绘又是北宋都城,大有政治寓意,此刻公然在酒宴上谈论,颇不合时宜。梁王甘麻剌为人木讷,倒还没什么表示,枢密副使囊加歹却是坐不住了,轻轻咳嗽一声,刚要举手止住此话题,阔阔真公主却起了好奇之心,问道:“世子是说,贾似道之后,便再也没有人见过《清明上河图》了,对吗?”
阔阔真公主是元世祖忽必烈都要礼敬三分的人,绝对不能得罪,她既然开了口,囊加歹只好就此打住。
王璋忙应道:“回公主话,是这样。”
阔阔真公主身后女官汪小佩忽插口道:“说来说去,还是波罗先生留恋杭州。既然如此,不妨请一位高明画师,绘一张《杭州四季图》,以为留念。”
马可·波罗大喜道:“此主意甚好。我之前怎么就没想到!”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贯只哥接口道:“波罗先生要的是意象,还是实景?中国画名叫丹青,强调意境,意存笔先,画尽意在,追求的是一种‘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感觉。”
他见马可·波罗一脸懵懂,便笑道:“看波罗先生神情,还是界画 更合适你。不过在中国,界画画师可不大好找。”
更合适你。不过在中国,界画画师可不大好找。”
名医危碧崖当即拱手道:“想不到贯平章竟然是位书画行家。”
贯只哥笑道:“内子好舞文弄墨,这些我都是从她那里听来的。”
贯妻出自著名的廉氏家族,众人闻言也不意外。
马可·波罗便又发声请教丹青和界画的区别,危碧崖、陈思恭等人都加入了进来。陈思恭虽只是商人,对绘画也有所涉猎,告道:“传统中国画讲究写意及气韵,并不重写实。而界画是因建筑而生,更注重工整写实,造型准确。只是正如贯平章所言,界画画师甚为少见,通常只有皇家因建筑宫殿宫室,才会奉养界画画师。比如《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他原先只是游学京师,后来因生活所迫,才开始学习绘画,且专工界画,因为朝廷需要这样的人才,后来他果然进了翰林图画院。”
马可·波罗叹道:“如此说来,要找到一位写实绘出杭州城貌的画师,也是相当不容易了。”
女官汪小佩问道:“波罗先生最爱杭州的哪一处美景?”
马可·波罗笑道:“自然是繁华街。”
繁华街即经朝天门往北的街道,南宋时名御街,是杭州全城最繁华区域,为中心商业区。街道两旁画栋雕楼,商肆林立,“无一家不买卖者”。商品琳琅满目,纷繁多样,数不胜数。街巷中还有若干行业市街及娱乐表演集中的“瓦子”,令人目不暇接,热闹非凡。
江西行省平章贯只哥接口笑道:“我还以为波罗先生会说西湖,或是钱塘呢。”
马可·波罗连连摆手道:“繁华街,一定是繁华街。天下再没有什么地方比繁华街更好玩了,吃喝玩乐,应有尽有。”
梁王之女宝塔实怜公主还是第一次来到杭州,忙插口问道:“比大都还好玩吗?都有些什么呀?”
马可·波罗应道:“好玩的可多了。”
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开了,再也不曾回到跟《清明上河图》及汴梁相关的话题上来,枢密副使囊加歹本就对汪小佩印象很好,此刻越发感激,特意朝她点了点头。汪小佩亦按蒙古风俗,举手回礼。
这时候,有侍卫进来禀报道:“永福大师到了。”
座中朱清等人尚不知僧官杨琏真迦已转危为安,闻言均感愕然。阔阔真公主倒不惊奇,先转头看了女官汪小佩一眼,见对方并无异议,这才道:“请永福大师进来。”
大元尊崇藏传佛教,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原因,元朝在宗教上其实相当开明,对各种宗教均采取兼容并蓄的优礼政策。即便是蒙古上层贵族,也是信仰不一,有信奉蒙古原始宗教萨满教的,有信奉景教的,也有信奉伊斯兰教的。杨琏真迦进来时,诸人均只是举手示意。独有高丽王世子王璋站起身来,但却不是相迎杨琏真迦,而是口称要出去方便,急急出厅下楼去了。
浙西廉访司书吏倪昭奎侍立在门边,见状忙跟了出去。他见王璋称是如厕,却不去楼中专为贵客准备的豪华茅间,而是径直出了聚远楼,颇为惊讶,追出去叫住对方,问道:“王世子要去哪里?”
王璋随口应道:“我有些气闷,想四处走走。”见倪昭奎做出欲言又止状,便问道,“倪书吏有事吗?”
《清明上河图》一度是今日席间的中心话题,而高丽王世子王璋当众透露该图早已流回中原,且落入权相贾似道之手,更是闻所未闻之事,倪昭奎自是极感兴趣,所以见到王璋独自出来宴会厅,便认为是个大好机会,特意追上前来,想私下打听南宋时《清明上河图》流回且落入权相贾似道手中是不是真有其事。毕竟宋人从不曾听闻过,而且贾似道门下幕客如廖莹中 、胡三省
、胡三省 等,皆为当时知名的藏书刻书大家,各有著述记载贾似道所藏图书字画,均不闻有《清明上河图》记载。
等,皆为当时知名的藏书刻书大家,各有著述记载贾似道所藏图书字画,均不闻有《清明上河图》记载。
倪昭奎大致说了原委,王璋见他不过是名普通书吏,本不愿理睬,但刚好江浙行省省务提举马致远也在一旁。王璋今日才得与马致远相识,却对马氏才名仰慕已久,见对方虽未明言,但目光却也落在自己身上,明显也有探究《清明上河图》之意。王璋到底还是年轻,不免很有些轻飘飘起来,便欣然告知倪昭奎,称《清明上河图》从金国再度流回中原一事,是从贾似道门客胡三省处听闻——
贾似道确实得到了《清明上河图》,但手段却不大光彩,内中隐讳甚多,即便他是本朝宰相,也有所顾忌,故对此画秘而不宣。但廖莹中是贾似道心腹,采买鉴定《清明上河图》一事,便是由其经手。而胡三省又是廖氏至交好友,故而知晓其事。
两年前,元廷为稳定人心,派人访求江南名士,罗致朝中为官,谢枋得 、胡三省均在名单之中。谢枋得为人高洁,坚决不肯仕元,入大都后绝食而死。而隐居于家乡宁海的胡三省也被地方官府拘禁,只是因病暂未启程。
、胡三省均在名单之中。谢枋得为人高洁,坚决不肯仕元,入大都后绝食而死。而隐居于家乡宁海的胡三省也被地方官府拘禁,只是因病暂未启程。
刚好此时高丽王世子王璋到贾似道家乡天台游历。宁海与天台相邻,王璋听说胡三省受地方官员威逼后,出于对胡三省的仰慕,出面周旋。他是皇帝忽必烈亲外孙,又是未来的高丽国王,地方官员如何敢不给面子?于是上书奏称胡三省年老病重,已不堪任用,元廷遂作罢征召一事。
胡三省曾因做过贾似道幕僚而饱受世人非议,尤受乡人鄙视,因而后半生对名声极为重视,这次得以保名节,自是对高丽王世子王璋格外心怀感激,奉为座上客。王璋爱好搜罗名家字画,趁机打听昔日贾似道所藏,胡三省遂说了贾似道最珍爱字画为《清明上河图》一事。
倪昭奎闻言,这才信服,踌躇道:“胡三省仍然在世,既是他亲口所言,自是可信。”
又思忖着问道:“那幅《清明上河图》,当密藏在贾似道天台老家,贾氏身败后,便被没入台州官府。台州官府本该将所有贾氏财物封箱后送来临安,既然不见《清明上河图》踪迹,极可能在台州时便出了意外,为人私下截留,王世子可由此再追查下去?”
王璋似有心事,不愿意再过多谈论《清明上河图》一事,只道:“追查过了,没有下落。兵荒马乱的,名画失落,固然遗憾,但也是正常之事。”又朝马致远点了点头,自朝前庭去了。
倪昭奎呆立当场,若有所思。马致远上前拍了拍他肩头,叹道:“先进楼吧,酒宴才过三巡,杨永福人也到了,黄公望一个人在里面候命,万一有事,怕是支撑不住。”
再说那进来宴会厅的僧官杨琏真迦,已无昔日霸凌神色,先上前朝梁王甘麻剌行了一礼,用蒙古语说了一大番客套话。
其实杨琏真迦地位尊崇,根本无须如此。但他此刻受前宰相桑哥牵累,已然在朝中失势,而早先他更因天师张留孙与梁王之父太子真金结下过不小的梁子 ,虽然皇太子真金已死,但梁王风头正劲,少不得要低头阿谀奉承一番。
,虽然皇太子真金已死,但梁王风头正劲,少不得要低头阿谀奉承一番。
梁王甘麻剌始终是一副木讷表情,看不出喜怒。他倒是极有耐心,等杨琏真迦洋洋洒洒地说完,略微举了举手,以表谢意。
杨琏真迦见梁王甘麻剌并无恼恨之意,心下稍平,这才向阔阔真公主谢道:“贫僧专程赶来拜谢公主。”虽未明说因何而谢,但以目下情形而论,自是指阔阔真公主在皇帝忽必烈面前为他说情了。
阔阔真公主举手道:“永福大师不必多礼。我在卜鲁罕草原,也听说过大师的名字。”
杨琏真迦受宠若惊,当即大讲卜鲁罕部落的来历,以及与孛儿只斤皇族的渊源,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虽然恶名远扬,但也是博学之士,又曾游历天南海北,见闻广博,竟有许多卜鲁罕部落之事,就连阔阔真公主自己也不知道。阔阔真公主本人信奉佛教,当面向杨琏真迦请教了几句教义后,这才转头叫道:“佩娘,请你代我向永福大师敬酒。”
女官汪小佩遂站起身来,取了一只空置金杯,斟满奶酒 ,端下来奉给杨琏真迦。杨琏真迦忙接过金杯,一饮而尽,又道:“多谢公主。贫僧也要回敬公主一杯。”示意汪小佩将金杯再斟满。
,端下来奉给杨琏真迦。杨琏真迦忙接过金杯,一饮而尽,又道:“多谢公主。贫僧也要回敬公主一杯。”示意汪小佩将金杯再斟满。
汪小佩笑道:“适才倒给永福大师的,是阔阔真公主自己从卜鲁罕带来的马奶酒,是公主娘亲手酿制,所携不多,大师还喝得惯吗?不如改饮其他酒。”
马奶酒在蒙古人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即便元朝建立后亦是如此,大元皇帝祭天及祭祀祖宗,均要用马奶酒,即所谓“祭天马酒洒平野,沙际风来草亦香”。然梁王之女宝塔实怜在大都长大,早已抛弃草原习俗,过的是典型的城市生活,饮惯了果酒,根本不喝奶酒,闻言忙道:“原来这奶酒是阔阔真姊姊从家乡带来的啊,那可是珍贵极了,还是多留些给阔阔真姊姊带去伊儿汗国,咱们大伙儿都改喝葡萄酒 吧。”
吧。”
黄公望一直站在门边奉召,闻言忙命人去搬葡萄酒进来,当场开了封,分装入大肚酒壶,再将酒壶置于各宾客面前案上。
杨琏真迦见高丽王世子王璋已起身离开,也不等侍女斟酒,自行走到其案前,取大肚酒壶往金杯中注满,又走回堂中,举杯道:“贫僧谨祝阔阔真公主福如东海,儿孙满堂,子孙后代世世为伊儿汗国可汗。”
黄公望听在耳中,心道:“此僧虽然作恶多端、恶贯满盈,到底还是个人物,见过大世面,赞语倒也得体。对于大元朝,以及远嫁伊儿汗国的阔阔真公主而言,真没有什么比生下子嗣、子嗣又继位为可汗更重要的了。”
阔阔真公主果然春风满面,笑道:“多谢永福大师吉言,将来……”忽见杨琏真迦抛下金杯,双手捧腹,忙问道:“大师可是不舒服?”
杨琏真迦脸白如纸,额头汗水滚滚而下,只道:“贫僧……贫僧……”却是说不出更多的话来,更慢慢瘫倒在地。
众人正惊愕不解之时,下楼如厕的高丽王世子王璋疾步冲了进来,连声高叫道:“不要喝!都不要喝!酒里有毒!”
侍奉在一旁的侍卫长斡朵思不花反应最快,抢上一步,横臂将案上的酒菜通通扫落,又一把扯起惊愕于当场的阔阔真公主,强行将她拖离酒案,带到楼角,以防有变。
王璋看到地上的杨琏真迦,愣了一愣,又见宝塔实怜公主正要举杯满饮,忙一个箭步窜上前去,挥手将她手中金杯打落。宝塔实怜闻不惯奶酒味道,已经忍了许久,好不容易等到最爱的葡萄酒上来,正预备痛饮一场,却突然出了意外,不由得吓了一跳。她年纪还小,骤然生变,竟“哇”的一声哭出声来。
枢密副使囊加歹霍然站起,抚刀喝道:“都不要动!来人,速速封锁聚远楼!没有我的命令,不准任何人出入。”
恰在此时,一名侍卫抢将进来,扬声叫道:“朱万户,不好了……”
海漕万户朱清早已站起身来,闻声忙问道:“出了什么事?”
那侍卫蓦地拔出腰刀,直朝朱清刺来。事出突然,朱清一时愣住,竟不知闪避。一旁的泉州富商陈思恭眼疾手快,挺身挡在朱清面前……
这一刀刀势甚猛,如闪电流星一般,径直刺入陈思恭胸腹。那侍卫发现杀错了人时,已收手不及,呆了一呆,随即拔出刀来,一股血箭射出,喷了他满脸。
他行刺海漕万户朱清,未能一击得手,倒也不再进击,不待其他蒙古侍卫围上来擒拿,就先行抢奔到后窗边,纵身从窗口跃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