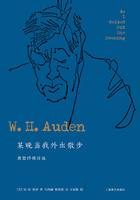
第48章 诗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当我们必须哀痛的情状如此之多,
当悲伤无处不在,我们的脆弱良知
和极度苦痛公然曝露在
整个时代的评说之下,
我们会提起哪一位?只因每天,那些
正为我们行善的人都会在我们中间死去,
他们知道这从来不够,但求
有生之年能有略微的改善。
这位博士亦如此:八十岁时,他仍希望
去思考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的任性
那么多貌似合理的崭新未来
经由威胁或阿谀正强令服从,
但他的愿望已被他否定:他双眼紧闭
无视最后的场面,有些问题对我们来说
很稀松平常,比如亲友们齐聚一堂
会对我们的死亡心生疑虑和嫉妒。
只因到最后一刻,他萦绕于心的仍是
他以前的那些研究,夜晚的动物群落、
那些仍在等待进入他
明亮的认知领域的幽灵们
全都失望地转向了别处,此时在伦敦[113]
他被剥夺了他的终身兴趣,
肉身复归了泥土,
一个杰出的犹太人已在流亡中死去。
惟有仇恨会快乐,眼下正期望扩大
它的门诊业务,而它那些邋遢顾客
以为他们经由杀戮就能被治愈,
正在花园里遍撒着骨灰。
他们还活着,而他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已被他真实无悔的追忆彻底改变;
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如老人般
去回想,且如孩子般言行笃实。
他一点不聪明:他只是吩咐
不幸的“现在”去背诵“过去”
如在上一堂诗艺课程,或迟或早,
当背到很久以前就备受指责的
那一行诗句时,它就会结结巴巴,
且会突然明白自己已被何者宣判,
生命曾何其富足、何其愚蠢,
于是宽宥了生活,变得更谦卑,
得以像一个朋友般去接近“未来”,
无需一衣橱的理由借口,也无需
一副品行端正的面具或一个
过于常见的尴尬姿态。
难怪,在他尚未确定的手法下,[114]
那些骄傲自负的古代文化预见了
君主们的堕落,预见了
无效营利模式的崩溃:
若他已成功,唉,“普遍生命”
会变得不可能,国家的基石
会四分五裂,复仇者们的
合作共谋也会被阻止。
他们当然会吁求上帝,但他走自己的路
如但丁般来到了迷失者中间,他走下
臭气熏天的壕沟,在那儿被损害的人们
过着惨遭遗弃的不堪生活,[115]
他让我们见识了何为罪恶,并非如我们所想
是那些必遭惩罚的行为,而是我们信仰的缺失、
我们否认时不诚实的语气
以及压迫者的贪欲。
倘若他稍稍露出专制的姿态,
他所质疑的父辈的严苛,就仍会
附着在他的语调与面貌里,
那是一种保护色,
因他已在敌意氛围中生活了那么久:
倘若他常常犯错,有时显得荒唐可笑,
对我们而言,此刻他就不再是
一个个体,而是某种整体舆论倾向,
我们都在它的影响下各自过活:
如同天气,他要么添堵要么有所助益,
傲慢者仍将傲慢,会发现
增加了一些难度,暴君试着应付他,
却没怎么把他放在心上:他悄无声息地
包围了我们所有的成长习性且一路延伸,
直到在最偏远破败的公国里
疲惫不堪的人们凭直觉
预感到了变化,因而备受鼓舞,
直到那不幸的孩子,在他的小小国度里、
在某个排拒自由的家庭中、
在酿着恐惧与忧虑之蜜的蜂巢里
此刻感觉更平静,莫名坚定了逃跑的念头;
而当他们躺在为我们所忽略的草地上,
那么多久已忘却的事物
被他毫不气馁的光芒所揭示,
重又归还给我们,再显其宝贵价值;
那些我们长大后曾以为必须放弃的游戏,
我们不敢笑出声时的窃窃私语,
没人注意时我们扮出的鬼脸。
但他期望于我们的比这更多。欲获得自由
常常意味着忍受孤独。他将整合
被我们自己好心的正义感
弄得支离破碎的不均等的部分,
会恢复智慧,使之愈加广阔,会缩减
意志的控制领域,使之只能运用于
枯燥乏味的争论,他将让
儿子重温母亲的丰沛情感[116]:
而他会让我们铭记在心,我们中的
绝大多数人会彻夜满怀激情,
不仅因为它必须独自呈现的
奇妙见识,也因为它需要
我们的爱。睁大了哀伤的眼睛
它那些讨喜的生灵仰望着,无言地
乞求我们让它们紧随在后:它们是
渴望未来的流亡者,而未来蕴藏于
我们的力量之中,它们也将欣喜异常,
若被允许可以如他那般效力于启蒙,
即便会被我们唤做“犹大”,如他
所曾经历,凡效命于它的人都必得承受。
一个理性的声音已沉默。在他的坟墓之上
“冲动”的同族[117]哀悼着这个被深爱的人:
厄洛斯[118],城市的缔造者,是如此悲伤,
而反常[119]的阿佛洛狄忒正在哀泣。
193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