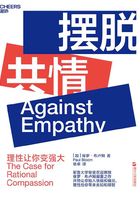
8个有关共情的错误观点
认知共情是一个有力的武器,每一个想要成为好人的人都需要它,但它自身却是与道德无关的。与之相反,我认为情绪共情实际上对道德具有腐蚀作用。
情绪共情,也就是被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等哲学家称为“同情心”的东西,常常被简称为共情。很多学者、神学家、教育家和政客都对共情大加赞颂,认为这是一种高尚的品质。但实际上,如果你正在进行一个困难的道德决策,觉得需要去感受一下他人的痛苦和快乐,那么你最好就此打住。对共情的投入可能会让你觉得很舒服,但这毫无益处,而且可能会导致错误决策和不良后果。更好的方法是运用理性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让更为冷静的怜悯和善良之心帮你做决定。
虽然有时候我也会认可共情确有好处,但总体而言,我认为没有共情我们会做得更好。对于这个立场,有很多反对意见,下面我就来介绍几个,讨论一下这些观点为什么是不合理的。
01 你口口声声说反对共情,但共情其实就是善良、关怀、怜悯、爱、道德,等等,而不是你所说的感受他人的感受。
我真的很讨厌有关术语概念的争论,因为只要能够懂得对方所说的话,具体使用什么词汇其实是无关紧要的。我确实对共情有一个特定的观念,但如果你希望把这个术语用作另一个含义,那也悉听尊便,没什么不可以的;同时,如果你认为共情实际上是道德的意思,那我要说明,我并不反对道德。
但是,我对共情这个词的使用并不是空穴来风。在英语里,empathy(共情)这个词最能描绘感受他人的感受的情况,而且比sympathy(同情)和pity(怜悯)都更合适。例如,如果你处于狂喜之中,我也因此而感受到这种强烈的愉悦,那么我可以说自己在跟你共情,但如果说我很同情你或者怜悯你就会显得非常奇怪。另外,同情和怜悯指的是对他人感受的回应,而不是镜像反映出同样的情感。如果你替一个穷极无聊的人感到苦恼,这是同情;如果你也感到无聊,这才是共情。如果你因为一个人的疼痛而感到悲伤,这是同情;如果你也能感受到他的疼痛,这才是共情。
心理学家使用“情绪传染”(emotional contagion)这个词来表达一个人的情绪感受弥散、流传到另一个人身上的过程,如看到他人哭泣,自己也会感到悲伤;见到别人开怀,自己也会心潮澎湃。即便你此时此刻本来没有什么情绪,见到他人的苦难也会物伤其类;甚至即便他人并未表达出自己的情绪感受,你也能通过推己及人来揣测他们的内心,继而与他们共情。
Empathy(共情)跟compassion(同情、爱心)和concern(关怀)都有关联,而且有时这几个词会被当作同义词。但跟共情相比,同情和关怀的用法更加广泛。说自己对上千万的疟疾感染者共情会显得非常奇怪,但说你非常关心他们或者对他们充满同情就很合情合理。同样,同情和关怀并不需要镜像复制他人的情感,而在人们充满情感和善意地对经受酷刑的人伸出援手,说他们正在对被帮助的人共情就很恰当。
不论怎么说,你都会发现,很多人,也就是那些强调要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思考、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等的人,真的认为道德源自我所描述的那种共情。
02 共情能力强的人更善良、更关爱他人、道德更高尚,这就说明共情是善的力量。
很多人都对此深信不疑。毕竟,说一个人共情能力强是一种恭维,共情可能与智力和幽默感在人们心中的分量相差无几。如果你想要在网上交友,那么,在个人描述中放上“共情能力强”肯定会让你变得更有吸引力。
人们对共情跟其他优秀特质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其实是经验性的,但我们可以用标准的心理学研究方法来测试一下。例如,你可以先对一个人的共情能力进行测量,然后看看能否根据其得分准确预测助人之类的良善行为。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精确地测量一个人的共情能力很困难。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成果,但研究发现,共情跟善行之间的相关性其实非常弱。相反,有证据证明,较高的共情能力会让人在面对他人的痛苦时惊慌失措,做出荒谬的决定,而且往往会使人变得残暴。
03 缺乏共情能力的人都是精神病态者,都非常可怕,所以我们需要共情能力。
诚然,标准测试会说,精神疾病患者缺乏共情能力或者至少更不愿意去对他人共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变态狂魔。只有当能证明精神疾病真的是由缺乏共情能力引起的时,才能说它证明了共情的重要性。
这也是一个可以在实验室检验的命题,但得出的结论却并不支持这种观点。正如后面会讲到的,精神疾病患者的问题往往与缺乏自我控制能力和恶的本性相关,而不是与缺乏共情能力相关。另外,没有证据证明缺乏共情能力与攻击、挑衅或者残暴行为有什么关联。
04 道德的某些方面可能与共情无关,但共情却是道德的核心所在。没有共情,也就没有正义、怜悯和同情。
如果这个观点的意思是人只有具有共情能力才会去做善事的话,那么很容易就能看到其中的谬误。想一想你如何评判下面这些事情:开车时往车窗外扔垃圾、偷税漏税、在建筑物上写种族歧视的话,等等。不需要对某个想象的或真实的个体产生共情,你就可以知道这都是错误的行为。再想一想挽救落水儿童和慈善捐赠。这些行为里或许有共情的成分,但显然不是必需的。
批评者会勉强承认,没有共情人们或许依然可以做好事。但他们会认为,没有共情,人们或许根本就无法真正地关心他人,或许就不会有任何同情或者关爱之心。但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例子又一次证明了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例如,我看见一个小孩因为害怕狂吠不止的狗而号啕大哭。我可能会急忙上前抱起他进行安抚,并且对他非常关爱,但是,这里面并没有共情的成分。我没有感受到他的那种恐惧,一丝一毫都没有。
不仅如此,还有更多通过实验得到的证据也能证明这一点。例如,塔妮娅·辛格和她的同事证实了,对一个人共情和对一个人同情是截然不同的——不仅在脑神经的区域上泾渭分明,两者产生的效果也是大相径庭。
05 难道你不需要任何情感压力来激发你成为一个好人的动机吗?毕竟,只有冷冰冰的理性是不够的。
大卫·休谟有句名言:“理性是且只应当是激情的奴隶。”良好的道德意图需要对不同事情进行价值排序,良好的道德行为也需要有某种动机来推动。毕竟,即便一个人知道最应该做什么,他也需要有足够的动机才会去做。
我对此深信不疑,也从来没看到过任何针对这种观点的有效的质疑。但是,认为这个观点支持共情却并不成立。休谟所说的“激情”可以是很多东西,如愤怒、羞愧、内疚,或者是积极方面的同情、善良和爱。没有共情,你照样可以有动机去帮助他人。
道德领域的伟大学者、休谟的好朋友亚当·斯密对共情这个概念非常熟悉。他曾经思考过到底是什么改写了人类的自私,让人们愿意帮助他人。他的确是想到了共情,但随后就因为共情的力量太微弱而将它否定了。相反,他认为应该是刻意的深思熟虑和对做正确的事的渴望让人们变得如此。
06 共情可以被用来做善事,有很多例子说明共情会带来积极的改变。比如反对奴隶制,道德领域的每一次革命都是以共情为导火索的。此外,共情也能激发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善行。
我同意这个观点。共情可以被用来支持良好的道德判断和行动,但前提是要先冷静地进行理性思考。例如,如果正确的行为是给一个无家可归的儿童提供食物,那么对这个儿童的痛苦共情就会激励我们去这样做。如果正确的行为是包容一个曾被我们鄙夷蔑视的群体,那么对这个群体中的成员共情就会让我们去这样做。如果正确的行为是加入对某一个国家的战争,那么对该国政府暴行的受害者共情就会让我们义愤填膺地参战。无论是慈善机构、宗教团体还是政治党派,都会把共情当作工具。如果这些机构有正确的道德目标,那么共情就会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力量。虽然我认为把共情当作道德指南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但我并不怀疑共情可以被当作一种策略来促使人们做好事。
对此,我有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研究生时期,我读到了彼得·辛格的一篇文章,他认为富裕的人应该把财富用在帮助那些真正需要的人上。辛格认为,选择把钱花在华服或珍馐之类的物品上,简直就跟因为怕弄脏自己昂贵的衣衫而对落水儿童袖手旁观一样不可思议。我被这篇文章的观点深深打动了,于是反反复复地跟朋友们提及这件事,而我们讨论的地点常常不是酒吧就是饭馆。有一次,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在饭馆里大快朵颐就是在做道德上等同于杀害儿童的事情。
后来,终于有一个被我惹火了的哲学系学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所在,他问我为穷人捐过多少钱。我只好尴尬不已地承认:一毛都没有。这件事让我如鲠在喉,于是几天后我寄明信片(这发生在有互联网之前)给一个国际慈善机构,询问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在打开他们回复的信件之前,我以为会看到一些有关他们工作内容的具体描述,但他们的方法比这要聪明得多。他们寄了一个孩子的照片给我。那是一张很小的塑封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印度尼西亚的小男孩。我还依稀记得信的内容:“我们知道您还没有确定是否要支持我们的组织。但如果您决定伸出援手,这就是您将会挽救的那个生命。”
我不知道这件事激发的是不是共情,但肯定是某种情感上的恳求,冲击的是我的心灵而非头脑。而且,这个办法非常有效:多年之后,我依然在给这个孩子的家庭寄钱。
毋庸置疑,这样的情感肯定能激发善行。在有些情况下,它可能会让人做出非常好的事情。在《陌生人溺水》(Strangers Drowning)一书中,拉里莎·麦克法夸尔描述了很多做善事的人或者“道德圣贤”(moral saints)。这是一些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他人的人。他们知道世间充满了疾苦,并且无法对此袖手旁观,他们挺身而出仗义援手。在她所描述的人中,有些是深思熟虑后刻意行动的人,比如泽尔·克拉文斯基,又比如阿伦·皮特金(Aaron Pitkin),他也看过辛格的那篇文章,并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他想,如果有一个饥肠辘辘的儿童在贩卖机旁眼巴巴地看着你,没有人会自顾自地去买一瓶苏打水;而对他来说,现在恰好就有一个挨饿的孩子站在贩卖机旁。”
麦克法夸尔描述的另外一些人是情感导向的,他们被他人的痛苦打动。这种高度的敏感性让他们苦不堪言,但同时也会驱使他们做出那些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改变。
针对那些愿意把肾脏捐献给陌生人的人,乔治城大学心理学副教授阿比盖尔·马什(Abigail Marsh)及其同事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发现,在标准的共情测试中,这些极端利他的人的得分并未超过一般人。引起研究者兴趣的是这些人的杏仁核,也就是脑中主要参与情绪反应的结构。阿比盖尔及其同事之前的研究发现,精神疾病患者的杏仁核比正常人的小,并且在观看惊恐的人的照片时,他们的反应也比正常人小。于是,研究者推测这些做出善举的人的杏仁核更大,并且对惊恐的面庞有更加强烈的反应。而这恰恰就是他们在研究中的发现。
这究竟有什么含义呢?一种可能是,这种脑解剖和反应上的差异都是由人的性格引起的:冷酷残暴、麻木不仁会让你对他人的恐惧逐渐变得不敏感,而善待他人、关爱同类却会让你对他人的恐惧更加敏感。另一种可能是,这种脑上的差异是原因而非结果:你早期对他人痛苦的敏感程度可能会直接影响你长大后成为什么样的人,当然,对他人痛苦的敏感程度与共情能力密切相关。
关于共情激发的善举,我当然可以大书特书,但这对共情的辩护作用却极其有限。所有强烈的情感都会有某些积极的影响,不仅是共情,就连愤怒、恐惧、报复的渴望都可以带来好的影响。
人们往往能轻而易举地指出共情的益处,却对它的代价视而不见。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因为人们都有一种将行为归因于自己希望的缘由的自然倾向,于是就认为共情是这些善举的源头。也就是说,人们通常认为共情是很多善良和公正行为的根源,同时认为引发无效或者残酷行为的是其他缺少共情成分的东西。但是,这其实只是一种幻觉。
所有人都有很强的偏见,认为虚构情节有巨大的能量来激发人的共情。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汤姆叔叔的小屋》和《荒凉山庄》这样的作品通过故事让读者深深感受到了人物的悲惨处境,继而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但人们却忘记了,还有一些其他的作品用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世界。斯坦福大学文学教授乔舒亚·兰迪(Joshua Landy)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例子:
在每一部《汤姆叔叔的小屋》之后,也会有一部《一个国家的诞生》 ;每一部《荒凉山庄》旁边,也会存在一部《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
;每一部《荒凉山庄》旁边,也会存在一部《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 。每一部《紫色》(Color Purple)
。每一部《紫色》(Color Purple) 之后,都会有一部《特纳日记》(Turner Diaries),当年俄克拉何马州爆炸惨案的元凶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开的那辆满载爆炸物的货车后座上,放的就是这本白人至上主义的小说。这里的每一部作品,都激发了读者的共情:伟大的狄更斯让读者用悲天悯人之心同情小杜丽(Little Dorrit);西部小说作家让读者看到在印第安人攻击下的悲苦无助的殖民者的形象;《阿特拉斯耸耸肩》等书的作者安·兰德(Ayn Rand)创造的那种精明强干的“工作创造者”形象,更是时时受到无所事事的寄生虫骚扰。
之后,都会有一部《特纳日记》(Turner Diaries),当年俄克拉何马州爆炸惨案的元凶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开的那辆满载爆炸物的货车后座上,放的就是这本白人至上主义的小说。这里的每一部作品,都激发了读者的共情:伟大的狄更斯让读者用悲天悯人之心同情小杜丽(Little Dorrit);西部小说作家让读者看到在印第安人攻击下的悲苦无助的殖民者的形象;《阿特拉斯耸耸肩》等书的作者安·兰德(Ayn Rand)创造的那种精明强干的“工作创造者”形象,更是时时受到无所事事的寄生虫骚扰。
说了这么多,你可能依旧会认为,虽然共情从总体上来说并不可靠,但我们仍然可以利用共情来达成好的目标。但事实上,共情,或者说情绪,并非人们行为的唯一动机。乔舒亚·兰迪还为另一个选择做出了辩护,我觉得言之有理:
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改变人们的看法,如借助事实的力量。我知道这是老生常谈了,但想想那部反映全球气候变化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这部纪录片对环境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整部纪录片里没有任何惹人怜爱的角色或妙语连珠的台词。再想想《食品公司》(Food, Inc.) 、《杂食者的困境》(The Omnivore's Dilemma)
、《杂食者的困境》(The Omnivore's Dilemma) 以及乔纳森·萨弗兰·弗尔(Jonathan Safran Foer)讨论素食主义的作品《吃动物》(Eating Animals)。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并没有太多以肉制品工业为主题的畅销书,但这并没有妨碍人们逐渐走向更加明智的态度和立场。
以及乔纳森·萨弗兰·弗尔(Jonathan Safran Foer)讨论素食主义的作品《吃动物》(Eating Animals)。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并没有太多以肉制品工业为主题的畅销书,但这并没有妨碍人们逐渐走向更加明智的态度和立场。
07 你提到了很多共情的替代品,但这些东西难道就没有局限吗?
它们当然也有局限。我已经对共情的问题做出了说明,它就像聚光灯一样,只会让自己关心的东西占据中央。但是,参与道德行动和判断的其他心理过程也有偏颇之处。即便是有办法把共情从脑中完全移除,我们还是会关心自己的亲朋好友胜过陌生人。同情是带有偏见的,关怀也有倾向性,甚至成本收益分析也不是不偏不倚的。即便是竭尽全力想要做到一视同仁、客观公正,我们也仍然会倾向于选择更符合自身利益的结果。
但是,它们组成了一个在程度上有所不同的连续谱。这个连续谱的一个极端是共情,而且是最差劲的一端。中间地带是同情,也就是单纯地关心他人,希望他人过得好。虽然同情也有问题,但还不算太糟糕,很多实验证据都证明了这一点,具体内容我会在后面的章节一一讲述。
理性是这个连续谱中最好的那一端。迈克尔·林奇把理性定义为寻找正当理由和合理解释的行为——为一件事找到合理的理由并进行解释,让中立的第三方能够认为它是合情合理的。具体而言,理性依靠的是观察和逻辑原则,科学研究工作就是理性活动的一个范例。
理性同样也难免存在局限,毕竟人类本就不是一个完美的物种,但在最好情况下,它能给我们带来道德上的洞见。是理性让我们能够超越情感对自己的影响,认识到远在天边的一个儿童的痛苦跟邻家小孩的痛苦同样重要;是理性让我们能够理解,虽然一个儿童因为接种疫苗生病确实非常不幸、假释项目确实可能导致强奸和斗殴,但这些事情在总体上改善了人们的福祉,所以要坚定不移地推行它们,直到有了更好的选择。虽然同情之类的情感会让人去关心某种目标,但想要达成这些目标,却应该依赖理性思维。
08 你也承认了,人往往不能很好地运用理性。很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更是进一步指出了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力其实非常差,还不如去相信包括共情在内的各种直觉呢。
诚然,在运用理性思维时确实会遇到令人困惑、不知所措的情况,会基于错误的假设得出结论,也会被自己的私心左右。但这是理性思考质量不高的问题,而不是理性思考本身的问题。美国知名道德学家詹姆斯·雷切尔斯(James Rachels)把理性视为道德的必要组成部分:“道德,最起码的就是要试图用理性指导自己的言行,也就是说,去做那些最有理由去做的事情,同时,对自己行为所影响到的每一个人都赋予同等的权重。”雷切尔斯并不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描述人们面临道德困境时是怎么做的,而是提出了一种规范性的观点,认为人们应该这样去做。
其实这并没有乍听上去的那么矛盾。即便是提倡道德情绪(moral emotions)的人,也隐性地把理性放在了最优先的位置上。例如,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认为共情如此重要,他们不会只是坚持自己的立场死硬到底。相反,他们会提出证据,会谈论共情的积极后果以及与自己关心的重要事物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他们通过诉诸理性来为共情找到支点。
我并不是想要指责批判我的同人,而是指出他们在这个方面可能缺少了一些自我觉察。这也是当今社会令人啼笑皆非的一种状况:很多学者认为理性是薄弱和不可靠的,最多也只能算作掩盖自己私心的遮羞布或者修饰自己非理性情绪的障眼法;但是,为了把这种观点说清楚,他们又不得不著书立说,字里行间都是复杂的逻辑结构、对各种数据的引用以及深思熟虑的论点。这就好比一个人坚称诗歌不存在,却写了首诗来表达这个观点。
很多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宣称,人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按照理性行动。他们认为,只有极少数的人是既有脑子又有心灵的特例,而其他人都是情绪和感受的囚徒,不会动脑子。
我只能说或许存在这样的可能。但无论如何,这跟我的真实体验完全不符。迄今为止,我已经在很多地方讨论、讲授过了道德心理学,参与讨论的不仅有学术机构和研究者,还有高中生、社区民众以及宗教团体的成员。讨论这些话题时,我会列举一些共情把我们推向一个方向而客观的分析却指向另一个方向的例子,如威利·霍顿的案例。很显然,听众并不容易接受共情让我们迷失的观念。但在我的经验里,从来没有任何一个7岁以上的听众会对这些观点的力量视而不见,并且几乎所有人都认同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能搁置自己的情感冲动,我们就会做得更好。
在有外力协助的时候,人们运用理性的能力最强,而某些社群能够让人们的理性蓬勃发展。只要能学习、运用新的方法,每个人都可以突破自己的局限。
我并没有对科学持盲目乐观的态度。科学家也是人,因而必然也可能会徇私舞弊、固执己见、因为各种力量而远离真相。但与此同时,科学本身确实成就非凡,因为科学社群成功地营造出了一种氛围,使理性的争论能够在其中自由进行、开花结果。我相信,在其他很多领域也是如此。我们有能力理性思考,并且能够在道德领域中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