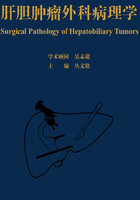
第三节 病理-生物学背景下外科治疗的展望
过去百年只要病理证实为肝癌,就千方百计去消灭它。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分子生物学和系统生物学的进步,认识到肝癌如同其他癌症既是局部病变,更是全身性病变,肝癌临床治疗的目标除消灭肿瘤外,还应加上对肿瘤与机体的改造,希望残癌能“改邪归正”,或降低其侵袭转移潜能,希望机体能提高其抗癌能力,以达到“带瘤生存”的目的。 因为已证实再彻底的手术切除也难以保证没有漏网的循环中的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CTC)。 此外,对现有的各种疗法也应一分为二,不仅要肯定其疗效,认识其不良反应,还要注意其“反作用(opposite effect)”,并采取对策。 这是提高消灭肿瘤疗法疗效的一条捷径。 我以为观念的转变,将明显扩大肝癌外科研究的视野。
预期21 世纪提高肝癌外科疗效的目标将从单纯消灭肿瘤变为尽可能多地消灭肿瘤基础上,加上改造肿瘤和机体。 提高肝癌外科疗效有多种途径,有些途径疗效提高的幅度较大,如早诊早治;有些则提高的幅度较小,如肝癌手术切端远近、手术指征和并发症的研究等。 有些是实质性提高疗效,如新疗法的研究;有些则是在肝癌某一亚群中疗效的提高,如某一疗法适应证的研究,可能较大幅度提高肝癌外科疗效的途径,下面的划分只是突出从不同角度的论述,实际上它们是相互联系不能截然分开的。
一、早诊早治仍重要但有限度
20 世纪70 年代起步的小肝癌研究至今已有40余年历史,但国际抗癌联盟(UICC)仍提出“早期发现可挽救生命”的口号。 因小肝癌切除的10 年生存率是大肝癌切除者的一倍,而且肝癌大小和切后生存率呈负相关。 如前所述,我所住院肝癌患者预后的明显提高也主要由于小肝癌切除比例的提高。美国肝癌预后正在改善,也主要由于早诊早治;意大利过去20 年肝癌生存率的提高也主要因早诊早治。近年局部治疗(如射频消融等,实为手术切除的延伸)和肝移植兴起,扩大了小肝癌患者的受益面。
尽管早诊早治还有研究的空间,如近半数AFP阴性肝癌的早期诊断,用基因组和蛋白质组技术已找到一些苗头。 但各种早治方法的疗效已接近其高限,如前所述,小肝癌切除的5 年生存率40 年没有提高;即使平均直径只有2.2cm 小肝癌,根据1305例的统计,射频消融的5 年生存率也只有59.7%。提示治后癌转移复发仍是瓶颈。
为此研究早诊早治后肝癌转移复发的防治,将是进一步提高早诊早治疗效的关键,这首先需要有小肝癌治后预测转移的指标。 我所对此虽有研究,但进入临床常规尚需更多探索。
过去几十年已证实,手术切除后继续采用继续消灭的办法虽可进一步提高疗效,但未能彻底解决问题,为此需要从更广泛的角度找出路。 我以为出路在于单纯从病理学角度看问题变为从病理-生物学角度看问题,也就是从单纯消灭的方针变为消灭与改造并举的方针。 对于已形成癌灶的转移复发,再切除、射频消融、TACE 等已证实可提高疗效,但对可能漏网的极少数残癌,采取继续消灭的策略收效甚微。 从生物学的角度,值得探索的面很广,如神经、免疫、内分泌、代谢、抗炎等全身性干预。 例如,我所在实验研究中发现,肝癌姑息性切除后合用干扰素α 与“松友饮”,可抑制由姑息性切除诱发的残癌转移潜能增强,从而延长生存期。
二、综合治疗模式将改变
癌症是多因素引起、多基因参与、多阶段形成的复杂病变;癌症既是局部病变,更是全身性病变,为此综合治疗是长远战略方向。 综合治疗在外科治疗中的作用,一是通过综合治疗使部分原先没有外科切除指征的变为可切除,二是综合治疗进一步提高了外科治疗的疗效。 癌的侵袭转移潜能是可变的(可变坏,也可变好),如能变好,则带瘤生存就成为一个目标。 外科综合治疗可大体上归纳为两大类:
(一)“消灭肿瘤+消灭肿瘤”模式
外科治疗与其他消灭肿瘤方法(射频消融、介入、放疗、化疗)的综合与序贯应用,这是从病理学背景采取的对策。 “降期(缩小)后切除”是这种模式综合治疗的典型例子,它导致不能切除肝癌预后的改善。 20 世纪后期我所便已从事这方面研究。最新文献仍有报道,如吉西他滨+奥铂使部分晚期肝癌患者转为可治。 这种综合治疗模式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如实验研究发现分子靶向治疗剂索拉非尼可减少肝癌术后的转移复发。
(二)“消灭肿瘤+改造肿瘤/机体”模式
消灭肿瘤疗法(含外科治疗)和改造肿瘤与改造机体方法的综合与序贯应用,这些反映了从病理-生物学背景采取的对策。 ①外科治疗+生物治疗剂:早在2000 年我所便已发现干扰素α 在实验研究中通过抑制血管生成而减少复发,并在临床随机对照研究中证实其临床价值。 ②外科治疗+抗感染治疗。 外科治疗可导致炎症和缺氧,而炎症和缺氧又可互为因果;这样,一系列抗炎剂已成为潜在的辅助抗癌剂。 已有报道,服用阿司匹林者降低慢性肝病患者的肝癌发生率。 ③外科治疗+抗病毒(HBV/HCV)治疗:如文献报道,长效干扰素+利巴韦林可减少丙型肝炎相关肝癌的术后复发。 ④外科治疗+分化诱导治疗:三氧化二砷治疗一种类型白血病有效的机制,主要是使白血病细胞变得分化较好。 我所也发现三氧化二砷可诱导CD133+肝癌细胞分化,减少荷瘤鼠肝癌切除后的复发,延长生存期。 ⑤外科治疗+中医中药:我所的实验研究发现,中药丹参的提取物丹参酮ⅡA,能抑制姑息性肝癌切除术后的转移,并延长荷瘤鼠的生存期;其作用机制之一是肿瘤血管内皮正常化,通过调节缺氧诱导因子1  (HIF-1
(HIF-1  )而改善肿瘤缺氧,抑制肝癌细胞的上皮-间质转化,抑制肝癌的转移。 ⑥外科治疗+其他非消灭肿瘤疗法:早年肝动脉结扎是不能切除肝癌的外科治疗方法之一,和近年TACE 的原理相仿。 我所实验研究发现,单纯肝动脉结扎虽抑制肿瘤,但促进癌播散,不延长动物生存期;而合用P13K 抑制剂-LY294002,可抑制因缺氧导致的上皮-间质转变(EMT)从而提高疗效;我所还进一步证实,缺氧促进残癌转移的机制主要是激活β-catenin。 至于外科治疗合并全身性干预将在后面叙述。
)而改善肿瘤缺氧,抑制肝癌细胞的上皮-间质转化,抑制肝癌的转移。 ⑥外科治疗+其他非消灭肿瘤疗法:早年肝动脉结扎是不能切除肝癌的外科治疗方法之一,和近年TACE 的原理相仿。 我所实验研究发现,单纯肝动脉结扎虽抑制肿瘤,但促进癌播散,不延长动物生存期;而合用P13K 抑制剂-LY294002,可抑制因缺氧导致的上皮-间质转变(EMT)从而提高疗效;我所还进一步证实,缺氧促进残癌转移的机制主要是激活β-catenin。 至于外科治疗合并全身性干预将在后面叙述。
三、消灭肿瘤疗法促残癌转移将引起重视
作为癌症治疗的主要手段,包括外科治疗在内的消灭肿瘤疗法,已经应用一个多世纪,取得了肯定的疗效,但整个肝癌人群的总预后仍不满意。 过去重视消灭肿瘤疗法的不良反应,较少关注其“反作用”,其反作用主要是促进残癌转移,这方面的报道日见增多,我所对此也进行了多年的研究。 为此研究其“反作用”的机制及其干预将有助进一步提高消灭肿瘤疗法的疗效。
近年我所建立了的高转移人肝癌裸鼠和细胞模型,应用此模型的实验研究提示:姑息性切除,放疗,化疗,肝动脉结扎和最新的以抗VEGF 为主的分子靶向治疗,均可促进残癌的转移潜能。 其机制主要是通过缺氧、炎症、抑制免疫等,导致上皮-间质转化(EMT),并伴有一系列基因的改变。 我所发现:姑息性切除可促进残癌转移,部分通过上调VEGF 和 MMP2/TIMP2;放疗促进远期残癌转移主要通过TMPRSS4 诱导的EMT;肝动脉结扎的促转移作用则主要与缺氧导致瘤内缺氧和EMT,而缺氧激活β-Catenin 是促转移作用的重要机制;奥铂化疗诱导EMT,伴下调E-钙黏蛋白,促肺转移。 我所发现索拉非尼(sorafenib)的促残癌转移作用与通过JAKSTAT3 信号通路下调HTATIP2、与抑制自然杀伤细胞,以及抑制来自宿主的白介素12b 有关。 关于消灭肿瘤疗法促癌,近年文献报道日多,如放疗致癌细胞死亡,通过凋亡机制,产生很强的生长刺激信号,促残癌增殖;抗血管生成治疗促进残癌的侵袭性。为此在外科综合治疗应用其他消灭肿瘤疗法时,应统筹考虑如何干预消灭肿瘤疗法的促转移作用。
我所发现不少临床正在使用的无关药物,在干预消灭肿瘤疗法“反作用”方面有一定作用:①细胞因子,如干扰素 α 可延长姑息性切除后生存期。②抗炎剂如唑来膦酸通过消除肿瘤相关巨噬细胞(抗炎)而提高索拉非尼的疗效。 ③传统中药在这种“反作用”的干预方面也有一定作用。 我所发现一个含5 味中药的小复方“松友饮”可通过诱导凋亡、下调MMP2 和VEGF 而延长裸鼠生存期;我所还发现奥铂(化疗)治疗后残癌转移潜能增强,而这种增强可被松友饮抑制;我所还发现松友饮可增强干扰素的作用,抑制姑息性切除后转移潜能的增强。值得注意的是,松友饮中的一个成分丹参酮ⅡA 通过使血管正常化,可延长姑息性切除后的生存期。④我所还发现酪丝亮肽,一个三肽,可抑制放疗的促转移作用。 所有这些都为临床提供潜在的途径以进一步提高消灭肿瘤疗法的疗效。
四、癌转移复发将重视全身性干预
所有外科治疗的最终瓶颈,包括肝癌肝移植,仍然是癌的复发转移。 癌侵袭转移潜能是外环境(包括治疗措施)、机体、微环境和癌细胞互动的结果。为此转移的干预应重视薄弱环节,包括微环境和全身的干预,而微环境通常是受全身调控的。 当然,肝癌转移防治也要充分发挥现有疗法的作用,事实上此前一直继续采用消灭肿瘤疗法,如对复发转移的再切除、局部治疗、TACE、放疗、化疗和针对VEGF的分子靶向治疗,虽也提高了疗效,但未能彻底解决问题。 本段将重点讨论全身性干预,这是从癌的生物学特性出发的。
现代肿瘤学主要建立在病理学的基础上,即一旦显微镜证实为癌症,便千方百计去消灭它。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深入,视野由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其结果一方面使消灭肿瘤疗法更精准,而另一方面又常因此忽略全身的作用。 近年科学的发展,使人们逐步注意到癌症全身性干预的重要。 ①神经系统:文献报道,肿瘤细胞的侵袭转移由神经递质主导,肿瘤细胞表达多种神经递质,从而支持心理社会因素与肿瘤进展有关的理论;还有认为神经系统在癌症发病中的作用是,通过体液和神经通路,将癌细胞的信息转达大脑,大脑可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对肿瘤生长作出调节。 为此,通过神经系统的干预值得思考。 ②免疫系统:由于发现免疫既有保护宿主作用,又有促进肿瘤作用,从而使免疫治疗冷却下来。 免疫治疗还有一个难题是肿瘤抗原性弱,不足以引起足够的免疫反应。 近年发现抗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抗体可明显增强抗肿瘤效应,这种免疫治疗是针对免疫细胞提高其抗癌免疫反应,而绕开肿瘤抗原这个难题。 这种免疫新药Yervoy(ipilimumab)虽然导致晚期黑色素瘤患者生存期明显延长,但仅对20%~30%患者有用,且常伴有严重甚至致死的自身免疫反应。 此外,发现分子靶向治疗剂Imatinib 的抗癌作用是通过免疫刺激;发现长效白介素10 促进肿瘤免疫可供治疗用。所有这些信息提示新的免疫治疗剂值得重视。 ③内分泌系统:早年便已注意到内分泌系统与癌症的密切关系,近年除雌激素和雄激素外,还注意到甲状腺激素,黄体酮等。 ④代谢干预:近年这个领域已成为一个热门领域:ATP 消耗促癌代谢;肿瘤细胞代谢与分解脂肪有关;脂肪细胞可促癌转移并为肿瘤迅速生长提供能量。 肝癌增殖主要与糖代谢相关,而非血管生成;长效精氨酸可使晚期肝癌病情稳定。值得提出的是,2012 年的一篇文章称:全身PTEN(抑癌基因)水平升高可导致较正常的代谢状态,能量消耗增加,脂肪积累减少,有助细胞避免癌变。 甚至有认为癌症是代谢蜕变。 所有这些都提示代谢干预的重要性。 前面一段提到的抗炎剂和中医中药,其实也大多属于全身性干预性质。 近年十分强调的“改变生活方式”,尤其是适度运动,也同样是从全身干预角度提出的。
难以指望通过这些全身性干预可以消灭一个已成形的肿瘤,对已成形的肿瘤还是需要采用外科等消灭肿瘤疗法,然而如果忽视消灭肿瘤疗法后残留的有限残癌,将可能导致癌转移复发而死亡。 改造残癌和改造机体正是控制这些残癌所必需的。
五、个体化治疗将分为整体与分子水平
不同的肝癌患者有其共性,但也有其个性。 这是由于不同的患者有不完全相同的病因因素、遗传背景、全身状况等的影响,导致癌的不同生物学表型,表达为不完全相同的分子标签。 鉴于分子生物学的进展,Hayden 在2009 年《自然》(Nature)发表文章认为“癌症个体化治疗日益临近”。 然而个体化治疗的实施需有前提:①要摸清不同个体的生物学特性才能有的放矢,这就需要研究预后指标,建立肝癌的分子分型。 例如我所和美国合作发现,miR-26a 低表达者术后适合用干扰素,而高表达者则不适用干扰素,这才能为肝癌患者干扰素治疗的个体化提供依据。 ②需要从癌细胞、微环境和机体去寻找关键的相关分子,这本身就是很复杂的事情。 现在找到的相关分子虽不少,但需要整理和筛选才能转化为临床所用。 ③然后设计分子靶向治疗剂,而当前大多是针对单一的分子,针对多靶点的分子靶向治疗将是一个趋势。 糖复合物近年又得到重视,提示寻找靶分子的视野要更大些。
上面所述是分子水平的个体化治疗,其实个体化治疗的概念在祖国医学中早已存在,即“辨证论治”,这是从整体出发的个体化治疗。 我以为这也是个体化治疗所必不可少的,可与分子水平的个体化治疗相辅相成。 诚然,要实现整体与分子水平相结合的个体化治疗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