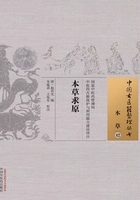
凡例
本草自李时珍泛引唐、宋以后之臆说,世人咸奉为圭臬,论者且谓 《本经》为张机、华佗所附托。然伊圣制方吻合于前,长沙及近代名医阐发于后。凡遵 《本经》者,俱登轩岐之奥窔[1],为济世之圣贤,谓为神农之书可也,谓非神农之书亦可也,吾亦取法乎上而已。
《神农本草》三百六十五种,上品百二十有五,为虚人久服补养之常用;中品百有二十,为通调气血却病之暂用,不可久服;下品百有二十,为驱寒、逐热、攻坚之急用,中病即止。今不分品第,以类聚之,非变经也,欲人便于查阅,经义明而性品自见也。
某药入某经、治某病,皆从形、色、气、味而出。盖天有五气,地生五味,以应人之脏腑。如春气温,应于肝胆;夏气热,应于心与小肠、命门;秋气平,应于肺、胃、大肠;冬气寒,应于肾与膀胱;四季之气冲和,应于脾胃,此以气治也。酸属木,入肝、胆;苦属火,入心命、小肠;辛属金,入肺、胃、大肠;咸属水,入肾、膀胱;甘属土,入脾、胃,此以味治也。红入心,青入肝、胆,黄入胃、脾,黑入肾、膀,白入肺,此以色治也。凡禽兽之心入心,肺入肺,及沙苑象肾入肾,牛膝象筋入筋,橘柚之皮象毛孔、走毛皮之类,此以形治也。又虎啸风,蝉鸣风,皆去风,此以类相从也。他若犬咬以虎骨,鼠咬以猫粪,鸡内金能化谷而治谷哽之类,是以相制而治也。蝉蜕、蛇蜕善退脱而去翳;谷麦本属土,发芽则曲直作酸;土得木疏,故消食,此以意治也。唐、宋以后,不讲 《本经》,指寒为热,指苦为甘、如柚本苦,以为甘,为酸,如芍本苦,以为酸。其所谓入某经、治某病者,遂纷淆而不足为准。今气味悉遵 《本经》,其 《本经》所未载者则参之 《别录》,考之方书,不敢妄从臆说。
上古以司岁备物,如厥阴风木司岁,采散风药;君相二火司岁,采热药之类。皆因人之有病,悉属脏腑有偏,必得物之偏气以治病之偏,其效乃速也。后人不能司岁备物,又以相反之药制之,失其性矣,是为识力不及者,防其误用之过也。然亦有加制以助其力,或加制以为引经,或加制以杀其毒,或加制以就脏腑之脆薄者,法亦不可废也。故理有可取则从之,如粟壳蜜炙则涩减,姜、附泡淡则烈除,生姜经煨则辛散,轻而温中亦微之类是也。其于理不合者辨之,如归、术加炒,则液亡;熟地烧炭,则枯燥无用之类是也。张隐庵概从气运论治,陈修园则力辟制法,皆偏见也。既不敢是古而非今,又何敢人云而亦云。
古人采药,多用二、八月,以二月萌芽,八月苗未枯而易识耳。其实,用根采于秋、冬而后实,人参春、夏采则轻浮。或采于未花之时而色鲜;紫草是也。用芽叶者,采于芽初叶长;用花者,采于花盛;用实者,采于成实之时,此其大概也。
药先标其形色、气味、生禀,所以主治之功能于前,令人识其本原,而后以 《本经》主治或 《别录》主治继之;再又以各本草、各方书之症治继之。其句疏字解,半宗前贤,今不能一一录其所本,详其姓氏,顺文气也,惜字工也,非敢淆乱而略美也。
鸡逾岭而黑,鸜鹆逾岭而白,山川水土之异也。故受清、受补,各有随地之殊。酒有饮斗石而不乱,有濡唇而颠眩者,赋禀厚薄之异也。故受攻、受补,亦各随人而别。丹溪好清,景岳重补,因其所处不同,一生之见功亦异,故各举其所见以为言。若偏执一说,则虚虚实实皆所不免。乃论者且谓古人之禀受皆厚,今人之气质尽薄,止守不寒不热者,以求稳当。岂古人寿皆百年,而今人尽皆夭折耶?此亦谬之甚者矣。
药有相须、相使、相恶、相反之说,虽不必泥,而亦不可不知,今节而录之。
古方言云母粗服,则着人肝肺;枇杷、狗脊不去毛,则射人肝肺。世俗似此之论甚多,皆谬也。盖人有咽、有喉,咽以纳饮食,则直入胃,乃传于广肠,及于大、小二肠,不入五脏;喉则上通天气,下通五脏,以行呼吸。其五脏之气,正如冶家鼓铸,凡饮食药饵[2]入腹,藉真气所蒸,则细研之石类,皆飞走其精英而达于肌骨,一如天地之气,贯穿金石土中毫无留碍;其余草木鸟兽,则气味亦洞达于五脏,及其气尽,则渣滓入于大肠,湿润渗于膀胱,皆败物不能化,惟当退泄耳。凡所谓某物入肝,某物入肾之类,皆气味到彼耳,非其质能到彼也。故谓毛能刺咽,粗石恐阻膀胱则可,谓其射肝着肺则不可。
目录每部留余地者,正欲俟高明增予之所未及也。
[1]窔 (yào要):喻深奥境界。
[2]饵:原作 “弭”,据文意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