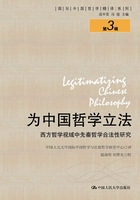
作为系统哲学家的荀子:朝向自然、心灵与理性的有机统一
成中英(Chung-ying Cheng)[1] 著
聂萌 译
一、导论
要想了解荀子,我们就必须从整体上通读并深思他所有的文章(他全集收录的32篇)[2],同时还须辨识出他在一系列彼此相联的论文的思考里发展出来的主要论题。荀子被认为是一个跟随孔子努力达到“吾道一以贯之”的系统哲学家。但他也像孟子一样回应所处时代的问题,旨在根据他关于秩序良好的社会的政治理想找到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更好的途径。因此,只有把他的时代与生活作为理解的背景,他的方法与观点才能被更好地理解,他的重要性才能被更好地赏识。比如,为何他坚持与孟子相反的性恶论?为何他提倡既追随后王又追随先贤?为何他为了发展政治管理与社会控制而提供了一个关于言与名的、崭新而详尽的重建?当然,我在此的建议并不局限于仅仅通过理智的历史途径通达荀子。相反,我希望展示出荀子理论化与系统化的一面,这对理解整个自然、人性、心灵、语言、人类社会和人类政府的基本问题是必要的。因为这些都是在荀子时代急迫需要重新思考与重新估价的哲学问题。
必须指出,在新近西方(美国)对荀子的研究中,柯雄文(Antonia S.Cua, 1933—2007)对荀子给予了最为充分的重视。他既用伦理思维的现代语言阐述和分析了荀子,又把荀子作为理解现代伦理的新维度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柯雄文提供了把荀子作为一个系统哲学家来研究的范例与钥匙。
给定了理解荀子的起初基础,同时也是理解古典时期任何哲学家的基础,我们现在可以断言,荀子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已把他的哲学系统从考虑天和人、学和知的区分与关联转移到政治管理问题上,这反映出他对儒家重建礼、义之计划的领会。但这个计划要求三个关于人的基本考虑以促成其发展:第一,对人性与人心的理解。了解在荀子那里性与心是如何区分的,非常重要,由此可以导出人性恶而人心却能变成理解与判断的敏锐的、反思的、批判的力量,提供相关的道德规范和正确的行动。第二,理解可被开发的作为宇宙资源的整个自然并了解发展人类设施的好处:他基于我们认识与估量的理性能力对天形成了一个更为积极的解释。第三,对与实相关联的名的理解:他发展了一套语言哲学,由此可以看到我们如何开始分享共同的价值标准与行动,以便行动一致且达成和谐而丰富的生活秩序。
语言的发展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荀子相信我们对语言的合宜理解与运用是达成有效政治管理和社会秩序的媒介。为了重建能够带来世界统一和天下太平的社会秩序和政治权威,我们的确需要足够多的关于自然全体的知识以及对人性与人心的合宜理解与教化。但这样的教化只能且仅能在此基础上被保证,即合理地将语言理解为确立社会秩序之功能性和政治管理之合法性的工具与媒介。这是对“礼”(典礼与社会伦理)的重建而非修复的一次新尝试,它暗示了“礼”的一种崭新意义以及一种基于对人心与人性更深认识的政治哲学。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荀子才可能一边批评孟子,一边给他的弟子(比如韩非子和李斯)以灵感。不幸的是,他们走到了律法主义的极端,这虽有助于中国的统一,但却渐渐侵蚀了人们对律法的信任。
带着这些理解,我们可以通过了解荀子是如何卓有成效地发展了孔子的社会哲学来看他如何应和了古典的儒家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他取代了孟子以王道和王制来建立政治管理的模式。但必须指出的是,他本可以把孟子整合为他体系的一部分而不必像他显示的那样抛弃孟子。在这个意义上,他的逻辑、语言与政治管理哲学还能被丰富与扩充为一个更整全的自然、心灵、政治理论。带着这样的新视角,我们可以找到荀子哲学在当今中国与全球化的世界里的一种更高水平的阐释关联与实际应用。
二、从柯雄文开始
虽然荀子的哲学已经在中国哲学史和荀子文本英文翻译的介绍中得到了各种描述和考察,但关于荀子的系统研究在当今时代还未得到全面尝试。我们必须视柯雄文为第一位从分析的观点来研究荀子道德哲学的当代哲学学者。虽然不能说柯雄文的研究涵盖了荀子思想的所有方面,但他却使荀子成为当代中国哲学里引人注目的中心,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说,保留了荀子在古典儒家传统中的中心而独特的位置。柯雄文的荀子研究是从1965年的著作《伦理论争:对荀子道德认识论的研究》[3]开始的。
之后,柯雄文在他1998年的著作《道德视域与传统:中国伦理学论文集》[4]中提出了许多洞见。在2005年的著作《人性、礼仪与历史:对荀子和中国哲学的研究》[5]中,柯雄文最终构想了荀子的人性哲学,并处理了与荀子的伦理、宗教哲学相关的许多其他主题。他所采取的立场与唐君毅类似,即把荀子的宗教部分视为伦理哲学的延伸,并把精神的诸种存在视为我们自身的创造物(伪)或“与我们的反思的伦理经验相伴随的品质,在宗教诫命的背景下对我们的伦理情感或思想的表达的结果”[6]。跟随他对荀子的思考线索,人们很可能期待柯雄文发展出关于荀子哲学的完备的系统研究,它植根于德与礼的某种统一,涵盖荀子思想的所有方面。遗憾的是,柯雄文没有足够的时间这样做。另外,人们也想看到柯雄文在构建他自己的伦理哲学时是如何受到他的荀子研究或荀子的影响的。他关于合理行为和典范人物的思想就是很显著的例子。
这样理解柯雄文,以下这个说法就是相当正确的:柯雄文在当代分析哲学的背景下开启了荀子研究。他早期与我就儒家哲学的交流为这种新的改变和冒险提供了某种基础,同时这种改变和冒险明显也是他受荀子自身的分析与论证方法吸引的结果。柯雄文想要做的是进一步概念化地分析荀子的核心观念,且达成一个经由逻辑与语言的论证而推进关于荀子主要论题的构想。这些都是柯雄文用以研究荀子的重要方法,然而它们与我早期为现代与西方的读者对中国哲学做理性的重建的提议是一致的。柯雄文成功地做到了这点,因此证明了概念性分析作为研究中国哲学文本方法的有效性。但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柯雄文把当代伦理学的概念加于中国的文本之上,要归因于他自己对当代伦理学的考虑。
在某种意义上,柯雄文对荀子做了一个与要求全面、系统了解的“向—解释”[7](to-interpretation)相反的“自—解释”(from-interpretation)哲学诠释学研究。柯雄文没有太多触及荀子对天的本体与宇宙的论题,而是把人主要认定为需要把共同体作为发展基础的伦理动物。正如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将看到的,在荀子之天人区分与关联的系统框架内认识到他在人的发展观念上与孟子的迥异是很重要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看到如何用荀子对人的完整理解来补充柯雄文的概念性分析,如我所倡导的系统哲学的观点那样。
三、天人的区分与关联
据说在公元前32年刘向编订《荀子》的时候,传世的《荀子》一共有322篇。最后,32篇被挑选出来,并被鉴定为荀子真正的代表作。这成为我们目前的《荀子》读本。通过阅读《荀子》,并基于我们对他传记背景的了解,我毫不怀疑荀子是一个系统哲学家。他几乎思考了他所处时代的所有主要哲学论题,并为一个构建完好的人类社会与共同体的理想和目标而写作和论证,认为这存在于基于礼义和礼法而发展的社会与共同体中,在这里不仅没有斗争和冲突干扰人们之间的有益关系,而且人之为人的潜能将会得到充分的实现。[8]在这个意义上,荀子既是一位社会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位社会现实主义者。他礼法社会的社会理想主义建立在学与教的社会现实主义的基础上,他的制度与政策控制(王制)建立在把“知道”既作为方法又作为目标的理性反思与逻辑说服的基础上。
在对他哲学思考的框架与内容进行了简短的概括以后,我们就可以追问:作为可以把所涉及的每个哲学论题很好地关联和整合起来的系统哲学,什么是荀子哲学的核心和最基本的考虑?提出这个问题是在寻求对荀子哲学根本观念与起点的洞见。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我们可借此懂得荀子的许多重要考虑和论题,然而这需要对如何预设他的哲学有番理解。我们需要某个阐释其他思虑的中心思虑带领我们更好地把握荀子在各方面的哲学思考中的议题和问题。比如,有学者谈及荀子人性恶的理论。这是他人性论与人的哲学的起点吗?不,我们需要看看别的地方来确定一个主题,它能够使我们解释为什么荀子认为人性恶以及在什么意义上为恶。
我认为,准确系统地理解起来,荀子核心与关键的观念是他对天与人所做的区分与关联。这个区分与关联已被描述为“天人相分”[9]。至于这种区分与分离为何可能以及如何可能,仍旧是一个难题。然而相当清楚的是,正是源于这种区分与分离,人既有自由又有责任来发展他的智力与对自身命运(即自我发展和自我意识)的控制感。这种区分基于这样的事实:尽管天有自身在时间的进程内不轻易改变的未定规律,但人却有智力与认知力为他的存活与发展对自然物进行探索。尽管天有一个律法般的存在,但人类却是一种以寻求自身在自然之中的善好富足为目标的目的论的存在。但是,如果人没有注意到自然规律并适应它们,那么他将不能存活或成功。另外,如果人类发展自身对知识与价值的认知与理性能力,那么他将在实现自身目标与存在的潜能上处于优势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有一种人依赖自然的内在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人类知识对自然的依赖关系。这个关系在荀子《天论》的第一段中有很好的表达:
在这篇文章里,荀子把他的观点置于天与作为国家统治者的人的区分之上,所以提到了尧和桀。但这个区分毫无疑问也适用于个人。个人为了自身的存活和富足必须调整并适应自然。事实上,整个人类在行动中都必须注意到自然的因果律。如果一个人不努力工作又不节省花销,那么他不可能靠天而变得富有。如果一个人不节省生命的资源并按时行动,那么他不可能靠天而获得平安。如果一个人违背了自然之道,任意放纵自己的欲望,那么他不可能靠天而取得成功。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自身生命的主人,没有自身的努力,天是无法使他顺达的。
正如人们可以看到的,正是由于自然的因果律,人努力则取得成功,懒惰则蒙受损失。人们甚至可以说,正是自然或天使努力的人成功,使懒惰的人失败。即便天有自己稳定的规律,人毕竟还是不能与天分离,因为作为人类,我们依赖天使我们努力发展自身,这事关获利,而缺失这样的发展,则事关遭损。这个天的力量的观点和荀子之天人的区分与关联的观念是完全相容的。天的稳定规律有潜力在人类个体与共同体的善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显然,共同体的形成、社会的发展、政治的组织以及礼义所统率的道德制度规则本身即是人对其导向人类目标之实现的智力与理性的使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天或自然为人类的发展与自我实现提供了基础,只要人类认识到它并拥有利用这种认识的智慧。因此,荀子在《天论》将近结尾的时候说:
荀子认识到天有其和谐运作的自主性,这在日月与四季的运动中得以展现。在拥有自然力产生生命并维持万物生长这个意义上,天对荀子几乎是一个宇宙的自然。它让“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321页)。他甚至把天想象为一种无人见其事、众人见其功的力量。他关于天的观点明显受到老子和庄子的影响,因为他的天论最终使得天关乎道,这道人们不能从具体样态识别,却能在其所生所存的具体事物上经历。在以上有力的宣言中,荀子清楚地表明:天具有可以被人利用的资源;人利用天的能力是人接近天的一种方式,也是人为自身的发展而发展天的一种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天人之间也有一种联合,这种联合不是在对一个崇拜对象的感情依恋上,也不仅仅是在宇宙论的理解或形而上学的沉思上,而是在为着实现人作为一个个体、作为一个共同体、作为一个国家的善好而参与天的力量的现实化的努力之中。
四、从对天的知识中发展人
在这个意义上,荀子表明天不仅是人类生命的由来和资源,而且是人类生命发展的资源,所以不仅人为着自己的善好来依靠天,而且天也依靠人来使它的力量和潜能可感且有效。如果我们把“天”这个术语替换为“道”,我们就很容易认识道家哲学的一个观点,即道利万物之生长而不争。但荀子与老子、庄子之间仍然有一个大的差别:老子和庄子让人模仿并追随道,所以人并不致力于达成自身的善好;然而,荀子却断言人需要像道那样付诸最大的努力去发展和行动,旨在企及自身的善好并实现自身生命的潜力。在这点上,荀子毫无疑问更接近儒家而非道家。我们会在稍后的讨论中更详细地阐明这个观点。
人需要发展自身,因为在荀子看来,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且事实上是自然中最富有生气与创造力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荀子会说:
所以,从本性上说,作为天的潜力的最佳代表,人能爬升于诸物之上。然而,人的潜能必须作为其本质的部分而得到发展,并且这将使人真正成为天的代表。很明显,荀子发展了孔子所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11]的儒家洞见。儒家所认为的道可以说是天的道,因为正是天创造了这个世界与人,并且在这种创造中有规律可循。由于意识到了自身的创造潜能,继续这个宇宙的创造并且使得人类文化与文明的创造成为可能,就成了人的责任。可以说,这样去做既是发展与称颂天的一种方式,它同时也实际存在于人类潜能的实现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荀子遵循了儒家的洞见,从而把人类共同体和人类文化的产生作为实现人与天之本性的绝对必然。由此,我们看到荀子是如何以与孟子大不相同的方式形成他自己的天人统一论的。在孟子那里,人们看到了对一种认识的寻求,即认识人在天那里的同一性,以及认识人在自身内在善那里的同一性。这种内在善产生了自然道德。对于孟子,道德即“反身而诚”[12]。我们可以看到,孟子沿袭子思,在天的原初创造力那里论证人与天的同一性,而荀子则论证人的潜能的发展以天的实现为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他对人与天的区分与关联的论证是天与把天作为人类发展目标之途径的人的同一性形式。如果我们能把孟子的观点视为“人性的启蒙理论”,那么我们就能毫无疑问地把荀子的观点视为“人性的完成理论”。我们不必去看两种观点的决然对立。两者都始于儒家对不断完善的人性的思考。它们相互补充,一起清楚地阐释了儒家人性论的全部隐意,即人性源于天又发展天。
然而,我想就荀子的天论作两个更为重要的评价。首先,荀子认识到天的自然运作与人的自然运作。自然(天)之物在没有人的干涉之下自我呈现。这并不是要把预想的种种特质归于事物或天。它和本质主义无关,也无涉现代反实在主义。[13]因此,四季的运动与气候的变化是自然的自然运作部分。人无须为此运作负责。荀子说:“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319~320页)其次,他断言人不应该与天的自然运作竞争(不与天争职)。在此,他强调了对子思在《中庸》里表达的参与天地之工作的观点的拒绝。他指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320页)。认识到这样的区分并且尽到自己的职分就叫作“能参”(能够与天地相配合)。如果逾越了,就只能是混乱。这里存在自然的运作与它们经由人的合宜配合的区分。
很清楚,荀子把子思和孟子的天人合一理论视作人对天地的竞争与侵占。基于当今环境伦理学的考虑,荀子的理论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荀子那里,人对自然的态度是通过配合天而利用天,虽然荀子的解释中也存在模棱两可之处,但他的确想让人通过探索天来利用天。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人是在利用天而不是消耗天、危害天与人呢?很显然,对荀子而言,这种探索和利用一定存在一个自然的界限。对他而言,此界限也有待人去发现。[14]
出于同样的原因,人类有自己的自然运作,然而这种运作需要通过机智地顺应自然来发展和转换。换句话说,一个人需要知道自己的生命归宿,这种归宿来自他对天或天之道(这个道在天的自然运作中得到展现)的认知。知道它旨在调整自己以适应它,而非试图改变它。在这个意义上,荀子想重新定义孟子以“知性”作为其基础的“知天”概念。在自己重新定义的过程中,荀子提到了感官的自然运作和心作为五种感觉之统帅的自然运作。
对荀子而言,人的自然器官的自然功能应该既保持秩序又为着更好的使用而发展,圣人就是如此而区别于常人的。对于后者,他们的器官常常是昏暗的、混乱的、放任的、不恭的,因此不能完满地实现它们的自然功用。他后来称之为“蔽”。[15]相反,一位圣人却能移去他的昏暗,“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322页)。
为了做到这点,一位圣人必须始于学,并且反思他自身的思考、认知和理解能力,以便越来越明了发展其自然功用对他提出的要求以及如何完成。他需要自觉地意识到他的能力、需要和目标。他需要知道他属于哪一类存在,从而能够在人的能力范围之内合宜地发展自身。他需要在自然和社会的背景下被其自身的自我塑造所转变,从而能利用天并通过构建与发展他称之为礼和义的文化形式与制度规范来帮助他人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荀子谈到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分。前者是那种尊重自身所有但不渴求天之所属的人,而后者则是那种放弃自身所有却渴求天之所属的人。君子通过发展其所有而最终成为圣人,心无遮蔽地处在为社会与文化的建立而发展原则的位置。对荀子而言,任何过度的欲望和偏离人类发展规范的成见都是蔽的形式,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16]
五、人的目的及学的途径
在澄清了荀子对人与天的区分与关联之后,荀子哲学的所有主要命题都将开始有秩序。事实上,这样的理解为定位人性与衡量人的价值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这样的一个框架里,一个人能够识别他的人生归宿与努力方向,因而可以在他的生活里找到意义。在这样的一个框架里,一个人能论及人类的理性与道德,据此可说人性能够加以发展和完成。我们能看到,如果谁想发展自身,那么他就需要学习和掌握自然知识,以便可以利用自然知识来避免过失和达成理解,从而为行动作出正确的决断。他也需要确保他能够发展自身,并且为了掌握原则、规范与准则而努力超越自身,从而使得自己能够作出负责的、可靠的行动决断。他还需要觉察到他的自我实现所仰赖的人类共同体与社会的景象。因此,他必须知晓他作为人的身份与地位,从而能够合宜而持续地追求生活的长期善好。一个人必须通过学习知道人类最终的理想归宿并努力实现它。
对荀子而言,人必须从先王、后王以及老师那里学习。因为正是在圣人的行为中,人们看到了发展自身品格与转化自身欲望的榜样,这样他们就不会因被遮挡或蒙蔽而陷入自私的利己主义与偏见。荀子评论到,如果不努力学习,如果不学习历史与经验,人就不可能合宜地使用自己的器官,就不可能形成对外部事物的正确理解。人将不能就什么最利于人的善而形成清晰的判断,从而无法达到使人类生活有价值、有意义甚至欢悦的更佳发展状态。
对学的关注引导着荀子去处理关于认知的基本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如何知晓道或天道。一种回答是,人们必须移除在生活当中遭遇到的遮蔽。荀子列出了十种蔽的形式:欲、恶、始、终、远、近、博、浅、古、今。[17]事实上,由于存在全然不同的事物以及不同的视角,所有这些不同都会对完整全备的认知构成遮蔽。因此,为了知晓道,人们需要反思他们是否被看待事物的一种角度、一种观点或一个预设的情感状态占据了。人们会很轻易地陷入这种头脑(mind)与心灵(heart)的狭隘,这是自然的。经验主义者不会阻止人们狭隘地采取观点。问题在于:人的脑/心是否能对所采取的立足点保持开放与反思,从而使得人可以看到别的观点,并基于更大的事物景象和更宽阔的认知视野来改善自己的观点?概括地说,我们能看到荀子提出了三种基本途径来打开人的脑/心,旨在超越蔽并且形成完备而清晰的认知。
第一种途径是从历史事例中学习。人们可以看到君臣不同的成败故事在整个历史背景下对克服蔽是如何有用。我们可以把那些故事仅仅视为在蔽和与蔽相对的明(清晰、明朗)[18]之间所做的奋斗。这就是为何对人而言学习历史是如此重要,因为人必须从经验中学习,而历史经验即是经验。通过学习历史与经验,人们或许就能对事物的性质了如指掌,判断力也会得到发展,这样一来,人们就能知晓事物差异中的定则。荀子把能够知晓或制定事物差异中的定则的人称为圣人,因为这样的人展示出了心灵(mind)与理性在清楚地观察事物、领会事物的目标及为正确的行动制定定则上的极大成就。因此,圣人将能把握事物的差异而不会遭到它们的相互遮蔽。
至于这些成就如何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发生,荀子仅仅诉诸能够成为知晓事物定则之基础的心灵之启蒙功能。我们可以视之为知晓道的第二种途径,它在于人类头脑—心灵的自我培养。事实上,荀子认为头脑—心灵的基本功能就是去知晓道,且它能够做到,因为人能培养自身的头脑—心灵以达到一种虚一而静的状态。他说:
正是在这种大清明的状态下,人们才能看到事物所包容的整体,而不陷入任何一种偏颇。人们将能够“坐于室而见四海”,“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415页)。换句话说,人们将超越事物所有的差异,获得一个看待事物的整体视野以及用以规制它们和引导它们进一步发展的定则。这是一种“中县衡焉”[19](413页)的状态。荀子将会认为孔子真正达到了这种心灵状态,因而成为一位圣人。所谓的“衡”正是荀子认定的“道”,注意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道比道家所认为的道多了组织与整理这两个基本功能。也许我们可以更多地把道视为认识论的和道德的,而非本体论的和宇宙论的,即便它可能来自一个宇宙之源,正如人们在天的自然功用里看到的那样。因此,这个道再一次更接近儒家而非道家:它是完全的认知与从一个目的论的观点洞悉事物是如何可能被组织并朝着更好的状态发展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荀子说“心知道”,并因为这种知识而说“可道”。站在人和人心的角度来认知道,这种知识就既是描述性的又是说明性的,既是经验论的又是价值论的。
还有第三种途径可以移除蔽、避免未来可能会发生的蔽并因此而知晓道,那就是从先王、后王以及圣人那里学习。《荀子·解蔽》的最后一段强调了这个观点。荀子认为,哪里有领会了管理的所有基本原则的王,哪里就有领会了事物的所有基本性质的圣人。在此,荀子是从已达成发展而非谋求发展或正值发展的观点而言的。根据这个观点,定则已经建立起来,因此在决定正误、好坏之时,导源于此的隆正就必须被遵循。[20]这会形成依法管理的观点,但也会形成权力的观点,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律法主义与法家统治。就此,很明显,前两种途径更适宜理解人类如何得以发展,以及一个理想的社会与政府如何在一个开放的反思与开放的学习过程中仍旧得以保持和维系。
六、交流与制度化
以天与人的区分与关联为前提,我们也能看到正名与礼义的制度化对保持与维系一个发达的人类共同体、社会与政府是何等重要。为了有一个能够维系的共同体、社会与政府,交流必须通过对名与语言的正确使用来维持。这是因为,如果一个人想实现他自身的潜力,完成人类生存与繁荣的核心价值,他就需要通过好的交流,因此需要通过对语言的合宜使用来达成与其他人的团结与信任。荀子在“正名”问题上的强烈兴趣在于认识名与它们的逻辑连贯性的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基础。[21]他想看到名与语言在这种连贯性中被保存,并且又能随时发挥交流和团结人的情感与思想的社会功能。因此,这个问题在他的第22篇论正名的文章里被涉及了。这再一次表明荀子有意识地遵循了孔子在这个问题上的建议,因此,可以说他以一种更为精巧及全面的方式说明与阐释了孔子的正名学说。[22]
基于这个正名理论,为了实现人性以及繁荣,荀子可以在人之潜力的发展上再推进一步,即探索使一个理想社会及一个理想国家得以建立的各种途径。这实际上是荀子努力的主要焦点:他希望建立一个由人类发展之典范因而也是所有人效估之核心的贤明君王所规制的有秩社会。因此,可以看到,荀子花了更多的篇幅和时间来论证和建构这样一个理想的规则。在当前所收的他的作品里,有11篇文章可以说是以理想的规则作为主题的。在这11篇文章里,第9篇《王制》对为政这个主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这一点非常突出,在这里政治管理、组织问题及行政管理问题皆得到了考察,其中一些还辅以历史事例进行说明。这篇文章值得独立分析与解释,尤其是基于当今的公共管理、政治管理与管理伦理学。[23]这篇文章足以说明荀子的政治哲学与社会理想论已达到了巅峰。
七、人性真的恶吗?
基于天和人的区分与关联来辨识荀子哲学的基本框架,其中一个主要目的是想表明需要对他的人性论进行重估以及给予其一个新的解释。传统上认为,当荀子提及人性恶时,他表现的是对人类存在之品质的消极态度,因而不尊重世界之中的人性。如果人性是恶的,那么我们如何能弥补它或首先信任它呢?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从唐代晚期开始荀子即被不公地排除在儒家的主流之外。与之相反,孟子被认为展现了对人性的高度自信,因为他主张人性为善且能实现人类社会的善。但事实上,我们必须注意,即便荀子反对孟子而主张人性恶,但他更多地聚焦于对普通人身上展现出来的普通欲望的观察,旨在论证为何普通人的行为需要改善。在他的观察之中有三个术语需要逻辑上的澄清:人、人性与恶。让我们先从人这个概念开始。在观察中,我们的确看到大多数普通人的行为展现出荀子在《性恶》篇中所识别的三种自私的特征:好利、疾恶、耳目之欲。因此,荀子的论述是对被我们视为与克服了如上自然欲望的君子相反的小人[24]的大多数人的概括。如果这样的欲望可被视为深深地扎根于人性之中,那么它们一定不会被改变或被从人性中移除。处置它们的唯一途径是通过人的其他力量来释放它们或控制它们。
很明显,在荀子这里我们可以采取后一种改善人类状况的方法,即通过引进理性或知识,将其作为控制私欲的手段。很明显,我们确实有理性和反思的知识来帮助我们克服欲望。然而,这种理性与反思的能力是不是也属于我们的本性呢?人性是否仅限于普通的观察?抑或人性的确有一个深度,它会在合适的时间与相应的情况下被揭示出来?稍后,我们将就人性的这一点多谈一些。最后,关于人类的欲望与本性,什么是“恶”的呢?说人性恶意味着什么呢?也许,对于第一种欲望,所谓的恶是指如果不对其进行控制,那么它将把人引入一种冲突与抵触的状况。类似地,对于第二种欲望,所谓的恶是指如果不对其进行控制,那么人随之将在个体之中遭遇伦理与道德的缺失,并因此而造成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对于第三种情性(“情性”是荀子的说法),即对感性愉悦的喜爱,如果不对其进行控制,那么就会同时导致冲突与争斗。在这三种情况下,随人的欲望与情性而动将不会促成更大的社会利益与财富,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灾难与可能发生的政治压制。因此,说人性恶等同于说它会带来恶的结果或后果,从政治—社会—道德的观点来看,它是不被认同的。基于这个事实,像“善”与“恶”这样的道德词汇在它们的使用中已倾向于描述该做什么与不该做什么,旨在避免不快的结果及达到合意的目标。
善的即是被接纳的、行得通的,恶的即是被拒绝的、行不通的。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到荀子说人性恶是在说某些欲望必须被控制以避免令人不快的后果。或者换种方式来表达,说一种欲望在未被监察或控制时是恶的,是在预测某些诸如混乱和专制的被拒绝的、行不通的后果。因此,我们确实可以提及柯雄文在他谈论荀子人性论时所指出的善与恶的后果感。[25]由于这些后果尚未在特定的情况下发生,所以我们甚至可以更精确地从一种预期感上提及善与恶。并不是那些感觉与欲望在本质上是恶的(事实上,它们在某种可以构想的社会与经济条件下对某种目的而言可以是有益的[26]),而是追求它们的可预期结果被认为是恶的。因此,它们是在关乎结果的预期上被认为是恶的。一旦我们看到善与恶在这个预期的角度上的使用,我们也能看到这两个术语在另一个预期的角度上的使用,即说人性恶就是说它需要改善、引导和提炼。如果我们聚焦在后一种对社会—政治—道德国家的预期的意味上说人性恶,那么就不存在人们基于后果的视线所见到的那么多的谴责或悲观了。
在对这三个术语“人/人性/恶”的基本分析之后,我们能看到荀子把“人性恶”的宣告或评论视为不发展人性的潜在危害的预警,及基于结果的善与利对发展人性的必要性的提醒。带着这样的理解,荀子的宣告或评论会有什么错呢?对那些希望维护孟子性善论的人,我们一定要说孟子迫于否认这个宣告及其实际的含义吗?完全可以想象,孟子不会否认人性可以被发展与改善,即便他可能认为人性原初是善的或本质是善的。他可能会同意荀子作为评论的宣告,并且在包含常见欲望的人性的扩展概念里基于改善人性的需要而赞同荀子。
人们可能会把荀子对孟子人性善论题的反驳视为对“性”这个词的误解。对孟子而言,人性或性植根于天地之间,当没有诸如欲求某些具体事物这样的矛盾因素时,它会自然地呈现自身。的确,人们在普通的世界里会欲求利益及感性愉悦,在具体的环境下表现出仇恨与嫉妒,然而人们在普通的世界里也会欲求爱,也会欲求因高尚行为所获的称赞、精神的安宁与美德,甚至在其他一些具体的环境下会表现出富有同情心的仁慈与宽容。人们会自然地厌恶仇恨的行为,嫌恶嫉妒的爆发。被激情所驱使的人性会非常复杂,对不同的对象,它会回应以各种各样的感情与欲望,有一些我们可能会视为预期的那样恶,有一些我们可能会视为预期的那样好。因此,荀子与孟子不必在关于人被激情所驱使的本性呈现不同的欲望与感情这件事上争论。根据荀子与孟子之间的争论,孟子可以接受荀子所说而不放弃他对人性存在之初本为善的评论与理论见解。所以,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是,若我们基于荀子之天人的区分与关联来阐释孟子,荀子能否接受孟子的观点。
我的回答是:我们确实能以适宜荀子对人性的理解方式在一种扩展的意义上重构孟子。孟子所论证的是,在既定的最佳环境下,所有的道德情感皆能在四端里得以识别出来。以乍见入井的恻隐之情为例,我们经历了奔走相助的冲动了吗?作为一个经验的陈述,说人们普遍地经历到这样一种冲动对证明仁德之始是无足轻重的,因为这个道德可能必须得同时包含公义的理性因素以及人们经历的情感,而不单单是这个情感因素本身。但人们可能会争辩说,情感因素为发现人性里更深的东西预备了契机,由此人们可能会理性地采取这个情感,按照道德律令的驱使行动。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到荀子如何能把导向自私的情感与欲望视作理性反思的一个契机,因而是诸如礼与义这样的美德理性发展的基础。事实上,荀子已论证并揭示了人心有知晓天道的能力这个事实,即把平衡、和谐、自制及诸种关系的整全视作进行道德评价的规范性基础,因此是实现或发展人性的更深层面的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荀子没有理由不认为孟子提供了人性的一个层面,这个层面将会自然地适应他在《解蔽》篇中所提出的人类对道的认知理论。他自私的欲望与情感的理论没有理由不可以与孟子纯洁的情感与意志的理论相调和,这在他反思的理性与规范的道的理论里也有所反映与体现。当然,理性与道在荀子那里的地位和情感与意志在孟子那里的地位仍旧存在根本的差异。但这个差异仅仅指出每一方皆呈现了人心的一个方面这样的事实;人心既要求有意识的领会,又要求有作为行动的决定性力量之因素的情感的回应。人心是理性/情感与意志的不可分的统一体,这使得人能够去知道,去按所知的行动,去按所行的获知。这正是构造与组成人性的方式,若我们可以谈及对人性之反思的领会的话,因为我们不仅希望用我们的欲望、情感与知识来解释我们的行动,而且希望在作为人而定义与发展自身的过程中顺着这个知识—情感与行动相互作用的线索来计划我们的生活。
重要的是看到在荀子那里,他把人性看作一个需要且要求发展的动态过程,正如在历史与理论的背景下所见的那样。人和自然、天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需要超越自私的欲望和情感,通过唤醒我们对体现在天的规律中的道的理解力和感知力,把自身转变为一个更高、更大的存在。荀子的《天论》篇已经确定了人性的这个潜在方面,正是基于此,关于社会之礼与义的哲学才得以发展。这是一个现实的理论,因为它建立在对天及天之道的现实的观察的基础上。实际上,正如我们在如上来自《解蔽》篇和《天论》篇的引文中所见的,荀子已经预设或确定了包含朝向发展的潜在的善的人性层面。我们可以把这种潜在的善视为控制私欲的能力,视为为着集体的生产力与相互提高而进行劳动分工和组织共同体与群体的能力。它们隐现于人性之中,荀子一般将其描述为“义”,正如他在《王制》篇所言“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识别出人性的这个隐而深的层面。但和孟子不同,他会认为人们只能通过学习、揭示既往的历史教训及圣王教导来获得它们。它们必须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意识到、经历到,才能成为人们行动的基础。历史与道德教训可以是有效的,它们在人类的情感里也有一个基础。人类的情感可以说是扩展了的人性的一部分。
我以上的论述已经澄清了以下这一点:对荀子而言,人性在所有可能的意义上都不是恶的。在他对恶的使用中,恶会伴随着善。他关于由于缺失善人们会欲求恶的观念是一种教导的观念。但却可以说,人们会在感觉恶的基础上追求善这个事实证明了人性毕竟确实是善的,因为在这个善里,恶仅仅是一种缺失的迹象。
我们必须进一步指出:确实存在道德上的恶,但这种道德上的恶不是作为社会共同体可预期的结果而成为恶,而是因为有意识地、有意图地利用知识,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追求自私的目的而成为恶。荀子在他的历史事例中已触及这个意义上的有意的恶,但他尚未区别于可预期的、归因于大多数人在生活过程中的自然欲望和情感的无意的恶。
最后一个问题关涉荀子人性论中的大清明理论,我们会问:普通人是否可以成圣?答案是:如果一个圣人可以成圣,那么普通人也可以成圣,因为圣人和普通人在他们基本的及扩展的性质上并不存在本体上的根本差异。荀子发展了他的人心理论,其准许圣人的智慧得以发展,以便让每个人都可以谈及对道的知晓。任何人没有理由不把道作为终极规范来学习,及把道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荀子也提供了知晓道的三个主要途径,如我在上文所揭示的那样。因此,所有人都可能成为圣人。同时,作为社会现实主义者与社会理想主义者,荀子把他的人性论看作他天人的区分与关联的基本框架之中的人类发展理论的一部分,看作他关于人类使用语言和发展人心的能力的结论性观点。因此,反思孔子,必须融合荀子和孟子。
八、结论
综上,在对荀子进行了新的——整体化、系统化、综合性的——分析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对荀子有一个全面而均衡的了解,既关涉他的理论内容,也关涉他在古典儒家哲学中的位置。荀子许多新的独特的特征反映了他在人类本身、人个体、人性、人的道德、人类社会与政府问题上的经验与反思。其中一个很大的贡献在于他对人性各种主题的推论式分析与系统化论述,这些人性主题对理解个体、社会与政府是至关重要的。他很重视对生活与社会的观察,并认为历史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里的事例与个案研究。因此,他为儒家提供了一个要求融合历史、理论与经验的新的视角。他也基于对被孟子和其他哲学家专门论及的人性的潜能与目的的道德反思,细心构造出一个关于社会动机与政治管理的完整哲学。在这个意义上,他同时融合了《大学》与《中庸》的传统,把他的哲学同时奠基于经验与反思之上。
除了方法论和政治哲学,荀子还基于经验与反思并关涉天与人的区分与关联,呈现了一个整全的人性论。正是他批判性地检视了子思与孟子的人性论及其角色,揭示了现实的一个需要通过伦理与教育来处置的维度。通过这种方式,他论证了人类历史与文化作为道德资源的合理性,道德是人的全面发展所必需的,因而对人类的生存与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他能把孔子所思的全部线索牵引到一起,并把孔子的洞见重建为社会—政治的理想和一项个人提交的、可实现的事业。在这个意义上,他完全涵盖了儒家的外在主义与内在主义的论题,并给予它们以完整的形式与有机的相互关联。虽然他常被理解为仅仅是一个自然主义的哲学家,但实际上却不是。他的道、天与人心对道的知晓的观念,为人与天的重新连结提供了基础。
虽然荀子看起来提倡一种许多人不喜欢的人性论,但通过聚焦人类存在的现实方面,这个人性论却正好变得更加动态化、开放,甚至有创造性。我们对荀子全面而系统的解读与诠释,将为更开阔、更连贯、更完整地理解与重建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儒家提供一种新的途径,作出这样的结论是合宜的。[27]
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
夏威夷州,火奴鲁鲁
注释
[1] 成中英(Chung-ying Cheng),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季刊》主编。主要研究领域:儒学与新儒学、诠释学与本体诠释学、形而上学与语言哲学。邮箱:ccheng@hawaii.edu
[2] 《荀子》文本有许多版本。在本文,我使用的是著名的传统中文文本——清代学者王先谦注释的《荀子集解》。我也参考了清代学者汪中介绍荀子的著名著作——《荀卿通论》。在段落的一致上,我使用了齐思和编辑的《荀子引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在页码的清晰上,我使用了高长山的读本《荀子译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3] Antonia S.Cua, Ethical Argumentation: A Study in Hsuen Tzu's Moral Epistemolog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4] Antonia S.Cua, Moral Vision and Tradition: Essays in Chinese Ethics,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98.
[5] Antonia S.Cua, Human Nature, Ritual, and History: Studies in Xunzi and Chinese Philosophy,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05.
[6] Antonia S.Cua, Moral Vision and Tradition: Essays in Chinese Ethics, p.189.See William David Ross, The Right and the Good,Indianapolis, Hackett, 1988 [1930].
[7] 在我作为方法论的本体诠释学(onto-hermeneutics)中,我区分了两种阅读与解释:一种是带有前理解的、形成“自—解释”的阅读与解释;另一种是基于对给定文本的客观理性的概念性分析与综合的、形成“向—解释”的阅读与解释。参见拙作《论中西哲学精神》,3版,55页及以后,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
[8] 我有一篇长文致力于基于荀子的道德与政治哲学整合法律与道德,旨在为展示如何把礼义与礼法统一为儒家政治管理的体系。See Chung-ying Cheng, "A Confucian-Kantian Reflection on Mutuality and Complementarity: Virtue and Law, " in Structuren der Macht-Studien zum Politischen Denken Chinas, ed. Harald Holz and Konrad Wegmann, Muenster, Lit Verlag Muester, 2005, 13: 291-333.
[9] 这个术语也可以被理解为“天人分离”,然而却是错误的。正因为天人之间有联系,人才可能发展自身。但这个联系存在于:根据观察,天独立于人的意志并且有自身运动变化的规律。这个联系取决于个体的人基于自然中的以及属于自然的变化而作出调整,然而自然将会以有利于真正修养良好的个体的方式释放它的潜在力量。
[10] 本文所有来自《荀子》的引文都引自高长山编辑的《荀子译注》。以下只标注页码。
[11] 杨伯峻:《论语译注》,19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12] 谢冰莹注译:《新译四书读本》,477页,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3。
[13] 当前有某种反本质主义的恐惧,在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中都存在,这可以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或古希腊哲学的比较中得到很好的理解。虽然亚里士多德希望从本质上来定义事物以便这些事物能在他的终极形而上学体系中被概念化,但中国哲学家却总是把对事物的观察和体验作为理解实在的最终基础。因此,在中国哲学里没有在一个封闭的思考体系里对诸种本质的希腊形而上学归属。另外,由于《易经》的观察途径,在宇宙中没有不变或不可改变的事物,而它们被人所体验和观察到的诸种自然特质却能在与人的联系及它们各自的联系之中得到理解。但这并不是说这些特质是由人构造出来的,或者它们是人为的,或者仅仅是对人类一时冲动的产物的因袭。相反,事物的诸种特质都是真实事物的真实特质,因为其真实性是被体验到的事实,且它们的名字是在它们反映了为这些事物及其诸特质取通名的人们之间的普遍理解的意义上成为惯例的。在这个意义上,事物的名字既代表了人类对事物的体验,又代表了为这种体验命名的社会惯例。对此参见《荀子·正名》。因此,我们必须区分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的及亚里士多德式的实在主义和与之相对的经验主义的、自然主义的、非亚里士多德式的实在主义。
[14] 应该指出的是,从现代工业过度发展的含义上来讲,无论荀子的完成观点还是孟子的启蒙观点,它们都没有构成对自然的侵犯。现代工业的过度发展导致了污染和生态失衡,并危及人类和其他生物的生存。
[15] 参见高长山:《荀子译注》,406~429页
[16] 参见高长山:《荀子译注》,406~429页。
[17] 参见高长山:《荀子译注》,407页。
[18] 荀子使用“明”这个术语来描述脱离了蔽的心灵状态。这个状态同时意味着被照明以及照明。心灵去照明暗示心灵有理性的光可以倾洒光线于事物之上,从而开启自己对体验与对象的清晰认知。虚一而静的状态是否一定是明,这尚不清楚。不过,人们可能会把它比作空间里的光,它不被察觉,但当照亮一个对象时会使该对象昭然。
[19] 这种认知状态与我所描述的“超融”相一致。但荀子似乎还提出了一个要求,即为了给不同的事物判定合宜的位置,为了引导或规定不同事物的合宜发展,人必须察见一个定则。也许我可以把这种状态描述为“超融而主宰”。
[20] 看到语言是如何发展为帮助或阻碍的吗?看看语言是如何发展到了我们拥有指谓与意义的普遍框架的程度,然而在此亦有混淆与混乱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没有办法阻止人们把语言的指谓看作它自身的实在——具体化的问题。最终的结果是以名乱实。也存在由于缺乏抽象而导致的问题,即以实乱名的情况。还有以名乱名的问题:忘记了每个名字有自身使用的语境与所适的目的,人们不能把它们混合起来而得出结论。杀一个盗贼不等于杀一个人,这是因为杀盗贼是由于其偷盗的罪行而杀一个人,而杀一个人不是由于他自身的罪行,而是出于某种别的外在的原因,因而这可能是一种罪行。我们的语言具有识别使用语言之目的的功能:杀一个人是把杀仅仅视为毫无理由的杀害,而杀一个盗贼是由于其偷盗而杀一个人。所以,它们因为拥有相同的指谓而相关联:一个盗贼是一个人,所以杀一个盗贼是杀一个人,不过是由于其偷盗而杀一个人,所以没有必要担心它们独立的目的和特性。
[21] Chung-ying Cheng, "Rectifying Names in Classical Confucianism, " in Proceedings of the XXV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Orientlaists: Essays in Asian Studies, ed. Harry Lambl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Asian Studies Publications, 1969, pp.82-96.
[22] 参见《荀子·儒效》、《荀子·君子》。
[23] 参见我在《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一书中发展的管理哲学,其中很重视荀子的组织与制度管理理论。
[24] “小人”这个术语不必用作道德谴责。它最初是用于指涉服从君子(即统治者)统治的普通人。
[25] Antonia S.Cua,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in Hunan Nature, Ritual, and History: Studies in Xunzi and Chinese Philosophy, pp.8-9.
[26] 诸如市场经济里的竞争。正如亚当·斯密看到的,正是私利与私欲在一个开放的市场里推动了竞争与创新,它们与某个最小化管理的政府相结合,就能通过一只象征经济理性的制度化的“看不见的手”为公众创造利润。
[27] 荀子的人性本恶论在宋明新儒家那里成为“气质之性”观念的来源。在张载、二程和朱熹那里,人性有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对理解全部的人与儒家君子的自我修养而言,二者必须充分地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