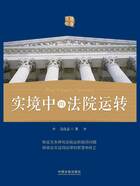
二、积极主动的参与者:治理体系中法院角色的初步印象
(一)狭义“治理”范畴中法院的“参与”角色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治理”有时表达的是一个专有的综合性概念,如社会治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治理整顿等;有时仅是一个普通的单项词语搭配而已,如治理水土流失、治理环境污染等。(表一[31])
表一 两类报告中关于“治理”的表述

续表

续表

续表

法院工作报告中,“治理”的基本方式有“综合治理”与“专项治理”两大类(对信访的“源头治理”既有可能是“专项”的,也有可能是“综合”的)。专项治理的对象涉及商业贿赂、农资打假、乱收费等;关于“综合治理”,2011年之前“治理”的基本固定结构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2012年之后逐渐变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社会治理”、“国家治理”。
在政府工作报告与法院工作报告的对比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治理”的定位不同,政府工作报告的表述一直是“加强”、“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而法院工作报告一直表述的是“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2014年工作报告中表述为“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从字面意思可以看出前者是主导,后者是参与。“积极参与”的方法有两大类:
首先,法院是“通过审判的社会治理者”,是“特殊的治理机关”[32]。法院“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在工作报告中主要被归入“刑事审判”部分,这表明法院主要依靠行使刑事审判权来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为达至良好治理效果,人民法院综合发挥审判权运行的不同功能:一是惩治、震慑。例如,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严打”、公判大会等运动式治理。[33]二是感召。通过减刑、假释促进罪犯的改造;通过从轻判处少年犯发挥“教育、感化、挽救”作用。三是宣教。从早期的印发布告和罪行材料、召开讨论会、座谈会、举办展览会等形式逐渐过渡到以案说法、典型案件集中报道、庭审直播等形式。
其次,法院延伸审判职能参与治理。“从治理主体与治理技术来看……法律的目的不仅仅是审判,而是具有改造社会的目的,科层制的法院组织系统本身即构成国家权力治理社会的装置。”[34]法院延伸审判职能的治理方式主要有“注重同家长、学校、社会结合起来,进行疏导、防范,共同矫治失足少年的不良行为”(1989年法院工作报告)、指导人民调解、发布司法建议等。其中,法院发出司法建议来参与治理,实现审判权的“自我超越”已为成熟的制度安排。[35]
如前所述,治理体系中政府与法院关系形成的第一印象源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或社会治理)”中法院的积极主动参与。政府主导,法院处于从属地位。如果将法院的积极参与角色推定为法院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那么在“坚持党的领导、政府负责、公众参与、社会协同、法治保障”的“中国式治理”格局中,[36]法院参与和公众参与的角色如何区分?法院在治理体系中的从属性角色是否就此确立?为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将法院参与治理的角色进一步放到更广阔的范畴去检验。
(二)“治理”范畴扩展的切入点
政策是“国家、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37]所谓“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其实就是一国“治国理政”方略的集中体现,而“行动准则”是“治国理政”方略转化为治国理政方式的落实。国家能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国家实行政策实现其目标的能力”。[38]因此,从政策的角度切入,可以有效地将“治理”的范畴扩大到整个国家层面,延伸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39]
1980年以来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政策”一词共出现932次,内容涉及经济、“三农”、社会保障、就业、科教文卫、民族、宗教、侨务、行政、外交等诸多领域,在报告中直接归入经济方面的政策共出现613次,总体上经济政策所占百分比为65.77%。[40]从历年经济政策出现频次与政策出现总频次的比例分析(图一),除1984年因突出阐述外交政策而使经济政策的比例显著下降之外,这一比例基本上处于1/2以上,并逐渐在1994年后升至3/5上下小幅波动。可以看出,三十余年来,经济政策一直是政策的主体,这与大众的普遍印象以及学者的理论解读是基本一致的。[41]经济之外的政策大致可以归入“大社会政策”的范围。1980年以来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政策”一词共出现131次,其中刑事政策65次、经济政策41次、未具体指明的政策17次、民事政策5次,(狭义)行政政策3次,司法政策和其他共9次。由于未具体指明的政策是指“党和国家的政策”,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语境中经济政策是“党和国家政策”的主体,因此实际上经济政策还是占据首要位置的。从文本对比解读,两类报告中“政策”的“经济”成分居多,遵循这一趋势,除特别注明外,下文中关于“政策”的表述是:主要由政府颁布和执行的、以经济政策及关联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国家政策[42],其他关于“政策”不同界定的争议不在本章讨论范围之内。

图一 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经济政策占全部政策的比例
三、围绕大局的服务者:治理体系中法院角色的历史维度
以历史变迁的大尺度丈量治理体系中政府与法院的关系,不难发现,“为大局服务”作为法院的工作主题之一,[43]不仅是对司法工作方向的政治定位,还涵摄了法院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官方立场。34年来的法院工作报告中共57次表述事关经济社会总体政策的“大局”或“全局”,其中27次是直接表述为服务大局(全局)或为大局(全局)服务,19次是表述为“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大局)”或者“把握大局(全局)”,其余的是关于法官树立大局意识的要求;共117次出现司法“服务”[44]的字样,既有宏观上的“服务大局”,又有制度层面的“下发了《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为完善农村的承包责任制提供了司法服务”(1987年法院工作报告),还有“在相关案件较为集中的地区设立劳动争议、金融等专门合议庭或审判庭,推广远程立案、‘一站式’服务”等具体举措(2011年法院工作报告)。将政府工作报告中“政策”关键词与法院工作报告中关于“服务”的表述进行对比(表二),可以清楚地发现法院治理立场的走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1.第一阶段:1984~2001年
1984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司法工作要“直接地更好地服务于四化建设”。一直到2001年,法院工作报告中年年出现为关键政策提供服务的表述,密集度大、主动性强,完全顺应政策的调整方向。“服务”出现的频次高,呈现活跃态势,是居于主流地位的司法理念,并主导着法院的司法行为。从与政策对比的角度,这一时期又可以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4~1988年,这一时期政策的关键是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并逐步推进改革开放,法院的工作重点也逐渐从平反“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转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第二阶段是1989~1993年,为防止经济过热和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政策关键词是“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法院相应的主要治理思路是“积极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全面深化改革服务”;第三阶段是1994~2001年,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政策更加科学成熟,政府提出“认真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人民法院参与国家治理的典型表述是“努力为改革、发展、稳定服务”。
2.第二阶段:2002~2008年
政府工作报告中“政策”一词出现次数总体上呈现一种相对较为稳定平缓的态势,而在2002年至2008年期间法院工作报告中“服务”出现的次数极低,甚至从2004年至2008年连续五年法院工作报告中未出现“服务”字样。从一个侧面表明在这一历史时期不再突出强调司法对政策的回应和对大局的服务。
3.第三阶段:2009年至今
2009年法院工作报告中共5次直接表述“服务大局”或“为大局服务”,服务立场随之强势回归。近年来,法院工作报告中既有“为经济社会有好又快发展服务”这样的宏观司法政策,又有“改进诉讼引导、查询咨询服务”这样的具体司法举措,服务理念成为贯穿法院工作的主线。
4.特殊历史时期
将政府工作报告中“政策”一词出现次数与法院工作报告中“服务”一词出现次数进行大体上的对比(图二),可以进一步验证上述历史阶段的划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服务”一词出现的次数分别在1990~1991年左右、1999年前后以及2009年之后三个时间区段显著增长,政府工作报告中“政策”次数在相应的时间区段前后也有一定程度的增加趋势,这三个时间区段正好对应“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亚洲金融风暴以及国际金融危机三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进一步证明法院的治理行为紧跟政策的调整。

图二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服务”次数与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政策”次数对比
表二 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政策”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的“服务”对比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综上,从政府与法院关系的历史维度分析,法院扮演的角色是围绕大局的服务者。这一角色是法院积极主动参与者角色在理念上的提升,两者本质上都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政府主导、法院从属关系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