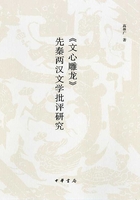
甲编 “性灵镕匠,文章奥府”:《文心雕龙》的儒家经典批评
“宗经”是《文心雕龙》立论的基石。在刘勰看来,“经”的意义和作用是巨大的:“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刘勰所谓的“经”就是指儒家经典,其核心即传统意义上的《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经的意义,特别是经对文章创作的意义是否如同刘勰所论的那样巨大和深远呢?显然不是,这是需要作具体、客观的分析评价的。但刘勰对儒家经典的推崇备至,却是贯穿于《文心雕龙》始末的。在“文之枢纽”部分,《原道》《征圣》《宗经》三篇集中阐释了刘勰对儒家经典的内容、价值、写作特点及对后世的启发和影响等方面的认识和思考。刘勰认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原道》),因此圣人的文章有鼓动天下的巨大作用。刘勰之所以强调“征圣”,是因为圣人的著作在政治教化、事迹功业和个人修养方面具有可资征验的巨大价值。而且,圣人文章对繁、略、隐、显的恰当处理,以及“衔华佩实”“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的风格特点,为后人的创作提供了范例。因此,“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征圣》)。
就文章创作层面而言,刘勰对儒家经典的尊崇,其原因也是有多方面的。首先,是基于对经典巨大的文学意义和文学价值的深刻体认。经典“衔华佩实”“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树立了文章创作的光辉典范,昭示了各种文体的写作手法,后世各种文体都源于经典;只要向经典学习,文章就会“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宗经》)。其次,借经典来针砭文章时弊,以图匡正文风。晋宋以来,“各竞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总术》),“率好诡巧”(《定势》),“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情采》),“辞人丽淫而繁句”(《物色》),“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要改变这种形式主义文风,在刘勰看来,就需“还宗经诰”“参古定法”(《通变》)。显然,提倡对经典书辞的体察和效仿,同时也包含有对时文的否定和批判倾向。再次,更重要的是,借助于儒家经典的权威性以提升其理论的可信性和说服力。三代至晋宋,儒家思想一直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儒家经典在士人眼里都是神圣而崇高的。以儒家经典为标准和范式来推原“文心”,显然更有助于正末归本,树德建言。
“文之枢纽”外,刘勰对儒家经典文学意义的开掘和阐释还散见于《文心雕龙》各处,随文述典,不拘一格。其中,论述最多的是《诗》《书》、“三礼”、《易》、《春秋》三传和《论语》。
《文心雕龙》五十篇,有二十七篇直接涉及了对《诗》的批评,涉及《诗经》的具体篇目就有《桃夭》《采薇》《伯兮》《角弓》《葛覃》《草虫》《大车》《小星》《关雎》《氓》等五十余篇。所讨论的问题,既有《诗》的作者及编次,也有《诗》的内容特点、艺术手法及文体特点等。其中,对《诗》的情采特征、章句锻造、比兴艺术、夸饰技巧、摹景手法等方面的总结和分析最为细密,也最有价值。论及《尚书》者,至少有《征圣》《宗经》《史传》等三十余篇,其余征引《尚书》原文、化用《尚书》事典、论及《尚书》人物篇章者,则难以数计。《文心雕龙》既肯定了《书》的文学性,也具体分析了《书》中属对、夸饰、事典等表现手法的运用,并多次论及了载于《尚书·夏书》中的《五子之歌》。刘勰对《尚书》“辞尚体要”创作原则十分推崇,“辞尚体要”也进而成为了《文心雕龙》最重要的美学思想。对“三礼”的有价值的评介和论述见于《宗经》《祝盟》《诏策》《章表》《书记》《练字》等十六个篇目中,涉及了《礼》的体制和法则、结构和章法、语言与文体等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在刘勰看来,“三礼”最突出的文学性意义在于“立体”和“据事剬范”,即蕴含和树立了文章创作的基本范式和准则。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角度较早、较深刻地对《易》进行分析探讨者,当首推《文心雕龙》。《文心雕龙·序志》在谈到《文心》的体例构设时讲到:“障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文心》的纲目恰好合于“大衍之数”,这充分说明了刘勰对《易》学精神的尊崇和重视。《文心雕龙》文道观念的确立大量援引和运用了《易》的美学思想,体现出了与《易》相近的思辨逻辑。此外,《文心雕龙》还对《易》的地位和价值、文学性意义、丽辞范式、美学特征等诸方面作了精辟的释解。对《春秋》经传的批评主要见于《征圣》《宗经》《辨骚》《明诗》《铭箴》《史传》《议对》等篇,其中论及了经传的创作宗旨及相互关系、经传的叙事记言特点及对后世创作的影响等众多内容。“五经”之外,刘勰还论到了《论语》《孟子》《荀子》等传统意义上的儒家经典。不过,刘勰是将《孟》《荀》作为子书看待的。为行文方便,本章只讨论《论语》的相关问题,《孟》《荀》则列于“丙编”中。
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刘勰《文心雕龙》第一次从文学角度(而不是史学或经学角度)对“五经”的特质作了细致精当的归纳和分析,这是《文心雕龙》的巨大贡献。此外,《文心雕龙》对“五经”的文体学意义所进行的归纳和总结,也突出地显示了刘勰对文学文体的重视,而这也正昭示了魏晋文学的高度自觉。刘勰对“五经”之于后世诸文体创作的影响,或从语源角度加以考察,或从名称上予以追溯,或从文体源流、手法技巧、内在精神的关联等方面进行考辨,并据以提出了各种文体的具体写作要求,这些论述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在其论文叙笔过程中,《文心雕龙》鲜明地体现出了以经典为创作和评判标准的倾向;而全书无处不在的借助于典故、比附、引叙等形式对经典进行诠释和运用的情形,也直观地见出了《文心雕龙》对儒家经典的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