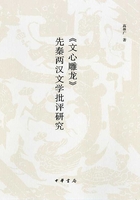
(三)摛风裁兴,藻辞谲喻:论《诗经》艺术
《诗》为“六经”之首,其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因而历来受到了人们的尊奉与推重。刘勰之前,先秦汉魏对《诗》的经学、史学意义上的评判剖析可谓汗牛充栋,但从文学角度对《诗经》进行考察和分析者,刘勰是最早,而且也是最全面、最精细的。在《情采》《章句》《比兴》等篇中,《文心雕龙》广泛而深刻地分析和论述了《诗》的情采特征、章句锻造、比兴艺术、夸饰技巧、摹景手法及声律事典的运用原则等。
1.为情造文,文以足言:《诗》的情采特征
《文心雕龙·情采》重点讨论了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如上所述,关于《诗》的内容特点,《文心雕龙》在《明诗》《时序》《奏启》《书记》等篇中都有精辟论述,肯定了《诗》的“无邪”特征及其“美刺”精神。关于“采”,《情采》开篇即云“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这就是说,包括《诗》在内的儒家经典都是有文采的。在一般人看来,《诗经》以外的经书不追求声律、辞藻、对偶的运用,似乎文采特征不那么明显。但刘勰不这么认为,“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总术》),文是用来补充言的,《诗》《书》都应包括在内,因此《诗》《书》都是“文”,而非“笔”。由此看来,刘勰所谓的“采”实际上包含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经书中的“秀气”和“雅丽”,即所谓“精理为文,秀气成采”“圣文之雅丽,故衔华而佩实”(《征圣》);二是指一般文学作品中的辞藻、对偶、声律等。显然,这两个层面的内容《诗经》都具备,《诗经》因而成为了最富有文采的典范之作。《原道》云:“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刘勰认为,《诗经》文采华美,比之前代的简单质朴,更胜一筹;而《雅》《颂》尤其具有“文胜其质”的特点,在它的影响下所产生的优秀作品,日新月异。《明诗》中也讲:“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子夏监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八个字,很能概括《诗》的文采特点。
刘勰对文章创作中文采运用的基本认识是两方面的,一是不排斥文采;二是反对过分使用文采。《诗经》是最符合刘勰这一美学原则的。在《情采》中,刘勰援引了《诗经·卫风·硕人》中“衣锦褧衣”句,意谓穿了锦绣衣服还要外加一件罩衫,以免文采太过于显露。这一例证形象地表明了刘勰“恶文太章”的观点。在刘勰看来,文采的运用必须顺应文章表达的自然需要,否则就会流于矫饰和虚浮。在《原道》中,刘勰又举文王之制《诗》作《颂》来说明这一问题。
刘勰以为,《诗》与《颂》既宣扬了王道教化,又具有自然而成的文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刘勰本着“论文必征于圣”(《征圣》)的认识,欲以《诗》等圣人之制规范当时的诗文创作,明显体现出了对当时浮靡文风的不满。
在《情采》篇中,刘勰更盛赞了《诗经》“为情而造文”的特征: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
刘勰认为,风雅之作“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属“为情而造文”;后世辞赋之作,感情虚假,文辞浮华,属“为文而造情”。两者相较,刘勰肯定充分肯定了《诗经》的真实和自然,而对当时辞赋创作所显现出的矫情和浮夸予以了批评。刘勰一贯认为,最理想的文章应当是“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真实自然的情性,再加上华美的文辞,这样写出的文章才能“衔华佩实”“符采相济”,才是最好的。在二者并重的基础上,刘勰强调了内容的决定作用:“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文采的安排和使用应服从内容的需要,“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刘勰的论述显然是针对“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的齐梁文坛而发的,这样一来,其“为情而造文”“要约而写真”“文不灭质,博不溺心”的观点就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意义。
2.随变适会,环情草调:《诗》的章句锻造
《文心雕龙·章句》云:
寻诗人拟喻,虽断章取义,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
这段文字分析论述了《诗经》的章句特点,大致说来,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诗经》善用比喻句,其章节和句子如剥茧抽丝,层层相环,又像从鱼鳞排列,层次井然;二是,《诗经》注重全篇表意的启、承和结,句首的字词已经埋伏了中篇的意思,结尾的词语,呼应了前文的内容,各章之间相互照应,意脉连贯;三是,《诗经》“外文绮交,内义脉注”,即外在的语言形式与内在的思想感情有机交融,内外一体,文质彬彬。这是就《诗经》篇、章、句的安排和锻造而言,虽然不够具体,但却是符合《诗经》的创作实际的。
《文心雕龙》还论及《诗经》联章积句、博文该情的问题。《征圣》曰:“邠诗联章以积句,儒行缛说以繁辞,此博文以该情也。”“邠诗”即指豳风,“邠诗联章以积句”具体即指豳风中的《七月》。刘勰指出,诗文创作中的繁、简、隐、显应依据创作时的实际需要而定。《春秋》往往以一字寓褒贬,如“郑伯克段于鄢”,一“克”字即表明了作者的态度;《礼记》以“缌不祭”三字点出了穿丧服的人不宜参与祭祀的道理。这都是“简言以达旨”的例子。而有些时候则须“博文以该情”,用繁富的文辞来表达丰富深刻的内容。刘勰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七月》之“联章以积句”。《七月》是《诗经·国风》中最长的诗篇。全诗共八章,每章十一句。《七月》广泛反映了先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既要描述他们一年四季的艰辛劳作,又要表现他们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关系,非“博文”当然无法“该情”。刘勰论述了《七月》在形式上具有联章积句的特点,并指出这样的形式安排是出于感情表达的需要,这无疑是符合《七月》的创作实际的。而刘勰在这里所提出的“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的创作原则,也长久而深远地影响到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其实,联章积句不独存在于《七月》,《诗经》中的大部分篇章都运用了这一手法。如《蒹葭》《生民》等都属此列。这一手法包含有后人所谓的铺叙、重章叠句等,是对《诗经》章句特点的精辟概述。
《诗经》章节的组合形式,有时用单句,有时用偶句,刘勰对此亦作了评判。《丽辞》云:“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刘勰认为,《诗经》句式的运用是“适变”的自然结果,毋需劳神费力,苦心经营。《诗经》的这一特点正符合《文心雕龙》“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的丽辞原则,因而得到了刘勰的称许。《章句》篇更具体地谈到了《诗经》句式的特点:
至于诗颂大体,以四言为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为句。寻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三言兴于虞时,《元首》之诗是也;四言广于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见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杂出《诗》《骚》;而体之篇成于两汉:情数运周,随时代用矣。
《诗经》中的《雅》《颂》乃“大体”,即郑重的体裁,所以多用四言。需要说明的是,“四言为正”是汉代最为普遍的诗学观念,刘勰对这一观点是认同的。《明诗》曰“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雅润”即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亦为四言创作的基本宗旨。但刘勰同时也客观地指出,《小雅·祈父》和《周颂·维清》用到了两字句[8];不仅如此,《诗经》中也有六字句、七字句的情况,如《小雅·雨无正》“谓尔迁于王都”,《小雅·鹿鸣》“我有旨酒,以宴乐嘉宾之心”等等。这样的描述是符合《诗经》的实际的。我们知道,四言虽然是《诗经》的基本句型,但并不是唯一的句型,《诗经》中一言至八言的各类形式都具备。
那么,“言”之多少能否成为衡文之标准呢?刘勰说:“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适应诗歌创作情势变化的需要,字数、文句、节拍等都会随变适会,所谓“夫裁文匠笔,篇有大小;离章合句,调有缓急;随变适会,莫见定准。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正说明了这一问题。“四言为正”之谓,显然是其“宗经”思想的产物;而“随变适会”云云,又体现了他“通变”的文学史观。刘勰持“情数运周,随时代用”的观点,对于诗歌句式的逐步加长、长句代替短句的趋势持肯定态度。
如何合理遣词用字,亦是诗歌创作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文心雕龙》的许多篇章都列举了《诗经》字词运用和安排的精炼和准确。在《章句》篇,刘勰还重点讨论了《诗经》中“兮”运用的特点和意义。
又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承句,乃语助余声。……据事似闲,在用实切。巧者回运,弥缝文体,将令数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
《诗经》句内用“兮”字,其作用刘勰归纳为二:一是“语助余声”,二是“弥缝文体”。“语助余声”是就其在诗歌音乐性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而言的,即可以补足音节,令诗歌韵律完整、余味隽永。如《诗·氓》“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中的“兮”就属于这种用法。“弥缝文体”是就虚字在诗歌结构方面所起的作用而言的,即可以使诗歌文辞严密,圆融和谐。刘知幾《史通·浮词》对此有过阐发:“夫人枢机之发,亹亹不穷,必有余音足句,为其始末。是以伊、惟、夫、盖,发语之端也;焉、哉、矣、兮,断句之助也。去之则言语不足,加之则章句获全。而史之叙事,亦有时类此。”[9]其中,“去之则言语不足,加之则章句获全”,正恰当地道出了刘勰所谓“弥缝文体”的确切含义。考之于《诗经》的创作实际,显然,刘勰所论不差。但,归根到底这些认识只是就“兮”字浅表层次的作用而言的。实际上,“兮”等虚字的运用更有其之于诗歌内容和情调方面的独特作用。刘淇《助字辨略序》云“构文之道……虚字其性情也”[10],此论颇为精辟。钱锺书先生指出,虚字在诗歌中具有“使语助以添逶逦之概”“多摇曳以添姿致”之效[11]。这一论述,已可贵地涉及了虚字在诗歌审美方面所起到的独特作用,真正触到了问题的核心。
3.写物附意,婉而成章:《诗》的比兴艺术
比和兴这两种表现手法在《诗经》中得到了最广泛的运用,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文心雕龙》专设《比兴》一节对这两者予以讨论和探讨,其开篇即云:
《诗》文宏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
《毛传》释诗,只注明他认为是“兴”的诗句,这样的情况在《毛传》中共出现了一百一十六处。对此,刘勰的解释是“‘比’显而‘兴’隐”,即赋和比相对而言较为明显,容易区分和鉴别,兴则涵义深婉,意义难明,因此必须加以特别的提示和说明。考之于《毛传》实际可以看到,刘勰的这一认识是正确的。不过,《毛传》之“独标兴体”往往在于附会《诗》与君臣伦理之关系,进而宣扬其儒家思想,本意并不在从艺术表现层面来探讨“兴”的深婉性与含蓄性特点。刘勰“‘比’显而‘兴’隐”论,则是就《诗》文学性特点而言的,显然刘勰的论述更符合《诗经》的创作实际。
在讲到比与兴的创作原则时,《文心雕龙》大量举证了《诗经》中的例子:
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义取其贞,无从于夷禽;德贵其别,不嫌于鸷鸟: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也。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锡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诲,蜩螗以写号呼,浣衣以拟心忧,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义也。至如“麻衣如雪”“两骖如舞”,若斯之类,皆比类者也。
何为“兴”?《周礼·大师》郑众注曰“兴者,托物于事”意无穷,兴也”[14]。各家阐释问题的角度不同,故给出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刘勰说:“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兴则环譬以记讽。”刘勰的解释突出强调了三点:一是,引起下文;二是,根据事物间曲折微妙的关系来寄托所要表达的思想;三是,一定具有讽谕意义。强调“兴”在文理语势和思想情感方面的引起下文,是没有错的;但突出讽谏和托谕,显然是不确的。刘勰援引的例文是《关雎》和《鹊巢》。雎鸠雌雄有别,古人认为它是有德行的贞鸟,所以用来譬喻“后妃之德”;尸鸠住在鹊巢里,贞洁纯一,“犹国君夫人来嫁,居君子之室”(郑笺),所以用来象征诸侯夫人的美德。刘勰对这两则例文意义的释解,与《毛传》是完全一致的。他坚持认为兴一定是“环譬以记讽”,是“托谕”的,因而承袭了《毛传》的观点和认识,这是刘勰的不足。不过,这两则例子均属“依微拟议”“婉而成章”者,“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其“兴”的特点是成立的。刘勰同时指出,“依微拟议”造成的结果往往是含义“明而未融”,深奥难懂;所以,必得“发注而后见”,即借助于注才能使人读得懂。这一认识是客观的。
关于“比”,刘勰解释为:“比者,附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比则畜愤以斥言。……盖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者也。”刘勰的论述突出了“比”的以此物比附彼物的特点,同时强调了形象性和切于事理的艺术原则,较之郑众“比者,比方于物也”、钟嵘“因物喻志”之论,显然更为精当和细密。但刘勰“畜愤以斥言”的认识显然是不正确的。将比局限于指斥过失,源于汉儒郑玄,其注《周礼·大师》曰:“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对此,孔颖达《毛诗正义》作了纠正:“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孔颖达认为,比和兴都可以美、刺皆具。因此,比不只是“斥言”,同时也可以用来赞美。
《文心雕龙》将“比”分为“比义”和“比类”两类,并大量引《诗》例以证。“比义”类,刘勰举出《卫风·淇奥》《大雅·板》《小雅·小宛》《大雅·荡》《邶风·柏舟》中“有匪君子,如金如锡”“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等五例;“比类”类则举出《曹风·蜉蝣》《郑风·大叔于田》中“麻衣如雪”“两骖如舞”两例。这些例子,或比人事,或比物理,皆鲜活生动,切近事理,正符合刘勰“写物附意,飏言切事”的审美原则。
4.意深褒赞,义成矫饰:《诗》的夸饰技巧
夸饰,现代修辞学称之为夸张。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将之列入“积极修辞”一类,并定义曰:“说话上张皇夸大过于客观的事实处,名叫夸张辞。”[15]刘勰之前,王充《论衡》卷七十八有“语增”“儒增”“艺增”诸名目,对夸饰有所涉及。《文心雕龙》单列《夸饰》一篇,具体而精辟地论述了夸饰的特点、运用原则和在创作中的积极作用等。刘勰认为,《诗》《书》等经典对夸饰的运用有度有节,恰如其分,足以为后世之宪章。《夸饰》云:
虽《诗》《书》雅言,风俗训世,事必宜广,文亦过焉。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舠,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且夫鸮音之丑,岂有泮林而变好?荼味之苦,宁以周原而成饴:并意深褒赞,故义成矫饰。大圣所录,以垂宪章。
刘勰言,虽然《诗》《书》用的是当时的规范语言,这种语言风格有教化世俗、训导世人的作用,但所用事例仍不免有所增饰,语言文辞亦多所夸饰。刘勰举出了《诗经》用夸饰的六例:《大雅·崧高》之“崧高维岳,骏极于天”;《卫风·河广》之“谁谓河广,曾不容舠”;《大雅·假乐》之“干禄百福,子孙千亿”;《大雅·云汉》之“周初黎民,靡有孑遗”;《鲁颂·泮水》之“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怀我好音”;《大雅·绵》之“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并特别指出,猫头鹰的声音是难听的,难道会因在学宫的树林中栖息就变得悦耳动听了?苦菜的味道是苦的,岂有长在周家的原野上就会变得甘甜的道理?《诗经》之所以会这样描写,是为了加强赞美,在事义上用了夸饰手法。
虽然刘勰没有从修辞学意义上对夸饰的结构和意义做更深入的解析,但从所举例证来看,他已经注意到了夸饰“扩大”和“缩小”的两个主要类型。奇特之夸张(如《河广》之“一苇杭之”“曾不容舠”“跂予望之”“曾不崇朝”等)虽然在客观上不能成立,但在主观上却是合乎情理的,合情而不合理,“壮辞可得喻其真”,是符合艺术原则的。
刘勰同时指出,增饰要恰到好处:“然饰穷其要,则心声锋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诗经》的夸饰,形象地表现了事物的本质特征,恰切地抒发了作者的美好情意,因此能夸而有节,并引发读者的强烈共鸣;而扬雄、司马相如、张衡等人的辞赋,“奔星与宛虹入轩”“鞭宓妃以饷屈原”,虚用滥行,饰而有诬,有失其理,这是不恰当的。他希望能“酌《诗》《书》之旷旨,翦扬马之甚泰”。由此可见,刘勰在以《诗》为创作范式的同时,也激烈地抨击和批评了辞赋家之滥用夸饰,诬过其理。对此,黄侃先生《文心雕龙札记》有过非常精当的论述:“文有饰词,可以传难言之意;文有饰词,可以省不急之文;文有饰词,可以摹难传之状;文有饰词,可以得言外之情。古文有饰,拟议形容,所以求简,非以求繁;降及后世,夸张之文,连篇积卷,非以求简,只以增繁。仲任所讥,彦和所诮,固宜在此而不在彼也。”[16]
5.写气图貌,以少总多:《诗》的摹景手法
自然景物对作者创作情思的感召和触发作用是极为明显的,古人对此多有论述。如陆机《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17],钟嵘《诗品序》“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18]等等。《文心雕龙》更是专列“物色”一篇,深入探讨了摹景状物的原则和方法等,其中大量涉及了对《诗经》写景艺术的认识和评价。刘勰说: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刘勰认为,《诗经》作者对自然景物的感触是十分敏感的,因此能够产生无穷无尽的联想。他们流连于自然万象,歌咏视听所及之物景。接下来,刘勰从三个方面总结和归纳了《诗经》物类描摹的特点。一是,能拟其形,即所谓“图貌”“属采”和“附声”。这里的“貌”“采”和“声”是指客观外物的具体形貌、色彩和声音。二是,能传其神,即所谓“写气”。这里的“气”显然是指物象的内在神气和韵致。三是,能做到心物相融,主客一体,即所谓“与心徘徊”。《神思》中有过类似的话:“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摹景写物追求形神皆备和心物交融,这在魏晋人的文论、书论和画论中多有体现。如,钟嵘《诗品序》强调“指事造形,穷情写物”,谢赫《古画品录》主张“穷理尽性,事绝言象”[19]等等。在这里,刘勰将形、神、心三者统融在一起,进而对诗歌创作中的摹物写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突出体现了刘勰论文的深邃和细密。客观地讲,《诗经》中的感物写景,未必都达到了刘勰所讲的“随物宛转”和“与心徘徊”,但刘勰据以提出的创作原则却是极富启示性的。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刘勰摘引了《诗经》中《桃夭》《采薇》《伯兮》《角弓》《葛覃》《草虫》《大车》《小星》《关雎》和《氓》等篇中的写景名句,对其景物描写的特点作了精当的分析和评判:“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虫草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刘勰主要从两个方面对上述诗篇的写景特点进行了评价:一是用语形象生动,简洁明快,富有表现力,能准确地描摹出物景的状貌形声;二是既能穷其理,又能穷其形,做到了形神兼备,情貌无遗。考之上述诗篇的创作实际,应当说,刘勰的归纳和分析是十分精辟的。刘勰一向重视诗歌字词的锻造和锤炼,并对《诗经》中字词运用的准确和生动多所赞誉。《练字》篇甚至还谈到,即使偶然出现字词“重出”现象,《诗经》依然能够做到恰当和融通:“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诗》《骚》适会,而近世忌同;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重出”是同一个字在句中再度出现的情况。如《诗·卫风·氓》中“及尔偕老,老使我怨”句,出现了两个“老”字;《诗·邶风·静女》中“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句,出现了三个“美”字。重出容易造成字句之间的相互干扰,但《诗经》《楚辞》运用恰当,因此并不影响表达效果。
《物色》还论到了《诗经》色彩词运用的恰当和准确:“至如《雅》咏裳华,‘或黄或白’,《骚》述秋兰,‘绿叶’‘紫茎’。凡摛表五色,贵在时见;若青黄屡出,则繁而不珍。”《诗·小雅·裳裳者华》有“裳裳者华,或白或黄”句,以“黄”“白”摹色,既描绘出了花儿绚烂美丽的色彩,同时也刻画出了其高贵、娴雅的神态。刘勰认为,色彩词的运用是为了点染,贵在偶然一见;若频繁出现,就会显得繁芜而不足珍贵。这样的提法显然是针对当时文坛“模山范水,字必鱼贯”的倾向而言的。《裳裳者华》“物色虽繁”而“析词尚简”,正符合刘勰“善于适要”“以少总多”的审美要求。
不过,刘勰认为《诗经》炼字之精“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这样的断语似乎有些绝对。他还讲:“且《诗》《骚》所标,并据要害,故后进锐笔,怯于争锋。”言《诗经》摹景写物语言准确形象,能切中要害,这是对的;但讲后人模仿因袭,莫敢争锋,这是不够客观的。
《诗》乃文章之奥府,万世之典范。除上文所述外,刘勰还对《诗》“率多清切”(《声律》)的声律特点予以褒扬,盛赞其清丽自然、合于规范的用韵特点;此外,《事类》篇称“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将《诗》视为文章事类之渊薮,并肯定了《诗》对屈宋、扬雄等援事取譬的巨大影响。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诗》为“六经”之首,其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因而历来受到了人们的尊奉与推重。刘勰之前,先秦汉魏对《诗》的经学、史学意义上的评判剖析可谓汗牛充栋。但从文学角度对《诗经》的考察和分析,显然刘勰是最早,而且也是最全面和精细的。要正确、公允地推原和探究《诗经》的相关问题,要深入分析和正确评价刘勰的文学史观,显然刘勰的认识和论述是不能不引起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