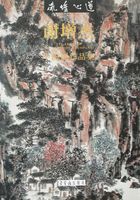
一画开天——谢增杰的山水精神与笔墨之道
长期以来,谢增杰潜心于大写意山水画创作,其力之所及,继芳躅于前贤,启新境于荒陬,并始终以大气象、大格局、大境界的彰显为大写意山水的审美旨趣,借笔墨而大写当下时代雄浑磅礴、恢宏高远的精神气象,这在写意精神渐呈萎靡、失落之势的当代中国画坛,尤其彰显出超拔于时风之上的艺术精神与文化品格。
未及弱冠之年,增杰即在大写意名家陈一峰、雍生先生的启蒙下,孜孜于探索常被世人视为畏途的大写意;后又经不懈努力,进修于当代中国画名家范扬先生门下;此后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领域最高学府——中国艺术研究院,师从著名山水画家许俊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兼得同院著名山水画家袁学君先生的言传身教。巍巍黉宫,艺术殿堂,增杰以其优入圣域般的心境,在中国艺术文化的灵山道海,饫烟云之供养,窥造化之灵枢,悟山水之精神,探笔墨之奥窔,并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而今,他年方不惑,即以其探骊得珠之奇,声誉鹊起,弥足可贵。其逸笔墨戏,虽零缣片楮,人或宝之,足见其造诣之深。
观增杰大写意山水,但见其纷披大笔,如风行雨散,润色开花,其物象造型、笔墨结构、空间布局,皆法无定相,气概成章。而其崒嵂巉岩、丘壑林木、云泉飞瀑,气势雄浑者,毕现北宗山水石骨铮铮、肌理苍苍的阳刚大美:其骨相清奇,古拙沉厚,其间皴擦点染,恍然似有斧劈奇纵峭拔、恣肆逸宕之势,又有刮铁纵横争折、起伏衄挫之态;而神韵深婉处,则突显南宗山水石润水明、溪岸空蒙的盎然诗意:其间遥岑远岫,迤逦起伏,林木丛筱,葳蕤婆娑,而河湖川濑环绕,波光潋滟,滉漾在目。其气象萧森清旷,境界幽谧玄远。而无论北格南韵,增杰之驰毫骤墨,无不情驰神纵,矩矱从心,迥出意表,其笔势犹如天马骇足,奔蛇走虺,迥脱廉纤;又似孤蓬自振,惊沙坐飞,跌宕于风烟无人之境。味其心法三昧,笔与心机,释冰为水,无有畦畛,悟其妙处,其犹庖丁发硎、郢匠运斤、轮扁斫轮者欤!而复观其笔墨法象,则莫不应物宛转,俯仰中节,与夫山川脉络、云迹水文相辐辏,似有逸怀浩气,吞吐大荒,不可遏止,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清人石涛曰:“以我襟含气度,不在山川林木之内,其精神驾驶于山川林木之外。”明人周履靖,说法更显高旷:“广大悉备,以天地为骨法,以造物为笔墨,以日月为神采,以雨露为染绚,以四时为生意,以海岳为运用,以宇宙为襟度。斯画家不传之秘也。”增杰的大写意山水精神,与此若合符契。
增杰的山水创作,不以精雕细琢的实写为功,而是在看似粗头乱服、率尔操觚的肆意挥写中,直接将山水写意提升到“解衣般礴”“以形媚道”的至高境界,其文心画意,形成了以“艺道合一”为核心的大写意山水美学。这既是对传统山水精神的因循与持守,同时,也融入了画家匠心独运的艺术哲思。具体说来,这种哲思大致包含两个方面:一、在坚持古典文人写意山水超验品质与道玄色彩的基础上,辅以写生中因观物取象而来的视觉感受与心灵感悟,从而既合理地消弭了大写意山水易拘泥于程式而缺乏生动鲜活之气的缺陷,也成功地规避了写生山水普遍存在的得之于“真”而失之于意浅神浮的痼弊,故其大写意山水,蕴含了一种“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的创作心态与精神旨归,从而呈现出鲜明的内省性特质;二、在“以形媚道”的文化语境中,诉诸“万法流转,道通为一”的哲学观,画家破除了诸多对立性因素之间的藩篱与壁垒,成功地跃升到古与今合一、物与心合一、有法与无法合一、图式与道象合一、书法与绘画合一的无限自由之境,这成为画家超拔于时下二元对立惯性思维的桥梁与法门,使其大写意创作直抉中国艺术精神之堂奥。以上两点,作为增杰的艺术哲学,在其创作实践中得到了一以贯之的运用与发挥。
如果进一步从本质论的维度把握增杰的大写意美学,或许不难发现,他其实已经在“万法流转,道通为一”的哲学观下,将画道文心提升为一种“一画”论的智慧本体图式。众所周知,“一画”的概念乃清代画家石涛所提出。在中国古典文化语境中,“一画”既是一种笔墨之象,即笔墨本体图式;又是一种象外之象——道,即宇宙本体图式,而笔墨本体与宇宙本体的合一,正是中国人特有的智慧本体。因此,中国古典绘画又有“一画开天”之说,清人戴本孝曰:“开天一画无生有,万象流形画在首。”石涛亦谓:“此一画收尽鸿蒙之外,即亿万万笔墨,未有不始于此而终于此。”关于“一画”的本体论意义,研究者已多有诠释,但令人遗憾的是其深文隐蔚、余味曲包的思维方式及其方法论、实践论意义,却鲜有人论及,而这恰恰是其更富理论价值的部分。“一画”论之宏旨,其实在于它建构于本体论即形而上维度上的齐一万物、消弭对立的宇宙思维。从这一意义说,“一画”论之奥旨与“万法流转,道通为一”的哲学观其实并无二致,而其不同仅在于它们的呈现方式:如果说后者是“言”,前者就是“象”。《刘子·崇学》论曰:“至道无言,非立言无以明其理;大象无形,非立象无以测其奥。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学不传。”基于此,“一画”正是探寻增杰画道文心之津逮,其理由在于:画家弥合了创作中的诸多矛盾和对立,重构了“万法流转,道通为一”的艺术原理。
古今合一,正是增杰基于“万法流转,道通为一”——也即“一画”弥合万有的思维方式,而建构起的大写意美学精神。增杰的大写意山水创作,转益多师,取法宏阔,而其艺术精神断断乎不为古今町畦之所拘,这与其智圆行方的为人处世原则和秉要执本的思维方式不无瓜葛。因而,他不但以其涉猎之广泛、收藏之宏富,浸淫陶冶于古典南北山水各派,而且不避对现代山水名家的借鉴与吸取。总之,凡古今中外艺术之所长而能启迪其审美者,他无不旁搜远绍,兼容并蓄,含英咀华,融而化之,甚至古意苍茫、浑穆质朴的钟鼎彝器、碑版权量、瓦当封泥、简牍帛书等古代文物,他皆能以寻坠绪之茫茫的钻研精神与辨彰清浊、掎摭病利的独到眼光,发掘隐含其中的审美因素,并多能悠然心会,张皇幽眇,出以己意。其古今合一、博观约取的艺术取径,正是“一画”精神的具体彰显。石涛曰:“古今法障不了,一画之理不明。一画明,障不在目而画可从心。画从心则障自远矣。”此堪称高屋建瓴之论。而对艺术史稍有研究者,似乎不难将“古今合一”的艺术观念连缀成“伏脉千里”的美学文脉:早在南朝时期,谢赫既已明确提出“迹有巧拙,艺无古今”的著名论断,唐代孙过庭主张“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清人石涛更是疾呼“今人古人,谁师谁体;但出但入,凭翻笔底”——而追根溯源,老子所谓“反者道之动”、《周易》中“阴阳互根”的易学观,庶几可以视为“古今合一”的思想渊源。而究其实,“古今合一”的画学观,无疑就是强调中国画传承与通变的辩证统一,而在传承上,也应不拘古今。然而,直至今天,愿意将“古今合一”视为一种画学观并以“一画”比照、解读之者,似乎并不多见。人们更多地是在西方进化论、现代性话语等的影响下,将“革命”“创新”奉为中国画的不二追求,画界充满了过量的激情,以至于使中国画的发展日益偏离画学真义与本土特征。增杰长期浸淫古典文化艺术,禅心一点,勘破古今,故其大写意取法与创作,往往不拘一格。而细究之,其大写意山水结构大致脱胎于北宗,而又以南派山水之韵致重构全景式北宗山水的笔墨方式与美学格调,而其融通南北的资源,不仅源自古典山水,他径入黄宾虹、八大、石涛、弘仁、髡残、龚贤、董其昌等,并经由吴门而上窥董巨、元四家,兼容李郭、刘李马夏;同时,也取径于现代以来以李可染、贾又福等为代表的图真式山水体格,以及以陈子庄、黄秋园等为代表的写意性山水形态。但他师其心而不蹈其迹,创新通变意识鲜明,其丘壑营造和笔墨结构,去北宗笔墨之浮薄躁硬而存其气象之雄浑深闳,化南宗气局之狭隘阴柔而留其神韵之蕴藉空灵,从而形成了一种融北骨南韵、清刚隽秀为一体的新型山水样式。
因为取法的宏阔广泛,但又因其不蹈故常、翻新出奇的创造精神,增杰的大写意山水创作表现出强烈的“有法与无法合一”的特征:其表征于画面,则主要呈现为笔墨的逸笔草草,造型的舍形悦影,布局的随意生发,空间的蹈虚揖影,故其满纸云烟,节脉似散乱无序而气机鼓荡流衍,格局似意造无法而神韵亹亹无尽,其间起伏逸宕,收揽吐纳,或发之唯静,其体安然而若素,或望之唯逸,其势恣纵而难遏;其表征于创作状态,则主要表现为解衣般礴,空诸依傍,放笔直取,故其笔毫动旋运转之际,一管而尽方圆曲直、凸凹阴阳、虚实开阖、动静刚柔变化之能事,行气如虹,凌厉飞动,其势如水之就深,如火之炎上,其笔墨所至,天机诡谲,不可端倪,大有横绝太空、吞吐大荒之气概。这种看似心法无轨的艺术特征,其实正是破解“有法”藩篱之后所形成的“无法而法”的自由状态,其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因而往往是画家真性乍露的形象表现。诚如石涛所说:“无法而法,乃为至法。”故他立“一画”之法,其目的即在于齐一和弥合有法与无法,也即“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也”。“有法”,使创作有章可循,避免陷入“野狐禅”的泥淖;“无法”,使创作脱略畦径,不致陷于“泥古不化”的止境。概言之,“无法”乃为创作“立极”,“有法”乃为创作“返本”。故石涛又曰:“凡事有经必有权,有法必有化。一知其经,即变其权;一至其法,即功于化。”清代王概亦谓:“或贵有法,或贵无法,无法非也,终于有法更非也。惟先矩度森严,而后超神尽变,有法之极归于无法。”借此审观增杰的大写意山水,其菩提三昧寓于其中矣。
心与物的合一,是增杰大写意山水画创作的又一策略与法门。基于师缣素与师造化的合一,增杰在遍临广观历代山水名迹的基础上,不断深入大自然写生,其行踪遍及众多名山大泽。在“身所盘桓,目所绸缪”的山水游观中,他察乎山川脉络、云纹水迹阴阳变幻之奇,参乎天地造化、晨昏寒暑节律交替之异,既以视觉(造化之物)为圭臬,又以心源(主体之心)为洪炉,故其笔下山水,无不融入了画家对于天地万物的独到理解与深切感悟,以及画家脱略蹄筌、想落天外的审美意趣。这正如石涛所说:“夫画者,形天地万物者也。”又曰:“夫画者,从于心者也。”可见“形天地万物”与“从于心”是辩证统一的。石涛之论,恰与唐代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论,形成隔世呼应。所以,石涛一方面强调:“山川人物之秀错,鸟兽草木之性情,池榭楼台之矩度,未能深入其理,曲尽其态,终未得一画之洪规也”;另一方面,他又坦言:“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归之于大涤也。”这种看似矛盾对立的观念,实则正是画家“心物合一”的结果。而其间的矛盾对立,则被石涛的“一画”所消融,绘画创作因而成为一种诗意化、审美化活动:“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陶泳乎我也。”这种主客合一的艺术观念,典型地反映出古典山水美学的核心精神,其与古典诗学“情景交融”的意境说,原理如出一辙。作为这一艺术美学的典型再现,清代画家恽南田在《题洁庵图》中写道:“谛视斯境,一草一木,一丘一壑,皆洁庵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其意象在六合之表,荣落在四时之外,将以尻轮神马,御泠风以游无穷。真所谓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尘垢韫糠,绰约冰雪。”其中诗意盎然之美,正是主观情思与客观物象交融一体的审美创造。对于增杰而言,心物合一,既是他效天法地、观物取象并启发创作灵感、破解画法藩篱的艺术源泉,又是他涵泳心性、澄怀味象并造就诗意化心灵、复归写意真源的精神渊薮。诉诸这一艺术美学,大写意山水画创作被增杰成功地提升到“含道映物”的审美境界。
践履“心物合一”的法门,进而臻于无役于物的无限自由之境,是增杰大写意山水的重要精神指向。在此过程中,图式与道象的合一,成为实现自由精神的无上妙谛。所谓“图式与道象的合一”,即石涛所说“一画鸿蒙”之法,其精神特质在于:“此一画收尽鸿蒙之外,即亿万万笔墨,未有不始于此,而终于此。”据此,大写意山水创作,其落笔一画,即有鸿蒙初开之形,因而也寓鸿蒙道象之妙,故而元代郝经有“万象生笔端,一画立太极”之说。从绘画法式的角度说,此“一画”成为贯穿创作始终的基本法则与笔墨仪轨;从艺术精神的角度论,此“一画”则成为“众有之本,万象之根”。所以,“一画落纸,众画随之;一理才具,众理付之。审一画之来去,达众理之范围”。作为一位深研传统文化的大写意画家,增杰深谙“图式与道象合一”的深刻哲理。因而,他在绘画实践中,擅于以“一画”之形推原其形而上之“道”,所谓“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即隐含了“由技进道”的艺术精神。由此,“一画”可以衍化出无数之画,并也为笔墨格调、艺术风格、美学神韵定下了基调。而最重要的是,增杰由此实现了自由精神的飞跃,所谓“吾道一以贯之”,正是他以“一画”破解胶执与蒙昧,进而臻于无为而无不为之天地境界的经典写照。唯是时,其驰毫骤墨,完全摆脱了法式的仪轨与羁縻,其绘画创作成为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逸笔墨戏”。因而,无论其创作状态,还是其笔墨风格,无不表现出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的典型特征。这正如石涛所说:“受事则无形,治形则无迹。运墨如已成,操笔如无为。尺幅管天地山川万物,而心淡若无者,愚去智生,俗除清至也。”故增杰的创作,真正做到了“能圆能方,能直能曲,能上能下。左右均齐,凸凹突兀,断截横斜,如水之就深,如火之炎上,自然而不容毫发强也。”宋杨亿序《景德传灯录》曰:“机缘交激,若拄于箭锋;智藏发光,旁资于鞭影。”此语可谓道尽增杰大写意艺术精神之玄机。
书法与绘画合一,则成为增杰建构并践履写意精神和笔墨之道的基本途径与方式。书画合一,即以书入画的笔墨意识与实践方式。关于此,画史足以撰写一部皇皇巨著:从南朝王微“并辩藻绘,核其攸同”、谢赫“骨法用笔”的倡导,到唐代张彦远“书画同体”论的提出,再到宋代文人画“草书三昧”的发扬,直至元明清数代以“书画本同”“书画同源”“画法关通书法津”等为代表的观念建构,可以说,一部中国画史几乎就是一部“书画合一”的笔墨本体意识波澜壮阔的演进史。然而,令人扼腕的是,自近代“美术革命”思潮兴起以降,“书画合一”的文脉传统在巨大的历史误读和吊诡的文化逻辑中,被生生切断,弃若敝履,以书入画的笔墨之道砉然冰泮。其直接后果是,它使中国画创作与发展犹如缺钙的巨婴,表面硕大光鲜,内里却柔媚无骨;更甚的是,它遮泯和扼杀了中国画的美学品位与文化高度,使数千年来积淀于书法而传输至绘画的民族文化精神、哲学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意趣、宇宙意识等丧失殆尽,中国画真正降格至“画”的层级!视觉化的倾向,难道不是当代中国画发展不争的事实?依我看,书画关系的割裂,当是其毋庸置疑的重要原因——当然,与之颉颃的主因之一还有“诗画一律”传统的失落。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判断,与对书画艺术文化精神的认识,我无法不对增杰“书画合一”的艺术意识与创作实践刮目相看,并感到由衷的庆幸与钦佩!
在书画并进的艺术生涯中,增杰的书法研习,从一开始就被提升到文化修为的高度。数十年而下,他广泛涉猎北碑南帖,而尤其得益于颜真卿法书与篆隶、魏碑等金石碑学书法的修炼。其书法以苍朴浑厚、奇崛古奥的金石气骨见胜,也不乏南帖松灵虚和、蕴藉散淡的韵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书法修炼,给增杰的大写意绘画创作带来了无所不在的影响:其书骨画魂,两相凑泊,神用象通,适道俱往。其妙处,笔墨俱显金石碑学之气骨与草情隶意之风神:其提按顿挫者,缓则鸦行,急则鹊厉,或重如高山坠石,或轻似散羽浮空,顿之则有岳峙渊渟之态,导之则呈漪澜成文之韵,而其笔意所至,或沉雄奇崛,或古拙逸宕,或纵横争折,或粗犷豪纵,或俊逸疏秀,守道兼权,随态运奇;其使转动旋处,则辗转腾挪,收揽吐纳,颦申奋迅,或疾若惊飙戾天,或迟若流霞散绮,其笔势迥脱廉纤,不落畦径,放逸生奇,其笔力则刚健中含婀娜,浑朴中杂流丽;其起伏遣留处,则腾气扬波,含文包质,力弇气长,如力士之拔山,若船夫之荡桨,而其笔墨法象,则百体千形,巧媚争呈,或凝重如屋漏痕,或沉厚如印印泥,或苍古如虫蛀木,或滞涩如锥画沙,或圆劲如折钗股,无不真力弥满,格调清奇。
如果说,笔墨上的“以书入画”使增杰的大写意山水建构起“以线立骨”的审美仪轨,那么结构(章法)上的“以书入画”则使增杰的大写意山水焕发出“计白当黑”的审美意趣。书法结构(章法)入画是一种更高层级的图式转换,以往的研究者鲜有关注这一层面的学术问题者,他们宁可从西方艺术的所谓“平面构成”中寻求现代中国画的创新资源,也不愿意相信中国书法天然含蕴的远比西方艺术“平面构成”意识丰富、深刻得多的“空间观念”——它承载着我们华夏民族文化元典时代因效天法地而来的宇宙意识,而其实,西方艺术的“平面构成”从来就没有少从中国书法的空间意识(在形式上表现为以黑白关系构成的字内空间、字间空间和行间空间的集合)中吸取灵感和启迪。这是多么“吊诡”的文化奇观,不得不说,中国文化的自我侏儒化是多么地令人匪夷所思!从这一意义说,增杰以书法空间入画的艺术意识,庶几为提升中国画艺术的文化品位献祭了一瓣心香。
具体运用中,增杰有意识地将书法结构(章法)中的照应映带、疏密虚实、揖让避就、纵横正欹、俯仰向背、天覆地载等空间形式,与山水画中物象构成的置陈布势即:起承转合、聚散开阖、均衡照应、宾主揖让、顾盼掩映、参差错落等,形成一种空间意识的对应,书法中由“画——笔画”而“字——结构”、由“字”而“篇——章法”的图式构成原理,被增杰匠心独运地化用于山水画由“线”而至“单元图象”、由“单元图象”而至“整体画面”的空间构成关系。这种感而遂通的图式转换,给增杰的山水画空间至少带来了两方面的深刻影响:
其一,山水意象在书法艺术抽象化空间原理的启导下,真正实现了“计白当黑”的审美转换,其表征于画面,就是在空间形式上导致了以疏简化、符号化为特征的山水图式的诞生。这种转换,在审美趣味的层面上,意味着增杰已将山水画创作从客观图真的视觉经验传达,提升到主观写意的心象意趣发抒的高度;而在审美哲理的层面上,则意味着增杰将繁颐多变、佹形僪状的宇宙万象,转化为“囊括万殊,裁成一相”的抽象性、象征性笔墨语言;其在审美表现的层面上,则意味着物象结构与画面组织的删繁就简,化实为虚,从而达画之变,形成开阖相间、奇正相生、计白当黑的画面空间。增杰的众多山水作品,皆典型地反映出“计白当黑”“萧散清空”的艺术特征:《九华钟声出翠微》《九华万壑云缥缈》《九华山高峰连峰》等作品,特具弘仁山水遗风,其错落有致的大小山石,结构上大块留白,间以河湖萦带,一片虚白,而其远岫遥岑,多以湿笔带墨,形成大块面黢黑山体,其画面的黑白对比关系形成了强烈的审美张力;《山中岁月乐悠悠》,则以顶天“离”地的章法布局,形成上实下虚的空间对比,益显山势嵯峨、天高地迥之奇;《山光水色共参差》一作,则以上方与左、右虚空为法,形成了摇曳生姿、放逸生奇的山水空间。审观之,其简淡萧散之趣,虚灵清空之意,颇显出老子“为道日损”的哲学灵智。清画家王昱曰:“清空二字,画家三昧尽矣。学者心领其妙,便能跳出窠臼,如禅机一棒,粉碎虚空。”笪重光《画筌》亦曰:“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如果说,王昱的观念“勘破”了增杰山水空间的哲学根源与精神旨趣,那么笪重光的画论正“道出”了增杰山水空间的美学原理与实践方式。
其二,在书法空间意识的启导下,物象造型和画面真境趋向解构,绘画空间从“重法”向“重势”转变,因而由静态化空间向动态性图式过渡,绘画变得愈来愈像书法的结字、成篇那样,可以进行自由构景和因心造境。因而,在增杰的笔下,物象造型几乎完全打破了形质和结构的束缚,而成为一种意象化造型图式,其画面构图也突破与超越了纵深空间,而不断趋向平面构成关系,物象基本成为一种表情达意的抽象化、符号化图式元素,自由驱驰地进行书法式结构的抽象图式演绎。当是时,增杰几乎完全摆脱了时空观念的限制和自然属性的束缚,进入到自由抒写与心灵表现的艺术境界,天地造化,随其剪裁,阴阳大化,任其分合。因而,画面种种“空间之形”都被增杰转化为生命律动的“时间之流”,艺术中的运动、旋律、节奏等一切在视觉上无法直观呈现的种种因素,无不在线条、线结构的轻重徐疾、提按衄挫、腾挪起伏、纵横激扬、回旋低昂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而“时间之流”又无不映现于阴阳虚实的“空间之形”,时空冥合,主客消泯,“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程颐),其以山水空间映现的宇宙时空,成为一个“无往不复,天地际也”的生命证境。
一画开天,万象流形。增杰的大写意山水美学及其创作实践,突出地彰显了“万法流转,道通为一”的“一画”之道,其悟道之深,造诣之高,在同龄人中是较为鲜见的。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寻绎增杰得以于杂遝纷呈的山水画坛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但是,以增杰目前的年龄,他的探索时间还很漫长,因而,所谓“通会之际,人书(画)俱老”之说,似乎在冥冥中预兆了他必将在绘画创作上臻于更高、更远的境界。对此,我是坚信不疑的——以其不蹈故常的艺术个性、不受羁縻的创造才情、不落蹄筌的哲学灵智,最重要的是,以其不随以止的殉道精神。
(王先岳:中国国家画院美术学博士后,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后,文化部艺术发展中心中国画创作研究院教学部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