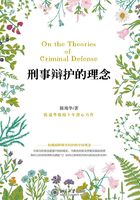
五、辩护权的权利主体
2012年《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律师向在押嫌疑人核实有关证据的权利,引发了有关被告人是否享有阅卷权问题的讨论。在律师界看来,唯有赋予在押嫌疑人、被告人查阅案卷的权利,才能保证其有效地行使辩护权。但很多检察官、法官对这一主张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嫌疑人、被告人尽管是辩护权的享有者,但阅卷权却只能由辩护律师独立行使。无独有偶。在如何保障律师“会见权”问题上,也出现了一种要求确立在押嫌疑人、被告人“申请会见权”的观点,认为会见权并不是辩护律师单方面行使的诉讼权利,在押嫌疑人、被告人也应属于会见权的主体,他们一旦提出正当的会见请求,不仅未决羁押机构应当安排律师会见,而且那些从事辩护活动的律师,也有尽快会见委托人的义务。当然,也有律师提出了担忧:目前就连律师“会见在押嫌疑人的权利”都遇到重重困难,在押嫌疑人获得“会见辩护律师的权利”并不具有太大的可能性。
在被告人是否享有“阅卷权”“会见权”问题的背后,其实存在着辩护权的权利主体这一理论问题。具体而言,作为辩护权的享有者,被告人只能通过辩护律师行使其诉讼权利,这是否具有正当性?难道我们在承认被告人拥有“诉讼权利能力”的同时,却要否定其“诉讼行为能力”吗?由此看来,作为辩护权利的享有者,被告人能否独自行使各项诉讼权利,这不仅是一个制度问题,更是一个有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按照传统的诉讼理论,阅卷权尽管来源于被告人的辩护权,却是辩护律师所独享的诉讼权利,无论是嫌疑人还是被告人,都没有阅卷权。所谓的“证据展示”或“证据开示”,也是在检察官与辩护律师之间展开的证据交换活动,嫌疑人和被告人都被排斥在这一活动之外。这是因为,设置阅卷权的目的主要在于保证辩护律师进行防御准备,有效地展开庭审质证。而被告人一旦有机会查阅案卷材料,就会了解公诉方所掌握的全部证据信息,轻则容易进行串供、翻供,重则会导致仇视、报复被害人、证人甚至同案被告人的现象出现。更何况,被告人假如获得了查阅、摘抄、复制公诉方案卷笔录的机会,就有可能全面了解案件证据情况,并根据这些证据情况来确定供述和辩解的内容,从而出现故意提供虚假陈述的情况。在这一方面,被告人与证人的情况有些相似。法学理论强调证人的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要求证人在作证之前不得接触其他证据,不得旁听案件审理过程。同样,被告人作为了解案件情况的“特殊证人”,也不能通过接触案卷来产生先入为主的预断。
然而,这种将嫌疑人、被告人排斥在阅卷权主体之外的观点是很难成立的。这是因为,被告人是辩护权的享有者,当然也可以独立行使阅卷权。在中国刑事审判制度中,被告人在行使举证权和质证权方面,与辩护律师享有完全相同的权利,他们既可以向法庭提出本方的证据,也可以对公诉方的证据进行质证,对控方证人也可以进行当庭交叉询问。既然如此,不去阅卷,不了解公诉方掌握的全部证据材料,被告人怎么进行有效的法庭质证呢?另一方面,有些为被告人所独知的专业问题或者案件事实,只有允许被告人亲自阅卷,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质证意见,并最终协助辩护律师做到有效的辩护。尤其是在被告人与辩护律师的辩护思路存在分歧的情况下,让被告人充分地获悉公诉方的证据材料,了解公诉方掌握的指控证据,可能是保证被告人作出理智选择的重要手段,也是督促辩护律师展开有效辩护的必由之路。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赋予了被告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使其享有辩护权,律师属于其辩护权的协助行使者。但与此同时,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在证据法上又属于独立的法定证据种类,被告人其实具有“证人”的品格,属于案件事实的信息来源。被告人作为当事人的地位与作为“证据信息之源”的身份,其实经常会发生冲突和矛盾。主流的诉讼理论强调被告人拥有选择诉讼角色的自由,也就是承认所谓的“供述的自愿性”,强调禁止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但是,对被告人阅卷权的剥夺,对其翻供、串供的严密防范,无疑将被告人置于无法自由选择诉讼角色的“诉讼客体”境地。而唯有赋予被告人独立的阅卷权,使其有机会通过全面阅卷来展开充分的防御准备,才能使被告人的当事人角色得到有效的发挥,而被告人与辩护律师共同的防御下,被告人的辩护权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
在辩护权的权利来源和权利主体方面,值得反思的还有“会见权”问题。在这一方面,中国法学界和律师界主要关注的都是“辩护律师如何会见在押嫌疑人”的问题。那么,作为一项辩护权利,“会见权”究竟是律师的权利还是在押嫌疑人的权利?如果这一权利仅仅属于律师所独有的“诉讼权利”,那么,辩护律师就要“争取从外围进入羁押场所”,突破侦查部门和看守所的两道审批“门槛”。但是,会见权与其他辩护权利一样,都来源于作为委托人的嫌疑人,也当然应当为嫌疑人所直接享有。假如会见权只是意味着律师主动会见在押嫌疑人的权利,那么,嫌疑人在未决羁押状态下就不能提出“会见辩护律师”的申请,而只能被动地等待律师的会见,消极地接受律师所安排的会面。但嫌疑人在丧失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一旦遇到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尤其是需要及时与辩护律师协商的情形,难道他就不能提出会见律师的请求吗?这种单方面强调“律师会见权”的制度,怎么能保证嫌疑人获得有效帮助呢?
很显然,所谓“会见权”,其实是“律师申请会见在押嫌疑人”与“在押嫌疑人要求会见辩护律师”的有机结合。我们过去一直将“会见权”界定为“律师会见在押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这是非常不完整的。律师作为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帮助者,通过会见在押的委托人,可以了解案情,获悉相关的证据线索,进行充分的防御准备,逐步形成和完善自己的辩护思路,并且说服委托人接受并配合自己的辩护思路,从而达到最佳的保护效果。这些都是律师会见在押委托人所能发挥的诉讼功能。但是,作为身陷囹圄的当事人,嫌疑人、被告人一旦委托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就应当拥有要求会见辩护律师的权利。一方面,对于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会见律师的需要,律师有时候并不十分清楚,单靠律师的主动会见经常难以满足委托人的法律服务需求。另一方面,在押的委托人一旦遇到诸如侦查人员违法取证、管教民警纵容同监所人员虐待或者有关部门威胁、利诱嫌疑人、被告人改变诉讼立场(如将拒绝供述改为当庭认罪)等情形,只有获得及时会见辩护律师的机会,才能向律师进行必要的法律咨询,协调诉讼立场,避免作出不明智的观点改变。而对于这些发生在未决羁押场所的情形,律师在“外面”是很难预料到的,也往往无法通过主动的会见来加以解决。
由此看来,无论是阅卷权还是会见权,其实都是为实现辩护权而存在的。嫌疑人、被告人既是辩护权的享有者,也当然应当属于辩护权的行使者。作为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代理人,辩护律师可以依据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授权,有效地行使各项辩护权利,这是确保被告人辩护权得以有效行使的制度保障。但是,辩护律师所行使的辩护权利既来自被告人的授权,也不能完全替代被告人本人对各项辩护权利的行使。作为辩护权利的享有者,被告人假如对辩护律师失去了信任,完全可以撤销授权委托,也可以否决辩护律师对某一辩护事项的处置。不仅如此,被告人在信任辩护律师的情况下,既可以完全委托辩护律师代行各项诉讼权利,也当然可以与辩护律师一起,各自独立地行使辩护权。事实上,被告人对阅卷权、会见权的有效行使,既可以对辩护律师的阅卷、会见形成必不可少的补充和保障,又可以发挥难以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赋予被告人阅卷权和会见权的理论意义在于,保证被告人在阅卷、会见等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使得被告人与辩护律师作出更为充分的防御准备。应当强调的是,辩护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有效地实现委托人的辩护权。无论是“阅卷”还是“会见”,都不应当成为辩护律师的“独享权利”,甚至成为嫌疑人、被告人所无法“染指”的律师权利。否则,阅卷权、会见权的制度设置,势必发生功能上的“异化”,这些权利甚至会变成辩护律师所独享的权利。从理论上看,嫌疑人、被告人放弃行使辩护权的唯一正当理由应当是,嫌疑人、被告人相信辩护律师代行这些权利,会取得更好的辩护效果。但前提是嫌疑人、被告人应当拥有独立行使这些权利的机会。而在剥夺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前提下,辩护律师完全代为行使这些权利,可能并不符合嫌疑人、被告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