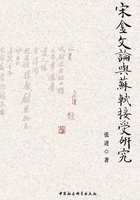
第二节 欧阳修推扬“平淡”诗美
梅尧臣首倡平淡诗美,有功甚大;而欧阳修知之、推之,贡献尤巨。论者对此予以充分肯定,如:
宛陵梅先生以道德文学发而为诗,变晚唐卑陋之习,启盛宋和平之音,有功于斯文甚大。欧阳文忠公知之最深,既题其诗稿,又序其集,又序其所注《孙子》,又铭其墓而哀之以文。盖文忠公之知先生,犹子房谓沛公为殆天授者,是岂容赞一辞哉!(刘性《宛陵先生年谱序》)[44]
宋初诗文尚沿唐末五代之习,柳开、穆修欲变文体,王禹偁欲变诗体,皆力有未逮。欧阳修崛起,为雄力复古格。其时曾巩、苏轼、苏辙、陈师道、黄庭坚等,皆尚未显。其佐修以变文体者尹洙,佐修以变诗体者则尧臣也。其诗旨趣古淡,惟修深赏之。(四库馆臣《宛陵集提要》)[45]
指出欧阳修对梅公知之最深,深赏梅诗之旨趣古淡,而梅尧臣也辅佐欧阳修变革诗体,二人乃志同道合,趣味相投。
一 欧公推赏梅诗之古淡、闲淡
欧阳修曾说:“昔梅圣俞作诗,独以吾为知音,吾亦自谓举世之人,知梅诗者莫吾若也。”[46]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说:“圣俞少时,专学韦苏州,世人咀嚼不入,惟欧公独爱玩之。”[47]是知欧公与梅公有“知音”之交,欧公独赏梅诗之“古淡”“闲淡”,爱玩不已。
欧公《六一诗话》中有一段精彩议论,比较梅尧臣与苏舜钦诗之不同风格,其云:
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余尝于《水谷夜行》诗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气尤雄,万窍号一噫。有时肆颠狂,醉墨洒滂霈。譬如千里马,已发不可杀。盈前尽珠玑,一一难拣汰。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辞愈精新,心意虽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又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苏豪以气轹,举世徒惊骇。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语虽非工,谓粗得其仿佛,然不能优劣之也。[48]
欧公谓苏诗的“笔力豪隽”与梅诗的“深远闲淡”,二者各极其长,不能分别其优劣。然而他指出,苏诗之雄杰,苏诗之癫狂,有如“千里马”,一发不可收;又如满目“珠玑”,令人难以拣汰。而梅诗的“闲淡”,有如老来的美女,风韵犹存;梅诗的“古硬”,又如“食橄榄”,反复咀嚼,真味久在。他说“苏豪以气轹”,举世皆为“惊骇”,皆能赏识;而“梅穷独我知”,梅诗就好比“古货”难以出售。因为它不大符合时人的审美口味,一时还不能得到普遍的接受。欧公点明梅诗的“古淡”“平淡”是一种成熟的美,老境的美。在他看来,更为难识、难得。他在《再和圣俞见答》诗中说:
子言古淡有真味,太羹岂须调以虀。
怜我区区欲强学,跛鳖曾不离污泥。
问子初何得臻此,岂能直到无阶梯。
如其所得自勤苦,何惮入海求灵犀。
周旋二纪陪唱和,凡翼每并鸾皇栖。
有时争胜不量力,何异弱鲁攻强齐。[49]
欧公将梅公的“古淡有真味”,比作“大羹”,不须调和,而自有真味美味。《礼记·乐记》云:“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郑玄注:“大羹,肉湆,不调以盐菜。”欧公自谦自己欲强学而不得,譬如跛鳖不曾离开污泥;又将梅诗比作“鸾皇”(鸾与凤),将己诗比作“凡翼”(普通的鸟);又将梅诗比作“强齐”,将己诗比作“弱鲁”,赞美之词,流溢纸上。
由于欧公的极力推赏,梅诗遂风行天下。欧公在《梅圣俞墓志铭并序》中,精辟论述了梅公其诗之风格,得益于其君子人格:
而圣俞诗遂行天下。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坚。……圣俞为人,仁厚乐易,未尝忤于物,至其穷愁感愤,有所骂讥笑谑,一发于诗,然用以为欢,而不怨怼,可谓君子者也。[50]
欧公认为,梅诗的风格,并不是简单的“平淡”,而是丰富而有变化:“初喜为清丽、闲肆(悠闲自然)、平淡”“久则涵演深远”,是就其风格的变化及其给读者的感受而言;“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坚”,是就风格的辩证统一而言。梅诗在“清丽、闲肆、平淡”的主导风格中又包含着怪奇新巧的元素,而避免了风格的单一性。同时,其“清丽、闲肆、平淡”又非格力柔弱,而是气力弥满,老到坚实。简言之,平淡而含深远,平淡而出怪巧,平淡而有气力。这便是欧公对梅诗风格的解读。
欧公指出,梅诗平淡风格的形成是其“君子”人格的反映。其为人“仁厚乐易”,虽处穷而不忤逆于物,将自己的穷愁感愤骂讥笑谑发于诗,抒发的是他的人生态度,是心理的平和欢悦,而不是发泄怨怼的情绪,所以可称为“君子”。欧公所论,对于我们理解梅尧臣的君子人格,理解“平淡”诗美的实质极有助益。这也印证了本章的论点:处穷而能超然淡泊,才能成就“平淡”的诗歌风格。
欧公的极力推赏与王安石的“推仰尤至”,奠定了梅诗的崇高地位。陆游说:
先生当吾宋太平最盛时,官京洛,同时多伟人巨公,而欧阳公之文、蔡君谟之书与先生之诗,三者鼎立,各自名家。文如尹师鲁,书如苏子美,诗如石曼卿辈,岂不足垂世哉?要非三家之比,此万世公论也。……欧阳公平生常自以为不能望先生,推为“诗老”。王荆公自谓《虎图》诗不及先生《包鼎画虎》之作,又赋哭先生诗,推仰尤至。[51]
陆游认为,宋初太平之时,欧阳修之文、蔡襄之书法与梅尧臣之诗,三者鼎立,各自名家,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至于尹洙(字师鲁)之文,苏舜钦(字子美)之书与石延年(字曼卿)之诗,不是不可以垂世,却比不得欧、蔡、梅三家,“此万世公论也”。又举出王安石对梅公的“推仰尤至”。宋末刘克庄亦称:“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淫哇稍息,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尹下。”[52]当然,对梅诗的“平淡”,也有持不同意见者。朱熹《朱子语类》载:“或曰:‘圣俞长于诗。’曰:‘诗亦不得谓之好。’或曰:‘其诗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53]一向推崇平淡诗美的朱熹对梅诗不十分看好,认为他不是平淡,而是“枯槁”,与杜甫说陶诗“枯槁”略同。[54]南宋初期颇有诗名的张嵲评曰:“圣俞以诗鸣,本朝欧阳公尤推尊之。余读之数过,不敢妄肆讥评。至反复味之,然后始判然于胸中。不疑圣俞诗长于叙事,雄健不足,而雅淡有余。然其淡而少味,令人无一唱三叹之意。至于五言律诗,特精其句法步骤,真有大历诸公之风。”[55]说明宋代大家虽然都推崇平淡之美,但对平淡的审美内涵的理解与具体评判,是有差别的。这也是诗歌接受过程中很正常的事。
二 改革文风以“平澹典要”取士
欧公既推赏梅诗之古淡、平淡,并进一步以此为诗歌鉴赏与评论的重要标准。如云:
世好竞辛咸,古味殊淡泊。否泰理有时,惟穷见其确。[56]
辞严意正质非俚,古味虽淡醇不薄。[57]
又知物贵久,至宝见百炼。纷华暂时好,俯仰浮云散。淡泊味愈长,始终殊不变。[58]
其为文章淳雅,尤长于诗,淡泊闲远,往往造人之不至。[59]
欧公认为:世人竞好“味重”,而“古味”“淡泊”,其虽淡而醇厚;“纷华”的文辞只能暂时被人叫好,俯仰之间,便会如浮云散去,唯“淡泊味愈长,始终殊不变”,而且“淡泊闲远”的境界,往往是人难以达到的。可知,欧公是从诗歌发展史的开阔视域来观照诗歌的古味淡泊,实际上是在追求诗的本真,追求诗的高境,以反对晚唐五代以来险怪、绮丽、雕琢的诗风,其思路是借复古以革新。
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和思路,欧公在权知贡举时,对科考取士作了重大的改革,以“平淡造理”为择取的标准。韩琦在《欧阳公墓志铭并序》中说:
嘉祐初,权知贡举时,举者务为险怪之语,号大学体。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澹造理者,即预奏名。初虽怨 纷纭,而文格终以复古者,公之力也。[60]
纷纭,而文格终以复古者,公之力也。[60]
欧公“取士”的择取标准是,黜去好“险怪之语”者,而“取其平澹造理者”,此项大胆革新举措,在开始时引发怨谤纷纭,后来逐渐被社会接受,对北宋文格诗风的改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刘性《宛陵先生年谱序》也说:
宋嘉祐二年,诏修取士法,务求平澹典要之文。文忠公知贡举,而先生为试官,于是得人之盛,若眉山苏氏、南丰曾氏、横渠张氏、河南程氏,皆出乎其间。不惟文章复乎古作,而道学之传,上承孔孟,然则谓为文忠公与先生之功非耶?[61]
可见以“平澹典要”取士,不仅改革了文风,亦拔擢了一批真正的人才,如苏轼、曾巩、张载、程颐等,日后成为宋代文化之顶级人物。
三 借梅诗提出“穷而后工”的命题
梅公长欧公5岁,其59岁病亡。几年后欧公在“将告归”时“因求其稿”,题其诗稿,又序其集,充分论述了梅诗的艺术感染力,并借此提出“穷而后工”的命题。
欧公在《书梅圣俞稿后》中,从论“乐”的巨大感染力量入手,进而论梅诗。他说:
八音五声……至乎动荡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盖不可得而言也,乐之道深矣。……盖诗者,乐之苗裔与!汉之苏李、魏之曹刘得其正始,宋齐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时,子昂、李、杜、沈、宋、王维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声,或得其舒和高畅之节,而孟郊、贾岛之徒又得其悲愁郁堙之气……今圣俞亦得之,然其体,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读之,可以喜,可以悲,陶畅酣适,不知手足之将鼓舞也,斯固得深者耶,其感人之至,所谓与乐同其苗裔者邪。[62]
孟子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63],荀子说“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64],欧公发挥了圣贤之意,认为“乐”有着可喜可悲或歌或泣的巨大感染作用。诗乃乐之苗裔。唐人之诗,或得其“淳古淡泊之声”,或得其“舒和高畅之节”,或得其“悲愁郁堙之气”……而梅诗亦得之于“乐”,读梅公之诗,感觉如春秋之风物英华,变态百出,使人可以喜,可以悲,陶畅酣适,其入人之深,感人之至,完全达到“与乐同其苗裔”的审美效果与感染力。欧公的高度评价,以梅诗的审美接受为视角,反映出欧公的诗歌接受美学思想。
欧公又作《梅圣俞诗集序》,解答世人“诗人少达而多穷”之见,提出“穷而后工”的命题: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65]
在欧公看来,“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为什么呢?他认为原因有二:其一,士之有才而不得施于世,“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能亲近自然山水,自能建立起较为纯粹的审美关系,往往能“探其奇怪”,写出独特的山水景致;其二,诗人内心郁积的忧思感愤,往往借助于比兴手法抒发怨刺情绪。此内情外景之融和,即能写出一般人难以体验、难以言说的东西,故愈穷则愈工,愈工则感人。梅尧臣的诗,正是抒发其“不得志者”,处穷而乐于诗而发之,故得其工也。欧公以梅诗为典例,提出“穷而后工”说,得到士人的广泛认同。特别是苏轼,继承与发扬了欧公这一观点,对其作了进一步的理解与阐发。如他在《题王晋卿诗后》中说:“晋卿以贵公子罹此忧患,而不失其正,诗词益工,超然有世外之乐……”可谓深得欧公之精髓。“穷而后工”也成为苏轼重要的创作观念之一。[66]
欧阳修对梅诗之古淡平淡之所以深美之、扬厉之:一在于其志同道合,他说:“宛陵梅圣俞善人君子也,与余共处穷约,每见余小有可喜事,欢然若在诸已。”[67]二在于改革文风,如前所述。三在于他的贫寒出身与坎坷经历相关。欧公自谓“吾生本寒儒”[68]。《宋史》本传载欧公“四岁而孤”“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入仕后因耿直敢言,“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69]。他说:“君子轻去就,随卷舒,富贵不可诱,故其气浩然;勇过乎贲育,毁誉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见于喜愠,能及是者,达人之节而大方之家乎?”[70]足见其处穷而能恬然淡泊,风节自持。他强调“穷而后工”,但不喜那些遭贬之士,“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故戒人“慎勿作戚戚之文”[71]。所以欧公之诗,清新秀丽,平淡有味;欧公之文,平易自然,纡徐委婉。苏洵称其文:“纡馀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72]朱熹言其文“虽平淡,其中却自美丽,有好处,有不可及处,却不是阘茸无意思”[73]。欧公诗文的“平淡”“美丽”与“不可及处”,不独在字面,乃在其人生境界之淡泊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