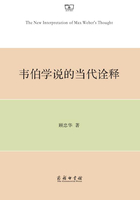
2 “现代性”的社会学分析——从韦伯到哈贝马斯
历史主义发展成一种具有特殊意涵的知性能力,它概化了我们的世界观。……日常生活中我们同样应用附带历史色彩的概念,如“资本主义”、“社会运动”、“文化过程”等。这些动力被理解为潜在的势力,流变不停,并在时间中由一点向另一点移动;即在日常的反省层次上,我们寻求决定时间架构中当前的位置所在,而让历史的宇宙座钟告诉我们是什么时候了。
——卡尔·曼海姆,《历史主义》
一、前言
西方文化思想界近十年来最令人瞩目的动向之一,便是围绕着“后现代”概念展开的讨论。28各种标举着“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建筑、音乐、戏剧等文化现象,除了眩目翻新的表现形式以及争赶时髦的消费心态之外,本身似乎蕴含有强烈的象征意味,暗示着我们一向用来指称当代情况的“现代”一词不足以概括未来。就“后现代”概念背后的逻辑而言,因为“现代社会”正急速向“后现代社会”过渡,“现代”迟早会像古代、中古一般成为一个历史时段的代称,或是人类文化记忆中的某个符码。本文并不拟检讨此种将“现代人”所有具体经验予以“历史化”之尝试是否具备知识上的妥当性(adequacy),但“后现代”概念的提出,无疑吸引了包括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重新注意到“现代性”的界定问题。事实上,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可说始终是以观察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形态为其核心任务,因此在古典社会学理论中即已对“现代”的特质作过不少探讨。不过,自社会学成立一百多年以来,关于“现代”或“现代性”的功过评价业已经过几度转折。本文的目的在阐明这一问题对社会学的重要性,并评介主要由韦伯和哈贝马斯所代表的反省观点——毕竟在未能适切掌握“现代性”一词的实质内涵和特指涉之前,所谓“后现代”种种仍不免流于空泛(Bernstein,1985:25)。
二、“现代性”的社会学意义
1.由“现代化理论”谈起
前面提到,社会学的古典著作中不乏对工业文明兴起的背景及其后果予以研究分析。尼斯贝特(Nisbet,1967)尝谓,工业革命与民主革命所促成的社会转型乃早期社会学者共同关心的经验对象。而滕尼斯(Tönnies)区别社区(Gemeinschaft)和社会(Gesellschaft)两种组织形式,以及涂尔干在“分工论”(1893)里划分机械连带和有机连带,实已奠立下“现代化理论”中“传统”与“现代”的两组对立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现代化理论”自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期曾经长期影响了吾人对于社会变迁的看法。一般说来,“现代化”(modernization)意指包括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政治民主化等社会总体结构的变迁过程,亦牵涉到与此相关联的人格特质、文化价值和宗教信仰上的“必要”改变。在此意义下,莱普修斯认为现代化理论中设定的“现代”概念已超越纯粹的描述性用法,而建构出一套具有显著特征的类型概念。他进一步分析所谓“现代化”的具体内容可分成四个层次:(1)指涉社会结构在某些特定历史时空下表现之某种配置情形(configuration);(2)指涉被划归为“现代性”的各项属性;(3)指涉社会普遍演化之过程;(4)指涉有意识及有计划提高社会系统功能绩效之发展过程(Lepsius,1977:13)。简言之,现代化理论基于社会演化“一体适用”的原则,以西方社会的发展成果作为衡量“现代性”的标准,而欲应用来解释、预测非西方社会由“传统”或“前现代”形式逐步向“现代”转型的进展程度。现代化理论固然有沿袭自古典社会学的思想传承,但其理论模型的分析架构基本上衍生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诸如模式变项(pattern variables)和AGIL四系统模型莫不强调现代社会在行动(action)和系统(system)两个面向皆朝向理性的增长、适应能力的增强,以及规范价值更形普遍化(value generalization)的演化目标前进(Parsons,1977)。对帕森斯而言,“现代”即是“理性”实现之明证,无须再作质疑;而其他现代化理论的倡导者在纷纷提出“现代化”的指标——工业化、都市化、世俗化、民主化乃至核心家庭、成就取向等——之际,往往假定了西方文明的成就“不止是‘可欲的’,同时也是任何社会发展的‘一个自然的最后阶段’”(金耀基,1978:147)。现代化理论中隐含的价值判断色彩以及单线演化观,随着战后大部分第三世界地区实际发展经验的受挫,在1980年代一时之间成为众矢之的,禁不住严厉的诘难而显得黯然失色(萧新煌,1985)。
2.批判的观点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现代化理论多少反映了当代西方人思想意识后面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尤其突显出西方近代以来对历史的过去与未来所赋予的特殊意义。德国史学家科泽勒克(Koselleck)指出,中古世纪的欧洲人深受基督教末世论的影响,对于遥远的“未来”根本抱着巨大的恐惧感,很难去想象甚至计划“未来”。直到启蒙时代以后,一些思想家对人类的天赋理性产生了信心,开始肯定人类社会有自我改善的可能性;黑格尔更宣称十八世纪的欧洲已迈进一个新纪元(The New Age),正处在向“现代”过渡的关键时刻。根据科泽勒克的研究,十九世纪社会演化说的提出,象征了西方文化中“时间”观念的重大转变,人们对于“未来”由原先的消极看法变为积极乐观,不仅期望“未来”将会带来幸福承诺,同时更回头重新诠释历史,把十五世纪视作世界向“未来”开展的一个分水岭。事实上,西方史学中古代、中古与现代的分期概念在十九世纪中期逐渐定型,代表了历史经验的重组,也使“现代”这个名词蕴含了可以向未来无限延伸的意义(Koselleck,1985)。
我们或许可以说,人类主观上对“时间”和“历史”的感受可能因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而会有所不同。但在西方文化挟着优势力量不断向外扩展之后,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人类,不论居住在世界哪个角落,逐渐都被容纳到单一而同步进行的普遍时间模式中。科泽勒克称这种情形为“异质时间的同时性”(Gleichzeitigkeit der Ungleichzeitigen;contemporaneity of noncontemporaneous),亦即所有人类过去存在过形形色色的社会形态,今天全被拉到同一条时间向度上——而这正是“现代”最根本的特征之一!更有甚者,在现代化理论中任何非西方社会都被切断了历史联系,完全只凭目前的社会现状来标定它们在“开发程度表”上的位置。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统一时间,预设了人类未来发展的普遍同质性,唯有如此,比较“现代化”的程度才可成为可能;哪些指标代表“先进”,哪些代表“落后”,皆可以标准化而且用来衡量“世界村”中每一个个别成员的表现。严格说来,这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全新经验,同时也让我们更理解现代化理论强调其普遍有效性的心态背景:因为既然源自于西方的独特时间模式已获致事实上的普遍性,加上西方文明的成就又被认定是“现代性”的唯一标准,那么西方的发展经验似乎理所当然也可以普遍化了。二十年来数量庞大的现代化研究,基本上不脱这一份将特殊历史过程加以抽象为普遍原则的特色。
无论由理论建构还是由实践关联的层次而言,现代化理论经过上述的剖析之后,显露出其最大的盲点,也就是它把非西方社会与其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时空连续性不恰当地截断了。一方面它假设今天属于“落后”的地区只有一个目标,便是接受“先进”的技术与制度设计,遂行“现代化”计划;另一方面它忽视非西方社会想以三五十年来完成西方历经数百年的变迁过程,必定会产生“压缩效果”(compression effect),制造出更多未曾预料到的副作用,反易导致社会不安。伊朗的例子,一举暴露出现代化理论在理想和现实巨大差距下的严重问题。现代化理论既遭受到实际发展经验的无情考验,西方学者不得不重新检讨形成西方“现代性”的历史条件,此时韦伯的著作被认为足以提供更宽广的视野,能够弥补现代化理论缺乏历史深度的遗憾(Eisenstadt,1987)。韦伯究竟留下过哪些重要线索,使得困扰于“现代性”问题的“现代人”仍须乞灵于古人呢?
三、西方经验的重新评估
1.韦伯的“理性化”概念
韦伯一生的研究对象,在时间的纵深以及地域的涵盖上绝不仅止于现代的西方文化,但他贯穿所有研究领域的基本关心点,是想回答“何以西方会成为今天的西方?”这个高度复杂的问题(Schluchter,1979)。针对西方本身的历史发展,韦伯采用溯源或发生学的(genetic)方法,以贯时的(diachronal)观点探寻“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在精神风格(ethos)上的发端与递变,且更回溯及古代犹太教的宗教特征;就西方现代文化的独特性而言,他则采用比较方法和类型学(typology),以共时的(synchronal)观点将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各具悠久历史的文化个体和西方相互对比,其目的仍是希望通过这种比较而能更清楚地掌握西方文化发展的特异之处(Schluchter,1983:12)。综合他前后十余年的考察心得,韦伯于1920年出版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第一卷“序论”里,扼要而有力地表明了他所问的“世界史之问题关联”(universalhistorischer Problemzusammenhang):
生为欧洲现代文化之子,我们在研究世界史时,不可避免且有充分理由来提出如下的问题,即在西方,而且唯有在西方,曾出现一些文化现象,其发展方向——至少我们(西方人)乐于如此想象——具备了普遍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意义和效果。这究竟应归功于怎样的连锁因果效应?(Weber,1981:9)。
在韦伯的思虑当中,促成西方朝向“现代”发展的一连串因素乃是环环相扣,自然不排除有许多历史的偶然。但就“客观可能性”的判断形式而言,西方近世以来深入各个生活领域(如音乐、建筑、艺术、宗教、科学与经济……)的“理性化”趋向,就像百川汇流的大河般,浩浩荡荡地冲破“传统主义”的藩篱,刷新了人类对于“世界”的控制和支配能力,也造就了今天我们统称为“现代”的文明成果。这股潮流,由它在经济和科技上的高度效率来看,确实是莫之能御。因此,代表西方现代文化动力的“现世支配之理性主义”(rationalism of worldmastery),相较于所有非西方文化中关联到人生态度之其他类型的“理性主义”,注定在彼此冲突时占尽了有利条件,而更能贯彻其自身之主张。29这么说来,韦伯在他“世界史”式的观察中,似乎预先为现代化理论的普遍宣称奠下了“正当的”(legitimate)基础。但若深一层去探究,我们会发现现代化理论只撷取了皮毛,却完全舍弃掉了韦伯对“现代性”黑暗面的忧患意识,正因如此,现代化理论在对“现代”的意义理解上,不免以天真乐观的亮丽色彩整个地掩盖住了韦伯原意中深刻的文化悲观主义。
诚然,韦伯的悲观心理多少受到当时风气的影响(Kalberg,1987),不过他所提出的理由实则超越了时代的限制,而触及“现代性”本身的根本病因,吊诡的是:韦伯认为让“现代”蒙上阴影的,归根结底竟也是那一股如脱缰之马的“理性化”力量。关于韦伯使用“理性”、“理性化”和“理性主义”等概念时的多重涵义,许多诠释的作品皆已提出讨论(Brubaker,1984;Löwith,1982),与本文题旨有关的,主要是(1)“理性化”过程与“价值领域”之分化与冲突;以及(2)现代社会中,“目的理性”(Zweckrationalität;purposive rationality)日渐制度化带来的后果。现分述如下:
(1)韦伯在论及西方的文化发展时,始终强调片面的唯心或唯物论皆不足以解释“西方现代理性主义”之兴起。由于我们所面对的现象是一整套的“生活形态”(Lebensstil),“理性化”概念亦须有其相对应的复杂意义,至少它绝非单线的演化模型,而是包含了多元趋向与内在冲突的可能性(Weiss,1987)。事实上,韦伯眼中的“现代”是一个“价值多神论”的时代,亦即主张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宗教、法律、政治、经济、科学、艺术,乃至色欲等),在“理性化”过程里愈益获得相对的自主性,最后导致各种价值之间无从避免的冲突斗争(Schluchter,1988a)。他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中,曾经举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诗集《恶之花》来印证这一论点,而波氏正是1859年首次发明了modernity(现代性)一词的诗人。韦伯对现代人面临价值选择时的困难处境(我们或可举例说:环保或经济成长?)既有如此深刻的体会,同时又反对笼统的“进步”观,则所谓的“理性化”或“世界的解除魔咒”就不见得仅具有正面的肯定意义,却还提供了对西方现状反省与批判的思想线索。
(2)“理性化”落实到行动层次上,意指行动者对手段策略的选取应用,将更能说是有效达成预设之行动目的。韦伯称此种行动倾向为“目的理性”,亦可说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表示行动者的考虑纯粹以效果最大化为唯一原则。“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式的行动建立在对于目的-手段关系的合理评估,尤其在经济的劳动生产方面,这种理性表现的力量特别显而易见。韦伯于《经济与社会》中,一度把经济行动简单划分为“传统的”和“目的理性的”两大类型(Weber,1968:69)。“传统的”经济行动接近于本能状况,以固有之传统技术谋求需要之满足:“目的理性的”经济行动则要求有计划地分配和运用资源,以成本观念生产商品并在市场中进行交换,生产因此不再只是为了维持必要之生计,而是经过有效的计算与管理来求取经营利润的最大化。就人类经济活动的发展而言,这两种类型自然是连续而渐变的,但从西方历史或甚至“世界史”的角度观察,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文化意义”(Kulturbedeutung)便在于“目的理性”彻底取代了“传统”式的经济理念,并进而形成相配合的社会组织与制度,使得人类支配外在环境的计算能力大幅提高,创造出空前的文明成就。问题是,“目的理性”的制度化意味着手段逐渐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韦伯指出,“目的理性”过度膨胀的结果,使得“价值理性”(Wertrationalität; alue rationality)或“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的行动倾向相对萎缩,影响所及,伴随“现代”在物质享受充分发达而来的,是让有识之士必须正视的“意义危机”(Schöllgen,1985)。当韦伯提到现代的文明人,
处在一个不断透过思想、知识与问题而更形丰富的文明之中,很可能“对生命倦怠”,而非享尽了生命。(Weber,1985:130)
似乎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现代人“漂泊的心灵”(伯格语)背后之根源(Hennis,1987)。认为韦伯著作中一贯追问现代人何去何从,流露出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这是他从早期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便开始不断思索的主题之一。事实上,韦伯对“现代性”的分析与诊断,归根结底仍是建立在他深入探索资本主义之精神渊源的研究心得上。资本主义作为西方现代文化重要的型塑因素,究竟在哪些方面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
2.资本主义与现代文化
韦伯曾明白表示:
资本主义已是一个无法连根铲除,因此只有加以容忍的历史发展结果。任何想回到从前,再恢复社会父权基础的尝试,今天已完全行不通了。(Schluchter,1981:257)
基于这样的认识,韦伯特别着重资本主义“破旧立新”的革命力量以及它在文化层面造成的广泛冲击。韦伯一再强调,资本主义若是仅指贪得无厌的营利欲,那么人类史上凡是具备客观机会的所在,无论何时何地,都存在过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但韦伯所定义的“西方现代理性的资本主义”绝非营利欲的表现结果,倒不如反过来说,是人们对于自然本能的贪欲能够加以抑制,或至少理性地缓和(Weber,1981:12)。由于韦伯主张卡尔文教派信徒特有的一种“入世禁欲主义”(inner-worldly asceticism)和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微妙的亲近性,并在其他种种条件(地理环境、科学技术、法律制度……)相配合之下,形成了西方历史上十分独特的结构组合,也在几百年之内塑造出现代资本主义今天的面貌。此一因此被称为“韦伯命题”的论点,曾经引起过激烈的辩论,迄今未绝(MacKinnon,1988;Pellicani,1985)。而韦伯本人在“反批评”的最后答辩中,作过更进一步的说明:他指出(1)《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中心旨趣,并不在资本主义得以扩张的理由,毋宁是探讨经过宗教与经济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现代处境里,“人类的发展”问题;(2)《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容,主要欲证明现代的“职业观”有其宗教伦理的根蒂;(3)最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点明现代资本主义早已无需源自宗教的“精神”来支持,“职业”与人格中之内在伦理核心不再具有主观上的统一性(Weber,1978a)30。
“职业人”(Berufsmenschentum;the vocational man)一词,在韦伯的著作中,几乎可以等同于他所理解的“现代人”。然而,资本主义在制度层面上不断理性化的结果,使得“职业人”今天成为社会分工“事理上之必然”(Sachzwang),其中“宗教的根蒂”业已萎缩。“清教徒渴求为职业人,我们现在却被迫为职业人”,这句话道尽了生长在资本主义“钢铁时代”中,个人的渺小与无奈。对韦伯而言,现代文化受到资本主义洗礼后,展现在个人面前的生活世界,是一个“解除魔咒”的世俗功利主义笼罩一切的世界。理性的计算、科技工具的运用以及计划性的社会变迁在在扩大了“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的影响范围,乃至现代的经济、政治、社会组织无不朝向“形式理性”的运作原则(Haferkampf,1987)。在此意义下,个人除了注定背上“职业人”的硬壳子之外31,在时时面对组织内部秩序的要求与宰制——官僚支配实际上只肯造就一批顺服适应的“秩序人”(Ordnungsmensch)(Schluchter,1980:126)。我们因此也不难了解韦伯在阐述“现代性”的特质时,并未局限于表彰人类理性的成就,反而刻意以悲观的语气,反讽一批“没有精神的专家,没有情感的享乐者”或许会成为代表“现代”的“最后的人物”。这批身受“职业人”与“秩序人”双重压力的个人,表面上看来都拥有了传统社会无法想象的自由选择机会,实际上却愈来愈像资本主义这部大机器中的小零件,在严密组织的官僚科层体制里循规蹈矩地运转,这是“理性”中“非理性”的成分。
韦伯针对“理性化”过程本身的吊诡,只给予“实然”层次的犀利分析,并未提出一套“应然”的规范要求。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形式理性”或“目的理性”逐渐凌驾“实质理性”或“价值理性”之趋势的认识,可说是从另一个角度讨论了马克思所谓的不“异化”问题。早在20世纪初期,卢卡奇、洛维特及兰茨胡特(Landshut)等人,即已注意到韦伯和马克思两者之间的共通处:他们的诠释,更影响到其后“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文化的诊断与批判。阿多诺、霍克海默著《启蒙的辩证法》,马尔库塞写作《单向度的人》和弗洛姆使用“逃避自由”的比喻,大量继承了韦伯和马克思的人文主义思想,只不过由于韦伯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将会被社会主义取代,这些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成员们大都立场鲜明地拥护马克思,同时批评韦伯在为资本主义辩护(Marcuse,1971)。1970年代开始,西方的“韦伯学”重新厘清了韦伯“理性化”概念的多重涵义,加上社会主义这一试图解决资本主义弊端的理想,在制度实现上暴露严重的“官僚化”问题,遂使“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的理论家摒除了对韦伯的政治成见,企图由韦伯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中撷取精华,进行更高层次的综合努力。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1981/1982)是此番尝试的代表作,他本人对“现代性”的反省剖析亦是近几年来关于“后现代”辩论的主题之一(Habermas,1985;Huyssen,1984)。身为当代的思想人物,哈贝马斯是否较他的前辈们更能够全面地掌握住“现代”的现象与本质?
四、现代社会的理性重建
1.哈贝马斯的诊断
从韦伯对西方发展经验的探索评估中,可以肯定的是西方“现代”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尤相应于资本主义的政经制度与生活方式,必须在西方的历史脉络下方能显现它们的内在逻辑的贡献,即在于他殚精竭虑提供了一套西方今天“之所以这样,而非别样”的解释模型,并就其可能性予以内在的批判。哈贝马斯的理论建构则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元理论式”(meta-theoretical)的主张,俾能根据某些判准来臧否现状(McCarthy,1982)。他批评“现代化理论”其实把韦伯对“现代”的具体陈述抽象化了,致使“现代化”似乎成为与时空条件没有必然关联的唯一社会发展模式(Habermas,1985:10)。但是,他也认为韦伯绝对化了西方“理性化”过程的进展方向,未能悟及基督新教伦理所反映的,仅只是片面特选的“理性化”面向,不足以穷尽此一概念。基于此,哈贝马斯回头检视“理性”的指涉意义,希望“正本清源”地理出创造现代文明物质基础的主导力量,问题是韦伯悲观地预言此种类型的理性将会不断膨胀,而不愿或无法追究人类“理性”中或有制衡的因子存在。哈贝马斯向来反对理性与实践(praxis)的截然划分(Habermas,1973),因此他在多年思索之后,正面提出了“沟通理性”(comnunicative rationality)来作为和“目的理性”相较量的行动依据。
据他的分析,“目的理性”导引出的目的-手段关系,纯粹以行动者己身利害为考量,属于“策略性行动”,缺乏超越功利目标的社会整合效果。现代社会在人际互动愈形密切的情况下,“目的理性”根本无从担当规范重建的迫切任务。“现代”的病征,对哈贝马斯来说,完全在过分迷信“目的理性”,殊不知如此一来,社会各子系统之间以及个别成员之间由于利害的冲突、资讯的垄断,必定充斥着受到扭曲的沟通。当西方社会演进到“后期资本主义”,政治势力大举介入一般经济和社会文化的行动领域,此时制度的结构和危机产生之形态亦跟着起变化。经济危机将连带引发政治系统中的合法性危机,进而转嫁到社会文化系统,增加规范上的混乱秩序,制造出社会成员普遍的动机危机(Habermas,1976)。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系针对现代社会层出不穷的整合与操纵问题而设计,目的在揭露光靠“策略性行动”无异治丝益棼,徒使主政者与社会大众充满无力感。不过,哈贝马斯在替“后期资本主义”危机的成因把脉之余,念念不忘的是师法马克思的实践观,要为现代社会的病态发展开一张标本兼治的药单。他在《沟通行动理论》下册中确认“现代性”的潜力仍未充分发挥,理由是选择性的西方“理性化”过程集中于系统的层面,却在无意间摧毁了人类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的共识根基——即承载行动意义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通过对于米德、涂尔干等人就符号、语言、意识之社会整合功能所作的申论,哈贝马斯归结出唯有重建“沟通理性”,以指向相互理解的“沟通行动”提升社会整体的学习能量(learning capacity),期使个人有更大的空间培育出成熟完整的“道德自主人格”(Habermas,1979)。他对现状的批判,因此围绕在“系统”施加于“生活世界”上的宰制与切割,极力主张生活世界内在的张力必须抗拒系统压迫过来的“殖民化”方不致堕入现代文化自设的悲剧陷阱。韦尔默曾阐释哈贝马斯的观点如下:
理性化的吊诡乃在于,生活世界之理性化本为系统理性化与分化的前提与起点,其后(系统)借助具现于生活世界的规范约制而愈趋自主,终致系统之指令(imperative)开始工具化生活世界,并威胁其存在。(Bernstein,1985:56)
由是可知,哈贝马斯更细致地描述了“理性化”不同的作用层次,试图在诊断病源后,赋予“生活世界”作为实践之着力点的角色。32当代社会理论中,哈贝马斯纵横融会了语言哲学、心理分析、诠释学、认知心理学以及现象学派、符号互动论、结构功能论等理论知识,独树一帜地构建起一套由个人道德意识到社会演化无所不包的庞大体系,堪称其探索之课题便展现了现代生活多元丰富的面向。而他所以大声疾呼“沟通理性”要在教育、政治民主和社会运动等行动领域落实规范性的导引效果,是懔于启蒙时代以来建设“理性社会”的理想一旦破灭,人类将无能驾驭现代科技与经济生产力结合所迸发出的宰制威力。他形容“现代”有若一“未完成的计划”,虽然漏洞百出,但曲折演化的成果并不应被轻易抹煞,因应于下阶段的发展,端赖人们力求“理性”的扩充而非窄化,方能确保“现代”予人类历史带来的是福祉,不是毁灭。
2.“现代性”的规范内涵——代结语
十九世纪的社会思想家们曾忧心忡忡地观察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冲击。在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概念中,属于旧秩序的宗教、道德维系力量正急速萎缩,而新秩序犹待建立,此时出现如涂尔干对失序(anomie)的关切,韦伯针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悲观预言,以及马克思提出的“异化”理论,在在反映了“现代”特有的内在紧张。今天,哈贝马斯仍然扣紧了富有批判精神的危机意识来反省人类的处境,但经过将近百年来历史演进,哈贝马斯能够更清楚地视“现代”为一个史无前例的、不断自我创新的“新时代”。这个时代的判准无法依靠过去的传统,只有从自身的经验中导出规范(Habermas,1985:15)。他从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和社会化三个层面分析了人类社会共同规范产生的条件:文化再生产保证了日常生活“有效知识”的一致性,亦即提供了作为共识基础的诠释图式(如语言、文字、符号等);社会整合关系到人际间正当且有规可循的协调合作,有助于团体认同感之凝结;社会化则教导新成员熟悉现实环境中之行为模式,使个人发展其自我认同并成为具有充分沟通互动能力的成熟个体(1985:398)。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生活世界中与规范有关的发展趋势呈现出几个特色,即原本有其安定性的知识内容不断受到修正或质疑:价值与规范朝向更普遍的明文形式(如法律);社会化的目标愈益塑造以自我实现为理想的极端个人主义。由于这些趋势具有结构上的强制性(1985:400),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必须借助互为主观的“沟通理性”作为媒介,适时适地达成共识的判断,而无法单纯以诉诸权威来解决。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看到哈贝马斯对“现代”的后续发展抱持着审慎的信心,和赶搭“后现代”列车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他似乎更努力去获致黑格尔所谓的“反省之经验”(Bernstein,1985:192),并尝试深入检讨“现代性”的限制及其补救之道。就社会实践的立场而言,哈贝马斯开“药方”或许未必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他的眼光放得更长远。他在总结对自黑格尔、尼采以降,西方思想家们环绕着“现代”这个论域所表达的反应时,语重心长地表示:
现代欧洲是为一个世界奠下了精神前提和物质基础,在此世界中某种心态(译按:指系统强制的自我膨胀)取代了理性(Vernunft)的位置——这乃是尼采开启之理性批判(Vernunftkritik)的真正重点。谁还会比欧洲更应该有能力由自身的传统出发,鼓起勇气、集中精力来重新发挥智慧——我们需要所有这些质素,以期能将长久以来盲目趋向系统维持与系统扩张强迫心态的前提消除掉。(Habermas,1985:425)
正如韦伯般,哈贝马斯同样强调“解铃还须系铃人”。但是起源于欧洲的“现代革命”早已席卷全球,没有一个非西方文化能自外于这场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庞大的“现代化”浪潮。当然,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过程有其十分模棱两可的内涵,“现代”在非西方社会的表现形式亦是五花八门,很难用单纯的理性/非理性二分法加以评估。毋宁说受到“现代”洗礼的非西方社会,所踏上的已是一条不归路,这中间夹杂着脱离传统脐带的痛苦、渴望改善生活的追求以及面对社会转型的迷惘等种种复杂矛盾的情感。我们今天听到自西方传来自我批判的声音,似乎在提醒正以“迈向现代化”为标榜的所有非西方社会,不要忘了“现代”的物质成就也会强索精神上的一定代价。“现代性”或可包容更多元化的理性成分,非西方社会实须以前车为鉴,及早省思自身社会的现实处境,未必得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的“发展”模式。既然西方与非西方在时间向度上已同属“现代”,为何不更海阔天空来共襄丰富“现代性”的盛举呢?毕竟“历史的宇宙座钟”并未宣告“现代”已匆匆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