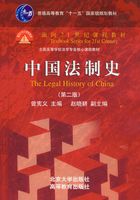
第一节 中国法律起源与夏代法制简况
一、中国法律起源
(一)夏奴隶制国家的产生
原始社会因历史条件所限,不可能产生带有阶级专政属性的国家,也不可能产生体现为国家形态的法律。人类社会只有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后,才能产生服务于统治阶级需要的国家与法律。中国和世界早期文明地区一样,在经过漫长的发展时期,以及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后,开始出现私有制,社会也开始分裂为对立的两大阶级,即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奴隶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激起奴隶阶级的不断反抗,这种对抗性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时,就需要建立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来加以调控,于是便产生了最初的国家。依据我国古代文献记述与考古发掘的实物证明,可以初步肯定,夏初(距今四千年左右)已具有国家产生的基本特征。“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 。传说大禹王在会稽之山大会部落首领,防风部落酋长因迟到,被大禹处死而且碎尸
。传说大禹王在会稽之山大会部落首领,防风部落酋长因迟到,被大禹处死而且碎尸 。这表明大禹王已形成凌驾于其他部落之上的“公共权力”。这种权力的基础,在于他已掌握一支强大的武装部队。据《尚书·费誓》正义引《世本》说:夏王少康之子杼,已经制造出铠甲。《越绝书·记宝剑》载:大禹时期,开始用铜制造兵器。另外,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其前期相当于夏代。从这一时期出土的遗物里发现有我国最早的青铜武器,诸如弋、戚、箭镞等。这进一步证实夏初已具有用金属武器装备的精锐武装。此外,据有关文献记载,这一时期还产生了奴隶制国家实体附属物——诸如司法机构与监狱等强制机关。
。这表明大禹王已形成凌驾于其他部落之上的“公共权力”。这种权力的基础,在于他已掌握一支强大的武装部队。据《尚书·费誓》正义引《世本》说:夏王少康之子杼,已经制造出铠甲。《越绝书·记宝剑》载:大禹时期,开始用铜制造兵器。另外,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其前期相当于夏代。从这一时期出土的遗物里发现有我国最早的青铜武器,诸如弋、戚、箭镞等。这进一步证实夏初已具有用金属武器装备的精锐武装。此外,据有关文献记载,这一时期还产生了奴隶制国家实体附属物——诸如司法机构与监狱等强制机关。
在禹死后,其子启打破氏族禅让的传统,承继大禹王位,建立起奴隶制专制国家,实现了“家天下”的君王世袭制。原始共产制度被奴隶主国家制度所代替,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即依照夏王的世系延续下来的奴隶主阶级统治的时代。
(二)原始习惯到奴隶制习惯法的转变
法同国家一样,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都有自身存在的必要条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 的反映。原始社会虽不能产生体现为国家形态的法,但却产生了法的胚胎形态——氏族习惯。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的起源,实质上是氏族习惯向奴隶制习惯法的质变过程。
的反映。原始社会虽不能产生体现为国家形态的法,但却产生了法的胚胎形态——氏族习惯。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的起源,实质上是氏族习惯向奴隶制习惯法的质变过程。
距今约有五千年的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父权制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化、氏族习惯向奴隶制习惯法转化的重要时期。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大体相当于这个时期。
原始社会的任何进展,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父权制替代母权制,同样说明了这个道理。父权制与母权制相比,物质生产有了新的发展。最有代表性的,是当时冶铜业的发生。据《越绝书·记宝剑》载:“禹穴之时,以铜为兵”。这是古代典籍中最早反映父权制时代冶铜业发生的文字记述。这种记述还可以从考古发掘中得到印证。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河北唐山大城山遗址,发掘出两块红铜牌;甘肃武威皇娘娘台、临夏大河庄和秦魏家等齐家文化遗址中,都普遍地发现有红铜器 。因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的人们还不可能大规模地发展冶铜业,也不可能将金属工具广泛地应用到各个生产领域。但冶铜业的出现,却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日后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提供了重要条件。
。因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的人们还不可能大规模地发展冶铜业,也不可能将金属工具广泛地应用到各个生产领域。但冶铜业的出现,却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日后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提供了重要条件。
与此同时,父权制时代进一步改进了石制工具,制造了磨制扁平的石铲、磨光穿孔的石刀、装有木柄的石镰等 。生产工具的改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为社会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剩余粮食。农业生产的提高,促进了畜牧业与手工业的发展。陕县庙底沟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二十六个废坑中,发掘的家畜遗骨,比同地仰韶文化遗址一百六十八个废坑中所出土的总和还要多,反映了当时畜牧业发展的状况。在手工业方面,从考古发掘来看,已有相当的发展。陕县庙底沟、长安客省庄、邯郸涧沟等龙山文化遗址中,相继发现规模较大的陶窑,以及刻画精细、品种繁多的陶器
。生产工具的改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为社会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剩余粮食。农业生产的提高,促进了畜牧业与手工业的发展。陕县庙底沟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二十六个废坑中,发掘的家畜遗骨,比同地仰韶文化遗址一百六十八个废坑中所出土的总和还要多,反映了当时畜牧业发展的状况。在手工业方面,从考古发掘来看,已有相当的发展。陕县庙底沟、长安客省庄、邯郸涧沟等龙山文化遗址中,相继发现规模较大的陶窑,以及刻画精细、品种繁多的陶器 ,反映了当时制陶业的水平。此外,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中,发掘出以粗麻为原料而织成的平纹细麻布
,反映了当时制陶业的水平。此外,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中,发掘出以粗麻为原料而织成的平纹细麻布 ;南京北阴阳营青莲岗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近三千件玉及玛瑙饰物
;南京北阴阳营青莲岗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近三千件玉及玛瑙饰物 。
。
父系氏族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不仅为社会提供了剩余产品,也为私有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首先,剩余产品的增多,促进了农业、畜牧业与手工业的社会分工,产生了以直接交换为目的的简单商品经济。史书记载颛顼时期有“祝融作市” ,尧舜时,“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
,尧舜时,“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 。这种说法虽不全为事实,但它反映了部落与部落、氏族与氏族、个人同个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已有明显发展。
。这种说法虽不全为事实,但它反映了部落与部落、氏族与氏族、个人同个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已有明显发展。
随着父权制社会的发展,商品交换与个人财富的聚集日益增强,并最终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与阶级的分化,以及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不平等关系。与此相适应,氏族习惯的内容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按照母权制习惯,死者墓地的选样,以及安葬等,都由氏族公共组织按一定的规格统一组织成员进行,不容稍有逾越。私有制与阶级分化产生以后,则允许按照死者生前的地位与财富的多寡,选择墓地与安葬方式。泰安大汶口遗址的穷人墓地,远离公共墓地中心,墓坑窄小,随葬物也少,有的甚至根本没有随葬品。而地位显赫的富人,其墓地一般位于公共墓地的中心,墓坑宽大,棺椁讲究,随葬物品也多而精美,最多的有一百八十余件 。这表明父权制习惯中已出现维护私有制与不平等关系的新内容。
。这表明父权制习惯中已出现维护私有制与不平等关系的新内容。
父权制习惯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确认部落联盟酋长的权威地位。《尚书·尧典》有“(虞舜)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的记载。《国语·鲁语》也有“禹朝诸侯于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的记述。文献中记载的这类传说,反映了氏族习惯的某些变化,即不但确认部落联盟酋长的权威地位,而且赋予他们临事处置的大权。这类习惯到奴隶制确立以后,则被改造成为维护君主专制的习惯法。
(2)确认保护私有财产的习惯。父权制社会逐步改变了母权制的平均分配传统,规定个人所获猎物为自己私有财产,不归集体分配。此外,氏族公社的公有财产以及集体掠获其他部落的财产,按照父权制的习惯,氏族首领与部落联盟酋长可以取得超出常人的更多份额,不再实行平均分配。至于他们利用职务侵吞公有财物,随意处置掠获财物已变成普遍现象。《管子·揆度》有关尧舜将掠获的“粟与其财物”出手转卖,“以市虎豹之皮”的记述,即反映了这种情况。
(3)确认有关处罚的习惯。原始社会的舜禹统治时期,特别是大禹统治的时代,氏族公社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不单部落联盟制、军事民主制发展到高峰,有关处罚的习惯也发展到顶点。根据文献记载,这一时期确立了不少有关处罚的习惯。《尚书·舜典》载有“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竹书纪年》说:“帝舜三年命皋陶作刑”。《新语·道基》说:“皋陶乃立狱制罪,悬赏设罚,异是非,明好恶,栓奸邪,消佚乱,民知畏法。”另据《左传·昭公十四年》引《夏书》说:“昏(劫掠)、墨(贪赃)、贼(杀人不忌)杀,皋陶之刑也。”原为黄淮地域部落首领的皋陶,做了联盟机关的“士”职(掌管审断的职位),所以,规定处罚习惯的任务,自然落到他的身上,但仍须征得舜的同意方能实行。
因史书的记载既有当时情况的反映,又有后人附会的成分,故应作分析说明。首先,这里出现了“刑”、“法”、“罪”等概念。以“刑”而论,上古时有两种写法:即“ ”与“ ”。《说文解字》刀部说:“
”。《说文解字》刀部说:“ ,刭也”,即单纯的杀戮。《说文解字》井部解释:,“罚罪也”,即带有惩罚犯罪的含义。诸如“刭”一类的杀戮,在原始社会后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舜典》说虞舜时代有“刑”的出现,是可信的。至于带有“罚罪”性质的“ ”,显然是奴隶制国家为区别原始时代的“刑”而另行别设的。后人将两者通用了,而当初确有质的差别。
,刭也”,即单纯的杀戮。《说文解字》井部解释:,“罚罪也”,即带有惩罚犯罪的含义。诸如“刭”一类的杀戮,在原始社会后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舜典》说虞舜时代有“刑”的出现,是可信的。至于带有“罚罪”性质的“ ”,显然是奴隶制国家为区别原始时代的“刑”而另行别设的。后人将两者通用了,而当初确有质的差别。
“法”在古代也有两种写法:即“佱”与“灋”,前者先于后者出现。《尔雅·释诂》说:“法”,首先是“常也”。所谓皋陶“制法”,不过是制定常行的处罚习惯。“灋”按《说文解字》解释,带有“平之如水”与明断罪与非罪的含义,这显然是奴隶制国家产生后,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而后创的。西周康王时的《大盂鼎铭》就有“灋保先王”的铭文。
《说文解字》又说:“罪,捕鱼竹网”,即说罪最早源于“网”,设网的目的在于防止漏鱼。舜禹时期的“制罪”,就是为“奸邪”行为构筑罗网,以便“异是非”、“明好恶”、“消佚乱”,而不具有阶级社会中“罪”的犯法含义。
值得一提的是,皋陶在规定处罚习惯时,把贪赃(墨)行为与劫掠(昏)、杀人行为并列,一并处罚。它反映了部落联盟机关约束职事人员,严厉制裁渎职、贪污行为的意图。
据蔡枢衡先生考证,“眚,灾,肆,赦;怙,终,贼刑”,这段《舜典》的记叙,是真实可信的 。这段文字反映了舜统治前后氏族习惯有关处罚的原则。“眚”(音省),指过失;“灾”,指不可抗御的自然灾害;肆,则指因饥饿而捕食杀人的,可以实行减免处罚的原则。“怙”是故意,“终”是一贯,此类杀人行为,则适用严厉处罚的原则,一律处死。这些原则的出现,反映了父权制处罚习惯的发展。到奴隶制确立后,又被发展成为习惯法的刑法适用原则。
。这段文字反映了舜统治前后氏族习惯有关处罚的原则。“眚”(音省),指过失;“灾”,指不可抗御的自然灾害;肆,则指因饥饿而捕食杀人的,可以实行减免处罚的原则。“怙”是故意,“终”是一贯,此类杀人行为,则适用严厉处罚的原则,一律处死。这些原则的出现,反映了父权制处罚习惯的发展。到奴隶制确立后,又被发展成为习惯法的刑法适用原则。
《舜典》所说的五刑,特别是“金作赎刑”,实际上到西周末年吕侯制《吕刑》时才真正出现,所以,有关“刑”的记载是不大可靠的。《尚书·吕刑》在一般学者看来是比较可信的。它对于原始社会后期的处罚方式作了这样的说明:“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爰始淫为劓、刵(去耳)、椓、黥”。又据《后汉书·刑法志》说:“(禹)自以德衰而制肉刑。”前者说明苗人部族是较为先进的部族,较早规定了处罚的方式;后者说明禹承舜位后,才规定了处罚方式。据史书记载,禹在位时曾三伐苗人,禹时的处罚方式很可能是从苗人那里学来的。所谓“五虐之刑”,主要指:黥(面上刺字)、劓(割鼻)、刵(去耳)、椓(破坏生殖器官)、处死五种。这五种处罚方式,到奴隶制社会以后,则演变为墨(同黥)、劓、剕(去脚)、宫(同椓)、大辟(死刑)等奴隶制刑罚体系。
需要指出,上述几个方面只是父权制习惯的变化内容,而不是氏族习惯的全部内容。以这些变化了的内容而论,它们已具有法的胚胎性质,但又没有脱离习惯的范畴,更不可能成为国家形态的法。尽管如此,它们的出现却预示着奴隶制习惯法统治的时代即将到来。
(三)习惯法的产生
大量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证实,夏代已经产生奴隶制国家和体现着奴隶主阶级意志的习惯法。
河南阳城地望与登封县告成镇发掘出两座东西相连的夯土城堡遗址,告成镇还出土了青铜器的残片。这些都是夏代早期的文物。据碳素测定,其年代距今为四千年左右 。河南夯土城堡是夏奴隶制国家诞生的标志,青铜器则是夏奴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标志。正如恩格斯早已指出的:“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深壕宽堑成了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河南夯土城堡是夏奴隶制国家诞生的标志,青铜器则是夏奴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标志。正如恩格斯早已指出的:“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深壕宽堑成了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公元前21世纪,是夏奴隶制国家的形成时期。自此,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恩格斯正确指出:“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 “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夏启承禹以后,建立夏王朝,用王位世袭制取代氏族禅让制,给原始公社制度以致命打击,并导致它的最终解体。启称王后,沿袭禹的传统,将所辖地区划分为九州,即所谓“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 。与此同时,夏奴隶制国家把夏邑作为统治的中心,并按地区的不同部署原有的部落,建立了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武装力量与管理国家的整个官僚体制,如《礼记·明堂位》所说:“夏后氏官百”。此外,还建立了作为国家实体附属物的监狱等强制机关。这一切表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在夏代已经形成。
。与此同时,夏奴隶制国家把夏邑作为统治的中心,并按地区的不同部署原有的部落,建立了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武装力量与管理国家的整个官僚体制,如《礼记·明堂位》所说:“夏后氏官百”。此外,还建立了作为国家实体附属物的监狱等强制机关。这一切表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在夏代已经形成。
伴随夏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奴隶制习惯法也同时孕育而生。夏代法律的起源,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奴隶制的确立,引起社会制度的剧烈变化,以及旧的传统势力的强烈反抗。据史书记载,东夷部族的首领伯益以及与夏同姓的有扈氏部族都曾起兵反抗。奴隶主阶级的残酷压榨与剥削,又造成平民的“不服”,以及奴隶们的“作乱”。在社会矛盾激化、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势下,夏代统治者在军事镇压的同时,不得不借助于法律,以维护君主专制的统治。
但因夏奴隶制国家初建,没有立即制定较完备的法律制度,只是将有利于奴隶主阶级的氏族习惯,赋以新的性质,上升为国家形态的习惯法。在夏代,习惯法占据主导地位。《左传·昭公六年》所谓的“夏有乱政,而作禹刑”,一方面说明夏代借用大禹的威望,增强其法律的威慑力量;另一方面说明,夏代法律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舜禹时代氏族习惯的部分内容。此外,适应阶级斗争与社会斗争的形势,夏代统治者还颁布了一些单行的命令,如《甘誓》等。总之,处于形成期的夏代习惯法,还是比较简单的,它的完善则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四)中国法律起源的特点
第一,中国法律产生于古代中国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它的法律起源具有独自的特点,即实行礼法结合。
夏代法律在形成中,不仅改造和吸收了父权制时代的某些习惯,也改造和吸收了原始社会沿用已久的“礼”的传统,从而实现了中国奴隶制最初的礼法结合。将奴隶主阶级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结合使用,是其他国家与法律形成时所不具备的。这种特点的形成,不但有古代中国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文化、民族习惯等方面的原因。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华民族既重礼仪又重法治的历史传统。夏王朝将礼法结合,凭借礼的精神统治力量强化法的镇压职能,依靠法的强制力推行礼的规范,从而为统治阶级构筑了严密的统治罗网,并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第二,中国法律在形成时具有早熟性。
同东方早期文明国家一样,夏王朝提前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形成了最初的国家与法。因此,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具有法律的早熟性。
第三,中国法律在形成时带有维护专制王权的特点。
自夏奴隶制国家产生以来,就实行“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政策,从而造成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稳步发展,以及商品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因此,在夏代社会中不可能产生与王权和宗法统治相抗衡的工商业奴隶主阶级以及相对独立的市民阶层,更不可能像雅典国家那样实行奴隶主民主制,而只能产生君主专制制度与维护专制王权的奴隶制法律。夏代法律维护专制王权,反映了奴隶制法的本质特点。这一特点经商、周一直遗传到封建时代,使得古代中国的法律日益君主专制化。
第四,因自然经济的稳固,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加之过早确立君主专制制度以及礼的规范的发展,使中国法律在形成时,就带有刑事法规发达而民事法规相对落后的特点。
夏王朝一建立,统治者便把礼摆到重要位置,无论在民事法律关系方面,还是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礼都起到了民事法规的实际调整作用。由于礼的作用增强,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使得民事法律规范在形成期的夏代法律中居于次要地位,没有发展到相应的水平。相反,为维护专制王权以及种族奴隶制的严酷统治,镇压被奴役的部族和平民、奴隶的剧烈反抗,以夏王为代表的宗族奴隶主阶级,十分重视习惯法中的刑法内容,并陆续颁布了一些简单的刑事法规,用以稳固奴隶制国家政权。这使得刑法内容在形成期的夏代法律中居于重要地位。
第五,由于夏代提早跨入阶级社会,奴隶制未能充分发展,所以,它的法律在形成时带有氏族社会的浓厚色彩,以及贵族宗法统治的显著特点。
夏王朝是早期奴隶制国家。尽管按照地域大致部署了原有的部落,但它并未彻底瓦解以血缘为纽带的贵族宗法统治关系。相反,以承认夏启统治地位为前提,把姒氏族(夏族的姓氏)以及与其有同盟关系的各氏族,按照新的宗法制度,变相地保留下来。因此,维护原有宗法关系的氏族习惯,也相应地转化为维护奴隶主贵族的习惯法。实行家国相通、亲贵合一的夏王朝,君主启是所有臣民的最高家长,各贵族又是各家族的家长,并任有官职。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夏代法律,也必然肩负二位一体的职能,亦即维护奴隶制国家制度与宗法制的统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中国法律在形成时必然带有氏族社会的浓厚色彩,以及种族奴隶制、宗法制的鲜明特点。
二、夏代法制简况
(一)法律形式
1.习惯法
夏代建立之初,习惯法成为当时法律的主要表现形式。因为当时不具备制定系统成文法的条件,更谈不到以成文法替代习惯法。相反,对于夏代统治集团来说,将传袭已久的有利于统治的原始习惯加以筛选补充,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变为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习惯法,而且对被压迫的平民与奴隶具有较大的迷惑性与欺骗性。这其中最明显不过的是,把原始社会的祭祀鬼神的“礼”,改造成为奴隶主阶级实施法律统治的工具。夏代习惯法统治方式,是中国阶级社会诞生以来最早出现的最为简陋的统治方式。这种统治方式的落后性,是由生产力水平低下以及立法技术的落后所决定的。
2.制定法
夏代统治期间,在沿袭习惯法的同时,也出现了制定法。《左传·昭公六年》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就是统治阶级适应形势需要,加速制定法出台的反映。
3.誓
誓是夏代君主在战争期间发布的紧急军事命令。正如《尚书·甘誓》所载:夏启在平息有扈氏叛乱时,曾于甘地发布“誓”,以此约束全体从征人员。
(二)法律内容
夏代法律,被后世典籍笼统称为“禹刑”。这里的“禹刑”不再专指夏代的制定法,而泛指夏代的所有法律。以下从几方面简略加以说明:
1.将原始社会的礼改造成为法律统治的有效武器
以习惯法为基本表现形式的夏代法律,虽渊源于氏族习惯,却与后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经过奴隶主阶级的改造,夏礼被赋予新的意志与内容,成为保护专制王权和奴隶制国家,以及维护奴隶社会秩序的有效武器。
礼最早起源于氏族社会,是原始人类祭祀鬼神祖宗求得赐福而举行的仪式活动。如史书所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 “礼之名起于事神,引申为凡礼仪之称”
; “礼之名起于事神,引申为凡礼仪之称” 。在愚昧落后的原始社会,适逢重要节日,都由氏族首领组织全体成员,为鬼神、祖宗神举行祭祀活动,礼成为体现全体氏族成员意志的行为规范。
。在愚昧落后的原始社会,适逢重要节日,都由氏族首领组织全体成员,为鬼神、祖宗神举行祭祀活动,礼成为体现全体氏族成员意志的行为规范。
夏启建立奴隶制国家以后,在神权政治法律思想的支配下,将改造后的“夏礼”与国家的重要活动结合起来;并赋予新的阶级属性和法律效力,从而变为奴隶制国家法律统治的有效武器。《论语·为政》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由此不难看出,夏代不但早已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礼,而且对殷周的“礼法结合”产生了重要影响。夏王朝为巩固新生的奴隶制政权,不仅需要大力提倡“忠君”的观念,而且还要倡导“孝”的思想,以便使“忠孝合一”,共同维护奴隶制国家制度与宗法制度的统一。为此,规定了“不孝”罪,并列为从严打击的对象。
2.法律维护专制王权,镇压各种违背“王命”和反抗国家统治的行为
夏代统治者出于维护专制王权的需要,首先将维护部落联盟酋长权威地位的习惯,改变为巩固君权的习惯法,用以维护夏王在行政、立法与司法上的统治地位。夏启在征伐有扈氏而发布的《甘誓》中规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止,汝不恭命”, “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即对从征人员不从“王命”者,一律处死在祖庙前,并且株连妻、子,罚作祭坛上的牺牲。法律完全变为君主专制的工具,以至言出法随,臣僚犯罪者无一幸免。
此外,应当指出:自夏代建立第一个奴隶制国家起,我国古代社会一直坚持以刑为主的法律体系。法律不但凭借严酷的刑罚手段惩办危及王权统治的政治性犯罪,同时也严厉制裁破坏国家统治、扰乱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诸如此类的法律规定,既来源于对氏族习惯的改造,又源于统治者适应形势发展制定的简单刑事法规,以便对习惯法的规定不足加以补充。据《吕氏春秋·先识览》载:“夏之将亡,太史令佟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先奔于商”。这里所说的“图法”,极有可能是夏代以图形文字为表述方式的简单刑事法规。这类刑事法律规范,只能是刑事镇压经验的简单概括,而不可能系统成熟。《唐律疏议》引《尚书大传》说:“夏刑三千条。”《周礼·秋官·司法》郑注说:“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笔者认为,说夏代刑书有三千条之多,显然是主观臆断,并不符实。但是,如果说夏代产生了最初的刑事法律规范,却不无道理。
夏代为有效镇压反抗奴隶主国家统治与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承袭并发展了舜禹时代习惯处罚方式,从而初步确立了奴隶制五刑制度。即墨、劓、剕、宫、大辟。据《左传》引《夏书》说:“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昏是“恶而掠美”,墨是“贪以败官”,贼是“杀人无忌”,夏代因袭皋陶之法,将此三种罪都处以死刑。当时的刑法执行情况,在现今河南二里头夏代残存遗址中有明显反映。在这些夏代墓穴遗址中,既有生前被碎尸而后被下葬的,又有死前被砍下头颅而后埋葬的,这显然是惩办严重刑事犯罪而执行大辟刑的反映。另外,在夏代墓穴遗址中,还有被砍去四肢的尸体,这是夏代执行剕刑的反映。
此外,夏王朝为巩固奴隶主阶级的长久统治,又承袭了舜禹时期流传已久的习惯处罚原则。即如《尚书·大禹谟》所载:“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此后,又于《夏书》中得到进一步肯定 。出于标榜“慎刑”的考虑,夏统治者宣称:宁可不按禹刑审案,也不能错杀无辜。这一原则的实施,对商、周乃至整个封建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出于标榜“慎刑”的考虑,夏统治者宣称:宁可不按禹刑审案,也不能错杀无辜。这一原则的实施,对商、周乃至整个封建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3.规定带有行政法规性质的《政典》,用以维护奴隶主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据《尚书·胤征》注云:“‘政典’夏后为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实际上,初建奴隶制的夏王朝,还不可能制定出一部类似《周礼》那样的包罗万象的行政法规大全。它的《政典》极有可能是简单的单行行政法规。《尚书·胤征》曾援引《夏典》说:“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杀无赦。”即对违背天时懈怠政令的官吏实行“杀无赦”的原则。夏代《政典》的制定,一方面说明,中国自有国家产生,就非常重视行政法律规范的建设,以此维护奴隶主阶级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又说明,我国古代行政法规一问世,就采取刑事处罚的方式,惩治渎职与失职的官吏,从而反映了我国自古即有的“依法治吏”的悠久传统。
4.确认土地“国有”的民法内容
夏代更改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度,确立土地奴隶主国家所有制。因为,夏王是奴隶制国家的象征,所谓的土地国有制,实际上就是王权所有制。按照夏代法律规定,王掌管全国的田土,享有充分的所有权。王可以分封或赏赐贵族功臣以土地,但他们只享有占有和使用权。这些土地归于国家所有的民法内容又直接影响了商、周两代,成为我国奴隶制时代通行的土地所有权的原则。
5.确认征收赋税的各项制度
夏代出于统治的实际需要,在其法律规范中也规定了一些调整经济关系的带有经济法规性质的内容。据《史记·夏本纪》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孟子·滕文公》也载:“夏后氏五十而贡”。这些记述表明,我国奴隶制国家建立后,曾经及时采取法律形式确立国有赋税制度。即以五十亩地为计量单位,并取其平均产值的十分之一,作为向国家缴纳的贡赋。
(三)司法制度
1.司法机关和审判制度
夏代中央最高司法官称“大理”,地方司法官称“士”,基层则称“蒙士”。他们分别掌管夏代中央、地方乃至基层的司法审判工作。
许慎《说文解字》说:“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 (音志)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
(音志)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 去”; “
去”; “ ……兽也,似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者”。以
……兽也,似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者”。以 触不直的神判方式,传说早在皋陶作“士”时就已经使用过。到夏代奴隶阶级统治时期,“
触不直的神判方式,传说早在皋陶作“士”时就已经使用过。到夏代奴隶阶级统治时期,“ ”字继续被用来宣扬以“
”字继续被用来宣扬以“ ”兽代天审判行罚的迷信,从中也多少反映了氏族神明裁判在早期奴隶制国家审判活动中的残余影响。夏代统治者在审判活动中,大肆宣传神兽“代天审判”与“代天行罚”的思想,是出于增强奴隶制国家审判的威慑力,以及强化司法镇压,巩固专制统治的实际需要。
”兽代天审判行罚的迷信,从中也多少反映了氏族神明裁判在早期奴隶制国家审判活动中的残余影响。夏代统治者在审判活动中,大肆宣传神兽“代天审判”与“代天行罚”的思想,是出于增强奴隶制国家审判的威慑力,以及强化司法镇压,巩固专制统治的实际需要。
2.监狱的设置
据《竹书纪年》载:“夏帝芬三十六年作圜土”。《史记·夏本纪》也有夏桀囚禁商汤于夏台的记载。夏代称监狱为“圜(音圆)土”。“圜者,圆也”,即用土构筑圆形监狱以关押人犯。上述记述表明,夏奴隶制国家建立后,不仅设置司法机关规定审判制度,还建立了最初的监狱制度。尽管监狱机构还相当粗疏简陋,但毕竟为商周的健全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