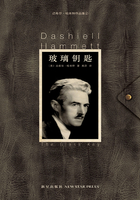
第2章 唐人街的尸体
1
两颗绿色骰子滚过同色的桌面,撞上了凸起的桌沿后又弹了回去。一颗很快停住,亮出排成两行的六个白点;另一颗滚到桌面中央才停下,上头只有一点。
“啊——”内德·博蒙特含糊地咕哝了一声,而赢家们把桌上的钱一扫而空。
哈里·斯洛斯拿起骰子,在苍白多毛的大手里把玩着。“下两注。”他往赌桌上扔了一张二十元和一张五元的纸钞。
内德·博蒙特抽身退下。“轮到他了,赌徒们,我得去补充赌本。”他说完穿过台球室走向门边,正好碰上要进门的沃尔特·伊万斯。内德说了一句“沃尔特,你好”,就打算继续走,但伊万斯在他经过时一把拉住他的胳膊肘,转过脸看着他。
“你……你……你跟保……保……保罗谈过吗?”说“保……保……保罗”的时候,星星点点的唾沫从伊万斯的嘴里喷溅了出来。
“我正要上楼去看他。”
伊万斯那张漂亮的圆脸上的瓷蓝色眼睛顿时一亮,直到内德·博蒙特眯起眼睛又说:“如果你没什么耐心的话,就别期待太多。”
伊万斯的下颌抽搐了一下。“但……但……但是她下个月就要生小……小……小孩了。”
惊讶的神色自内德·博蒙特的暗色眼睛里一掠而过。他将胳膊从那个比自己矮的男人手里抽出来,往后退了几步,深色小胡子下的嘴角歪向一边,开口说道:“沃尔特,现在时机不妙,而且——总之,你最好别盼着十一月前能解决,免得失望。”说完,他的眼睛再度眯了起来,审视着对方。
“但……但……但是如果你告……告诉他……”
“我会尽量催他。而你也应该明白,他会尽力的,只不过他现在处于一个艰难的时刻。”他晃了晃肩,脸色也暗淡下来,但眼中依然闪烁着警戒的光芒。
伊万斯舔着嘴唇,拼命地眨着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伸出双手拍了拍内德·博蒙特的胸膛。“你快上……上……上去吧。”他催促着,声音中带着恳求,“我……我……我在这里等……等你。”
2
内德·博蒙特在上楼的时候点着了一根有绿斑点的细雪茄。到了墙上挂着州长画像的二楼楼梯口处,他转向建筑的临街面,敲了敲走廊尽头那扇紧闭的厚橡木门。
一听到保罗·马兹维说“进来”,他就打开门走了进去。保罗·马兹维一个人在房间里,正双手插着裤兜站在窗前,背对着门,透过窗帘俯视楼下昏暗的唐人街。
“唔,你来了。”他缓缓地转过身来。保罗·马兹维四十五岁,与内德·博蒙特身量相仿,但多了四十磅精实的肌肉。他发色浅亮,中分头梳得服服帖帖;脸庞红润、轮廓坚毅,可以称得上英俊。他的衣装质地优良,仪表严整,因此毫无浮夸之嫌。
“借我一点钱。”内德·博蒙特关上门后开了口。
“多少?”马兹维从上装内兜里摸出了一个棕色的大钱包。
“两百。”
“赌输了?”马兹维给了他一张一百美元的支票和五张二十块的现钞。
“谢了,”内德·博蒙特把钱收好,“是啊。”
“你有一阵子没赢什么钱了,对吧?”马兹维把手收回裤袋的时候这样问。
“没那么久——一个月或者六星期而已。”
马兹维微笑了起来。“输钱的话,就算久了。”
“对我来说可不算。”内德·博蒙特的声音里有隐隐约约的怒气。
马兹维翻搅着口袋里的一堆硬币。“今晚赌得大吗?”他倚上了桌角,然后低头看着脚上铮亮的棕色皮鞋。
内德·博蒙特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金发男人,然后摇摇头说:“小意思。”他走向窗边,街对面的楼群之上天色昏沉。他与马兹维擦身而过,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个号码。“喂,伯尼,我是内德。佩吉·欧图尔现在的赔率是多少?就这么点儿?……好吧,每个替我押五百……好……我敢说肯定会下雨,那样的话,她就能击败‘焚化炉’了……行啊,到时候再告诉我赔率……嗯。”
他挂断电话,又转回到马兹维眼前。
“既然手气这么背,怎么不歇一阵子呢?”马兹维问他。
内德·博蒙特皱起眉头。“那没用,只会接着倒霉下去。我应该把一千五百块全押在一匹马上,而不是分开押。说不定扛过一次大的,眼下的霉运就到头了。”
马兹维低低地笑着抬起头来。“那也得你能扛得起啊。”
内德·博蒙特嘴角一垂,髭角也跟着耷拉下去。“只要是落到我头上的,什么我都扛得住。”他这么说着,走向了房门。
“我觉得你准可以,内德。”手握住门钮的时候他听见马兹维语气诚恳地说。
他转过身来。“可以怎样?”他不耐烦地问。
马兹维掉转了视线盯着窗外。“可以面对任何事。”
内德·博蒙特研究着马兹维闪避的神色,金发男人又开始不自然地摩挲着口袋里的钱币。内德扮出茫然的眼神,用十足迷惑的口气问:“你说的是谁?”
马兹维脸红了。他离开了桌子,朝内德·博蒙特迈了一步。
“你去死吧。”他说。
内德·博蒙特笑出了声。
马兹维也腼腆地笑了起来,掏出一条镶绿边的手帕擦了擦脸。“你最近为什么都不去我家?”他问,“妈妈昨天晚上还说她都一个月没看到你了。”
“这星期我大概会找个晚上过去。”
马兹维收起了他的手帕。“你应该来。你知道妈有多么喜欢你。来吃个晚饭嘛。”
内德·博蒙特再次走向房门,步子缓慢,一边眼角的余光注视着金发男人。
“你想见我就是为这件事?”手放在门把手上时他问道。
马兹维锁起了眉头。
“嗯,就是——”他清了清喉咙,“呃……啊,还有别的事。”他忽然收起了怯懦的表情,变得十分平静而自制,“星期四是亨利小姐的生日,你看我该送她什么?这种事情你比我懂得多。”
内德·博蒙特放开了门把手。等到转身面对着马兹维的时候,他已经藏起了震惊的眼神。他喷了口雪茄烟,开口问道:“他们要搞生日活动什么的,对吧?”
“对。”
“邀了你?”
马兹维摇摇头。“但明天晚上我会过去吃晚饭。”
内德·博蒙特瞥了一下手中的雪茄,然后再度抬眼看着马兹维的脸。
“保罗,你打算支持参议员吗?”他问。
“我想我们会。”
“为什么?”说这话时内德·博蒙特的声调十分柔和,他的笑意也一样。
马兹维也微笑了。“因为有我们帮助他,他才能击垮罗恩;而有了他支持我们,我们就可以压倒其他候选人,所向无敌。”
内德·博蒙特把雪茄塞回嘴里,继续轻声问道:“没有你——”他特别强调了“你”这个字,“——的支持,那位参议员这次选得上吗?”
“绝无可能。”马兹维冷静而肯定地回答。
内德·博蒙特沉吟了一会儿,又问:“他明白这一点吗?”
“他应当比谁都明白。而如果他不——这又关你什么事?”
内德·博蒙特冷笑了一声。“如果他不明白,”他意味深长地说,“你明天晚上就不过去吃晚饭了吗?”
马兹维皱起眉头,又问了一次:“这他妈的到底关你什么事?”
内德·博蒙特取出嘴里的雪茄,雪茄头已经被他咬裂了。“完全不关我的事。”他说着,脸上带着思虑的神色,“但你觉得其他候选人就不需要他的支持吗?”
“没人能得到专一的支持,”马兹维谨慎地回答,“不过即使没有他的支援,我们还是能搞得定的。”
“你承诺过他什么吗?”
马兹维的嘴唇扭曲了。“差不多敲定了。”
内德·博蒙特的脸色苍白。他垂下头,直到他得抬眼向上看着金发男人。“撇下他别管了,保罗,”他压低嗓子,声音嘶哑,“让他输。”
“哎,要真这么干我就见鬼了!”马兹维双手握拳搁在臀后,疑虑地轻声说道。
内德·博蒙特走过马兹维身边,用细瘦的手指颤抖着把雪茄按熄在桌上的铜铸烟灰缸里。
马兹维瞪视着这个比他年轻的人,直到他直起身子转过来。然后,金发的男人半是亲热半是恼怒地冲着他咧嘴笑了。“你犯了什么毛病啊,内德?”他抱怨道,“这么久以来你都没意见,然后没来由地丢出这个炸弹。如果我能搞懂你,那才见鬼呢!”
内德·博蒙特嫌恶地做了个鬼脸。“好吧,忘了我说的。”紧接着他又掷出一个疑问,“你觉得他连任成功后,还会买你的账吗?”
马兹维并不担忧。“我治得了他。”
“也许吧,不过别忘了,他这辈子还没做过亏本生意呢。”
马兹维毫无异议地颔首。“当然,而那就是我跟他合作的最佳理由之一。”
“不,保罗,不是,”内德·博蒙特认真地说,“那是最糟糕的理由。就算想破脑袋,你也得好好盘算一下。他那个没大脑的金发女儿对你的影响力有多大?”
“我要娶亨利小姐。”马兹维说。
内德·博蒙特做了个吹口哨的样子。“这也包括在你们的协议里?”他眯起眼睛问。
马兹维孩子气地笑了。“别人不知道,”他回答,“就你和我。”
血色星星点点地泛上了内德·博蒙特瘦削的脸颊,他尽可能地让自己笑得和善可亲。“我可绝不会四处宣扬这事儿,但你得听我一句劝。你想要什么,就得让他们写成白纸黑字,再找个公证人宣誓,而且要付押金。或者,最好是坚持在选举前举行婚礼。这么一来,至少不会丢掉你应得的那磅肉——她的话,可有大概一百一十磅呢,对吧?”
马兹维把脸转开,回避着内德·博蒙特的目光。“我不懂你为什么老把参议员当成骗子。他是个绅士,而且——”
“没错,我在《邮报》上读过——美国政治界硕果仅存的贵族之一。他女儿也是贵族。这就是为什么我警告你跟他们打交道时得留点儿神,否则到头来你什么都捞不到。因为对他们来说,你只是个低等生物,跟你犯不着遵守游戏规则。”
马兹维叹了口气:“噢,内德,别这么讨人嫌——”
但内德·博蒙特想起了什么,眼里闪现出恶劣的光芒。他说:“而且我们不该忘记,小泰勒·亨利可也是个贵族呢,或许你就是因为这个才不准奥珀尔再跟他厮混了吧。要是你跟他姐姐结婚,他成了奥珀尔的舅舅,那可怎么成呢?他就又能在奥珀尔身边打转了吗?”
马兹维打了个哈欠。“内德,你没搞懂我的意思,”他说,“我没有问你这些事,我只是问你该送什么礼物给亨利小姐。”
内德·博蒙特的脸失去了原有的光彩,被沉闷笼罩。“你跟她进展到什么地步了?”他的声音中并没泄露自己的任何想法。
“没有进展。我大概去找过参议员五六次。有时能看到她,但也就是能说句‘你好’之类的。你知道,我还没有机会跟她真正地聊一聊呢。”
一丝喜色在内德·博蒙特眼中一闪而逝。他用拇指的指甲捋了捋一边的胡子,然后开口:“明天是你第一次去那儿吃晚饭?”
“对,而且我不希望那是最后一次。”
“但你没收到生日宴会的邀请?”
“对。”马兹维迟疑着,“还没收到。”
“那你不会喜欢我给的答案。”
马兹维面无表情。“什么答案?”他问。
“什么都别送她。”
“哎,得了吧,内德!”
内德·博蒙特耸耸肩。“那你随便吧,是你自己要问我的。”
“可是为什么?”
“别送任何东西,除非你十分确定别人想从你那里拿到什么。”
“可是每个人都喜欢——”
“也许吧,可实际上情况要微妙得多。你送礼的时候,就相当于高调声明:你知道他们很高兴让你送——”
“我明白了。”马兹维说。他用右手的手指摩挲着下巴,皱眉道:“我想你说得没错,”他的脸色随之变得开朗,“但错过这个机会太可惜了。”
内德·博蒙特迅速接口道:“好吧,那就送花,或诸如此类,这样就可以了。”
“花?耶稣啊!我可是想——”
“当然,你想送她一部跑车或几码长的珍珠项链,以后有的是机会。一开始得循序渐进嘛。”
马兹维皱了皱脸。“内德,我想你说得没错,这类事情你比我在行。那就送花吧。”
“别送太多。”内德紧接着又说,“沃尔特·伊万斯正到处告诉全世界,说你应该把他哥哥救出来。”
马兹维把马甲的底边往下拉了拉。“那么,这个世界应该告诉他,蒂姆直到选举结束前都会待在牢里。”
“你打算让他接受审判?”
“没错,”马兹维回答,然后加重了语气,“内德,你他妈的很清楚我无能为力。每个人都在盯着选举,而且妇女团体闹得正凶。如果现在就处理蒂姆的案子,那等于自杀。”
内德·博蒙特朝金发男人狡猾地一笑,慢吞吞地开口:“我们还没打入贵族圈子呢,没必要那么早就担心妇女团体。”
“我们现在就得担心。”马兹维的眼神高深莫测。
“蒂姆的太太下个月就要生了。”内德·博蒙特说。
马兹维不耐烦地呼了口气。“真是添乱,”他抱怨道,“他们闯祸之前怎么就不先想想呢?这些人就是没脑袋,一个都没有。”
“他们有选票。”
“就他妈的因为这一点才难搞!”马兹维吼道。他瞪着地板好一会儿,然后抬起头。“等投票结束之后,我们会关照他的。但在那之前我们什么都不会做。”
“这个说法可没法安抚那票人,”内德·博蒙特斜睨着马兹维,“不管有没有脑袋,他们都习惯被咱们关照了。”
马兹维的下巴略略抬起,深黯的蓝色眼珠死盯着内德·博蒙特的双眼。“所以呢?”他柔声问道。
内德·博蒙特微笑着,还是一副就事论事的口吻:“你知道他们很容易就会说,你跟了参议员之前,可不是这么办事儿的。”
“那又怎样?”
内德·博蒙特依然笑着,语调丝毫未改。“你知道,光是这些就足以让他们开始讲闲话,说沙德·欧罗瑞可还是很照顾他的兄弟。”
原先专注聆听的马兹维,此时用一种非常慎重的平静语调说:“我知道你不会让他们这样瞎说的,内德,而且我相信你会尽力防止这些偶尔入耳的闲话。”
有那么一会儿他们沉默地伫立,盯着彼此的眼睛,双方脸上都没有什么表情。然后内德·博蒙特打破了沉默。“如果我们照顾好蒂姆的妻小,应该会有帮助。”他说。
“你说得对。”马兹维低下头,他眼中沉晦的神色消退了,“留心这件事,好吗?满足他们的所有需要。”
3
沃尔特·伊万斯在楼梯口等着内德·博蒙特。他睁大双眼,满怀希望。
“他……他怎么……说?”
“跟我告诉过你的一样:没办法。等过了选举,蒂姆就能有路子出狱,但这之前不能有变动。”
沃尔特·伊万斯垂下了头,从胸腔深处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
内德·博蒙特伸出一只手搭上对方的肩膀:“这段日子你们很艰难,保罗比谁都清楚,可他连自身都难保了。他要你去告诉蒂姆的老婆,别付账单——房租、食品费、诊疗金和住院费,都送过来给他就是了。”
沃尔特·伊万斯抬起头,用双手捉住内德·博蒙特的手。“老……老天在上……他真是个好人!”那双瓦蓝色的双眼湿润了,“可……可我希望他能把蒂姆弄……弄出来。”
“这个嘛,希望总还是有一点儿的,”内德·博蒙特抽出手,“我再跟你联络。”然后他绕过伊万斯,走向台球室的门扉。
台球室里空无一人。
他拿了帽子和大衣,走向前门。细长的雨线闪烁着银灰的色泽,斜斜地倾泻在唐人街上。内德微笑起来,对着雨幕悄声低语:“下吧,亲爱的,你可值三千两百五十美元呢。”
他转身走回去,打电话叫了一辆出租车。
4
内德·博蒙特把双手从那个死人的身上抽回,站起身来。死人的头微微倾向左侧,偏离了路缘,于是整张脸都映在了街角路灯的光晕里。这是一张年轻的面孔,前额有道深色淤伤,自金色鬈发的发际蔓延至一侧眉际,衬得他脸上愤怒的表情愈发深重了。
内德·博蒙特往唐人街两端看了看。前方目力可及之处均不见人影。而在另一头,两个街区之外的小木屋俱乐部门前,有两个男人正从汽车里出来。他们把车留在俱乐部门前对着内德·博蒙特,然后走了进去。
内德·博蒙特盯了那辆汽车几秒钟,突然转过头去重新打量着街首。紧接着,他一口气掠过人行道,闪进最近的一片树荫。他喘着气,汗水从掌心里渗出来,在灯光里星星点点地闪亮。现在他战栗了起来,于是竖起了外套的衣领。
他单手撑着树干,在树影里又待了大约半分钟,然后突然直起身子,朝着小木屋俱乐部走去。他前倾着身子,越走越快,等到看见有人从街对面走过来时他几乎都在小跑了。于是他立刻缓下步伐,挺直了身体。而在撞上内德·博蒙特之前,那人就拐进了一栋房子。
等内德·博蒙特走到俱乐部时,他已经平复了喘息,但不知为何嘴唇却依旧苍白。路过那辆空车时他看了一眼,然后踏上两端立着灯笼的台阶,走进了室内。
哈里·斯洛斯和另一个男人正从衣帽间走出来,穿过门厅。他们停下脚步,不约而同地开了口:“你好,内德。”斯洛斯又追了一句:“我听说你今天押了佩吉·欧图尔。”
“没错。”
“押了多少?”
“三千二。”
斯洛斯舔了舔下唇。“真不错。你今晚应该也玩一局。”
“再说吧。保罗来了吗?”
“不知道。我们才刚到。别拖太久啊——我答应了家里的女人今天要早点回家。”
“好的,”内德·博蒙特答道,然后走向衣帽间。“保罗来了吗?”他问服务员。
“来了,大概有十分钟了吧。”
内德·博蒙特看了一眼手表,十点半了。他上楼来到二层的前厅。马兹维穿着晚宴服坐在桌边,内德·博蒙特进来的时候他正伸手要拿电话。
“内德,你还好吗?”马兹维把手收了回来,宽阔而英俊的脸庞气色红润,神情温和。
“我经历过更糟的。”内德·博蒙特答道,同时关上了身后的门。他在离马兹维不远处的一把椅子上落座。“亨利家的晚餐如何?”
马兹维的眼角现出皱纹。“我也经历过更糟的。”
内德·博蒙特剪着白斑雪茄的一头,手指颤抖。与之截然相反的是,他的声音异常平稳。“泰勒在场吗?”他抬眼盯着马兹维。
“晚餐时不在。怎么了?”
内德·博蒙特伸开交叠的双腿,向后仰身靠在椅子上,捏着雪茄的手漫不经心地挥了挥:“他死在街头的排水沟边上。”
“是吗?”马兹维不动声色地说。
内德·博蒙特的身体向前倾去,瘦削的脸紧紧地绷了起来。雪茄的卷纸在他指间碎裂,发出薄脆的噼啪声。
“你听明白我的话了吗?”他暴躁地问。
马兹维缓缓点头。
“所以呢?”
“所以什么?”
“他被杀了。”
“好吧,”马兹维说,“那你希望我歇斯底里一下吗?”
内德·博蒙特从椅子里直起身来。“我该打电话报警吗?”他问。
马兹维稍稍抬了抬眉毛。“他们还不知道吗?”
内德·博蒙特直视着金发的男人。“我刚刚看到他的时候,旁边没有人。而在行动前,我想先见你一面。我去跟警方说是自己发现的尸体,行吗?”
马兹维的眉毛耷拉下来。“有什么不行的?”他面无表情地反问。
内德·博蒙特站起来,往电话的方向走了两步,停住,然后再度转向金发男人。“他的帽子不见了。”他加重了语气缓缓说道。
“反正他现在也用不着了。”马兹维怒视着他,“你真是个天杀的蠢货,内德。”
“我们之中确实有个蠢货。”内德回了一句,然后朝电话走去。
5
泰勒·亨利死于非命——参议员之子横尸唐人街
参议员罗夫·班克劳福·亨利二十六岁的儿子泰勒·亨利于昨夜十时许被发现死于唐人街潘美拉大道一角,警方判定为抢劫遇害。
法医威廉·胡普斯声称,小亨利系因前额遭棍棒或类似钝器重击后,后脑撞击人行道路石,造成头骨破裂及脑震荡而致死。
据悉,尸体最先由居于兰德尔大道九一四号的内德·博蒙特发现。此人前往两个街区外的小木屋俱乐部打电话报警;但在其联络到警察总局之前,巡警迈克尔·史密特已发现尸体并回报。
警察局长弗雷德里克·伦尼立刻下令彻底清查全市可疑分子,并声言将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尽快将凶手捉拿归案。
泰勒·亨利的家人声称,他大约于九时三十分离开位于查尔斯街的寓所……
***
内德·博蒙特将报纸放到一边,喝尽杯里残余的咖啡,把咖啡和碟子放在床边的桌上,然后重新倒回枕头上,面色蜡黄,神情疲惫。他把被单往上拉到颈下,两手交叠在脑后,双眼不满地盯着卧室两扇窗间挂着的那幅蚀刻版画。
有足足半小时,他躺在那儿,全身除了眼皮之外一动不动。然后他拾起报纸,把那篇报道重新看了一遍。阅读的时候,不豫的神色从他的眼睛里涌出来,蔓延至整张脸庞。他再度放下报纸,不情愿地从床上慢慢爬起来,在穿着宽松睡衣的瘦削身体外裹了一件棕黑交织的细纹晨衣。他将双脚探进棕色拖鞋,咳了几声,走进客厅。
那是个老式的大房间,天花板很高,窗户宽敞,壁炉上方有面巨大的镜子,家具上覆着很多红色的绒布。他从桌上的盒子里取出一根雪茄,坐进一把红色的宽椅子。接近中午时分的阳光在地上投射出菱形的亮格,他把脚搁在那上头。从他嘴里喷出的烟在弥散到阳光里时忽然变得浓郁起来。内德把雪茄从嘴边拿开,眉头深锁,咬着指甲。
敲门声响起。他坐直身子,双眼锐利,神色警醒。“进来。”
一个穿着白色上衣的侍者走了进来。
“喔,好吧,”内德·博蒙特的语调中带着失望,放松下来,再度陷进红绒椅中。
侍者经过他身边进入卧室,出来时托盘上放了几个盘子,然后离开了。内德·博蒙特把手上的半截雪茄丢进壁炉,走进浴室。等到刮脸、沐浴、更衣之后,他脸上的蜡黄已然消退,但举止依旧带着疲惫。
6
当内德·博蒙特离开房间,走过八个街区来到林克街一栋灰白色的公寓大楼前的时候,其实还未到中午。他按下门廊上的一个按钮,在门锁咔嗒一响后走进去,然后搭着狭小的自动电梯上了六楼。
他在一扇标着6B的房门前按了门铃。门立刻打开,开门的是一个小个子女郎,看起来还不满二十岁。她的眼神幽深而愤怒,整张脸除了眼眶周围也气得发白。“唔,你好啊,”她微笑了一下,一只手含糊地做了个安抚般的手势,似乎是在为自己的愤怒而道歉,嗓音里有种金属般的清亮。她穿着一件棕色的毛皮外套,可是没戴帽子。她的短发色泽近乎纯黑,仿佛瓷釉一般柔顺而闪亮地贴着浑圆的头形;她的耳垂上戴着一对嵌金的玛瑙坠。她往后退,同时拉开了门。
“伯尼还没起床?”内德·博蒙特走进门厅时问她。
愤怒又回到她脸上。“那个下三烂的浑蛋!”她音调刺耳地说。
内德·博蒙特头也不回地关上了门。
女孩走近他,紧抓着他的上臂试着摇撼他。“你知道我为那个痞子做了些什么?”她说,“我离开了一个女孩所能拥有的最美好的家庭,还有一对把我当成圣女的好父母。他们告诉我他没有一点好;每个人都这么告诉我。他们没说错,我是太笨了才会不明白。啊,我告诉你,现在我可明白了,那个……”接下来是一串刺耳的脏话。
内德·博蒙特纹丝不动,严肃地倾听着。现在他的眼神可不再像是一个老好人了。“他做了什么?”在她停下喘口气时,他问道。
“做了什么?他甩下我跑了,那个……”接下来又是一串粗话。
内德·博蒙特瑟缩了一下,硬挤出一个苍白的微笑:“我想他没给我留下什么东西吧?”
女孩合上嘴,将脸凑到内德面前。
“他欠你什么吗?”她睁大了眼睛。
“我赢了——”他咳了一声,“我本应在昨天第四场马赛里赢了三千两百五十元。”
她把双手抽离他的手臂,轻蔑地笑了起来。“那就试着去要吧。你看。”她摊开手,一个玛瑙戒指戴在左手的小指上;她又举起双手,碰了碰那对玛瑙耳环。“这些就是他剩给我的破玩意儿,而且要是我没戴着,他才不会留给我呢。”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内德·博蒙特刻意装出一副事不关己的口气问道。
“昨天夜里。虽然我是直到今天早上才发现的。不过那位狗娘养的先生最好求上天保佑,别让我再碰上他。”
她把手伸进衣服里,拿出来的时候握成了拳头。她将拳头凑近内德·博蒙特的脸,然后张开手掌。三张皱巴巴的小纸片躺在她的手心里。他伸手要拿时,她却又合拢手指,往后一闪,把手抽了回去。
他不耐地撇撇嘴角,手垂到了身侧。
“你今天早上看了报纸上头亨利·泰勒的事情吗?”她激动地问。
“看到了。”内德·博蒙特回答得相当冷静,但他的胸口却随着急促的呼吸而起伏。
“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她再度摊开手,亮出那三张皱巴巴的纸片。
内德·博蒙特摇了摇头。他眯起双眼,眸子里闪着光。
“是泰勒·亨利的借据,”她得意扬扬地说,“值一千两百元呢。”
内德·博蒙特正要说什么,又思忖了一下,然后漫不经心地开了口:“现在他死了,半毛钱也不值了。”
她把借据再度收进衣袋里,然后靠近内德·博蒙特。“听着,”她说,“它们从来就一文不值,所以他才会死的。”
“你是这么猜的?”
“随便你怎么说吧,”她告诉他,“可我告诉你:伯尼上星期五打过电话给泰勒,说只宽限他三天。”
内德·博蒙特用拇指的指甲扫过一边的胡髭。“你是不是气糊涂了?”他谨慎地问。
她一脸愤慨。“我当然气得发疯了,”她说,“我疯到打算带着这些借条去报警,而且现在就要这么做。如果你以为我不敢,那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大蠢蛋。”
内德似乎依然没有信服。“你从哪儿拿到这些的?”
“从保险箱里。”那颗光亮顺滑的头颅往公寓的方向昂了昂。
“他昨天晚上几点走的?”内德又问。
“不知道。我九点半到家,几乎一整夜都在等他。快天亮时我才开始觉得不对劲儿,到处看了看,发现他把房子里的每一分钱和我没戴在身上的首饰全扫空了。”
他又用拇指指甲去捋髭须,然后问道:“你觉得他会去哪儿呢?”
她跺了跺脚,双手握拳,激烈地上下挥舞,再次用愤慨的语气颤抖着诅咒起失踪的伯尼来。
“别闹了。”内德·博蒙特捉住她的手腕,紧紧地捏着,“如果你除了大喊大叫什么都不打算做,不如把那些借条给我,我来干点儿什么。”
她挣脱他的手,哭喊了起来:“我什么都不会给你,我要交给警方,其他谁也别想拿。”
“好吧,那就交给警方。丽,你觉得他会去哪儿?”
丽苦涩地说她不知道伯尼在哪儿,只知道自己希望他去哪里。
内德·博蒙特不耐烦地说:“没错,这些胡言乱语可真是太有用了。你想他会回纽约吗?”
“我怎么会知道?”她的眼神霎时变得机警起来。
恼怒令内德·博蒙特的脸上浮现出星星点点的红色。他猜疑地问道:“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她装出一脸无辜。“没怎么办啊。你指的是什么?”
他向她凑过去,郑重其事地缓缓摇着头。“我不觉得你不会把这些借据交给警方,丽,你会的。”
“我当然会。”她回答。
7
在公寓大楼一层的药房里,内德·博蒙特借用了电话。他拨了警察局的号码,说要找杜伦队长,然后说:“你好,杜伦队长吗?……我刚刚和丽·威尔希尔小姐谈过,她在林克街一六六六号伯尼·德斯潘的公寓。他似乎是在昨天晚上突然失踪了,留下了几张泰勒·亨利的借据……没错,她还说她几天前曾听到伯尼恐吓泰勒……不,你最好尽快来,或者派人过来……是……那也一样。你不认识我,我只是跟她谈了谈,因为她不想从伯尼的公寓打电话……”他又听了一会儿,然后一言不发地挂上听筒,走出了药房。
8
内德·博蒙特来到泰晤士街前段一排整齐的红砖楼房中的一户。按铃后,一个年轻的黑人女子来应门,深色脸孔上堆满了笑容。“博蒙特先生,您好吗?”她打开门,热情地迎接了他。
“你好,琼,有人在家吗?”内德·博蒙特问。
“有的,先生,他们还在餐桌边。”
他走到后头的餐室,保罗·马兹维跟他母亲面对面坐着,二人中间的餐桌上铺了红白相间的桌布。桌边还有一把椅子,但是没人坐,座位前的盘子和银餐具也没动过。
保罗·马兹维的母亲高大而清癯,一头金发从她七十多岁的时候开始逐渐退为银白。那双眼睛清澈湛蓝、灵动活泼,跟她儿子一模一样——她看着内德·博蒙特走进来时的眼神甚至比她儿子还要活泼一点儿。然而她皱起了眉头,然后开口道:“你总算出现了。这么不关心我,真是没良心的孩子。”
内德·博蒙特没心没肺地冲着她笑了:“啊,妈妈,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有自己的工作要忙呀。”他一只手朝着马兹维晃了晃,“喂,保罗。”
“坐下来,琼会想办法给你弄点吃的。”马兹维说。
马兹维太太朝他伸出骨瘦如柴的手,内德·博蒙特弯下腰去亲吻。她猛地把手抽回去,责备地问他:“你从哪儿学来这些花招的?”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已经长大啦。”他转向马兹维,“不用麻烦了,我才刚吃过早餐呢。”然后他看了看那把空的椅子,“奥珀尔呢?”
“躺着呢。她不舒服。”马兹维太太回答。
内德·博蒙特点点头,等了一会儿,然后礼貌地问:“不严重吧?”说这话时他看着马兹维。
马兹维摇摇头。“头痛什么的。我想这孩子是跳舞跳得太凶了。”
“女儿是不是头痛都搞不清,你可真是个好父亲。”马兹维太太说。
马兹维眼角又现出了皱纹。“妈,别在这个时候不讲道理啊。”然后他转向内德·博蒙特,“有什么好消息吗?”
内德·博蒙特绕过马兹维太太,走到那把空椅子旁坐下来。“伯尼·德斯潘昨天夜里溜出城,把我从佩吉·欧图尔身上赢来的钱也顺走了。”
马兹维瞪大了眼睛。
内德·博蒙特说:“他还留下了几张泰勒·亨利的借据没带走,总共一千两百元。”
金发男人的双眼又眯了起来。
“丽说他星期五打过电话给泰勒,给他三天去筹钱。”内德·博蒙特接着说。
马兹维用手背蹭了蹭下巴。“谁是丽?”
“伯尼的妞儿。”
“噢。”然后,见内德·博蒙特不做声,马兹维又问,“他有没有说,如果泰勒没筹到钱要怎么办?”
“我没听说。”内德·博蒙特用手臂倚着餐桌,然后冲着马兹维转过身子,“保罗,帮我弄个副警长什么的来当当吧。”
“看在上帝的分上!”马兹维嚷着,眨眨眼睛,“你做那个能有什么好处啊?”
“能让我调查更方便。我要去找这个家伙,有个警笛可以让我从交通堵塞中脱身嘛。”
马兹维忧心地看着这个比自己年轻的男人。“你为了什么这么急躁啊?”
“为了三千两百五十元。”
“好吧,”马兹维同意了,然后依旧缓缓地开口,“不过我觉得你昨天在知道被赖了赌金之前,就有什么烦心事儿。”
内德·博蒙特不耐地挥挥手。“走在路上绊到个尸体,你还指望我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吗?不过别提了,那件事现在不算什么,这个才重要。我得去逮住这个家伙。我必须得逮住他。”他的脸色苍白而严厉,语调郑重,非比寻常,“听好了,保罗:这不单是为钱——虽然三千两百元很多,但就算是五块钱也一样。我已经连续两个月一次都没赢过,这让我很沮丧。如果连运气都不在了,那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呢?然后我扛住了,或者觉得自己扛了下来,接下来一切就都能恢复正常了。我不用夹着尾巴,可以觉得自己又是个人物,而不是什么被踢来踢去的畜生。那笔钱的确重要,但它不是重点。要命的是反反复复地输钱对我造成的影响。你懂吗?我都快垮了。然后,等我觉得霉运终于到了头,这个家伙居然糊弄我。我受不了这个。如果就这么算了的话,那我就真废了。我才不打算罢手,我要去追他。无论如何我都要去,但要是你能做我的后援,事情就能顺利很多。”
马兹维张开五指,粗鲁地摸了一把内德·博蒙特那张憔悴的脸。“噢,见鬼,内德!”他说,“我当然会支持你。我只是不喜欢你卷进什么麻烦里,可是——老天!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最好是让你当个地方检署的特别警探。这样你就归法尔管,而他不会多管闲事的。”
马兹维太太站起身来,每只瘦削的手里都端着一个盘子。“要不是我规定过自己不插手男人的事,”她严厉地说,“我一定会说说你们俩,总是为了天知道的什么耍猴戏去瞎忙,也只有天知道你们可能会卷进什么样的麻烦。”
内德·博蒙特咧嘴笑了,直到她端着盘子离开房间,他才收敛起笑容问:“你可以现在就帮我安排吗?这样到了下午就万事俱备了。”
“没问题,”马兹维站了起来,“我会打电话给法尔。如果还有什么要我帮忙的,你就……”
“好。”内德·博蒙特说。然后马兹维出去了。
皮肤黝黑的琼走了进来,开始清理餐桌。
“奥珀尔小姐在睡觉吗?”内德·博蒙特问。
“不,先生,我正要送点儿茶和面包上去。”
“你上去问她,我可不可以去看她一下?”
“是的,先生,我一定照办。”
黑人女子离开之后,内德·博蒙特从桌旁站起来,在房间里徘徊。渐渐涌起的血色令他瘦削的双颊发烫,而颧骨下方尤甚。马兹维进来时,内德停下了脚步。
“成了。”马兹维说,“如果法尔不在,你就找巴布罗,他会帮你的,你什么也不必跟他解释。”
“谢了。”内德·博蒙特说,然后看着门口的黑人女子。
“她说你可以过去。”女子说。
9
奥珀尔·马兹维闺房的主打色调是蓝色。内德·博蒙特进去时,她身上穿了件蓝银相间的便袍,正靠着枕头半坐在床上。她跟她父亲和祖母一样,都是蓝眼睛,也同样骨架纤长、身材紧实,美丽的粉白色皮肤像婴儿一样细嫩。她的眼睛此刻有些发红。
她把面包片往膝上的餐盘里一丢,朝内德·博蒙特伸出手,笑着露出她健康的白牙齿:“你好,内德。”声调并不平稳。
他没握她的手,而是轻轻拍了一下她的手背。“哟,丫头。”然后他在她的床尾坐下来,交叠起双腿,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雪茄,“烟雾会让你头痛吗?”
“噢,你可别。”她答道。
内德煞有介事地点了点头,把雪茄放回衣袋,漫不经心地叹了口气。他在床尾挪了挪,以便能够直视着她。他的双眼因为同情而泛潮,嗓子也有些发干。“我知道,小姑娘,那挺难受的。”
她稚气地睁大了眼睛望着他。“不,真的,现在头已经不大痛了,而且也没那么惨啦。”她的声音不再颤抖了。
他抿了抿双唇向她微笑起来:“所以现在你是把我当成外人啦?”
“我不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内德。”奥珀尔的眉毛微微蹙了起来。
内德的唇角的线条与眼神都变得坚硬,他开口说道:“我指的是泰勒。”
奥珀尔膝上的餐盘微微移动了一下,但她的表情丝毫不变。她说:“是的,可是……你知道,我已经好几个月没见过他了,自从爸爸——”
内德·博蒙特突然站起身来。“那就这样吧。”朝门口走去时他回过头说了一句。
床上的女孩没有回应。内德走出房间,然后下了楼。
保罗·马兹维在一楼大厅里,正打算穿上外套。“我得去办公室处理一下那些水沟合约的事情。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顺路载你去法尔的办公室。”
内德·博蒙特刚说了一句“行啊”,就听到奥珀尔的声音从楼上传下来。“内德,哦,内德!”
“就来,”他答应着,然后对马兹维说,“你赶时间的话,就别等我了。”
马兹维看看表。“我是该动身了。晚上在俱乐部见?”
“嗯。”内德·博蒙特答应着,然后再度上了楼。
奥珀尔已经把餐盘推到了床脚。“把门关上。”她说。待他关上门,她在床上挪了挪,在身边空出一个位置给他坐。然后她问:“为什么那样对我?”
“你不该跟我撒谎的。”他坐下,严肃地说。
“可是,内德!”蓝眸试探着对上他棕色的双眼。
他问:“你上次跟泰勒碰面是什么时候?”
“你的意思是跟他谈话?”她的表情和声音很自然,“已经好几个星期前了,而且——”
内德猛地站了起来。“得了吧。”他边走向门边回头说道。
奥珀尔在他刚踏出一步时就叫了起来:“噢,内德,别这么为难我。”
他缓缓转过身来,面无表情。
“我们难道不是好朋友吗?”她问。
“当然,”他不紧不慢地从容回答,“但如果我们互相欺瞒,我就很难记得朋友这回事了。”
奥珀尔在床上扭动着,脸颊压着最高的那个枕头上哭了起来。无声的泪水滴落在枕头上,洇出一块灰色的印迹。
他回到床边,再度坐在她身旁,把她的脸从枕头上扶起来,靠着自己的肩膀。
她又悄悄地哭了几分钟,嘴唇紧抵着他的外套,话音闷闷地传出来:“你知道——知道我一直在跟他约会吗?”
“知道。”
她坐直了身体,警戒起来。“爸爸知道吗?”
“我想不会吧。我不清楚。”
她把头埋回他的肩膀,接下来吐出的字眼也依旧含混。“噢,内德,我只有昨天下午跟他在一起,一整个下午!”
他伸出手臂抱紧了她,但什么也没说。
又过了一会儿,她问:“你想会是谁——谁杀了他?”
他瑟缩了一下。
奥珀尔突然抬起头。现在她身上一丝软弱都没有了。“内德,你知道吗?”
他犹豫着,舔了舔嘴唇,咕哝了一句:“我想我知道。”
“谁?”她狠狠地问道。
他再度犹豫了,躲着她的眼睛,然后慢慢地问:“你能保证不告诉任何人,除非时机到了吗?”
“可以。”她很快地回答,可是他要开口时,她双手攫住他的手臂阻止了他,“等等,我不能保证。除非你先跟我保证凶手不会逍遥法外,他们会被捉住,而且会被惩罚。”
“我不能保证。没有人能。”
她瞪着他,咬着嘴唇,然后说:“那好吧,反正我答应你。是谁?”
“他有没有告诉过你,他欠一个名叫伯尼·德斯潘的赌徒一笔钱,还不了债?”
“这……这个德斯潘——”
“我想是的。但他有没有告诉过你欠债的事情?”
“我知道他惹上麻烦了。他告诉过我,但没说是怎么回事,只说他和他父亲为了钱吵了一架,说他很——他用的字眼是‘绝望’。”
“没提到德斯潘?”
“没有。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觉得是德斯潘杀的?”
“他有一千多元泰勒的借据,没收到钱。昨天夜里他匆忙出城,警方现在正在找他。”内德压低声音,微微转身看向奥珀尔,“你愿意做些事情,好让他被绳之以法吗?”
“我愿意。什么事?”
“我指的是有点不光彩的事儿。你想想,要给德斯潘定罪必然不容易,可是,如果真是他干的,你愿意做一些——呃——下流的事情,好把他给钉牢吗?”
“做什么都行。”她回答。
他叹了口气,抿起了嘴唇。
“你想要我做什么?”她热切地问。
“给我一顶他的帽子。”
“什么?”
“我要一顶泰勒的帽子。”内德·博蒙特说着脸红了,“你能替我弄到一顶吗?”
她困惑了。“可是为什么呢,内德?”
“好把德斯潘实实在在地钉牢。我现在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你能不能替我弄到?”
“我——我想可以,可是我希望你——”
“要多久?”
“我想就今天下午吧,”她说,“可是我希望——”
他再度打断她。“你不会想知道任何事的。你知道得越少越好,去弄帽子的事也是。”他伸出手臂环住她,把她的身体拉向自己,“你真的爱他吗,丫头?或者只是因为你父亲——”
“我真的爱他,”她啜泣着,“我很确定——我确定我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