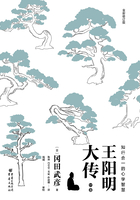
第1章 “知行合一”说
席元山入门
前文已述,正德四年(1509),贵州提学副使席元山因久仰王阳明的大名,特意前往王阳明的住处,向他请教学问。
席元山(1461—1527),名书,字文同,号元山,四川遂宁人,弘治三年(1490)进士,后升任礼部尚书,嘉靖六年(1527)又加封为武英殿大学士[1]。六十七岁去世,谥号“文襄”。席元山非常推崇陆学,曾著有《鸣冤录》,为陆学辩解。在晚年时曾推举王阳明出任大臣。
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记载,席元山对宋明理学非常感兴趣,他把王阳明迎请到自己的住处,向王阳明请教“致知”和“力行”究竟是一层功夫还是两层功夫。王阳明告诉他,知行本自合一,不可分为二事,也就是“知行合一”。席元山非常钦佩王阳明,特地请王阳明主持贵阳书院,还亲率贵州诸生向王阳明行弟子礼,而且一有空暇,就会前来听讲。王阳明也借此机会,在贵阳大力提倡“良知”说。
但“良知”说是王阳明在晚年提出的,他在贵州时根本就没有提过“良知”说。《阳明先生年谱》中记载:“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同异之辨。”
席元山后来又著有《鸣冤录》,仔细想来,该文应该是根据《阳明先生年谱》中记载的这次辩论而作。
接着《阳明先生年谱》又记载道:“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书怀疑而去。明日复来,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渐有省。往复数四,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同异,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与毛宪副修葺书院,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
总而言之,席元山师从王阳明之后开始意识到,与其讨论朱陆之异同、明辨古人之是非,倒不如判明自己内心的是非。至于王阳明当时悟得的“格物致知”究竟是什么,席元山又是如何理解的,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说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席元山对此又是如何认识的,《阳明先生年谱》中一概没有记载,我们对此也一无所知。但是,我们可以从王阳明与门人徐爱后来有关“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的问答中,推测出王阳明和席元山交谈的大致内容。
王阳明没有按照席元山的提问去回答朱陆之说的异同,而只是谈了自己所悟到的“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说。对席元山来说,如果能领悟到“理”存在于“性”中,那么朱陆之异同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明了了。所以说,王阳明虽然看起来没有回答席元山的提问,但其实已经回答了。
王阳明开口评论朱陆之异同,并且明确表达出自己的意见,那是后来的事了,后文将对此予以详细介绍。后来,由于弟子们就朱陆同异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王阳明没有办法,只好站出来,公开表明了自己对朱陆同异的看法。
那么,王阳明在贵州时为什么不公开表明自己的看法呢?
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王阳明觉得与其争辩古人做学问的是非,还不如先去体悟圣学,以求得“吾性”;其二,当时朱子学风靡一时,如果大力宣扬陆学的话,势必会成为众矢之的,所以,为了避开锋芒,王阳明没有公开表明自己的看法。
朱熹和陆九渊的学问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王阳明不得不加入朱陆同异的辩论中。虽然表面上朱子学盛行一时,人们却不能否认陆学潜藏的事实。自元朝中叶开始,朱陆同异的辩论就已经出现,王阳明自然也不能摆脱这一风潮。
后来,朱熹的高徒陈淳[2]极力排斥陆学,再加上朱子学比陆学更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所以在陆九渊去世之后,朱子学便逐渐兴盛起来。陆九渊有四大高徒——沈焕[3]、舒璘[4]、袁燮[5]和杨简,人称“四明四先生”或“明州四先生”。陆九渊死后,他的四大高徒在浙江四明(今宁波)地区讲学,所以陆学主要在四明地区留存下来。由于受陈淳排斥陆学的影响,陆学一蹶不振,逐渐陷入衰败。至元代,朱子学被指定为科举之学,迎来了大繁荣,而陆学基本上仍处于隐藏不露的状态。
朱熹和陆九渊死后,虽然朱子学派极力排斥陆学,但是陆九渊的心学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朱子学。这一过程类似于宋代儒学中的“形而上学”和“心学”的形成与发展。在宋代,当时的儒学界也极力排斥禅学和道家之学,却不知不觉地受它们的影响,最终形成了儒学的“形而上学”和“心学”。朱熹的再传弟子、著名大儒真德秀[6]可能也是因为受陆学的间接影响,所以才创作了《心经》,论述了从古至今的心法。自宋末一直到元代,学术界已经出现了朱陆二学殊途同归的看法。
元代朱子学的大儒吴澄认为,陆学主张的是“尊德性”,朱子学主张的是“道问学”,二者同等重要,没有轻重之分,所以吴澄也被认为是陆学派的儒学家。后来,思想界又兴起了朱陆同异的辩论。元末的赵东山、明初的程敏政认为,虽然朱子学和陆学存在差异,但它们所追求的结果是一致的。朱子学没有忘记“尊德性”,陆学也没有忘记“道问学”。尽管朱熹在年轻时和陆九渊的立场相异,但是晚年他和陆九渊的立场趋于一致。
到明代后,朝廷更加重视朱子学,不仅将其指定为科举之学,还打压提倡陆学的人士,从而在表面上形成了朱子学兴盛、陆学悄无声息的态势。但是实际上,不少明朝大儒已经把“心上”功夫当作自己做学问的要旨,出现了重视心学的倾向。朱子学和陆学在暗地里相互接近,相互影响,最终出现了一位专门提倡心学的朱子学者——陈献章。
清初大儒黄宗羲把陈献章的心学视作阳明学的先导,但陈献章的心学是“主静心学”,而王阳明的心学则是承继陆九渊,是“主动心学”,二者的方向明显不同。陈献章的心学沿袭的是朱子学,因此可以说是“宋学”,而王阳明的心学沿袭的是陆九渊的心学,因此可以说是“明学”。这也恰好体现了宋代精神和明代精神的差别:一个主静,一个主动。
如果能够领悟到“致知”和“力行”的本体是统一的,那么理解“知行合一”说就会变得很简单。如果不是通过这种“体认”,而是单纯地依靠理论去解释“知行合一”,理解起来就会很困难。王阳明曾经从各种角度论证过“知行合一”说。综合起来看,经他阐述,“知行合一”说的实质已经变得非常明晰了。
在王阳明看来,如果能够体认到“知行”的本体,那么“知行合一”说就很容易理解了。王阳明晚年时认识到“知行”的本体就是“良知”。这样一来,“知行合一”说就变得更加具体了。但是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并不是仅仅作为一种知识让人们去理解的,而是需要人们深切“体认”的。“知行合一”说是王阳明学说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还将予以详细介绍。
行而知之
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说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自古以来,虽然众人皆知“知”与“行”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但一直都是将二者分开,各自论述。尤其是到了朱熹的时代,对“知”与“行”的论述已经非常精微。朱熹曾提出“先知后行”说,认为必须首先认清万物之理,然后才能去实践,否则实践就会变得毫无根据。朱熹的这一认识在当时被认为是常识,是绝对的真理。
在朱子学一统天下的时代,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说,众人不能理解其本意,甚至惊愕,也是很自然的。被称作“王门颜回”的王阳明的高徒、妹婿徐爱,一开始听到“知行合一”说时,也流露出惊讶的表情。
总的来说,长于理性的人会很难理解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本意,这和长于智慧的子贡无法理解孔子的“一贯之道”[7]是一样的道理。无怪乎孔子会对子贡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孔子告诫子贡“道”并不是用道理就能说清楚的。后来,长于德行的曾子继承了孔子的“一贯之道”。曾子比子贡“鲁”,即我们所说的愚钝。当孔子说出“吾道一以贯之”的时候,曾子的回答只有一个字——“唯”。所以说,子贡的理智和智慧并不是真正的理智和智慧,否则他应该理解孔子的“一贯之道”。与此相反,虽然曾子被视作愚钝之人,但他其实并不愚钝,不然怎么能悟得孔子之道的真谛呢?又怎么能参透“一贯之道”呢?
总之,长于理智和智慧的人一般都会陷入偏见。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朱子学都是“主知主义”[8]的学说。因此,在一个朱子学至上的时代,人们必然难以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徐爱最初也难以理解老师的“知行合一”说,所以曾与自己的同门师弟黄绾和顾应祥[9]展开辩论,试图去理解“知行合一”说的主旨,但是一直未能如愿,最终不得不直接向王阳明请教。(《传习录》上卷)
先生曰:“试举看。”
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悌者,却不能孝、不能悌,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地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
“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
“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称他知孝、知悌,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悌的话,便可称为知孝悌。”
“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
“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功夫!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甚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甚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
王阳明从“知觉与好恶之意是一体”以及“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的立场出发,对“知行合一”说进行了阐释。
毫无疑问,“好恶之意”其实就是“行”。明末大儒刘宗周也非常重视“好恶之意”,并且将“诚意”视作自己做学问的宗旨,认为“意”非“已发”,而是“未发”,并将“意”视作“心”之本体。
如何修行“知行合一”
王阳明虽然提出了“知行合一”说,但是对于如何修行“合一”的“知”与“行”,并没有给出很好的办法。徐爱曾向他建议将“知”与“行”分开来修行,这一建议其实又回到了朱熹的立场上。朱熹坚持“知行并进”论,换句话说,就是坚持“穷理”与“居敬”并进。王阳明对此又是如何回答的呢?(《传习录》上卷)
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
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
“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
在王阳明看来,“知行合一”原本就是古人的意思,今人将其分作两件事去做,其实违背了古人本意。古人认为“知”存在于“行”中,“行”也存在于“知”中。而古人之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则是因为世间总有一些无知的人,所以要既不陷入妄行,也不轻视实践。古人为了防止世人陷入虚妄,同时也为了补偏救弊,不得已只好必说一个知,方才行得是,又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
总而言之,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说,是为了帮助世人脱离偏弊,同时也是为了帮助世人脱离朱熹的“先知后行”之弊。
王阳明曾对弟子黄直诉说过自己提倡“知行合一”说的动机:“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王阳明提出了“心即理”,还提出了“知行合一”,晚年又提出了“致良知”,这些主张其实都围绕着一个宗旨,那就是要彻底清除潜伏在人心中的不善之念。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就会违背王阳明的本意,也会生出很多弊害。事实上,王阳明的追随者都违背了王阳明的本意。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只相信良知的完美,而忽视了修行。
“知行合一”说的发展
前文已述,王阳明在壮年时曾阐述说:“知行合一”是“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到了晚年,王阳明又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知行合一”说。
嘉靖五年(1526),王阳明曾写过一篇《答友人问》(《王文成公全书》卷六),用以答复友人提出的四个问题。通过《答友人问》,我们基本上可以弄清王阳明是如何发展“知行合一”说的。
友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自来先儒皆以学问思辨属知,而以笃行属行,分明是两截事。今先生独谓知行合一,不能无疑。”
对此问题,王阳明的回答是:“此事吾已言之屡屡。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若着实做学问思辨的功夫,则学问思辨亦便是行矣。学是学做这件事,问是问做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这件事,则行亦便是学问思辨矣。若谓学问思辨之,然后去行,却如何悬空先去学问思辨得?行时又如何去得做学问思辨的事?”
可以看出,王阳明反对将《中庸》中的“学问思辨”与“笃行”区分为“知”与“行”。
接下来,王阳明又阐述了“知行合一”的理由:“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元来只是一个功夫。”
王阳明通过“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阐明了“知”与“行”原本只是一个功夫,即“知行合一”。这和王阳明壮年时期的“知行论”比较起来,“知行合一”的主旨更加清晰,“知行一体”的精神也更加明确。与其把王阳明晚年对“知”与“行”的阐释称为“知行合一”,不如称作“知行一体”更为恰当。王阳明的“知行论”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一程度,主要是因为他在晚年确立了“心即理”的本体就是“良知”。
王阳明在龙场先是悟出了“万物之理皆在吾性之中”,也即“心即理说”,然后才提出了“知行合一”说,但他真正完善“知行合一”说是在晚年。
嘉靖三年(1524),王阳明给妻侄诸阳伯写了一篇《书诸阳伯卷》(《王文成公全书》卷八),其中写道:
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宁有心外之性?宁有性外之理乎?宁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义外”之说也。
理也者,心之条理也。是理也,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发之于朋友则为信。千变万化,至不可穷竭,而莫非发于吾之一心。故以端庄静一为养心,而以学问思辨为穷理者,析心与理而为二矣。
若吾之说,则端庄静一亦所以穷理,而学问思辨亦所以养心,非谓养心之时无有所谓理,而穷理之时无有所谓心也。此古人之学所以知行并进而收合一之功,后世之学所以分知行为先后,而不免于支离之病者也。
提倡“知行合一”说的王阳明自然会批判将“存养”和“居敬”视作两层功夫的朱熹,也自然会批评朱熹提出的“先知后行”说。
因此,他在《答顾东桥[10]书》(《传习录》中卷)中,曾这样阐述:
既云“交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则“知行并进”之说无复可疑矣。又云“功夫次第不能无先后之差”,无乃自相矛盾已乎?
“知食乃食”等说,此尤明白易见,但吾子为近闻障蔽,自不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
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歧之险夷者邪?“知汤乃饮”,“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无可疑。
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谓不见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谓“此亦毫厘倏忽之间,非谓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尚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说,则知行之为合一并进,亦自断无可疑矣。
王阳明在给顾东桥的答书中阐述了“知行合一”说的主旨,指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并强调说,正因为“心即理”,所以“知行”才是“合一”的。此外,王阳明还基于“知行合一”说的立场,指出了朱熹“心理二分”说和“知行二分”说的弊害。接着王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又继续写道: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
“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即如来书所云“知食乃食”等说可见,前已略言之矣。此虽吃紧救弊而发,然知行之体本来如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者也。
“专求本心,遂遗物理”,此盖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
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
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此后世所以有“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
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暗而不达之处,此告子“义外”之说,孟子所以谓之不知义也。
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学问即行,行即知
一般来说,人们普遍认为“学问”是“知”,“实践”是“行”,而且往往将二者区别看待,然而对于王阳明来说,“学问”就是“行”,“行”也就是“知”。王阳明曾经系统地论证过《中庸》中提到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和“笃行”之间的关系,从中也可以了解王阳明的上述观点。
王阳明还从“知行合一”说的立场出发,对朱熹的“知行论”进行过批判,这在上文中已经做过一些介绍,而王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也对此做过更加详细的阐述:
夫学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
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笃者,敦实笃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笃其行,不息其功之谓尔。
盖学之不能以无疑,则有问,问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思,思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辨,辨即学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问既审矣,学既能矣,又从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谓笃行,非谓学、问、思、辨之后而始措之于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谓之学,以求解其惑而言谓之问,以求通其说而言谓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谓之辨,以求履其实而言谓之行。
盖析其功而言则有五,合其事而言则一而已。此区区心理合一之体,知行并进之功,所以异于后世之说者,正在于是。
朱熹是基于“主知主义”的立场而提倡“知行二分”说,王阳明则是基于“主行主义”的立场而提倡“知行合一”说,因此,阳明学被世人称为“实践哲学”也不是毫无道理的。王阳明接着又写了下面几段话,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实践哲学”的特色:
今吾子特举学、问、思、辨以穷天下之理,而不及笃行,是专以学、问、思、辨为知,而谓穷理为无行也已。天下岂有不行而学者邪?岂有不行而遂可谓之穷理者邪?
明道云:“只穷理,便尽性至命。”故必仁极仁,而后谓之能穷仁之理;义极义,而后谓之能穷义之理。仁极仁则尽仁之性矣,义极义则尽义之性矣。
学至于穷理至矣,而尚未措之于行,天下宁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为学,则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则知知行之合一并进而不可以分为两节事矣。
致良知
王阳明在晚年悟得“心即理”的本体就是“良知”,且“良知即天理”,所以他才能从“心即理”的角度来进一步发展“知行合一”说,并且认为,最终还得靠“致良知”去“穷理”。
所以,王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写道:
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穷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为未足,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广以裨补增益之,是犹析心与理而为二也。
夫学、问、思、辨、笃行之功,虽其困勉至于人一己百,而扩充之极,至于尽性知天,亦不过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岂复有加于毫末乎?今必曰穷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诸其心,则凡所谓善恶之机,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将何所致其体察乎?
吾子所谓“气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于此,而欲以外求,是犹目之不明者,不务服药调理以治其目,而徒怅怅然求明于其外,明岂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于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诚毫厘千里之谬者,不容于不辨,吾子毋谓其论之太刻也。
王阳明指出,如果“尽良知”,“知行”就可以“合一”。在他看来,《书经》(《尚书》,“五经”之一)中所说的“致知”就是指“致良知”。“致知”中的“知”是指对“是非”先天性的判断,也即他所理解的“良知”。要想让“知”达到极致,就必须通过实践,故“知行”是“合一”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宋儒根据《书经》中的“知之不难,行之不易”和《大学》中的“知至”,而得出了“知行二分说”,但王阳明得出的是“知行合一”说。尽管王阳明与宋儒所根据的是同样的经典,可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
嘉靖三年(1524),王阳明作《书朱守谐卷》(《王文成公全书》卷八)。
守谐曰:“人之言曰:‘知之未至,行之不力。’予未有知也,何以能行乎?”
予曰:“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无患其无知,惟患不肯知耳;无患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其知耳。故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
今执途之人而告之以凡为仁义之事,彼皆能知其为善也;告之以凡为不仁不义之事,彼皆能知其为不善也。途之人皆能知之,而子有弗知乎?如知其为善也,致其知为善之知而必为之,则知至矣;如知其为不善也,致其知为不善之知而必不为之,则知至矣。
知犹水也,人心之无不知,犹水之无不就下也,决而行之,无有不就下者。决而行之者,致知之谓也。此吾所谓知行合一者也。吾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陆九渊与“知行合一”说
前文已述,王阳明在龙场顿悟时得出“心即理”的结论,所以才得以创立“知行合一”说。但是,陆九渊也提倡“心即理”,为什么他没能提出“知行合一”说呢?这是因为陆九渊虽然也提倡“尊德性”,但他对于《大学》中“格物致知”的解释没能摆脱传统的束缚。
与陆九渊不同的是,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是彻底的“唯心论”,他明确指出“心即物”。尽管这样的认识是在龙场顿悟之后产生的,但在龙场顿悟之际,阳明恐怕就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由此看来,王阳明在龙场悟得的“心即理”应该比陆九渊的“心即理”更加“唯心主义”。也正因为如此,王阳明最终提出了“知行合一”说。
王阳明晚年对陆九渊的学说极力称赞,对朱熹的学说则加以批评。曾有友人问他:“象山论学与晦庵大有同异,先生尝称象山‘于学问头脑处见得直截分明’。今观象山之论,却有谓学有讲明,有践履,及以致知格物为讲明之事,乃与晦庵之说无异,而与先生知行合一之说,反有不同。何也?”(《王文成公全书》卷六《答友人问》)
虽然王阳明极力称赞陆九渊的学说,但他认为陆九渊和朱熹在“格物致知”的解释方面是相同的,二人体现的都是“主知功夫”,故而提出的是“知行二分”说,而他自己对“格物致知”的解释则与二人不同,所以才提出了“知行合一”说。
如上文所述,有人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存在疑问,王阳明的解释是:“致知格物,自来儒者皆相沿如此说,故象山亦遂相沿得来,不复致疑耳。然此毕竟亦是象山见得未精一处,不可掩也。”
“象山见得未精一处”,是指陆九渊还没有彻底地实现“唯心论”。王阳明将“心即理”发展为“心即物”,从他的立场来看,虽然陆九渊的学问很深奥,但是仍然没有达到“精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