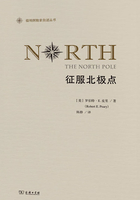
第4章 到达约克角
7月19日星期天,我们派出一艘小船,在爱情岬灯塔上岸,发送电报回家——最后一次。我想知道明年我第一次发送的内容会是什么。
在圣查尔斯角(Cape St. Charles),我们在捕鲸站前抛下锚。前一天有两条鲸鱼被捕获,我立刻购买了其中一条作为狗的食物。这些肉被堆在罗斯福号的后甲板。在拉布拉多海岸有好几家这样的“鲸鱼加工厂”。他们派出一艘在船头装有捕鲸炮的快速钢制蒸汽船。当一条鲸鱼被发现时,他们立刻追赶,而当足够接近时,就向这头巨兽射入装载着一枚爆弹的鱼叉,炸杀它。接着它被用绳子绑在船边,拖入捕鲸站,拉出到木道上,并且在那里被切开,硕大残骸的每个部分都被用于一定的商业目的。
我们在霍克斯港(Harks Harbor)再次停泊,我们的辅助补给船埃里克号(Erik)在那里等着我们,在船上差不多有25吨鲸鱼肉;一两个小时之后,一艘美丽的白色游艇跟进我们。我认出她是纽约游艇俱乐部哈克尼斯(Harkness)的瓦基瓦号(Wakiva)。冬天有两次在纽约港东24大街码头,她曾停在罗斯福号边上,在她的两次航行之间加煤;而现在,一次奇特的机遇,两艘轮船并排停泊在拉布拉多海岸上的偏僻小港口里。没有两艘船可以比这两艘更不相像:一艘洁白如雪,船上的铜制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如离弦之箭一般敏捷而轻灵;另一艘乌黑,缓慢,沉重,几乎如岩石一般牢固——每一艘都为特定目标而建造,并且都适应于那个目标。
哈克尼斯先生和一群朋友,其中包括几位女士,登上罗斯福号,我们女性宾客雅致的衣着进一步强调了我们船的乌黑、力量和不甚干净的环境。
我们在图尔纳维克岛(Turnavik Island)又停了一次,那是属于巴特莱特船长父亲的捕鱼站,我们接纳了一批拉布拉多皮靴,我们应该在北方会用得到。就在抵达这座岛之前,我们遭遇到一次猛烈的暴风雨。那是我记忆中曾经历过的最靠北的暴风雨。
然而我回想起1905年在我们的上行航程里,我们陷入非常剧烈的暴风雨中,如在南方水域航行时遭遇的海湾风暴一般地电闪雷鸣,不过1905年的风暴是在卡伯特海峡(Cabot Strait)附近,远比1908年的那些靠南边。
我们前往约克角的航行风平浪静,甚至缺少三年前相同旅程的小刺激,当时在离圣乔治角(Cape St. George)不远的地方,大家都手忙脚乱于从锅炉的上风口起燃并遍及一面主甲板的火警。也没有像1905年那样在我们旅程的早期受到迷雾的烦扰。事实上,从一开始起每个征兆都是吉利的,甚至让有点迷信的海员们认为我们的运气太好了,或许难以持久,与此同时,我们探险队的一名成员不断地“敲木头”祈求好运,就像他所表达的那样只是作为预防。说他的先见对我们成功有很大关系或许有些轻率,但是无论如何,那舒缓了他的心情。
随着我们保持向北航行,夜晚变得越来越短,也越来越亮,以至于当我们在7月26日午夜过后不久穿过北极圈,我们处在了极昼中。我曾来来回回20余次穿越北极圈,所以那种体验的细微之处对我而言有些迟钝了;不过我队伍中的北极“新手”古塞尔医生、麦克米兰和波鲁普,都相当地激动。他们的感受跟初次穿越赤道的人相同——那可是个大事件。
继续向北航行的罗斯福号现在就要到达北极地区最有趣的地点之一。那是沿着介于北面的凯恩湾和南面的(Melville Bay)湾之间北格陵兰西海岸中段夹在茫茫冰雪中的一块小绿洲。这里与周围地区成鲜明对比的是充沛的动植物,并且在近百年的时间里,有六七支北极探险队曾在这里过冬。这里还是一支爱斯基摩人部落的居住地。

这片小庇护地距离纽约大概3000英里航程,直线距离大约2000英里。它位于北极圈以北约600英里处,大概是从那个重要纬度标记到北极点一半距离。这里在冬天平均有110天漫长的北极夜晚,这段时间内没有光线落入视线范围内,只有月亮和星星的亮光,然而在夏季,太阳在相同数量的日子里每时每刻都是可见的。在这小片土地范围内被发现是驯鹿最佳的栖息地,它们找到了充足的牧草。不过当下我们对这个独特地方的兴趣只在于经过并带上若干这片寒冷地区的居民,他们在我们更远北方的争斗中会帮助到我们。
在我们抵达这片独特的小绿洲前,但是也已经超越北极圈好几百公里,我们来到我们上行旅程中最重要的地点,仿佛标志着我们前面任务的严峻。死在这片蛮荒北地的文明人无不留下他们的坟墓来给予那些后来者们深刻含义;而且随着我们持续向前航行,这些英雄尸骨的无声提醒述说着他们寂静却有力的故事。
在梅尔维尔湾的最南端,我们途经鸭岛(Duck Islands),那里是苏格兰捕鲸者的小墓地,他们是打通梅尔维尔湾航道的先驱者并且在等待浮冰化开时死在那里。这些坟墓的时间要回溯到19世纪早期。从这个地点开始,通往北极的干线上遍布着那些曾陷入跟寒冷和饥饿的可怕战斗的人的坟墓。这些简陋的岩石堆使任何有思想的人认清北极探险的意义。死在那里的人并不比我自己队伍的成员缺少勇气和智慧;他们只是缺少运气。
让我们顺着这条干线看一眼并且思索一下这些纪念物。在北极星湾(North Star Bay)是来自英国船北极星号的一两个人的坟墓,他们1850年在那里过冬。在外面的卡里岛(Cary Island)上是不幸的卡利斯特牛斯(Kallistenius)探险队一员的无名坟墓。再往北,在伊塔是海耶斯(Hayes)探险队的天文学家桑塔格(Sontag)的坟墓;再上面一点是凯恩队伍里的奥尔森(Ohlsen)。在对岸是格里利的不幸队伍中16人丧生的无标记之地。再往北,在东面或者格陵兰那边是北极星探险队的美国指挥官霍尔的坟墓。在西面或格兰特地那边是1876年英国北极探险队的两三名船员的墓地。而就在靠近谢里登角的中央极地海的海岸上是1876年英国北极探险队的翻译丹麦人彼得森(Petersen)的坟墓。这些坟墓作为以前为赢得奖赏所作努力的无声记录而竖立,并且它们稍稍暗示了那些在追求北极目标中付出在尘世最后时刻的勇敢却不幸的人的数量。
最初我看见鸭岛上捕鲸人的墓地时,我坐在那里,在北极的阳光下,看着那些坟头的木板,清醒地认识到它们所意味的。当我第一次看到桑塔格的坟墓,在伊塔,我小心地重新摆置围绕它的石块,作为向勇敢者的致敬。在萨宾角(Cape Sabine),格里利队伍的葬身之地,我是在七名幸存者在多年以前被带走以后第一个步入石屋废墟的人,并且我是在8月末的一次剧烈雪暴中步入那些废墟,看见了那些不幸者的警示。
通过鸭岛继续上行航程,在1908年靠近约克角,想到那里的座座坟墓,我做梦也想不到我自己队伍中的亲爱成员罗斯·G.马文教授,他跟我在一桌吃饭并且担任我的秘书,命中注定会把他的名字加入到这份北极牺牲者的长长名单里,而他的坟墓,在深不可测的黑水里,那是在这个地球上最北面的坟墓。
我们在8月第一天抵达约克角。约克角是标志着我的爱斯基摩人,世界上最北面的人类,定居的北极海岸延伸南端的险峻而陡峭的陆岬。就是那个陆岬,它的雪盖当我的船向北航行时很多次被我看见在远处从梅尔维尔湾地平线升起。在陆岬的底部,坐落着最靠南面的爱斯基摩村庄,那标志着一年又一年在这个部落成员与我自己之间相会的地点。
在约克角,我们才到了真正工作的开始。当我抵达那里时,所有文明世界可以产出的装备和辅助设备都在船上了。从那里开始,我将带上工具、材料、人员,北极地区本身将为它们的被征服提供装备。约克角,或者是梅尔维尔湾,是一条分界线,文明世界在一边,北极世界在另一边——北极世界有它的爱斯基摩人、狗、海象、海豹、皮衣和原始经验作为装备。
在我身后是文明世界,现在全无用处,再也不能给予我更多。在我前面横亘着无路可寻的蛮荒之地,要通过它我必须一步步踏出通向目的地的道路。甚至从约克角前往格兰特地北岸上的冬季营地的船上之旅也不是“一帆风顺”;事实上,在较后阶段都完全不是航行;那是与浮冰的挤压、碰撞、闪躲和捶打,总有可能性被这个对手回以重击。这就像熟练的重量级拳手的工作,或者带拳套的古罗马拳击家的工作。
梅尔维尔湾以上,世界,或者说我们所知道的世界,被抛在身后。当离开约克角时,我们已经把文明世界里多种多样的目标兑换为在那些广袤的蛮荒之地有位置的两个目标:人和狗的食物以及数百英里距离的跋涉。
在我身后的现在是属于我的一切,一个男人个人所珍爱的一切,家庭、朋友、家和所有那些将我跟我的同类联结的人类关系。在我身前是——我的梦想,曾驱使我历经23年一次又一次面对大北方冰冷拒绝来衡量自己的不可抗拒冲动的目标。
我会成功吗?我会回来吗?成功到达北纬90°并不肯定能保证安全返回。我们已经在1906年再次穿越“大水道”时了解那一点。在北极,机遇总是对抗着探险者。这个神秘地方高深莫测的守护者看来留有几乎用之不尽的王牌,来对付坚持不懈地进入游戏的入侵者。这日子是一条狗过的日子,但是这事业是一个男人的事业。

1908年8月的第一天,随着我们从约克角向北航行,我感觉我现在是真的面对最后的战斗。我生命中的一切似乎都在为这一天做准备。所有我多年的工作和所有我以前的探险都仅仅是为这最后和最高的努力而做预备。曾有人说过,朝向一个给定目标的指向明确的工作是为目标的达成所做的绝佳类型的祈求。如果是这样的话,祈求已经是我的一部分很多年。经过所有失望与挫败的季节,我未曾停止相信这北方的伟大白色秘密最终必将屈从于人类经验和愿望的强求,而且,当我背对世界并且面向那个秘密站在那里,我相信我将获得胜利,不顾所有黑暗和荒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