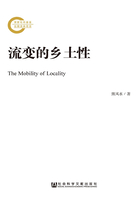
四 缺位市场下发展机会的迷失
在南村此阶段及以前的漫长历史中,市场机制一直处于缺位的状态,在农业生产之外,村民几乎没有其他的任何发展机会。
(一)重农抑商的传统
在历朝历代统治者和政治家的观念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只有稳定发展的农业,才能稳住国民,才能安定社会,才能富国强兵。在政治文化心态上,人们有强烈的农业依赖感,甚至把对农民和农业的控制视为国家或王朝的统治基础。为保证农业的稳定发展,必须把农民固着在耕地上,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生产要素变成现实的生产力,这就是重农的倾向。与重农相对应的是抑商,在封建统治者眼中,只有农业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导致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加。而商业只是把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进行交换,本身并不直接生产财富,不会导致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这种商业买卖与生产不相连,并且商人具有流动性的特征,这种贩运性质决定了商人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因而国家对商业一直是采取抑制的政策。当然,抑商不是废商,抑商政策的打击对象主要是私商,而不是官商,也不是要全部消灭私商,而是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作为农业经济补充的商业,往往被控制在维持小农经济的再生产限度内,超出这个限度,政府就会采取“抑商”措施。历代封建政府推行抑商政策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阻遏农业生产者弃农经商的倾向,当有大批的农民不安心农业生产而去经商的时候,农业的税收就得不到保障,甚至影响社会的安定;二是抑制大商人资本势力的恶性膨胀,当大商人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对国家的安全造成负面影响,“富可敌国”的商人历来被王朝政权视为心腹之患。
封建统治者在抑商政策上采取了很多具体措施,简要概括起来有这样三个方面:一是建立封建垄断的官营工商业,限制私营商业的活动范围。如建立“官盐”“官粮”等封建垄断行业,禁止私营商人在这些行业出现,极力限制私营商业的活动领域。二是加重商人的赋税负担,使商人无利可图,甚至破产。课以重税只是抑商的一个常规性手段,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非常规手段,如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强行要求商人出钱出力来修建一些重要工程、来为封建国防提供粮饷等,甚至直接采取没收、抄家等极端措施来剥夺商人的财富。法律不保护商人的利益,国家可以任意罗织罪名剥夺商人的合法财产。三是以律法贬低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商人在封建社会的地位很低下,封建社会地位的排列顺序为“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后一位。在封建统治者的法律压制和道德教化下,“无商不奸,无商不诈”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公理,“商人”不是好人的观念在很多农民的思想中已经牢牢扎根,“奸商”观念即使在今天仍然在村民的头脑中遗留着很深的印迹。在很多封建朝代,不允许商人的子弟做官,或者商人的子弟要经很多代以后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考取功名。有的朝代甚至还规定商人不许穿丝绸衣服等。通过这些方式来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因此农民不得不朝商业这条道路发展。
在经济生活中,中国历史上的自由市场经济萌芽,因为有“抑商”这个紧箍咒,中国古代的商业始终不能自由地发展,常常受到官方的干涉打击与民间的鄙视嫉妒,因而成不了正果,被限定在很小的范围以内,往往就是在集市的范围之内。布罗代尔认为,“西方发达的两个基本特征是:高级齿轮的形成,以及在十八世纪交换渠道和交换手段的增多,市场交易向高级形态转变;而中国的官僚体制阻止了经济活动以任何形式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唯有城镇的店铺和集市作为基本齿轮有效地转动” 。在稳固的自然经济和过度的政府干预之下,市场力量的发育与运作过程完全被扭曲。广大的农民就坚信“黄土生金”的信条,土地寄托着村民的全部生活和希望。村民精心耕作于那一块自留地,把土地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很少考虑土地以外的产业。农民的梦想并不是要拥有更多的金银,而是积聚更多的土地,占有更多的房产和粮食,使自己也成为土地的主人,从而摆脱地主对自己的盘剥并使自己也有机会剥削别人。即使从事某些手工业活动,如编织、酿酒、粮油加工等,也是与土地有着密切联系。“七十二行,庄稼为王”“玩龙玩虎,不如玩土”“要想吃饱饭,须用汗水换”这类谚语在村落中家喻户晓,代代相传。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今天,这种观念还有着残留的影子。在“士、农、工、商”社会评价体系的影响下,村民观念中是重仕轻商。重视当官,轻视经商,即官本位思想。村民教育孩子的时候,可以经常听见这样的话:“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后就吃上国家饭(借指当官)了”,而很少听到村民对孩子说“好好经商,长大后去做生意”这类的话。
。在稳固的自然经济和过度的政府干预之下,市场力量的发育与运作过程完全被扭曲。广大的农民就坚信“黄土生金”的信条,土地寄托着村民的全部生活和希望。村民精心耕作于那一块自留地,把土地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很少考虑土地以外的产业。农民的梦想并不是要拥有更多的金银,而是积聚更多的土地,占有更多的房产和粮食,使自己也成为土地的主人,从而摆脱地主对自己的盘剥并使自己也有机会剥削别人。即使从事某些手工业活动,如编织、酿酒、粮油加工等,也是与土地有着密切联系。“七十二行,庄稼为王”“玩龙玩虎,不如玩土”“要想吃饱饭,须用汗水换”这类谚语在村落中家喻户晓,代代相传。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今天,这种观念还有着残留的影子。在“士、农、工、商”社会评价体系的影响下,村民观念中是重仕轻商。重视当官,轻视经商,即官本位思想。村民教育孩子的时候,可以经常听见这样的话:“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后就吃上国家饭(借指当官)了”,而很少听到村民对孩子说“好好经商,长大后去做生意”这类的话。
重农抑商,自古有之,抑商不仅不尊重商人,而且贬低商人,在这样的社会制度里,产权意识自然无从说起。中国有着辉煌的四大发明,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但四大发明中没有一个发明是以人名命名的,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四大发明是什么,但很少有人能确切地知道四大发明是哪个人或者说哪些人发明的。不重视产权是抑商的表现之一,没有产权观念,技术创新就缺乏长久的激励机制,是靠天才式的灵感,而不是制度。在顽固的文化传统的心理积淀之下,重农抑商的观念,即使在今天,也在诸多方面表现出来。政府和民众对于企业与个人的经营自由,仍然常常进行不合理、不合法的干涉。成为今日中国市场经济痼疾的政企不分现象,既是传统计划经济的遗留,也是传统文化缺乏尊重个人自由的表现。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小农经济的“本分”思想,有时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敢想、敢闯、敢干的灵性,使人缺乏敢于开拓、敢于冒险、勇于进取的精神,影响了人们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
(二)人情经济制约了市场经济
在乡土社会,出于生产生活的各种需要,在现实中也会有各种产品的交换,但这种被用于交换的产品往往还谈不上“商品”,这种交换是一种“人情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人情经济制约了市场化经济的发展。“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很难存在的。这并不是说这种社会就不需要交易,就不发生交易,而是说这种交易是以人情来维持的,是一种相互馈赠的行为。馈赠和贸易在本质上都能达到互通有无的目的,只是在清算方式上有差别而已。” 也就是说,血缘社会奉行的是“人情”原则,商业活动奉行的是“理性”原则,两者是相抵触的,血缘社会与商业活动不相容。
也就是说,血缘社会奉行的是“人情”原则,商业活动奉行的是“理性”原则,两者是相抵触的,血缘社会与商业活动不相容。
人情交换与市场交换的差别体现在诸多方面,这里概括三点。
第一,“市场交换只认物,不认人。人情交换是既认人也认物。在市场交换中,双方关心的是能否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多的收益,至于对方是谁,则是毫不重要的事情。人情交换的前提条件则是‘有关系’的人,可能是朋友、熟人,甚至亲戚等,即使原先不存在‘关系’,也要想方设法先建立起‘关系’。根据对方和自己的关系,交往的深浅,来决定人情交换的浓淡厚薄。” 传统社会南村小农经济是一种生存型经济,要风调雨顺人们才能过上平安太平的日子,如果有天灾人祸发生,或者家庭中有重大的事情如建房子、红白喜事等,那么单纯依靠家庭的实力往往显得不够,这时候亲朋好友、隔壁邻居等就会“送礼”。在生存型经济的年代里,“送礼”除了有加强交往、增进感情的功能之外,也有实实在在的“经济帮助”功能,如果没有这些经济帮助,村民家庭中的很多“大事”就无法完成。这种经济帮助是一种典型的人情交换,人们会根据人情的亲疏决定交换的多寡。
传统社会南村小农经济是一种生存型经济,要风调雨顺人们才能过上平安太平的日子,如果有天灾人祸发生,或者家庭中有重大的事情如建房子、红白喜事等,那么单纯依靠家庭的实力往往显得不够,这时候亲朋好友、隔壁邻居等就会“送礼”。在生存型经济的年代里,“送礼”除了有加强交往、增进感情的功能之外,也有实实在在的“经济帮助”功能,如果没有这些经济帮助,村民家庭中的很多“大事”就无法完成。这种经济帮助是一种典型的人情交换,人们会根据人情的亲疏决定交换的多寡。
第二,市场交换遵循等价原则,人情交换秉承不等价交换原则。在市场交换中,用于交换的商品可以明码标价,有着明确的价格,即使交易双方在开始阶段在价格上有不同看法,但经过讨价还价的环节,最后总能在价格上达成一致,使交易顺利完成。在人情交换中,可用于交换的人情,所涉及的范围极大,不可能做到明码标价,因为人情本无“通价”,无法用货币衡量,人情总是“特价”的。礼的厚薄所表达的是关系的远近和情谊的浓淡,而不是价值的高低和使用价值的优劣。但人情也并非完全“无价”,人们常说“欠了人情”,如果完全是无价,哪来这欠债之感。尽管老百姓的心,都有人情一杆秤的定盘星,也都尽量做到“人情收支平衡”,但人情不可能是完全等价交换,所以一般来说总要加倍偿还。俗话说:“人家敬我一尺,我要敬人家一丈”,意思就是说,人情交换并不能遵守完全对等的原则。
第三,市场交换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即时结算,人情交换的原则是“来来往往,永不清账”。在市场交换中,买卖双方非亲非故,可以就商品进行讨价还价,争得面红耳赤也无所谓,反正成交结账以后,大家都是两不相干,无恩无怨。“经济账可以结清,经济交换中的赊购赊销、期票、汇票、债券、支票、信用证等,都是信用凭证,但这只不过是把结算的时间延期而已,最终都是要清算的,而人情的交换,在往来上是有时差的,不可能是即时结算。实际上没有最终的清算,因为没有通价,所以是算不清的。虽然人们常说‘知恩必报’、‘冤有头债有主’,但世间的恩恩怨怨永无终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和‘以命抵命’的结果,都是结下新的人情债。人情债的清算,就等于断情、绝交、结仇或以命相争。人情交换不能是单次博弈的‘一锤子买卖’,必须是连续性博弈。如果是经济交换的‘一锤子买卖’,那就要‘亲兄弟、明算账’,‘交情是交情、生意是生意’。长期的共同生活使人们‘低头不见抬头见’,想退出博弈都难。” 村落社会是熟人社会,人情交换可以延续很长时间,甚至可以延续好多代人,产生“世代恩仇”。
村落社会是熟人社会,人情交换可以延续很长时间,甚至可以延续好多代人,产生“世代恩仇”。
乡土社会是人情经济,人情经济使得市场经济的发育被局限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农村往往只能产生“集市”这种规模很小的交易场所。“在乡土社会中,街集是专门用作贸易活动的场所。街集一般都不在村子内部,而在距离村子较远的一片空地上,大家都以陌生人的身份来到这里,把原有的关系暂时搁开,交易当场结算,不涉及到其他社会关系。” 在南村的副业中,捕鱼是最主要的,在满足了家庭的需求之后,如果鱼还有很多,常见的是两种方式处理:一是送给村子里和自己关系好的人家;二是拿到街上(就是镇上的集市)去卖。这两者是分开的,遵循不同的逻辑,在村子内部,是不会谈“卖”的,只会是“送”。“送”是人情交换,“卖”是市场交换。
在南村的副业中,捕鱼是最主要的,在满足了家庭的需求之后,如果鱼还有很多,常见的是两种方式处理:一是送给村子里和自己关系好的人家;二是拿到街上(就是镇上的集市)去卖。这两者是分开的,遵循不同的逻辑,在村子内部,是不会谈“卖”的,只会是“送”。“送”是人情交换,“卖”是市场交换。
(三)计划经济与割“资本主义尾巴”
新中国成立以后,出于对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综合考虑,中国选择的是传统的经济模式。“传统的经济模式是由三个基本方面构成的:①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②以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和低物价为主要特征的宏观政策环境;③以计划分配资源、重要部门的国有制和人民公社体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管理体制。传统模式的这三个主要内容具有形成上的历史因应关系和运作上的相互配合、相互依赖的逻辑联系。” 在资源配置上,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资源分配的权力集中于国家,国家通过行政性的指令性计划,直接安排产值产量、物资调拨和固定价格。在生产和经营管理上,搞“一刀切”、单一化,忽视多种经营。为了加快互助合作的步伐,逐渐消灭属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国家对粮、油、棉和副食品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实现国家对乡村资源的计划性管制,这是工业化过程中国家在农业问题上采取的政策。“通过对农产品实现统购统销,有效地阻止了商品经济在农村的蔓延。”
在资源配置上,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资源分配的权力集中于国家,国家通过行政性的指令性计划,直接安排产值产量、物资调拨和固定价格。在生产和经营管理上,搞“一刀切”、单一化,忽视多种经营。为了加快互助合作的步伐,逐渐消灭属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国家对粮、油、棉和副食品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实现国家对乡村资源的计划性管制,这是工业化过程中国家在农业问题上采取的政策。“通过对农产品实现统购统销,有效地阻止了商品经济在农村的蔓延。” 这为进一步开展乡村动员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政府采取计划的、行政的、强制的手段,以消灭非计划经济活动。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对市场经济的排斥和压制,市场经济无从谈起。
这为进一步开展乡村动员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政府采取计划的、行政的、强制的手段,以消灭非计划经济活动。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对市场经济的排斥和压制,市场经济无从谈起。
具体到南村的微观环境上,则是实行人民公社制的生活集体化模式。村民在队社里统一劳动,通过工分制计算劳动量,收益由公社统一核算。建立公共食堂,把全体公社社员都组织到以公共食堂为中心的集体生活中去,禁止家庭小锅小灶。政府规定农民将生产资料、公共积累和基本物资等全部移交到公社。在一些极端的时期,自留地、家庭副业统统被取消,家里不准开火,许多人只有先到食堂打饭,然后回到家里一起吃。在意识形态的对抗中,走上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道路,卖个鸡蛋都有可能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买东西要去国营或集体的商场、商店。限定地点,并且限定时间(白天),人们仿佛又回到了汉唐时期“市”“坊”分开的时代。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村民的眼中,商人和资本家都是剥削者,他们不劳而获,所以是革命的对象。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自由贸易受到了严格限制,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被限制到极小的程度。社员个人主要靠生产队的分配安排生活,只有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才能保证生活。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私批修”“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运动形式,使得市场经济不可能有机会发育,实际上,村民是在极力避免进行商品交易,极力避免“露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拥有“土地”资产的地主成为被批斗的对象,“贫穷”是无产阶级的代名词,“富有”被看成是有资本主义嫌疑或者说倾向,这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长剑始终悬在村民的头顶上,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因为某个缘故而劈刺下来,这个缘故最有可能的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就是商品生产与贸易。村民“怕露富”的心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改革开放初期,依然很浓厚地保留着,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村民盖房子时慢慢地把“土砖”改成了“火砖”,但村民往往是采取“土砖”和“火砖”搭配的方法,用一部分“土砖”,也用一部分“火砖”。这一方面是与经济上不富裕有关;另一方面是村民“不敢”全部用火砖,第一户全部用“火砖”盖房子的人家会显得太“刺眼”,被认为是“有钱人”,继而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万元户”是村民们根据长期的观察判断出来的,而没有哪户人家去主动承认自己是“万元户”。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割资本主义尾巴”导致“怕露富”的惯性思维在心理上的延续,这种心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村民外出打工的步伐,成为制约村民致富的羁绊。
(四)自给自足下市场经济的“无空间”
市场经济的发育和繁荣,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分工和产品剩余。只有分工了,人们生产出来的产品才会各不一样,才会有需要相互交换的动力;只有产品出现了剩余,人们才有可能拿去交换。从南村的现实情况看,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没有给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空间。
第一,农业生产无专业分工。农业生产没有太多技术含量,是只需要出力气的“蛮活”。在农业耕作中,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只是在男女间、老少间做一些分工,如男的耕田、女的插秧,成年人挑担干重活,小孩和老人做手头上的轻活等。这种分工合作与其说是为了提高效率,还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男的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帮忙罢了,是一个家庭内为了更好地完成农业生产而实行的劳动力自发互补,根本不是向专业分工方向发展。没有分工,村民生产的产品就没有差别,每家每户基本上都一样,不存在交换的需求。与自然相交换,向土地讨生活,是小农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村民需要什么,就在田地里种植什么。村民们吃的是田地里种植出来的各种农作物,住的是用泥土的土坯盖起来的房屋,穿的是用家庭纺织品做出来的衣服,这种交换是“人和土”间的交换,而不是“人和人”间的交换。
第二,自给自足无产品剩余。村民在田地里辛勤劳作,生产出来的东西是用以满足自己和家庭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换。南村人均田地稀少,村民把田地的利用程度最大化,尽量让田地在一年四季里都能种植上东西,用以满足家庭需要,即使是这样,只有风调雨顺才能基本满足需求,根本谈不上有多少产品剩余,可以用于交换。如果遇上饥荒之年,则温饱都不能解决。村民过着“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简单、原始生活。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田地只能为村民提供可供生存的资源,不可能提供交换产品来与外界取得联系。同时,外界也没有什么经济力量和信息力量能够有力地渗透到农村中,因此,南村也就几乎处于一种完全封闭的状态。农民一生中满足于用自己双手生产的产品,或用食品和劳务向邻居换来的产品。去城镇集市的人虽然很多,但在集市上他们只买不可或缺的铁犁头,而把出卖鸡蛋、黄油、家禽或蔬菜所得的货币留着纳税,他们不能算真正投入市场交换,而只是来去匆匆的过客。在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中,不可能有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兴起,最多只是以镇为单位的一个个小集市的出现,用以满足村民一些最基本的交换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