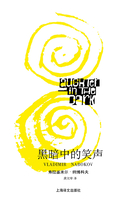
▇
从前,在德国柏林,有一个名叫欧比纳斯的男子。他阔绰,受人尊敬,过得挺幸福。有一天,他抛弃自己的妻子,找了一个年轻的情妇。他爱那女郎,女郎却不爱他。于是,他的一生就这样给毁掉了。
这就是整个故事,本不必多费唇舌,如果讲故事本身不能带来收益和乐趣的话。再说,裹满青苔的墓碑上虽然满可以容得下一个人的简短生平,人们却总是喜欢了解得尽量详细一点。
一天晚上,欧比纳斯忽然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不过说实话,这主意并不完全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因为康拉德的作品里有一句话曾提到这种设想。不是那个著名的波兰人,而是《一个健忘者的回忆》的作者乌多·康拉德,——他还写过另一篇故事,讲的是一个老魔术师在告别演出时倏然遁去。不管怎么说,欧比纳斯喜欢这个主意,反复琢磨它,让它在头脑里生了根。久而久之,在心灵的自由王国里,这主意就成了他本人的合法财产。作为艺术评论家和绘画鉴赏家,他常喜欢开玩笑地在他收藏的现代风景画或肖像画上签署某位古代大师的名字,再用这些画把他的家装饰得像一座精致的美术馆——当然,那全都是一些漂亮的赝品。有天晚上,为了松弛一下他那博学的头脑,他开始撰写一篇评论电影的短文。那不是什么高明文章,他并没有特别的才气。就在这个时候,那绝妙的主意冒出来了。
这想法是由彩色动画片引起的,那时候动画片刚刚时兴起来。他想,若用这种技法,把一幅人们熟悉的名画,最好是荷兰大师的作品,用鲜亮的色彩完美地再现于银幕,然后让画幅活动起来,那该多美妙!根据名画上静止的动作和姿态在银幕上创造出与原作完全协调一致的活动形象。比如说,一爿酒店,里面有一些小小的人物在木桌旁尽情饮酒,画面上还露出阳光照耀下的一角场院,院里有备好鞍的马匹——这图画忽然活动起来,那个穿红衣的小人放下手中的单柄酒杯,端盘子的姑娘猛地挣脱了身子,一只母鸡在门旁啄食。还可以让酒店里的那些小人走出来,从同一位画家所绘的风景中穿过——也许天空是褐色的,水渠里结了冰,人们穿着当时那种古怪的冰鞋,按当时流行的古老样式兜着圈子。也可以让几个骑马的人走在雾中湿漉漉的大路上,最后回到原先那爿酒店。然后所有人物逐渐各就各位,光线恢复原状。也就是说,让画面上的一切恢复到原作的本来面目。也可以拿意大利画家的作品来作试验:远处蔚蓝色的锥形山峰,一条白亮的盘山小路,游客们小小的身影正沿着山路蜿蜒而上。甚至宗教题材也不妨一试,不过只能选取人物画得极小的作品。动画设计师不光得充分了解原画的作者及他所处的时代,还得具有足够的技巧,以避免电影中人物的动作与原画作者描绘的动作发生矛盾,无法吻合——他必须根据原画设计出银幕上的各种动作——嘿,这完全办得到。至于色彩……一定要比一般动画片的色彩复杂得多。情节嘛,就得凭电影美术家去想像啦。他可以尽情地运用自己的眼睛和画笔,用自己创造的色彩描绘出一个浸润着个人艺术风格的世界!
过了一些时候,他和一位电影制片人谈起这个主意,可那人一点也不感兴趣。制片人说,这种影片的制作相当精细,需要对原先的动画制作法进行一系列别出心裁的改进,这就得花一大笔钱。他说,因为影片的设计处于试验阶段,所以一部片子的长度最多只会有几分钟。即便这样短,多数观众也会感到腻烦,片子就会失败。
后来欧比纳斯和另一位制片商谈起他的主意,又碰了一鼻子灰。“可以先搞一部简单的,”欧比纳斯说,“让一扇彩色玻璃窗上的图案——比如一个纹章图案或是一两个圣徒活动起来。”
“恐怕不行,”制片商说。“我们不能拿这种异想天开的玩意儿来冒险。”
可欧比纳斯仍不愿放弃他的设想。他终于打听到一个名叫阿克谢·雷克斯的聪明人,那人专会出新鲜点子。事实上,雷克斯设计的一部波斯神话片在巴黎趣味高雅的观众当中颇受欢迎,却使出钱拍片的人破了产。欧比纳斯想见雷克斯,却听说他刚刚回美国去了。那人在美国为一家带插图的报纸画漫画。后来欧比纳斯设法与雷克斯建立了联系,雷克斯似乎对他的主意挺感兴趣。
三月里的某一天,欧比纳斯收到雷克斯一封长信,可就在接信的时候,欧比纳斯的私生活——纯粹是私生活——发生了一次突然危机。所以,他这个美妙的主意本可以继续生存下去,本可以找到一块地盘扎根、开花,却在最后的一个星期里莫名其妙地凋谢、枯萎了。
雷克斯在信里说,不要指望能够说服好莱坞。他还头脑清醒地建议说,既然你欧比纳斯很有钱,何不自己出资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呢?这样的话,只要交给他雷克斯一笔钱(他说出一个惊人的数目),先支付一半,他可以根据布鲁盖尔的画作,比如说《箴言》,设计一部影片,或者随便由欧比纳斯选定一个题材,再由他绘制成动画片。
“如果我是你,就愿意冒这个险,”欧比纳斯的内弟保罗说。他身体壮实,脾气温和,前胸口袋上别着两支铅笔、两支钢笔。“普通影片花销更大,就是那种又打仗、又炸楼房的片子。”
“不过,那样的开销赚得回来,我花钱拍这种影片可就赚不回来了。”
“我好像还记得,”保罗喷着烟——他们快吃完晚饭了,保罗抽着一支雪茄——说,“你曾经打算出一大笔钱,并不少于他提出的这个数目。你到底怎么啦?前不久还挺热心的,怎么凉下来了?你该不会打退堂鼓吧?”
“呃,我也说不清。我发愁的是那些具体事务,否则我还会坚持原来的设想。”
“什么设想?”伊丽莎白问。
这是她的一种习惯——人家当着她的面已经谈得一清二楚的事情,她还要发问。这只不过是一种神经质,并不是由于她愚钝,或者心不在焉。而且往往一句话没有问完,她会边问边意识到,问题的答案她早就明白,她丈夫知道她这个习惯,但从不因此而生气,反倒觉得挺有趣。他会不动声色继续讲下去,心里知道(而且盼着),她过一会儿自己就能解答自己提出的问题。然而,在三月里的这一天,欧比纳斯心烦意乱,很不快活。他忽然发起火来。
“你刚从月亮上掉下来吗?”他粗鲁地说。妻子瞧着自己的手指甲,和颜悦色地说:
“噢,对了,我想起来了。”
然后,她转身朝正在狼吞虎咽地吃一盘奶油巧克力的八岁女儿伊尔玛大声说:
“慢点吃,乖,慢慢吃。”
“我认为,”保罗吸着雪茄说,“每一种新发明都——”
欧比纳斯胸中窝着一股无名火。他想:“我凭什么要理那个雷克斯,为什么要在这儿闲磨牙,还有什么奶油巧克力,真是无聊透顶……我都快发疯了,可谁明白我的心思?我已经管不住自己了,没办法,明天我还得去,坐在黑洞洞的大厅里,活像一只呆鸟……真是莫名其妙。”
的确是莫名其妙。结婚九年了,他一直规规矩矩约束着自己,从来没有——“说实在的,”他想,“不如直截了当把这件事告诉伊丽莎白;或者和她一道去外地避一避;或者找个心理医生谈谈;或者干脆……”
唉,不行。哪能仅仅因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吸引了你,就开枪把她杀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