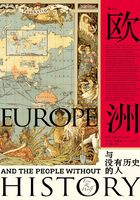
第2章 1400年的世界
1271年,威尼斯商人尼科洛·波罗(Niccolo Polo)、马费奥·波罗(Maffeo Polo),偕尼科洛之子马可(Marco),由地中海东岸出发,行经伊朗到达波斯湾边上的霍尔木兹(Hormuz),又由霍尔木兹往东北行抵达喀什噶尔(Kashgar),再由旧日的丝路到达北京。三人在中国和南亚长期旅行,而后乘船回欧洲,于1295年返回威尼斯。大约40年以后,摩洛哥学者型官员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h)启程赴麦加朝圣,行经伊朗、安纳托利亚(Anatolia)和克里米亚半岛(Crimea)到达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由此,他前往中亚和印度,在德里(Delhi)和马尔代夫群岛(Maldive Islands)的政府任职多年。在去过中国南部和苏门答腊以后,他于1349年返回故乡摩洛哥。3年以后,他又伴随许多摩洛哥商人穿越撒哈拉大沙漠到达西苏丹(Western Sudan)的马里王国(Kingdom of Mali),而后回到菲斯(Fez)口述游记,由一名书记员笔录。1405—1433年,中国宦官郑和7次下南洋,远达红海和东非海岸。1492年,一名受雇于阿拉贡女王(Queen of Aragon)的热那亚船长初次瞥见新世界。当看见巴哈马群岛(Bahamas)时,他以为到达了日本。
这类航海事件不是孤立的冒险事业,它们显示出当时存在的若干力量。这些力量正在把各个大陆拉近,并且不久就使世界成为一个人类活动的统一大舞台。为了要了解世界后来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必须了解它原来的样子。因此,我将追随一个被想象出来的1400年的航海家的脚步,描写他当时可能看到的世界。
这是“全球人类学”的一项工作。我将超越对特定的部落、文化区域和文明的描写,而将记述延伸到横跨至今仍然分离的两个半球(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旧世界”,以及南北美洲的“新世界”)的网络,也就是人类相互作用的网络。这些网络在时空中逐渐成长和扩散。有许多人口群,以往由西方人的观点所写的历史往往予以忽略或做讽刺性描述。我们若要说明上述网络,观察其成长与扩展,便必须追踪这些人口群的历史轨迹。有人认为他们是没有自己历史的人种,就好像人类学家研究的“当代原始人”。
在欧洲扩张以前,这些人口群之所以会广泛联结是显而易见的物质交流的结果。其中之一是可能引起争论的霸权政治与军事体系。两个半球分别出现了许多帝国,它们各自搜刮了不同地区的过剩物质。其次是远距离贸易的成长,将供给区域与需求区域联结起来,它也使联结商业通路两边的诸民族有了特殊的作用。帝国的兴建与贸易,又创造了广泛的交通线网。这些线网使不同的人口群借由支配性的宗教或政治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这些过程共同形成了一个世界,不久以后欧洲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将对它进行重组。
旧世界的政治地理
要了解1400年的世界,我们必须从地理开始。一幅旧世界的地图揭示了某些自然常数。其中之一是由东到西横亘欧亚大陆的大山脉。这条山脉由中国西部和南部的崎岖山地中崛起,一路升高成为昆仑山,再到“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和帕米尔高原,跨越厄尔布尔士山(Elburz Range)到高加索山、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s)、阿尔卑斯山,最后到达比利牛斯山。有时候,这些山脉妨碍北方与南方的接触;有时候,山脉链间的空隙鼓励人口流动和互相攻伐。在中国北部,汉人得修筑长城,把中国人留在长城内,把蒙古人和突厥人拦在长城外。中亚有道路向南进入伊朗和印度。在西部,侵袭者可以顺着多瑙河河谷进入欧洲的心脏地带。
本书最后面的地图指出了第二个常数,也就是主要气候区域的分布。这些区域造成不同的自然植被以及不同种类的人类生活习性。这张地图明白地指出了一个大的干燥地带,由西向东自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横跨伊朗高原进入中亚和蒙古。这一片是游牧民族的家园,他们在沙漠边缘以及草原上逐水草而居,只有在绿洲永久水源周围的地带才能耕种。在沙漠和草原干旱地带的南边,是温暖而潮湿的热带和亚热带森林与热带草原,这些地方往往宜于耕种,如西非、恒河平原、东南亚的半岛和岛屿,以及中国的南部。在干燥区域的北方是森林地带。在乌拉尔山以西,森林地带多雨,生长季节较长,因而在林木被清除以后便是良好的农耕地。在乌拉尔山以东,森林较为干冷,变为耐寒的泰加针叶林地带和无树的苔原地带,成为森林猎人喜欢的居住地。从事农耕的人很少来此,牧人也不能在此养活牲口。
比较可耕种和可改良农业地带的分布与沙漠和草原的分布,便可看到重要的对比。干燥地带的分布是连续性的,可耕地的分布则不规则,星罗棋布。游牧走廊便利离心流动。而间隔化的可耕地区则引导人们向心流动,聚居而成村落。草原与农耕地的对比,形成了人类活动在旧世界的主要方向,有时候将牧人与农民分隔开,有时又激励他们互动。
非洲西北部的农耕大致限于阿特拉斯山(Atlas)以北的地中海一侧,在南面和东面受阻于草原和沙漠。在摩洛哥的苏斯河河谷(Sus Valley)和西部地区、在阿尔及利亚的舍里夫(Shelif)和米提加(Mitidja)平原,以及在突尼斯的麦吉尔达(Medjerda)平原上种植的小麦,对于维持当地宫廷和供养精英分子起到了重要作用。突尼斯以东是的黎波里绿洲,再向东是尼罗河形成的大绿洲,也就是埃及。在罗马帝国时代,埃及的谷物曾经供养了罗马城。在此之后,它也供养了拜占庭和大马士革(Damascus)的阿拉伯人,以及1453年以后的土耳其人。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也愈来愈依赖多瑙河下游和黑海沿岸的谷物供应(参见书后的地图)。
在巴勒斯坦的梯田山坡上,有小片耕地。安提阿(Antioch,今日的安塔基亚〔Antakya〕)和大马士革一带是主要的农业绿洲分布区域。在罗马时代和20世纪曾经被开垦过的叙利亚草原,在生态上属于边缘地带,长久以来被弃置,任由游牧民族占领。在安纳托利亚,地中海和黑海沿岸以及山岭高原偶尔也有小块土地可以进行农耕,其他地方则是草原,东南部则是沙漠。居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伊拉克,一度物产丰富。从阿卡德人(Akkadian)的时代起,由于水利工程之便,剩余物产大量出现,遂足以支持国家的形成。在伊朗的萨珊王朝(Sassanid dynasty)统治下(226—637年),此地各种水利工程的兴建出现了一个高峰。但是,随着伊斯兰教徒的征服和巴格达成为有30万以上人口的首都,农业财富和人力资源却为这个城市所耗尽。这个情形造成农业生产额下降与贡物量逐渐减少(Adams, 1965:84 ff.)。13世纪中期蒙古人入侵,更是对生产力造成致命的打击。蒙古旭烈兀可汗(Khan Hulägu)摧毁了河谷下段的灌溉工程。
在扎格罗斯山脉(Zagros)以外是伊朗高原。高原上的大部分地区是干草原和沙漠,只有在沿着扎格罗斯山内侧边缘的一个扇形冲积地带上才有若干地块得天独厚,适合耕作。有时,耕地也借助地下暗渠延伸到较干燥的地区;在重力作用下水沿着河床流到边远的地块。在阿富汗和俾路支斯坦(Baluchistan),荒地和沙漠也把农耕地带限制在东部地区。
虽然这个地区有许多荒凉的沙漠和草原,但是以灌溉农业为基础的一连串都市化绿洲,成为往来于东西旅途中的商队的客栈和物资补给站。最重要的一条商队路线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由叙利亚北部的安提阿开始,经过雷伊(Rai,在德黑兰附近),而后穿越梅尔夫(Merv)和巴尔赫(Balkh,巴克特里亚〔Bactria〕)到达喀什噶尔。它在喀什噶尔分为两支,分别从塔克拉玛干沙漠(Taklamakan,即南戈壁〔Southern Gobi〕)的南北通过。北支通往库车(Kucha)和喀喇沙尔(Karashahr);南支通往莎车(Yarkand)和和田。南北两支在中国甘肃敦煌会合,由此进入中国腹地。因而,喀什噶尔是长途贸易的中心。马可·波罗曾赞美其花园及葡萄园,说它的居民在世界各地旅行和经商。由喀什噶尔开始,另一条路向北到达撒马尔罕(Samarkand)乃至伏尔加河(Volga)下游的撒莱(Sarai),由撒莱可以到达亚速海(Azov)和黑海。沿着这个庞大的欧亚山脉链的北面陡斜坡,可耕作的凹地散布其间。如果能阻止逐水草而居的牧人进入,人们便可在凹地上从事农耕。
因此,彼此相距遥远的农耕链,形成了一个大弧形,由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一直到中国的甘肃。交通和贸易路线将农业区域联结起来。这条长链子在政治和宗教上只统一过一次,也就是在7至8世纪伊斯兰国家的军队由阿拉伯半岛向东面和西面做扇形出击的时候。在此之后,链子的环节脱散,再未复合。政治的分隔又因宗教的门户之见加剧。每一种分裂又加深另一种分裂。
一再的分裂,削弱了这条长链子上的许多环节。孤立的农业区域滋生孤立的政府组织。这些组织在内部受到其支配资源有限的限制,而其边界的不设防,则使它们暴露于袭击和政权更迭之中。将这串珠状的地理政治结构连在一起的是贸易与宗教信仰。这些关系可以超越每一个孤立的组成部分,也可以广泛地聚合资源。可是,由于政治上没有统一的力量来保护它们,这些环节也因遭遇一再的干扰而断裂。
在欧亚山脉链的北部是一片大草原,形成了广阔的走廊地带,由东面的蒙古大草原穿过吉尔吉斯斯坦和俄罗斯大草原,一直延伸到紧邻中欧心脏地带的匈牙利大草原。这些是游牧民族最爱出没的地方。一直到俄国人在17世纪击败游牧民族及其可汗以后,南俄的大草原才成为永久耕地。
从俄国大草原往西是欧洲半岛。这个半岛是温带森林地带,可以开垦耕作。不过,它除了罗马人统治下的地中海地区以外,其他地区的发展都非常迟缓。它的四周几乎全是水域,如波罗的海、北海、大西洋和地中海。靠近水域是个优势,但只有在他们能成功守卫海岸并抵御来自南北两个方向的侵扰者时,才能使之变成真正能被加以利用的主要资源。但直到9世纪,这一任务才算完成。与此同时,经过1000年之久,欧洲的森林才得以被清除。一直到1000年,森林与农田的比例才对耕农有利。于是,有利于耕作与军事防卫的核心地区位于森林与海洋之间,而这个地区又往往有大河流贯,因而可以将货物运输出海。这些高产的优势地域是低地国家、塞纳河流域(Seine Basin)、莱茵河中游的灌溉区域、英国的泰晤士河流域、葡萄牙的特茹河(Tejo)流域以及意大利的波河(Po)流域。这些区域的过剩农产品促成政治力量的成长,成为不断发展的国家的战略供应基地。

图2-1 1400年的旧世界:主要贸易路线
横贯欧亚大陆的道路从丝绸之路东端的甘肃伸展到中国内地,进入一个与欧洲和伊斯兰国家完全不一样的政治-经济世界。欧洲被局限在半岛的外围地区,其地理政治的核心区域沿陆地的周边加固。伊斯兰世界纵向延伸,横跨欧亚大陆的脊骨,又伸展进入非洲的西部和东部。然而,中国却发展为一个结构紧密的单位,与西方国家相较起来显得硕大无朋。这个发展是渐进的。农业在中国北方的陕西泾河与渭河流域、山西的汾河流域和黄河下游扩展,支持了国家的形成。这个区域主要的作物是粟,不过公元700年以后小麦也渐趋重要。此时,这个古老的政治重心开始与产米的长江流域发生关联。7世纪初开凿的大运河将北方和南方联系起来。在此之后,长江以南又发展出第三个关键地区。汉人在3世纪初开始迁入这个地区的肥沃三角洲和盆地。7至8世纪,建立在改良的工具、种子和灌溉技巧基础之上的更复杂的稻作技术的出现,加速了汉人的南迁。
早在1世纪,在灌溉稻作农业的支持下,一个受到中国和印度模式双重影响的国家结构在湄公河三角洲兴起了。不过,在公元第一千年间邻近区域和岛屿形成的水利中心,却主要是仿效印度的模式。吴哥的高棉王国、爪哇中部和锡兰的王国都是这样。在印度,印度河流域的一个更早期的核心地区,曾支持了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和哈拉帕(Harappa)的国家体系。但是,这些国家在公元前1200年却由于印欧民族的入侵灭亡了。在此之后,干旱的印度河流域再没有恢复过去的关键性作用,只是有时成为中亚民族武装集结、待命入侵的地方。此后形成的国家都源于恒河流域,尤其是比哈尔(Bihar)和孟加拉地区。在那里,大米是主要作物。若年降水量只有40—80英寸时,人们便以灌溉辅助稻米种植。在年降水量超过80英寸的地方,人们便修筑水坝和堤防防洪。
亚洲东部和南部灌溉农业的发展,使得使用较不密集耕作方式的人口他迁。在印度,从事密集耕作的人,排挤像比哈尔地区的蒙达人(Mundas)和奥昂人(Oraons)等从事火耕的山居部落。在中国,汉人将他们的历史认同归结到在公元前700年以后以灌溉为基础发展出来的政治经济。在他们的南面是非汉人的“野蛮人”——苗族、瑶族和傣语民族。当汉人渡过长江进入“蛮”区时,他们便兼并了一些与他们类似的农业和政治模式的群体,而将从事火耕的人逐入更为多山和荒凉的区域。在其他地方,流动的耕作者,为了保护以亲属关系为原则组成的社会免受政治与经济压迫,纷纷撤退。因而,自12和13世纪以后,非汉族的少数民族的残余人口,便生存在中国西南的山区和邻近的缅甸、泰国、老挝和越南。在低地地区发展起来的灌溉农业核心区域,同样的过程重复出现,只不过是以较小的规模,山居者使用粗放的耕种方式,在山地和难以进入的内陆耕作。
贸易
我们这位想象中的观察者,在1400年行经旧世界的高地和堡垒时,当是沿着1000年来无数商人在相隔遥远的区域之间建立的广泛的商业路线行走才是。事实上,农业地区如群岛般分布,促使人类筑路加以连接,不论是海路还是陆路。这些路线,不论是长距离还是短距离,都需要维护和防御攻击。同时,任何控制了重要路线的群体,都能够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插足于这个交通线网,也可以切断联系,加剧这些可耕种岛屿间的分隔。因而,撰写旧世界的历史,可以从战略性的农业地区着眼,也可以从它们之间的联系着眼。
欧亚大陆的欧洲半岛,其最大的一个优势,是靠近周边的水路,从芬兰湾和波罗的海直到地中海东部。从这个海上网络的最东北极,可以到达伏尔加河,像8—10世纪间掠夺欧洲西海岸的北欧海盗一样,扬帆进入里海。不过,这条路线被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打断,一直到16世纪中叶才重新通行。丝绸之路从东地中海的港埠通往喀什噶尔,进入中国。地中海的第二条路线由阿勒颇到达波斯湾,从那儿再航行到印度和东南亚。第三条路线是陆海联运,横跨苏伊士地峡,而后通过红海和亚丁湾(Gulf of Aden)航行到非洲东部和印度以及更远的地方。在地中海南部的海岸地区,许多使用“沙漠之舟”骆驼商队的路线,横跨撒哈拉大沙漠,在尼日尔河(Niger River)拐弯处的城市加奥(Gao)和廷巴克图会合。由此,人们通过河运和驴子将货物运入西非的心脏地带。相反,从马来亚到菲律宾和日本,东南亚有无数可用来掠夺和贸易的路线。
这些路线的存在显示,长距离的交流对古代社会十分重要。商人一直以来将货物从生产过剩的地区运往物资缺乏的地区,并因这种服务而获利。由于交通设备有限,必须运用人力或畜力在陆地上运送货物,将货物放置在低吨位的船中在海上运输,因而运输频率最高的货物是奢侈品,每一件奢侈品均可产生高额利润。当珍贵货物贸易占优势时,贸易的交易往往便是在两个不同的区域进行。一个是本地贸易与交换,日常用品在严格限定的村落和城镇中流动;另一个是珍贵物品的长距离贸易。这些物品为满足精英分子的消费而生产,用以凸显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具有支配性的地位。

图2-2 紧邻水路的欧洲半岛
游牧民族
商人和其他旅行者在横贯旧世界的干燥地带,由非洲到亚洲的极远处时,便进入了游牧民族居住的区域。他们不仅是牧民,还往来驰骋于大多数连接绿洲和绿洲、核心地区和核心地区、区域和区域的交通路线之上。他们有骑兵装备,可以阻拦战略地点间的互动,也可以集结进攻绿洲和城镇的贸易中心。我们今日的形势对游牧民族是不利的,他们愈来愈没有能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发动战争。然而,在欧洲人打通通往东方的海上航线以前,游牧民族在横贯大陆的商队贸易中有重要的作用。他们以确保安全的承诺而收取贡金。F. C.兰恩(F. C. Lane)叫这种贡金为“保护金”。它成为游牧民族丰厚的收入。尼尔斯(Niels Steensgard)估计,由于欧洲人日后绕道好望角,直接与亚洲进行贸易,黎凡特地区的经济损失为三四百万皮阿斯特(1973:175)。
1400年,商队贸易与担任保镖的游牧民族都尚在全盛时期。游牧民族并不能独立生存于定居地带以外。游牧民族虽长于养牲口,随其牛羊逐水草而居,但是他们都靠农耕者供应谷物和工匠的产品。因而,游牧民族与农耕者往往因必要的交易而产生联系。这种交易的条件视交易人口的力量分配而异。在游牧民族有马匹的地方,他们在与定居人口交易的时候往往在突袭、机动性和攻击力方面占据优势。游牧民族分部、分等级的世系也占有战术上的优势。原本各自行动的许多世系,可以通过追溯一个共同的宗谱而结合,并由较高一级的世系领导。
这并不表示游牧民族始终预备好要攻打定居人口。当时有许多游牧民族与定居的村落处于和平共生的状态。许多游牧人口在每年的移动周期中也从事一点耕作,或者委托其联盟中的一个子群从事永久的耕作。影响畜牧与农业产品间交易价格的因素有很多。有些变化使牧人放弃畜牧而从事农耕。还有一些变化使农耕者放弃农田而专营畜牧。一个必须要问、而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是:究竟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游牧民族决定进行侵略性的战争,而不选择调解和共生的办法?
我们这位1400年的观察者无疑会认为,游牧民族是“上帝之鞭”。有400年之久,他们一再地攻打农耕中心。造成这个情形的原因不尽清楚。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探索了历史上从大草原到边界区发生的冲突的原因。有些边界地带的土地既可用于耕耘又可用于放牧,农耕者和游牧民族为占有这些土地而互相争执(1951)。这样的地区也是政治动荡地带。农耕者的统治阶级想要挑拨游牧民族自相残杀,而游牧民族也能探得定居地区的虚实。在4个世纪的时间里,在我们的观察者开启这次旅行以前,游牧民族,不论是突厥人、蒙古人、阿拉伯人还是柏柏尔人(Berber),他们影响力的强度和范围都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程度,使得这个时代明显地不同于之前或之后的时代。
在战时,游牧民族的长处是可以集结大量流动的兵力接受有效的指挥。但是在和平时期,这个能力却造成问题,很难持续统治被征服的人口而又不丧失自己作战的能力。据说汉化了的契丹人耶律楚材,曾对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说:“天下可以由马上得之,不可以由马上治之。”(Grousset, 1970:257)。因而,游牧的征服者为了巩固既得利益,就采用他们征服民族的行政模式。实际上,这表示大草原西部的游牧民族依循伊斯兰教的榜样,而东面大草原和沙漠上的游牧民族假借中国汉人的榜样。这一举措有着深远的影响。集中精力于日常行政技巧的结果,往往是削弱了维持军事威力的技巧。同时,提高豪华的定居宫廷生活依靠的税收基数,又招致其他敌对的游牧民族向征服者挑战(Lattimore, 1951:76—77)。其结果是统治的精英分子随着在战争中赢得的战利品的猛烈贬值或丧失(包括过剩的人口与其生产依赖的技术基础遭到毁灭)而在政治上产生轮替现象。
各游牧民族不仅与密集耕作的地区互动,他们之间也彼此互动。游牧民族入侵其他游牧民族的牧地,又为了控制最重要的贸易点而争执。譬如,据梯加特(Frederick Teggart, 1939)的说法,游牧民族每次在中国长城之下遭到败绩以后,便向后撤退攻打其他的游牧人口。这种压力一波波传递下去,一直到流动的入侵者在西部攻击罗马帝国的边界。虽然梯加特的描写或许夸大了这个过程的同步性,但是游牧民族沿干旱地带的持续移动,却将这个走廊变成密集互动的区域以及冲突的舞台。参与这些活动的,在北方是蒙古-突厥语族,在南方则是阿拉伯语族。
近东和非洲
突厥人
1400年,我们的这位旅客必曾遇见沿旧日丝绸之路移动的大量游牧人口。在喀什噶尔以东主要是说蒙古语的人;在喀什噶尔以西主要是说突厥语的人。公元1000年以后,说突厥语的人与城镇居民和农耕者的接触日益频繁。在伊朗北面的边界地区和邻近的大草原地带,这个现象尤其显著。在这些地方,当大草原上的战士得势时,农业与农耕阶层的势力便衰微。突厥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将其战士的意识形态与圣战的角色合并,而得以重新捕捉到早期主张扩张主义的伊斯兰教在意识形态上的活力。自11世纪起,突厥人逐渐取代了别的民族而成为替近东统治者服务的佣兵和军事奴隶。事实上,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和印度西北部这两个地区,他们在11世纪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权。13世纪中叶,突厥和切尔克西亚(Circassia)军事奴仆中的一名优秀分子,在叙利亚和埃及取代了库尔德人后裔的统治集团。
13—14世纪,成吉思汗及其麾下蒙古军队的西征,扫除了大部分的突厥人群体。突厥人先是与蒙古人联手,而后又从蒙古人的撤退中获利。譬如,在伊朗,塞尔柱(Seljuk)突厥人的一个王朝在13世纪前30多年在蒙古人的猛攻下覆亡,但是100年后蒙古人与说突厥语的人又恢复了竞争。最初赢得竞赛的是来自中亚河中地区(Transoxiana)的突厥人恐怖的帖木儿(Timur)。1400年,他的疆域由黑海一直延伸到喀什噶尔。但是,帖木儿于1405年逝世以后,这个国家开始崩溃。一个世纪以后,帖木儿汗国在中亚河中地区的心脏地带被乌兹别克人(Uzbek)攻克,领导乌兹别克人征伐的可汗是成吉思汗的后裔。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伊斯兰教什叶派萨法维教团(Safawi)动员游牧的土库曼人(Turkoman),在东部击败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的乌兹别克人,并且统一伊朗以对抗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由西方入侵。
奥斯曼人本是拥有梅尔夫城四周牧地的乌古斯部落(Oghuz)的后裔。他们的领袖是一个说波斯语的塞尔柱突厥人。他们是麦克尼尔(McNeill)所说的“掠夺者的边陲公国”的核心部分(1963:499)。自1300年起,他们从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一个基地出发侵袭和抢劫拜占庭聚落,并于14世纪下半叶迅速扩张,进入巴尔干半岛。到了1400年,他们已将一度强大的拜占庭人逼到了君士坦丁堡和萨洛尼卡(Salonica)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us)的东南部。1402年,当帖木儿在安卡拉(Ankara)击败他们之时,他们正预备对这些目标做最后一击。在与帖木儿的对抗中生存下来以后,奥斯曼土耳其人在15世纪恢复了扩张。他们在1453年征服了君士坦丁堡,并且建立了一个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帝国。
因而,我们的这位观察家会遇到在被帖木儿打败之前的奥斯曼土耳其人。他必会注意到穆斯林战士意识形态的力量。这种思想以圣战的口号激励奥斯曼人扩张,进入无宗教信仰者的领域;但他很少会注意到奥斯曼人建立起来以维持和管理被征服地区的制度。这个庞大的帝国将主宰近东达3个世纪之久,并阻碍欧洲人直接进入东方,使欧洲人的扩张转向西面的南北美洲,开辟绕道好望角的海上航线。因此,奥斯曼人值得我们简短地看一看他们发展出来的帝国结构。

图2-3 奥斯曼帝国的扩张
奥斯曼政体以苏丹及其王室为中心,包括他的军事奴隶,即著名的禁卫军。这些奴隶一般是从非伊斯兰教徒、战俘或被征服民族进贡的儿童中征召的。他们接受的是效忠苏丹的教育,并且只对苏丹效忠,而不效忠任何贯穿于国家机器中的亲属群体。游牧民族的分割性社会组织往往造成离间和竞争的问题。奥斯曼人的做法,旨在避免这样的问题。(奥斯曼人并非最初采用这种做法的人。早在8世纪,巴格达阿拔斯王朝〔Abbasid〕的哈里发,便从附近大草原上的突厥人中吸收了大量的奴隶。西班牙科尔多瓦〔Ćordoba〕倭马亚王朝〔Umayyad〕的哈里发,则偏爱斯拉夫人。)
军事奴仆被委派出去管理各个行省,并搜集其过剩产品以供养奥斯曼的军队,并且必须保证核心区域的食物供应。为此,他们也能终身享有一些贡物。在欧洲的封建制度之下,土地和劳力对于许多亲族来说可以传给子孙后代。而奥斯曼的君主则保留地契,不把土地给予他人,因而欧洲式的封建制度在此不得存在。奥斯曼政府也建立了对乌里玛(Ulema)的统治,乌里玛即伊斯兰教的法学家和神学家。和以前伊斯兰教的做法不同的是,奥斯曼将这些学者组成了一个管理阶层,他们对政府负责,统一律法,以消除因地方宗教差异而产生的离心力。军事奴仆和乌里玛共同组成了军人阶层。其他所有人都被归为庶民,以贡物支撑政府和官吏。
然而,奥斯曼的经济以货币的广泛使用为基础。多余的贡物,以及农民的农业产出和手工业行会的工艺品,放在地方性、区域性以及区域间的市场出售。因而,收税和政府稳定物价的措施都有赖于商人这个社会阶层。商人的活动对于政府是必要的,但他们始终威胁要摆脱政府的控制。商人由政府正式特许;政府官员密切监督市场销售,并加以抽税。但是,16世纪后期,奥斯曼境内的贸易,愈来愈与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以及黑海沿岸的商业中心联系起来。大部分这样的贸易都是走私,那时候确实是“走私者的天下”(Islamoğlu and Keyder, 1977:41)。同时,政府由于愈来愈无能力收税,就将以贡物酬劳官员的办法改为请人承包赋税。承包收税的人将收到的税交给政府,为此,他们有权在地方上收取贡物和税,并被予以处置权而从中谋利。但是,政府控制的减弱,造成地方权贵阶层的崛起。随着宫廷及其代表的权力日益衰微,这些人开始逐渐累积地方势力和商业影响力。
北非和西非
再向西,1400年北非的游牧人口也有关键性的作用。北非的每个城市或商业中心,周围都是农田和棕榈小树林,彼此之间又由沙漠或草原分隔。这些市镇通过许多贸易路线联结起来,但是它们的商队必须穿越荒凉而贫瘠的地区才能往来于这些贸易路线。半游牧民族和游牧民族控制这些地区,为己谋利。
虽然这个区域的地理和聚落模式,凸显草原与已耕地之间,以及城市及其农村内地之间尖锐的对比,但是北非的伊斯兰社会,却以“横向团结”跨越这些鸿沟(Laroui, 1976:35)。城市并不独立于周围的乡村而自治。每一个城市都有许多区域,每个区域的群体因种族、宗教和职业的差别而与另外的群体分开。这些群体在城镇和村落均有其分布。因而,城市、镇和农村形成了“地理、生态和社会的复合体,其中的地域和人口既不完全是都市的,也不完全是乡村的,而是二者的结合”(Lapidus, 1969:73—74)。主宰每一个区域复合体的是一些联姻家族的精英分子,其中包括地主、商人、政府官员、同业公会领袖,以及清真寺、学校和慈善组织的乌里玛。同时,共同的利害关系跨越区域界限将这些精英分子联系起来。长途贸易在商人团体中促成了一个商业关系网络,也促成了保证在广阔范围内商队交通安全的游牧群体领袖的联盟。此外,宗教领袖乌里玛在伊斯兰世界各处皆有,他们以宗教和法律的领袖和诠释者的身份将不同的区域联系在一起。最后,战略中心和要塞掌握在政治-军事精英之手。他们通常由一个至高无上的苏丹的军人奴隶组成。这些政治-军事精英负责收税和管辖,有时与宗教精英发生冲突,有时又与他们和解。
通过精英控制这片区域,以及与可以维护腹地商队路线和绿洲安全的游牧民群体结成有效联盟,有助于在这些政治体中维持权力。想要争夺控制权,就必须要与心怀不满的部落分支结盟,并尽力争取愤愤不平的城市商人与手工业者的合作。其结果是经常的交替变动。联盟中的异议分子考验统治者控制权的极限,一直到他们可以接掌控制权为止。在抓住权力以后,这个周期重新开始。
14世纪,柏柏尔朝臣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曾经精彩地分析了这个不断地结盟与解盟的过程,以之为游牧民族亲属团结与定居生活利害变化之间连续的交替。伊本·赫勒敦说明这个过程有其本身的逻辑。可是在北非,它是一个较大脉络的结果。这个脉络一方面是跨越撒哈拉大沙漠的贸易;另一方面也是与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的经济与政治力量的关系。
与西非进行跨越撒哈拉大沙漠的贸易,对于北非、近东,甚至是欧洲,都有战略意义。贸易路线穿越沙漠,进入跨越非洲的草原地带,又越过这个地带进入热带雨林地区。西非在班布克(Bambuk)和布尔(Buré)的金矿,在旧世界的黄金储备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世纪晚期,这个地区供应了西半球经济中2/3的黄金流动量(Hopkins, 1973:82)。雨林地带也为近东供应了大量奴隶。此外,这个地带也外销布匹、象牙、胡椒和可乐果(在伊斯兰教禁止使用酒类的地方,可乐果是很重要的兴奋剂)。反之,这个地带由北非进口马匹、黄铜、红铜、玻璃器皿、珠子、皮革、织物、成衣和腌制食品,并由撒哈拉大沙漠的矿场进口食盐。穿过撒哈拉大沙漠的西部到达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贸易路线,主要掌握在说曼德语(Mande)的迪尤拉族(Dyula)商人手中。这些商人已由尼日尔河支流巴尼河(Bani)沿岸的杰内(Jenne)向南扩张,到达森林地带边缘黄金和林产品的主要集散地贝格霍(Begho)。去往突尼斯和利比亚的东部贸易路线与豪萨族(Hausa)的商业网络联结起来。豪萨族从尼日利亚北部的卡诺市(Kano)和其他的豪萨市镇出发,往南与森林地带进行贸易。

图2-4 西非的主要贸易路线
当然,这个外在的网络具有政治意义。对森林与草原间和草原与沙漠间转移点的控制,使可以取得和把持这种控制的人有极大的权柄。这三个地带的分界线,对于西非国家的形成也十分紧要。这些国家中最早的一个是奥卡尔(Aukar),建立于公元800年以前,是以尼日尔河上游和塞内加尔以北草原地带上的市场中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个国家或许是索宁克人(Soninke)建立的,依照其统治者的头衔而被称为加纳。它控制了来自班布克金矿的黄金贸易,借由对它的垄断,并透过一群侨居的伊斯兰商人由摩洛哥取得必要的货物。11世纪,毛里塔尼亚(Mauritania)的柏柏尔人,即穆拉比特人(Al-Murabitun),攻陷了这个王国,而夺取了北向贸易的控制权。尔后到13世纪,加纳的一个旧日属国兴起,成为由马林凯人(Malinke)主宰的康加巴(Kangaba,马里)国。这个势力建立在对黄金贸易的控制和对从廷巴克图出发的贸易路线的霸权之上。
1400年,康加巴不断衰落。在这100年中,它终于屈服于以加奥为首都的桑海王国(Songhay)。桑海借由生活在绿洲至北方地区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列姆图纳(Lemtuna)柏柏尔商人而继续与北方贸易。桑海随后因摩洛哥人由北方入侵而覆亡。接下来,国家的形成沿旧日桑海的南面和东面进行。16世纪末叶,南方出现若干莫西族(Mossi)的国家,它们控制了由杰内到阿善提族森林地带通往下沃尔特(Volta)草原区域的路线。在加涅姆-博诺帝国(Kanem-Bornu)的东边,就是通往突尼斯、利比亚和尼罗河中游的贸易路线,这条路线由于豪萨族国家的兴起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豪萨族诸邦以东部两个主要的市场城镇卡齐纳(Katsina)和卡诺为中心。由这两个中心,豪萨人与西非森林地带说约鲁巴语(Yoruba)的民族及其邻人接触。
因此,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并非如欧洲所想的那样是孤立和落后的地区,而是一个关系网络的整合,这个网络将森林地带的耕种者与采矿者和草原与沙漠的商人以及北非定居地带的商人与统治者联系在一起。这个关系网络的经线是黄金(“摩尔人的黄金贸易”),纬线是其他产品的交易。这种贸易产生了直接的政治结果。在尼日利亚的贝宁(Benin)或豪萨的卡诺发生的事情,对突尼斯和拉巴特(Rabat)都有影响。当欧洲人日后由海岸进入西非时,他们会发现这块土地已有密集的市镇和聚落,并置身于交易网络之中,这些交易网络远超过沿海欧洲商业中心区的狭窄区域。
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贸易路线的北面终点,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影响力。一个接一个的精英在此崭露头角,每一个都依靠了与撒哈拉大沙漠与森林地带的互动。每一个精英都拴定在一个以亲属关系为原则的同盟之中,它通常是通过宗教思想动员起来的。前面已经提到毁灭加纳的穆拉比特人,这些人是宗教运动的活跃分子。11世纪,当阿拉伯游牧民族贝都因部落(Bedouin)进入毛里塔尼亚部分的撒哈拉大沙漠而威胁到游牧民族桑哈扎(Sanhaja)柏柏尔人同盟的资源基地时,他们从这个同盟中崛起。在军事-宗教寺院,他们倡言回到纯净的伊斯兰教。穆拉比特人的一支向南去控制加纳的黄金,另一支向北去征服摩洛哥和西班牙。他们使用西班牙化的名字穆拉比德人(Almoravids),在1090—1110年统治了安达卢斯(Al-Andalus)。12世纪,他们为穆瓦希德人(Al-Muwihiddin,西班牙化的称谓是阿尔摩哈德人〔Almohades〕)所取代。“穆瓦希德人”的意思是“一神论者”,属于麦斯木达(Masmuda)同盟。13世纪,由邻近西吉玛萨(Sijilmassa)商业中心的沙漠来的游牧民族贝尼马林人(Beni Marin)取代了穆瓦希德人。贝尼马林人为了自己的同盟参纳塔(Zanata)的利益,剥夺了桑哈扎和麦斯木达的权力。随后,贝尼马林人在两线同时作战,一方面在突尼斯迎战穆瓦希德人的残部(哈弗西德人〔Hafsids〕),另一方面迎战同盟自身中的一支西阿尔及利亚的扎亚尼德人(Zayanids),后者质疑他们对西吉玛萨的控制。哈弗西德人和扎亚尼德人与欧洲海岸进行贸易,尤其是与西班牙东部的阿拉贡进行贸易,想要抵制马林人的权势和补偿由游牧民族的劫掠而造成其本身内地的赤贫。在信奉伊斯兰教的格拉纳达(Granada)于1492年败给卡斯蒂利亚(Castile)王国以后,哈弗西德人与扎亚尼德人要求奥斯曼帝国的保护。为此奥斯曼帝国派来一支海盗舰队,他们自此以海上抢劫为主要收入来源(Abun-Nasr, 1971:167)。
1400年,我们这位旅客当曾遇见其时控制摩洛哥的贝尼马林人。然而,贝尼马林人随后日渐失势。16世纪,统治权转入一场宗教运动的领袖们的手中,他们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这个运动源于苏斯谷地的柏柏尔人,他们倡言对葡萄牙人发动圣战。16世纪末,这些萨迪人(Sa'dians)将致力于入侵和毁灭桑海国以重获对苏丹王国黄金的控制权。但是,他们也只能使黄金贸易从西部的商队路线转到东部。不久以后,这些摩洛哥的统治者,也会像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统治者一样以海盗行为攫取由欧洲人开辟的新的海上航线上的财富。
东非
东非也卷入到了陆上通道和海上航道的网络之中。其结果对一个1400年的旅客来说是很明白的。
住在东非的大致是说班图语(Bantu)的人口。虽然他们的历史尚有待阐明,但是考古学、比较语言学和民族历史学的证据都指出他们源自喀麦隆(Cameroon)中部。由此,两支人口以不同的方向向外迁移。第一支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东迁通过苏丹王国地带,从事谷物的生产、动物饲育和铁器制作。到了公元前1000年,若干属于东面一支的人口群,已到达东非大裂谷和坦桑尼亚的高地与肯尼亚的南部。公元前500年前后,这一支转向南行,跨越维多利亚湖(Lake Victoria)附近的热带雨林。由这一个入口,说班图语的农耕者和牧人向南往德兰士瓦(Transvaal)行进和向西南行进到达赞比亚(Zambia)中部、津巴布韦(Zimbabwe,罗得西亚〔Rhodesia〕),进入安哥拉。公元400年前后,南行者横渡林波波河(Limpopo River)进入德兰士瓦。
第二支说班图语的迁徙者由喀麦隆向南,沿海岸和河边的路线到达刚果河河口。他们与东行的饲育牲口和制铁器者迥异,仍是使用石器耕种并且食用根茎类农作物。在基督纪元开始前后,这两支民族可能已在安哥拉的北部会合。到了公元500年,他们向东继续扩展进入赞比亚和扎伊尔(Zaire)的东南部,开始了历史上清晰的建国过程。他们在前进时驱逐了当地原来从事狩猎采集的人口:说克瓦桑语(Khoisan)的原住民被逐入荒凉的西南非洲。今日他们仍是住在西南非,一部分是饲养牲畜的霍屯督人(Hottentot,或叫科伊科伊人〔Khoi-Khoi〕),一部分是采集食物的布须曼人(Bushmen,或叫桑人〔San〕)。
这些扩张的班图人逐渐与近东和亚洲的商人接触。至迟在10世纪,东非已有阿拉伯的商站,将奴隶、象牙、铁、犀牛角、乌龟壳、琥珀和豹皮输出到印度和印度以东的地方。早在7世纪,中国的文献便有来自黑非洲奴隶的记载。到了1119年,据说广州大多数的富有人家都蓄有黑奴(Mathew, 1963:108)。很可能牵涉这种早期外销贸易的是来自苏门答腊三佛齐王国(Kingdom of Sri Vijaya)的马来人,因为他们在8到11世纪控制了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贸易。虽然阿拉伯人可能从8世纪起便占有桑给巴尔岛(Zanzibar),但是东非第一个重要的港埠似乎是基尔瓦(Kilwa)。自11世纪起,它控制了由罗得西亚南方来的黄金贸易。其他重要的基地是摩加迪沙(Mogadishu)、基西马尼-马菲亚(Kisimani Mafia)和马林迪(Malindi)。当联系安纳托利亚和波斯湾及印度洋的贸易路线的重要性在13世纪超过蒙古人支持的大陆路线时,东非黄金、象牙、红铜和奴隶的贸易大幅增加。东非因此成为南海贸易网络的一个重要部分。东非由外销所得的回报,是印度的珠子和布匹以及中国的瓷器(大多为明代的瓷器)和由缅甸及越南来的陶器。
黄金贸易对非洲内地有极大的影响。到了9世纪,金矿的开采(有时开采到超过100英尺的深度)在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之间的地区十分活跃。“出口的黄金量可能异常巨大。”(Summers, 1961:5)采矿的人是使用铁器的牲口饲养者,可能也有一些农耕者。1000年左右,它们逐渐为新来者所支配,这些人可能说的是修纳语(Shona)。这些新来者与矿工住在一起,有石头造的大本营和仪式中心,最有代表性的是津巴布韦遗址。其首领接管了与海岸阿拉伯人的黄金贸易,并且攫取了林波波河河谷的象牙与红铜。赞比西河河畔的英格比伊莱德(Ingombe Ilede)的众多墓葬尚可看到他们对内地的影响力,可清楚看出红铜、铁和黄金贸易的范围十分广阔。

图2-5 班图语族迁徙路线图(After Phillipson, 1977; courtesy of the author)

图2-6 东非史前时期的采矿区
1400年,统治津巴布韦修纳人的是罗兹韦王朝(Rozwi),即穆塔帕王国(Mwene Mutapa)。早期的葡萄牙旅客和日后对这个地区的口述历史,都曾描写过这个政治体(Abraham, 1966)。我们知道的关于这些人的事情,使我们对于一个以进入半球性质贸易网络为基础的政府的形成情形,有异乎寻常的一瞥,也可以认识到一个发展中非洲王国的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在这些记载中修纳人是父系社会,他们组成若干“部落”或亲属团体。每一个团体都与祖灵有关系。这些祖灵的主宰是一个或一个以上代表和维持部落酋长制度创建人及其后裔群体的灵(Mhondoro Spirits)。在这些酋长祖灵之上的是奈比耶(Nembire)皇族的祖灵,它是皇族与神之间的联系者。津巴布韦同时是奉献给泛修纳神祇的仪式中心和麦比耶(Mbire)统治者的政治中心。这个政体统治者的荣誉称号是木威奈·穆塔帕。对土地的最终统治权属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又将土地的权利授予父系世系群的酋长们。这些酋长将来会成为“姆虹多罗”(Mhondoro)等级制中的资深部落神“姆虹多罗”之灵。为了回报最高统治者,得到授权的人贡献给他黄金、象牙、武器、牲口和锄头。而这些货物又被用作与海岸贸易的商品。虽然木威奈·穆塔帕的中央集权政体在15世纪中叶就崩溃了,但是后继的酋长国在新兴的葡萄牙人与东方的贸易中将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奈维特(Malyn Newitt, 1973:32)说:“东非的黄金与象牙被用于购买印度的香料。而香料是葡萄牙在东方主要要找的东西。如果不能控制这种贸易,葡萄牙人便永不能与伊斯兰教徒在印度的市场上一较高下。”
南亚和东亚
向东走横渡印度洋,再向东就是印度和中国及东南亚列岛的广大区域。罗马帝国早期曾一度繁盛的印度与西方的海上香料与黄金贸易,在2世纪以后已经式微(Wheeler, 1955)。这个情形使印度转向东南亚开展贸易(Coedés, 1964:44—49),而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接管了到东方的路线。4世纪和7世纪早期,广州有阿拉伯商人的居留地(Leur, 1955:111)。一直到10世纪,中国人还使用阿拉伯或伊朗的船只,以及中国南部和中国诸海非汉人的航海民族的船只,将货物载运出国。因此,在亚洲南部、东部和西部的核心地区之间,它们久已有贸易的关系。
可是印度和中国的发展,依靠的主要是农耕生产的过剩产品,而非对外贸易造成的关系。在扩张的过程中,印度和中国都发明了特殊的经济和政治措施,将取用过剩产品的人和生产过剩产品的人联系在一起。这些都是需要从其本身来研究的。我们稍后也会谈到东南亚,那里是中国与印度的交会点。
印度
我们这位观察者于1400年在印度各地旅行的时候,会看到许多已经成为废墟的城市。帖木儿于1388年入侵印度北部,击败了突厥-阿富汗苏丹们的军队。1398年他劫掠德里,屠杀其居民,将苏丹们的财富掳回了中亚河中地区。虽然新的阿富汗王朝在15世纪中叶开始重新巩固了部分势力,但是印度北部的政治局势自帖木儿入侵以后长期处于混乱状态。
如果我们这位旅客行经印度的村落,他必然会对当地人口长久以来分化出的世袭种姓制度有深刻的印象。早在公元前300年,出使旃陀罗笈多·孔雀(Chandragupta Maurya)王朝的马其顿大使,便曾汇报过一些种姓制度的特色。16世纪初,陪伴麦哲伦绕行世界的葡萄牙人巴博萨(Duarte Barbosa),也详细描写过这种种姓制度。(英文中的种姓制度“caste”是由葡文中的“casta”而来。)因而,种姓制度在印度有漫长的历史,它在欧洲人来到印度之前和之后,形成了这个次大陆上诸民族之间的关系。因而,我们需要详细且循序渐进地考查这个制度,它不但影响了变迁的方向,而且受到变迁的影响。
在印度语中,种姓制度一词的词根是“jati”。“jati”由“jan”(生产、生育)而来,其意是指由一个共同祖先生产的世代或血统。这个共同血统的观念可以引用于不同层次——大家庭、家系、地方层次的家系、一个区域中的家系丛以及阶级说(varna)的最高范畴,这种说法将所有单位分为四层阶序,最低的是失去阶级的人(Outcastes)——“不可触及的”或“贱民”的阶层。说什么人属于什么阶级,视在当时脉络中的利害关系而定。在有的情形下,若干阶级可以被合并以方便强调共性或联合。当情形有变化时,它们也可以分开(Béteille, 1969:157)。虽然各部分可以不断地分分合合,但是它们彼此之间也有高低顺序。种姓的高低代表了纯净或污染,这一点使印度人认为种姓制度的次序稳定而合理(Dumont, 1970:44)。
一群有亲属关系的人为了组成一个种姓,必须固守某些习俗,如饮食习惯或衣服式样,并举行共同的仪式。如果某一个种姓的一个部分想与同一个种姓的另一个部分分开,则它必须发展特定的习俗和仪式。如果两个部分合并,则必伴随以习俗和仪式的合并。虽然这个制度的指导原则说它的各种安排是静止固定的,但是实际上它里面可以有许多伸缩性和流动性。由于种姓的资格关系到经济与政治的权力,任何一个部分的行动都会影响到其邻近的部分。因而,任何一个种姓的流动,都会受到其他种姓对抗力量的阻挠。不过,在种姓阶序中,有些部分显然上升,有些部分就显然下降。最后,外人也可以在这个制度中占有一席之地。通常新的征服者可以爬到接近阶级组织顶端的地方,成为刹帝利武士阶级(Kshatriya)。非印度民族的群体也可通过被归入一个阶级的类别,从而进入这个体系。
然而,为了具体了解种姓制度如何作用,我们必须超越亲属组织和仪式特色去看种姓制度的政治经济。任何一个特定省份都有若干世系丛掌握领导和支配的职位。在其中心是首领的世系。这些具有支配权力的世系互相通婚,在全省范围内加强其统治地位。它们以仪式展示其地位,所以其支配形式不仅是政治性的,也是仪式性的。统治阶级中的各部分,在每一个村落中以地主和战士的身份控制当地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在省这一层级上,由支配的种姓来担任统治者,让省在政治上成为一个“小王国”(Dumont, 1957)。这样的小王国往往是一个更大的国家的一部分。省统治者在这样的大国家中政治地位如果上升,则在这个省中统治的种姓,其影响力也上升;地位若下降,则会威胁支配种姓的地位与团结,有可能使它降低到村落层级。
在概念上,种姓层级最高的是僧侣的亲属丛,或叫婆罗门(Brahmins)。他们是宇宙秩序、价值和规范的支承者(Dumont, 1970:68)。他们具体表现最高度的仪式纯净性。他们不会污染在他们之下的任何人,但却可被这些人污染。他们主持宗教事务,并按照古代梵文典籍作为行为标准。因此,纯净程度较低但想要增加纯净程度的种姓,便效法婆罗门的习俗和仪式,并由僧侣处求得认可。于是,婆罗门模式沿着种姓制度从上到下受到较低等级的效仿(Srinivas, 1961:Chap.1)。然而,模仿僧侣并非唯一取得较高地位的办法,也有人模仿武士和商人的模式。
婆罗门保证仪式的纯净;刹帝利,也就是武士阶级,表示权力。僧侣是宇宙秩序、价值和规范的承载者,而武士的领域是力量、财富和利己主义(Dumont, 1970:66)。但是由于力量创造权力,最终将等级和分支牢牢地黏合在一起的是武士阶层。在一个村落或几个村落中,地方的支配种姓尽到战士的职能。在意识形态上,这个统治的世系代表村落层次的皇家职能(Dumont, 1970:66)。因此,武士的权力是这个系统真正的关键,不管是谁,只要可以运用或夺取这个权力,便是以武士的身份起作用(Jayawardena, 1971:118)。不过在某些情形下,当商人群体的重要性超过武士时,较低阶级会想取得商人的身份(Sinha, 1962)。因此,种姓的分类可以配合权力与影响力的变化。而地方或省的许多世系,可以借此操纵而加强或扩张它们在更大地区中的地位。在国家的层次上,国王甚至可以重新分配种姓身份(Hutton, 1951:93—97)。在市镇中,种姓身份往往不如手工业行会中的会员资格重要(Lehman, 1957:523)。甚至在村落中,支配种姓的地位也不是绝对的。虽然支配种姓可以通过宴乐、交易和仪式来表示与服务种姓的特殊关系,但是其他较低等级的种姓却可以用模仿婆罗门的举动加以抗衡,以表示他们与支配种姓作对(Heesterman, 1973:101)。
地方的支配种姓,其手中最有力的王牌是对村落土地的控制。在英国人于18世纪开始土地改革以前,印度流行若干形式的土地所有权。其中一种形式是“bhaiacharya”保有权。在通行这种保有权的地方,支配种姓的一部分占有全部的土地。他们周期性地根据家户大小和需要的起伏把土地重新分配给他们的家户,这些人需要集体付给土王租金。另一种是“pattidari”保有权。在通行这种保有权的地方,土地根据宗谱地位分给支配种姓的一部分家户,但是租金仍是以一个单位整付。第三种是“bighadam”保有权。在通行这种所有权的地方,占有的土地面积大小不等,占有土地的人依自己占有土地的大小付租金。在英国人到来以前的印度,这些保有权的形式和税收的办法互不排斥,而构成在一个连续统一体上不断变化的点。持续的土地分割或强大的国家压力,可以削弱亲属纽带,也可以使根据宗谱等级的保有权,变化为根据家户需要的配给物。如果一个上升中的世系的首领逐渐拥有权势,保有权的变化也可以逆转。这些保有权制度的基础是亲属关系的权利和义务,包括要求支持的权利和首领要求亲族劳力和效忠的权利。因而,当这些要求发生增长和衰微的变化时,他们对土地的权利也有变化。当英国人接掌印度时,他们解释这些人与人之间浮动的关系为欧洲式的各种固定财产形式。他们制定了一个他们认为是财产法的自由制度,但事实上却取消了以前各种办法的适应能力。
两类人在村落中没有土地权。第一类人是以工匠或理发师身份给地主群体服务的种姓群体。他们可以与一个特定的地主家户有关联,也可以为整个地主种姓服务。这些村落中的仆人拥有自己行业所用的工具,而且得到一种“生活的保障”,这一点使他们与既无行业工具又没有世袭基础来对土地要求权利的那一种人迥异(Meillassoux, 1974:102—103;Newell, 1974:487)。这些人或是无土地的劳工或地主的自愿佃户,有些兼职皮革工人或鼓手。他们是村落统治阶层可以使用的劳力(Mencher, 1974),构成所谓“不可触及的”种姓。由于他们与较高阶级的关系有若干禁忌,他们的地位更形低下。这种不可触及的世袭阶级,其分布与生态的因素有关。不可触及的种姓主要集中在北部印度河-恒河平原人口密集的灌溉区以及南方肥沃的沿海地带,在这些地方他们大多是农业劳工。在比较干燥的多山地区,地主自己耕种土地,工匠往往来自较贫穷的地主阶级。事实上,随着资源的萎缩,村落地主有时将不可触及种姓的劳工逐出村外(Newell, 1974:487—488)。得以留在村中的劳工,主要听从村落地主的吩咐和命令。
印度社会的整个体系建筑一方面是蜂窝状和分节的,另一方面在不同的小穴窝与环节之间又可产生联系。这个情形最好在印度的政治生态学背景下加以了解。印度至少有三个。第一个是恒河平原的印度;第二个是沿海地区的印度;第三个是中部山区德干高原(Deccan)的印度。恒河流域的印度雨量丰沛,密集种植稻米。在历史上它是印度国家形成的中央地区。公元前322年—前185年,这儿是孔雀王朝的政体中心。300—600年,笈多王朝的君主(the Guptas)在此享有统治权。沿海地区的印度有一系列的河流三角洲和海岸地区,如沿东部科罗曼德尔海岸(Coromandel coast)的安得拉(Andrah)、泰米尔纳德(Tamilnad),西部的喀拉拉(Kerala,沿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 coast〕)、康坎(Konkan)和古吉拉特(Gujarat)。沿这些海岸的港埠,久已在长途海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第三个印度是德干高原上的印度,它由连续的大小山脉与另外的两个印度分开。分开德干高原与北方恒河平原的是一个山区,里面仍住着说南亚语言的人。分开德干高原与沿海低地的是东西高止山脉(Western and Eastern Ghats)。德干高原本身气候干燥,其自然植被是灌木丛,而其主要的作物如粟,都是旱地作物。用从零星水塘汲来的水灌溉,也可生长稻米和别的作物,但是往往在最需要水的时候水塘便干涸,这使德干高原成为一个周期性缺乏粮食的地方。
印度半岛今日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但是造成这种情形的密集的人口聚落和农业生产,其过程却是缓慢和不连续的,以至仍有一些零散区域掌握在食物采集者和刀耕火种者的手中。当中央集权的国家出现时,它们便使用权力赞助定居者同业公会或婆罗门组织从事清除、灌溉、深处采矿和边疆殖民的工作。但是政治上的中央集权不多见,只在孔雀王朝和笈多帝国的统治下达成,而也只有在恒河平原。在其他时候和地方,普遍的政治单位仍旧是“小王国”。“小王国”是由高级世系的土王统治的范围,它常常没有能力动员人民从事农业的扩张。再者,德干高原只能用零星的池塘灌溉,其结果是人口分散而非集结在一个水力核心地区的四周。在比较适宜但孤立的生态环境中,殖民与聚落的分散更使人口的分散和划分加剧。定居地区之间的地带,仍掌握在以亲属关系为原则组成的群体之手,他们敌视这些入侵的定居小邦。因而,印度文化范围的扩张,与中国文化范围的扩张,形式很不一样。中国的扩张是在于扩大一个同质的水力核心地区,将刀耕火种的农业人口逐入西南山区。印度的情形相反。印度给予各种不同人口在较大种姓网络中不同的地位,因而将它们都纳入了这个网络。
针对分裂,婆罗门提供了反抗的力量。在每一个个别的地方上由地主、工匠和奴仆组成的小单位,都由地方性的仪式和对一个“小”传统的崇拜团结为一体并为神圣的梵文经典所支持。无首领的民族群落,如果使其头人被认可为武士,将其妇女嫁给婆罗门和采取梵文的传统仪式,也可以变成较大文化网络的一部分。这些方式一直持续到今天,许多“部落”的成员因接受婆罗门的裁判而成为印度人。(山区说南亚语言的“在册部落”〔scheduled tribes〕,今日尚存。他们一直到今天都还用自己的人作为主要的诠释和教授宗教者,而不把这个地位给婆罗门〔Cohn, 1971:19〕。)婆罗门通常也引入一些新农业技术,比如犁耕农业和新作物,并与较广大的贸易和市场网络连接。邀请婆罗门在其村落中定居的国王和雄心勃勃的统治者,也授予婆罗门土地(Kosambi, 1969:171—172)。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婆罗门的支配势力和种姓制度模式在各农业地区和村落的重复出现,是回应生态学和政治上的划分。它一方面联系起僧侣、武士和商人这些高级种姓的成员,一方面将这些阶层的地方性种姓分支与地方上的工匠及附属群体联系起来。照希斯特曼的说法,它是“穷人应付帝国的办法”(Heesterman, 1973:107)。莱曼认为种姓制度模式将有组织性的服务与文化技巧引入印度乡村的结构,制衡了因长期有效中央权威的崩溃造成的漫长时期的紊乱(Lehman, 1957:151—152)。
以种姓制度为基础的农村结构,许多世纪以来,抗御了外来征服者一再的猛烈攻击。想统治印度的人,一个又一个派遣军队由山脉以北的大草原地带下到印度平原,通常是走由巴尔赫穿过隘口进入旁遮普(Punjab)的路线。1到3世纪是说伊朗语的塞种人(Sakas)和贵霜人(Kushan)。5至6世纪是蒙古-突厥的白匈奴(Epthalites),其分支古加拉人(Gujaras)留在印度成为拉杰普特人(Rajput,意为“王族后裔”)。11世纪是波斯化了的突厥人(伽色尼人〔Ghaznavids〕)。12世纪是来自赫拉特(Herat,古尔人〔Ghorids〕)的阿富汗人。13世纪初年是突厥王朝的古尔奴隶和蒙古人。14世纪晚期是帖木儿帝国已波斯化了的突厥人。15世纪是阿富汗人。
1525年,帖木儿的一个后裔巴布尔(Babur)在面对乌兹别克征服者时放弃了中亚河中地区,转而征服印度。他在击败阿富汗人和印度拉杰普特人的反对势力以后自立为王。他开创的统治体系,日后统一了印度次大陆大半的地方,并且一直统治到英国人占领印度为止。不过,这个莫卧儿王朝(Mughal Dynasty)只是一连串起自中亚草原地带的精英中最晚的一支。就其特征来说,他们根本不代表“传统的印度”,其实他们新赢得的势力,建筑在比他们自己更古老和坚实的社会构象之上。
中国
在中国丝路的东端,我们的旅客看到的是北方游牧民族与在长城以南定居的农耕者之间持续互动的另一个主要部分。在此前的世纪中,中国不断受到北方“野蛮人”的攻击。11世纪早期,来自热河的说蒙古语的精英——契丹(辽),曾经占领淮河以北的中国。几年以后,由来自中国东北地区森林地带的通古斯族女真人取代了契丹,其领域一直扩张到长江沿岸。到了11世纪末,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人已同时消灭了北方的女真人和当时仍旧统治江南的宋朝,并且跨越南方的山岭到达缅甸的八莫(Bhamo)和越南的河内。然而,蒙古诸王旋即内讧。到了1370年,明太祖将蒙古人逐回蒙古,结束了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因而,1400年这一年正处于明代初期汉人的再兴时期。
中国虽然迭受北方侵略,但是却构成一个有强大连续性的文化领域——黑格尔称之为“有周期性原则的国家”。这种连续性的战略条件,在于水利工程对中国的国家运作相当重要,这一点已由魏特夫(Karl Wittfogel)指出。这类水利工程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运河的灌溉沟渠,旨在将水引入农田;另一种是大水坝和水闸,使有人定居的地区不致遭受洪水的侵袭。除此以外,还有运输用的运河加以补充,使谷物可以流通到更多的地方。已知最早的一批大水利工程建于东周式微的时候(约公元前500年—前250年),其时列国激烈竞争。两个最重要的水利工程分别灌溉四川的成都平原(3500平方英里)和陕西的渭北平原(1000平方英里)。这些水利工程建于秦(公元前221年一前207年)将中国统一为一个帝国以前,可能也是巩固这个帝国的基础。运输用的运河或许也始于秦朝,但其最大的扩展却是在7世纪。水利工程的维持和扩大,逐渐成为中国政府的一大任务。为了这个目的,安排劳力和税收是历代政府最注意的事之一,而国家的式微往往与做不到这件事有关(Wang, 1936)。
7世纪以后,在江南进一步的农业殖民,使中国的财富增加。在苏南和浙江,灌溉稻米的种植有重大创新,这不仅表现在引入和扩大水利工程上,还体现在耕种土壤的工具和技巧的改良上,以及更为精细的肥料使用方法上。由苏南和浙江,灌溉稻米的耕作继续向南扩散。宋朝提倡这种扩张。宋人失去了长江以北的统治权,因而急于增加其剩余国土的生产力。较大的产量造成人口的大幅增加,而较多的人口又反过来增加了产量。606—742年,南方的人口增加了一倍;742—1078年,又增加了一倍(Elvin, 1973:206,208)。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自称为汉人,以别于其他的民族群体),或是吸收了长江以南非汉人的人口,或是把这些人口逐入不容易密集耕作稻米的地带。一度住在长江中下游的苗人被逐入云南、四川和贵州;一度住在东部海岸山区的瑶人被逐入他们现在居住的贵州。在这些无法从事精耕和维持中国官僚组织的地区,当地的酋长制和刀耕火种盛行(Fried, 1952)。

图2-7 稻田插秧,中国四川,布鲁诺·巴贝(Bruno Barbey)摄于1960年
但绝非所有的灌溉系统均为政府所修建。譬如,长江下游区域大半的水利工程均为富有的地主修筑。不过却可以说中国农业对水利工程特殊的需要,影响到典型中国官僚政治的发展。政府主办的许多任务,包括对水利工程的控制,都超越地方性或区域性贵族或团体的能力,中央政府因此创造了大量可能成为官僚的人才,使其官吏的供应可以源源不断。这些人可以执行政府层次的任务,并且防止地方上有权力者的分裂力量。

图2-8 汉族向中国南方的扩张(Elvin, 1973; courtesy of the author)
这种官僚政治有时被称为官吏制。官吏从士绅阶级中遴选出来。它的中文称谓是“绅士”或戴饰带的学者。饰带是帝国官职保有权的标记,“学者”指通晓中国经典的人。在理论上,官职只能保有一生,不能继承。可是在一生中,在职者可以免于强迫劳役和缴税,不受地方官在司法上的控制,也可以参加帝国的宗教仪式。礼节和思想意识的训练根据对经典的研习,尤其是根据对孔子谈话和著作的研习。孔子主张维持由“君子”理想具体表现的恰当社会关系。儒家典籍完成于贵族正在丧失权势而庶人正在兴起的时代。这些典籍叙述一种贵族式的举止,但是有功的庶人也可和贵族一样采取这样的举止。接受过这种举止训练的人奉行在宗教上受认可的习俗(礼),而且以礼而不是以法(实际的法律)裁决冲突。
虽然自秦始皇或秦始皇以前便有帝国的官吏阶级,但是只在7至9世纪唐朝的统治下它才变得显著起来。唐朝用它去抵制贵族家系的势力。到了1000年,这些士绅本身也取得了经济和政治的权力。许多士绅成为强大的地主,用农民的劳力耕种其地产,无需向国家缴税,并将其官职通过“荫”的继承特权传给子孙。正如较早时期的贵族创造以祖先为根据的家系一样,士绅也开始创造由家族精英管理的强有力世系领域。这些父系世系群控制宗庙、土地和墓园,并且裁决内部争执。他们在外人面前保障自己家族的共同利益,并且通过联姻和政治关系扩大势力范围。这样的世系群在中国的南方尤其凸显。在南方,他们往往是拓殖官员。事实上,中国大多数最有权势的世系群均可溯源到宋朝,也就是可以溯源到长江以南农业扩张的关键时期(Hu, 1948:12—13)。因而,可以了解为什么自14世纪末汉人的统治恢复以后,明朝与清朝的皇帝均力求控制和排斥士绅愈形独立的权势。明朝取消了“荫”的特权,并规定所有想任官职的人都必须参加科举考试。然而,只有在18世纪,满族政权清朝才用取消农奴制的办法削弱了士绅对土地的把持。
因此,士大夫阶级显然既非只是委身于由政府具体表现的较高理想的哲王,又非一个单纯的地方性地主阶级。他们的作用是将中央制度和地方性及区域性的制度予以衔接。他们的立场不免是矛盾的和容易改变的,要看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利害关系哪一个占上风而定。
士大夫阶级的作用和性质逐渐改变,而农民阶级的作用和性质也在改变。在公元前221年统治中国的秦国,也立法使农民有土地所有权。为此,农民直接向政府缴纳赋税,并为政府服劳役和兵役,而不向某个中介的贵族缴纳赋税,或为贵族服劳役和兵役(Wittfogel, 1931:50—51;Lattimore, 1951:441—442)。拉铁摩尔也指出,此举创造了一类无土地的人,成为永远听政府吩咐的流动人力(Lattimore, 1951:441—442)。汉朝、隋朝和唐朝初年继续这个扩大自由农阶级的政策,农民民团成为其军队的主力。他们往往没收大地产,并往往制定有利于较为公平分配土地的法规。
然而,到了8世纪中叶,这样的立法失效了,大地产迅速增加。农民民团式微,农民也不再免税。其结果是许多农民不是依附于地主以免缴税,就是出卖田地以求温饱。还有一些农民因受到威逼而成为受拘束的劳工。虽然当时也有一点奴隶制度,但其涉及的人口百分比很小(Wilbur, 1943:174; Elvin, 1973:74, n.1)。受拘束的劳力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佃户农奴,必须为特定个人服务,其身份可以继承,也可以买卖。在理论上只有士绅可以有自己的农奴,但在实际上没有饰带的地主也设法以法律上的拟制收养来获得农奴。第二种是被固定在田地上的佃户,他们可以和这块田地一起被出售。1400年,受拘束劳力耕作的庄园已是主要的地产形式(Balazs, 1964:125; Elvin, 1973:79—80)。一直到很久以后的18世纪30年代的清朝,农奴制才终于被废除。由于16世纪和17世纪农业的获利减少而别处的赢利机会增多,地主往往转而在其他方面投资。其结果是农民拥有土地的情形增加,但当时的情形与造成古代建立自由农制度的情形不同。
1400年前后,中国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开始改变。在古代,贸易和宗教的联系已使中国与邻国发生关系。在唐朝(618—906年),中国与印度的接触日增,也开门接纳来自南方的佛教影响力。在宋朝(960—1279年),南面的海上贸易大幅扩张。在蒙古人的统治下(1280—1367年),中国重新开启旧日的丝路与西方接触,并将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商人引入国内。(中国宦官郑和率领帝国舰队进入印度洋,并到达非洲海岸。郑和本人便是一名伊斯兰教徒。)蒙古君主尤其喜欢任用维吾尔人和景教徒为抄书吏和顾问,一面也削减儒家士绅的作用。
明朝在1367年将蒙古人逐出境外,并逆转了中国对外紧密交流的过程。中国于是闭关自守,断绝外交上的关系,这个情形也许是由于明人本身的本土化性格,在经过400年的外族入侵以后,明人想回到自己中国的根源。这个反动获得士绅的支持,因为在蒙古人的统治下,士绅的影响力受损,一旦外交政策逆转,他们便能从中获利。中国这个时候正有经济上的困难,中国的人口在蒙古入侵以前达到高峰,后则下降。或许如伊懋可(Elvin, 1973:298 ff.)所说的,这个反逆是工艺技术逐渐停滞的结果。技术与组织在当时已到达工业革命以前可能的生产力极限,因而造成了这种停滞。明朝力求确保中国北面边疆的安全,遂动员大军修建大运河连接南北以运输军队。这种战略强调运用国内的水路,而少用海岸的水路。这个时候日本的海盗与汉奸也正在侵扰海岸的水路。因此,在明朝的统治下,中国向后退缩,放弃了创新和探险而求取稳定。这个模式要到17世纪才有所改变。来自中国东北地区的通古斯语族女真部落联盟,借蒙古人之助与中国人的合作,建立了满族政权,也就是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东南亚
东南亚的半岛与群岛,位于印度洋与中国海交汇的地方。这是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领域相交的一个点。1400年,我们在这个区域可以同时看到印度和中国的影响力。这些影响是建立在一个较早的文化根柢之上的。这个文化根柢又以刀耕火种和旱稻临时种植为基础。东南亚大陆的“山民”(hill people)和印度尼西亚外岛的“部落群体”至今还在使用这样的耕作方法,它使得在宗谱上互相关联和分阶级的群落得以维持生存。在基督纪元开始前后,拓殖者引进了灌溉稻米的耕作方式和印度或中国的文化形式。可是,我们的旅客还是可以看到“山民”和“部落群体”的耕作方式一仍其旧。
印度对这个地区的影响力早于中国。引进印度文化的人大概是印度的商人。婆罗门伴随这些商人而来,以仪式的力量使当地酋长成为统治种姓或者刹帝利。借由授予这种仪式力量,他们创造了一个与早先在印度次大陆一样的政治基础结构。
公元前200年—公元200年,这些拓殖群体已在东南亚大陆和苏门答腊与爪哇这些大岛上定居下来。他们逐渐成为较有权势的精英,以皇家朝廷为中心,并从稻米的精耕或贸易中汲取资源。皇家朝廷的形式在各地都相当类似。其中心是一个神圣的神-王,住在同时是寺庙和堡垒的皇宫之中。与皇宫结合在一起的是国王的武装侍从、亲属群体、工匠和仪式专家。朝廷同时是权力的顶点和宇宙象征性的核心。在这个核心以外是许多诸侯(家臣)和同盟。他们贡献的资源,使中心可以报酬其徒众和加强其供养的基础。水利工程的兴建、力役的调度和拓殖,使剩余产品大增。大半的盈余都投资在兴建庞大的寺庙群,以强固皇权与超自然之间的关系,如8世纪在爪哇中部修建的婆罗浮屠(Borobudur),9世纪与12世纪修建的大吴哥和吴哥窟。这样的邦国虽然竭力加强皇家的领袖气质(或许由于这事花钱太多),但却常常是不稳固的,容易因朝代的对抗、地方豪强的反叛和王权的式微而崩溃。
尼德兰社会学家勒尔(J. C. van Leur)以这样的“内陆”邦国与他所谓的“海港侯国”做对比。“海港侯国”位于海岸或河口,不靠灌溉与劳役而靠商业。它们的食物得自附近奴隶耕耘的土地,其余来自“部落”人口的刀耕火种。这些“部落”人口通过其酋长的代办(海洋之王的臣属)将农作物供应给商业中心区。商人在这些侯国有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大半是外地人,根据其民族的来源而分开居住,各有发言人在政治和商业上代表他们。虽然有些商人在宫廷有影响力,但他们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职责。他们受制于君主及君主的侍从,并且模仿皇家随员的举止。
实际的情形比勒尔的二元理想类型更为复杂和多样。“内陆”王国和海港侯国至少有两次被囊括进同时包含它们两者的大结构中。三佛齐王国便是一个例子。7—10世纪,它由苏门答腊东部的巨港(Palembang)向外扩张,苏门答腊正好位于纵贯马六甲海峡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要道上。三佛齐王国显然是一个海上霸权,占领了苏门答腊和大半的爪哇。8世纪,它的一位皇室成员登基为高棉国王。第二个例子是14世纪核心位于爪哇东部的满者伯夷国(Madjapahit)。满者伯夷国在结构上是一个内陆王国,但是却广泛地与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大陆进行贸易。它逐渐占领了爪哇、苏门答腊、马来半岛的南部、婆罗洲和大半的菲律宾群岛。到了1400年,满者伯夷国已非常衰微,因为它的王朝发生争执而民众也在反抗它的榨取。这个情形在内陆国家层出不穷。同时,它的海上事业又因中国在南面海域的扩张,尤其是伊斯兰教在印度洋和中国海的商业世界扩大影响力而不断萎缩。随着信奉印度教-佛教的满者伯夷国的瓦解,在东南亚沿岸的海港侯国,其商人和统治者迅速皈依了伊斯兰教。
1400年,马六甲城盛极一时。它是1380年前后由三佛齐王国的一位王子率领的来自苏门答腊的一群海盗所建。这些人发动叛乱,与满者伯夷国对抗。到了14世纪末,王子皈依伊斯兰教,将苏门答腊富有的巴塞(Pasai)伊斯兰商业群落吸引到马六甲。他的伙伴变成这个新商业中心区的重要官员,并且供应他担任战争领袖、关税税吏,以及财务总长、首席大法官和皇家司礼的人选。马六甲城共有4个大贸易群落,它们各有其代表。这4个群落是古吉拉特人、卡林加人(Kalingas)和孟加拉人、来自群岛的商人和中国人。葡萄牙人皮雷斯(Tomé Pires)在一个世纪以后描写马六甲城,说它有四五万居民,61个“民族”参与它的贸易。他说:“马六甲的重要性与财富举世无双。能主宰它的人就能控制威尼斯。”
伊斯兰教信仰将散布在印度洋沿岸港口至菲律宾苏禄(Sulu)群岛的伊斯兰贸易点串联起来。游走四方的伊斯兰教苏菲派(Sufi)布道者,深入内地传教,使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与当地居民对人格化了的自然信仰互相混合。伊斯兰教尤其使新的港埠君主或海盗头目有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这些人就像伊斯兰国家的苏丹一样,是“真主在世间的影子”。港埠皈依伊斯兰教,重启了内陆国家与港埠侯国间的敌对。显而易见,这一次对商业之王们有利。最后,伊斯兰教也会主宰内陆国家。只有在巴厘岛(Bali),一群印度教-佛教的流亡者还维持着岛屿世界中完整的古老崇拜仪式。
新世界
新世界没有伊本·白图泰、马可·波罗或郑和这样的人留下游记。可是,我们可以用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历史学的证据,去重建一个1400年的旅客可能在美洲见到的情形。
这些证据指出西半球各个不同文化区域之间很可能有所互动,在有的地方更是可以确定。考古学家把表现出强烈内在相似性的地区称为“互动的地区”,因为类似工具、建筑形式和艺术风格在这些地区内部广泛地流布,指出彼此间有接触与社会关系。考古学家威利(Gordon Willey)指出,1400年美洲有两个“高等级”(high contour)的互动区域。这两个地区在考古学上的特征是从事密集型农业,包括灌溉农业;有人口稠密地带,包括建有精巧寺庙与宫殿的城市;有陶器或纺织物这样的手工艺产品(显然是为地位崇高的精英所制);以及拥有意识形态上层结构的宏伟证据(由此,精英将其掌控的势力范围的目标显示给一般老百姓)。安第斯山脉中部今日的秘鲁和玻利维亚就是一个这样的高等级互动地区。这个地区在15世纪成为印加帝国的心脏地带。但是在1400年,印加人尚是一群粗野的暴发户,他们占领了一个小地区,以高地城镇库斯科(Cuzco)为首都。另一个地区是中美洲,是今日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高地及其邻近的低地区域。当西班牙人征服美洲时,住在这个区域的是阿兹特克人(Aztecs)和玛雅人。然而,1400年我们的旅客还不太可能注意到阿兹特克人,那时他们不过是一小群佣兵,替一个较大的邦国服务。而此时玛雅人的后起精英们正自相残杀、争论不休,纷纷争夺更为荣耀的过去的遗产。
南美洲
在南美洲,农业集约化与拱形政治体系的兴起,其关键地区是绵延大陆西侧的安第斯山脉地带,安第斯山脉包含许多纵行的山脉,它们高达15000到20000英尺的山峰由高原盆地中拔起,也有适合人类居住的平原。山脉由西面的山系下降到太平洋海岸。这个海岸是一条仿佛荒漠的狭长地带。许多小河谷横切这个地带,由山坡下到大海。千年以来,沙漠和山坡地带都有农耕。沙漠借运河灌溉耕作,山脉借构筑庞大的梯田和泄水渠耕作。
安第斯山区的特色是海岸、山麓地带、高原和高地冻原构成许多迥异的环境和供给许多不同的资源,因而需要并且也可以有不同的人类活动。沿海居民可以在条件适宜的绿洲上种植棉花,并收集海鸟的粪便作为肥料。山麓地带可以生产玉蜀黍和胡椒。高原生产马铃薯和奎奴亚藜。在高地冻原,牧人饲养骆驼以取骆驼肉和毛,并且收集食盐。在安第斯山的东侧,居民种植古柯,也可由森林中取得蜂蜜、木材、羽毛和其他产品。同时,不同地带的活动往往是有所交叉的。因而,用骆驼牧人收集到的粪便作为肥料,便可提高农作物的种植海拔限度。在低处挖掘水塘和排水沟不仅对农业有利,还可以增加水的供应量和牛马的草料作物,使放牧可以延伸到较低的地方(Orlove, 1977)。穆拉认为(Murra, 1972),相近的海拔高度和交叉错杂的情况,促进了致力于生产活动的社会性组织的发展。这一点使居于社会复合体各层次的安第斯山居民(小村、村落、区域、王国、帝国的居民),都想在不同海拔高度上控制最大可能范围的生态地带。如果能使某个具有支配力的权威来控制,这是比较好的,因为这样可以系统化地聚集这些地带的资源,而后重新分配给各地带。穆拉说这就是为什么安第斯山的人喜欢通过互换和重新分配来组织交易的系统,而非通过私人和市场的公开交易,与世界上其他有密集型农业和国家体系、并在市场上交易资源的地区相比,安第斯山区的人,比较喜欢通过以等级制方式组织起来的政治群体代表之手,来引导货物的流通。
当西班牙人到达南美洲时,由厄瓜多尔的曼塔(Manta)以北到智利的毛利河(Maule River),都在印加的统治之下,但是1400年,印加的扩张才刚开始。1000—1476年,也就是印加开始统治以前的一段时期,事实上是政治崩溃的时期。考古学家称之为晚期中间期(Late Intermediate),因为它发生在早期统一时期和晚期印加统一时期之间。800—1200年,这个地区的居民曾致力于政治上的统一。从考古遗址中可以看到两种分布广远的艺术风格,每一种都与一个城市有关。一种是的的喀喀湖盆地南部的蒂亚瓦纳科的风格,一种是安第斯山中部阿亚库乔谷地(Ayacucho Valley)的瓦里城(Wari)的风格。蒂亚瓦纳科的艺术主题,如有美洲豹的嘴巴和蛇形头饰的“门神”(印加维拉科查神〔Viracocha〕的原型)和猫神,主宰了的的喀喀湖盆地,并向南伸入科恰班巴(Cochabamba)区域,直到干燥的阿塔卡马(Atacama)边缘南部。威利说这个风格是由拓殖者携带,或许是由拓殖精英携带过来的。北方的瓦里城位于曼塔罗河(Mantaro River)流域。其早期的成长大约是受到蒂亚瓦纳科的刺激。多彩和带有蒂亚瓦纳科式神话人物和动物象征的陶器,标示出这个风格的势力范围。携带来这个风格的人,大概是一些有支配力的精英。他们在乌鲁班巴盆地(Urubamba Basin)到马拉尼翁河(Maran~ón)中游和奥克诺(Ocono)到奇卡马(Chicama)沿海地区的地方性政治宗教中心,奠定自己的势力。较晚的瓦里城居留地由许多有计划的复合体组成。这个模式可能来自海岸地区,也开日后安第斯山区政权规划的先河。在这样的计划中,食物由政府管理的仓库根据区域分配,也在公路沿线和靠近重要居留地的地方安置控制站。

图2-9 安第斯山区
到了1250年,这两个较大的政治体系已经分裂为若干政治组织单位。好几个邦国为了控制高地而互相争战。另外几个邦国各主宰一段海岸地区。其中,最重要的是奇穆(Chimu),它统治着从奇拉(Chira)到苏佩(Supe)的北面海岸。其首都昌昌(Chanchan)位于莫切谷地(Moche Valley)。昌昌至少占地6平方英里,分为10个独立的有城墙围绕的方庭,每一个方庭均有住宅、天井、下陷的贮水池和墓葬。在这个中心区以外的是下属行政城镇和为数众多的村庄,由现存的证据可知在奇穆的疆域内有许多庞大的防御工事,还有一个巨大的跨山谷运河系统将水供应给各堡垒和中心。主干道的交通十分繁忙,它们主要用于流通贸易,并加强对众谷地的政治控制。日后,印加帝国使用的控制方式很可能是由这个奇穆王国传下来的。

图2-10 绘于陶罐上的战争图,秘鲁北部海岸莫切文化风格,大约绘于公元400年(Courtesy of Christopher Donnan, Museum of Cultural History, Los Angeles)
1400年,印加人在乌鲁班巴河谷的上游地区形成了一个小邦。那个时候,印加王朝大约已有200年的历史。但是一直到第九个国王帕查库提·尤潘基(Pachacuti Inca Yupanqui, 1438—1471年),印加才开始扩张。印加扩张的先头部队是职业军队,后又修筑公路和控制点以巩固征服的成果。
在印加帝国扩张的这个阶段,其社会是按照等级制来组织的一个神圣王朝。它是国家宗教的载体;它也是一个贵族政体,皇亲国戚和服从印加统治的地方统治者构成了贵族;它又是一个由拥有土地、实行内婚制的父系继嗣群构成的高等级的地区群体;同时包括继嗣群成员本身。男性通过修筑公共工程、务农和服兵役交纳赋税。妇女大半的时间织布,生产出来的布匹被集中放在印加的仓库中,以为酬劳忠实的臣民之用。织成的布匹带有不寻常的仪式价值。政府在新辟的农地上垦殖,尤其是在山麓可以种植玉蜀黍的地方垦殖。政府也维修灌溉工程和道路以及维持一个很好的邮传制度。这个邮传体系雇用送信人将音信由帝国的一端传到另一端。任何服从印加统治的人,都会在这个有等级组织和秩序良好的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但若拒绝便会招致战争,反叛群体通常会被要求迁出原居住地,前往离其故乡遥远的地方。
在秘鲁以北,安第斯山继续延伸到厄瓜多尔,而后分出支脉延伸到海岸的低地。厄瓜多尔高地的盆地不像秘鲁的盆地那么大或有生产力。但是其气候与安第斯山区中部类似,其主要作物为安第斯式的马铃薯和奎奴亚藜。然而,再向北,山脉进入亚热带和热带地区,主要的农作物却是玉蜀黍。这个地区的特色是有各种各样的地方性小气候,居民以刀耕火种、土壤选择、筑梯田和运河灌溉等变化多端的办法加以利用。这些活动的范围常很狭隘,并受到环境的限制。
安第斯山心脏地带的北缘,其特色是在地方统治者统治下的小规模政治领域,或是在一个最高统治者统治下的这些领域的联邦。在厄瓜多尔的南部,最重要的联邦是卡纳里联邦(Canari)。印加帝国在15世纪中叶毫不费事地征服了卡纳里联邦。但是在短短的60年以后,他们与西班牙人联合,摆脱了印加的统治。在厄瓜多尔的北部,是许多世袭酋长组织起来的卡拉联盟(Cara federation)。它对印加人的抵抗更加强烈。
在厄瓜多尔的海岸上,有一个航海业市镇的联盟,它们有一个最高头领,其首邑是曼塔。供养这儿稠密人口的是山坡梯田的密集型农业和广延的贸易。曼塔人长于航海,使用轻质木材和圆形木材制成的筏子,或许还曾与中美洲有过重要的贸易关系。西班牙人到来不久,曾掳获一个大的轻质木材筏。筏上有帆和舱,水手20人,载有30吨奢侈商品,由此可见这个地区贸易的规模。
在北面的哥伦比亚,最重要的国家是奇布查人(Chibcha)和泰罗纳人(Tairona)的国家。奇布查人占领了今日昆迪纳马卡(Cundinamarca)和博亚卡(Boyacá)地区的高地盆地,他们有两个分别由统治者吉帕(Zipa)和吉库(Zaque)统治的大国,以及若干小的独立国。西班牙人征服的时候,吉帕势力最盛。他在15世纪已击败若干对手巩固了自己的领土,并在16世纪早期胜过吉库。吉帕控制的人口在12万至16万人之间(Villamarín and Villamarín, 1979:31),有等级组织。许多家户群构成一个有首领的行政单位,许多有首领的行政单位形成一个半独立的群落,每一个群落对吉帕效忠,考古学家认为今日芬萨(Funza)附近的一个大遗址便是当时吉帕的首都。这似乎曾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城市,由草屋顶的寺庙、宫殿、仓库和住宅构成。山脊农田和山坡梯田生产的玉蜀黍、马铃薯和奎奴亚藜,在经济上供奉了这个国家。统治这个国家的贵族,由平民处抽取货物与劳力的贡赋。他们以农产品和纺织品,交易自己仪式和浮华消费所需的黄金。由考古学的证据看来,奇布查人的精英,因为发明了一种根据他们秘传的超自然知识发展起来的宗教礼拜仪式,而享有范围广大的文化领导权。
泰罗纳人住在奇布查人以北近加勒比海的一列山脉——圣玛尔塔内华达山脉(Sierra Nevada de Santa Marta)。其政治组织似乎与奇布查人的政治组织相似,由一个最高统治者统治若干半独立的群落。这些统治者住在庞大的中心。布里塔卡200号(Buritaca 200)遗址就是一个例子。这个遗址的使用期是1360—1635年。它沿内华达山脉北坡高峻的柯瑞亚山(Corea Mountain)山脊广布达1000英亩。这个中心有许多考究的工程,如楼梯、壕沟、马路、护墙和高坛,排列在不同的区域供居住、工作、公共典礼和宗教仪式之用。山麓梯田上的集约型农耕实行灌溉和轮耕制,生产玉蜀黍、豆类、树薯、甘薯和红辣椒。在这个遗址挖掘出的墓葬出土了精美的陶器和黄金制品。
奇布查人、泰罗纳人与哥伦比亚其他的人口,互相争战不休。这样的战事是仪式性的,是取得身份的手段,但也有经济上的作用。雷赫尔-多尔马托夫(Reichel-Dolmatoff)曾经指出,住在哥伦比亚雨量低、一年只收成一次玉蜀黍地区的人口,往往入侵一年二熟或三熟的地带,使80英尺的等雨量线简直成了军事上的一个前线(1961:86)。通过战争,人们也可以取得耕田和做家务的奴隶,这些奴隶还可以被用作宗教牺牲及供食用。
在其他好几个地区,如加勒比海岸的低地、大安的列斯群岛(Islands of the Greater Antilles)和玻利维亚南部的莫霍斯平原(Mojos Plain),其地方群落各有领袖,在一个至高统治者的统治之下组成一个较大的版图。在委内瑞拉的低地和加勒比海的岛屿上,这种版图建筑在玉蜀黍与苦树薯的耕种和海洋资源的基础之上。莫霍斯平原上的国家在河边平原上种植甜树薯和玉蜀黍,那儿人们培垄以防止洪水泛滥。这个地区与安第斯山高地有接触。譬如,据说莫霍斯的商人走到艾马拉(Aymara),以其棉布和羽毛交易金属工具和装饰物。安第斯山的贵金属和红铜便是沿这条路线到达遥远的巴拉圭河上游。16世纪征服墨西哥和秘鲁的西班牙人,就是在这里听说了西面有一个传说中的大莫霍斯王国(Realm of the Great Mojo)。印加的黄金饰物也顺乌卡亚利河(Ucayali River)而下,成为热带山区群落间贸易的一部分。
安第斯山脉以东是南美内陆的热带雨林。住在那儿的大多数人采取的是刀耕火种式的种植方式,种植苦(有毒)树薯,由狩猎和渔捞中取得蛋白质。居民通常组织成大的共同居住单位,其成员经由外婚制与婚后居留的规则被吸收进来。因而,亲属关系网络超越地方群体。首领可以动员出征,重新分配食物和其他货物,以及通过对舆论的管理协助解决争端。然而,他们没有制度化或习俗化的处罚办法。人与非人类的关系被编为神话,而形成各种力量的关系。巫师管理这些关系,他们通过使用能使人产生幻觉的药物,而与超自然接触。欧洲人到来以后,这些热带雨林的居民因疾病、抢劫奴隶、夺取剩余产品和彻底的种族绝灭而丧生。因而在1400年,他们的人数可能比之前要多得多。
热带雨林诸民族显然与安第斯山区的诸民族有重要的关系。热带雨林或许是干燥太平洋海岸若干种植成功的农作物的发源地,如甘薯、甜树薯和花生。在安第斯山区的历史上,总是拿东面山坡的产物,如古柯、羽毛、美洲虎皮、鱼毒和药品,去交易高地的农产品和工艺品。然而,印加帝国未能征服热带雨林的居民。他们跟猎头而其地富于金矿的希瓦罗人(Jívaro)作战失利。印加人向东南进军想进入低地,又在莫斯特恩人(Mosetene)占领的地区受阻。
从安第斯山中部往南,高地文化模式进入智利和阿根廷北部的荒漠地带,先是在蒂亚瓦纳科时代,后来是印加帝国时代。骆驼的放牧在这个区域很普遍,但是梯田上也有灌溉农作物。阿塔卡马人(Atacamen~o)以其范围广大的运输业著称。由于这种运输业,海岸的产品如鱼和食盐,可以用来交易高地的商品,如骆驼毛和烟草。迪亚吉塔人(Diaguita)以冶金术著称,但是印加人扩张进入迪亚吉塔人的区域以后,这和往更南方的皮昆切人(Picunche)区域扩张一样,他们想要的却是贵金属的本身——黄金、白银和红铜。印加也将说阿劳干语(Araucanian)的皮昆切人纳入其帝国之中,但是却不能征服南面说阿劳干语的人,如马普切人(Mapuche)和威利切人(Huilliche)。这些民族种植马铃薯、放牧骆驼,组织成自治的地方系群,地方系群属于由战争领袖统治的松散联邦。在比奥比奥河(Bio-Bio River)以南的潮湿的山毛榉和香柏森林,安第斯山的生态和政治模式延伸到了其南面的极限。印加人无法再向远处渗透。
中美洲
1400年,我们虚拟的观察者在中美洲见到的情景,比当时在安第斯地区见到的在政治上更分崩离析。墨西哥谷地的主要中心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在1世纪称霸于中美洲,南面至少到今日危地马拉市附近的卡米纳尔胡尤(Kaminaljuyu)和森林地带佩滕(Petén)的心脏地区蒂卡尔(Tikal)。特奥蒂瓦坎城在极盛的时候约集中了15万至20万人,几乎把四周的人群都吸引了过来。供养该市的农艺技术,大约是在附近冲击湖岸边修筑的运河灌溉和密集排水系统。它还控制了许多大黑曜石矿场,并有无数生产黑曜石工具的工场。可是到了700年,广大的特奥蒂瓦坎体系崩溃了。

图2-11 中美洲(Adapted from Weigand, 1978; courtesy of the author)
这个体系崩溃的原因无法详知了。很可能是由于当农业生产力到达扩张的决定性极限时,控制人口的宗教和政治机制衰退。在此之后,原来特奥蒂瓦坎城的居民纷纷搬回乡村地区,住在自己田地近处的较小聚落。同时,似乎贸易的体系也大为衰退。好战的团队外徙,向北到达绿松石的矿源,向南到达出产当时货币交易主要媒介(如珍贵的羽毛、黄金、可可豆)的地方。
特奥蒂瓦坎城的失势,连带使佩滕热带森林中的许多玛雅城市也衰微了。这些城市排水农业的扩张或许也遭遇了决定性的极限,而且显然也是过分将人口集中到城市的复合结构之中。或许像拉特耶(Rathje)所说的,玛雅地区周边生产黑曜石和玄武岩的人,已不愿将这些玛雅中心缺乏的对象供应给玛雅人以换取宗教上的赦免。相反,他们或许是想将珍贵货物的交易网络掌握在自己手中。

图2-12 尤卡坦半岛奇琴伊察(ChiChén Itzá)的战士庙壁画(1200年左右),描绘了乘舟的战士、从事日常工作的村民与一场奉献祈祷的仪式(Courtesy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New York)
特奥蒂瓦坎城灭亡以后,各路好战精英夸示各种不同政治合法性的象征,瓜分了特奥蒂瓦坎的世袭财产。这些后继邦国互相掠夺战利品,并且四处找寻新的领域。在一段短暂的时间里,中美洲心脏地带和重心北移到墨西哥谷地以外伊达尔戈(Hidalgo)的图拉城(Tula)。图拉成为托尔铁克人(Toltec)的首都。托尔铁克不是一个统一的帝国,而是多群战士、商人、农民和僧侣的聚集相交地区。这些人使用托尔铁克人的名号与象征,作为他们征服和殖民的特许状。有些群体向更北的地方迁徙,将耕作扩张到墨西哥高原以北的干燥地带。找寻绿松石、明矾、食盐、香和粗铜的托尔铁克殖民者或商人,可能曾经远达今日美国的西南部。
还有一些群体向南征服尼加拉瓜、危地马拉高地和尤卡坦半岛。12世纪,一个来自塔巴斯科(Tabasco)低地说琼塔尔语(Chontal)的普顿人(Putún)组织控制了尤卡坦半岛,并在奇琴伊察建都。这种迁移也许是试图将食盐、棉布、蜂蜜、柯巴蜡香和奴隶由塔巴斯科输入洪都拉斯,回程中由中美洲运回可可、黄金、玉和黑曜石。这些普顿人似乎与图拉高地的托尔铁克人结盟了。在图拉于1200年式微以后,普顿人控制的奇琴伊察也式微了。普顿人的一个分支迁徙到玛雅潘(Mayapan)的一个新中心。15世纪中叶,玛雅潘城也崩溃了,继之而起的是许多互相争战的小国家。
1400年我们的这位访客,在中美洲心脏地带墨西哥谷地这里,也会看到5个不同城邦间的冲突与争斗。主宰每一个城邦的是一个独立的精英集团。当时由一群说奥托米语(Otomí)的特帕尼克人(Tepanec)统治的阿斯卡波察尔科(Azcapozalco)城邦,显然势力日增。当时不会有人能预料到仅仅30年以后,这个城邦就毁于阿兹特克人之手。更准确说来,这群阿兹特克人应该是库尔华-墨西卡人(Colhua-Mexica),他们那时候不过是为特帕尼克人服役的一队佣兵。
北美洲
公元1000年以后,中美洲的两股影响力进入北美洲,一股由“托尔铁克”殖民者和商人带进干燥的西南部。这些新来者影响了霍霍坎人(Hohokam)和阿纳萨齐人(Anasazi)。霍霍坎人住在希拉河流域(Gila River Basin)的灌溉农地上;阿纳萨齐人住在科罗拉多高原(Colorado Plateau),以其多户口的大型复合建筑结构著称,采取灌溉和梯田式的密集型农耕方式维生。典型的西南仪式艺术大多来自托尔铁克时期末期(约1300年),并且似乎是中美洲雨神崇拜和当地各种宗教传统的融合(Kelley, 1966:107—108)。可是不久以后,定居生活的边界就急遽退缩了,因为愈来愈甚的干燥和战事使占领边境农业地区较为困难。
在中美洲影响力向西北方向延伸进入沙漠的同时,它在东北方向扩散到密西西比河、密苏里河和俄亥俄河汇流的温暖潮湿森林地区和河边的港湾,形成的文化被称为密西西比文化。在干燥的西部,今日可以复原中美洲影响力进来的路线。可是我们尚不知道聚落模式、建筑和仪式性艺术风格的原型是循什么路线到达密西西比海岸的。规模宏大的梯田状土台,围绕在城市广场四周,土台上面有寺庙、精英住宅和其他建筑物,与在墨西哥见到的特征有属类关系,而像哭泣的有翼眼睛、上有眼睛或十字的人手,以及人类的颅骨和肢骨这种引人注意的艺术刻画,又与增加的“南方崇拜”有关。但是只在陶器技术和被毁伤的牙齿上,才有确切的相似之处。有人说可以用与中美洲长距离贸易的商人(如阿兹特克的波其德卡〔pochteca〕)的接触来解释这些与中美洲相似的特征,可是我们对这些商人当年在东部森林地带寻找什么尚不清楚。
属于密西西比文化的一个较古老文化丛,叫“土丘墓葬”(Burial Mound)。“土丘墓葬”的得名,是因为这个文化丛的人将死者埋葬在土岗之下,并用从怀俄明远到东海岸地区得来的讲究、区别身份的物品殉葬。这些殉葬品说明有一个高级社会,并且它通过共同的象征体系与广大的地区沟通。不过纵有这种广延的互动,地方上的食物系统却变化多端,其中包括动植物和当地种植的细小动植物(如向日葵、假苍耳等),还有玉蜀黍。
相反,密西西比文化的人仰赖玉蜀黍、南瓜和豆类的耕种。这个生计基础供养的聚落模式,集中在大的市镇。大市镇有寺庙土墩和广场,其周围是有土岗的较小市镇,较小市镇之外又是一圈无土岗的村落。密西西比人的殖民地围绕卡霍基亚(Cahokia,靠近今日的圣路易斯〔St. Louis〕)的中心向外迁移,远至威斯康星州和佐治亚州。这种迁移随身携带的南方崇拜和较早的土丘墓葬文化一样注意给予死者慷慨的安葬,并且特别重视战争中的勇武。这种崇拜可能有政治上的功能。其大遗址之一俄克拉荷马州的斯皮罗土丘墓葬(Spiro Mound),“似乎曾是一个总部,在政治上获得重要地位的后裔,往往在此处借由祭拜伟大的祖先,来获取意识形态上的力量”(Brown, 1975:15)。这种墓葬艺术的原料如红铜和贝壳,由广远的范围而来,这个范围从苏必利尔湖(Lake Superior)一直到佛罗里达的浅滩。
密西西比人由密西西比河流域中部做离心式扩散。他们遭遇了周围土丘墓葬诸文化并影响了这些文化。当密西西比势力在1300年以后或许由于激烈的战事而式微以后,这些区域性的文化又复苏了。这些文化是与来到北美的欧洲人遭遇的族群的祖先,这些族群有俄亥俄河河源的易洛魁人;阿巴拉契亚山脉(Appalachians)南部的切罗基人(Cherokee);密西西比河下游的纳奇兹人(Natchez);以及密苏里河流域的波尼人(Pawnee)、曼丹人(Mandan)和其他“村落印第安人”(村落印第安人一面以村落为中心耕种,一面每年夏天也狩猎野牛)。易洛魁人和“村落印第安人”日后在毛皮贸易中将有显著的地位(第6章)。切罗基人则在发展南方棉业时被驱离(第9章)。然而,纳奇兹人后来却消失了。纳奇兹人的等级制度很复杂,分为一个以“大村”为枢轴而转动的“太阳”皇室世系群、两个并行的贵族世系群和一种被称为“臭鬼”的平民层。这个制度似乎是密西西比人与较早似加勒比海湾区传统接触的结果。18世纪,法国人毁灭了大部分的纳奇兹人,将许多纳奇兹人卖到西印度群岛为奴。剩下的纳奇兹人则与克里克人(Creek)和切罗基人混合。可是由于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富于幻想的小说《阿达拉》(Atala),他们仍生活在欧洲人的想象中。

图2-13 密西西比人的扩张
因此,我们这位1400年的旅客,在南北美洲“高等级”的两个地区,必曾目击大规模的政治分裂,以及安第斯山与中美洲影响力地带周围各邦国间猖獗的战争。除了邻近这两个核心地区的制造战争的小邦国与联邦以外,在南美的热带森林和北美的东北森林地带,尚有其他的农作地区。
当刀耕火种的农耕民族扩张进入这些地区时,他们攻击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人,后者于是撤退到边缘地区。这些狩猎采集者对于环境中资源的使用有极大的差别。住在南北美洲大洋沿岸的群体,如北极极地附近的猎人、北美洲太平洋海岸的渔人、狩猎海生哺乳动物的人和智利列岛的贝类采集者,都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在农耕所不及的山脉和大草原,其他的群体搜寻猎物和野生植物以为食物,如北方森林的猎人,从加利福尼亚山区到中美洲边界的干燥美洲地区的橡子和草籽采集者,以及南美洲查科地区(Chaco)和大草原上的驼马和鸵鸟狩猎者。这些人在欧洲人到来以前一直住在这样的地方,有时扩张进入可耕地带向农耕者挑战,比如在特奥蒂瓦坎衰落之后的美洲干旱地区,有时则会开发利用当时农业技术还无法耕作的地带。
在1400年世界的各处,各民族间互相关联,自以为在文化上有差别的许多群体,因亲属关系与仪式性的忠顺而发生联系;许多邦国扩张,将其他民族纳入较广大的政治结构之中;精英群体一个继一个出现,控制了农业人口并建立了新的政治和象征性秩序。贸易网络由东亚到黎凡特,横跨撒哈拉大沙漠,由非洲东部经过印度洋到东南亚列岛。“新世界”也有征战、兼并、重新合并和商业,在东西两个半球诸民族通过可渗透的社会界线互相攻击,导致逐渐混合和互相交织的社会与文化团体。如果当时有孤立的团体,那么也是暂时的现象,是暂时被驱逐到交互行动地区没有人过问的团体。因此,社会科学家独特而分离的系统模型和一个无时间性的“接触以前”民族志学的现在模型,都不能充分描写欧洲人扩张以前的情形。它们更不能让我们了解欧洲人扩张创造出来的世界性的联系系统。
我们的这位旅者尚未涉足欧洲。这个时候的欧洲正要发动海外扩张。欧洲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对广大的世界来说是不重要的。阿拉伯人称之为“西海上的法兰克人之地”。最初到达亚洲的欧洲人是葡萄牙人。他们在马来亚被叫作“斐林吉”(Feringhi),中国人称之为“佛郎机”(Fo-lang-ki)。中国人到后来才逐渐知道葡萄牙人和那些住在澳门的意大利耶稣会会士、尼德兰人与英国人是有区别的。在世界的另一面,阿兹特克统治者不知道来到美洲的西班牙人究竟是神还是人。不过一个有经验主义头脑的特拉斯卡拉(Tlaxcaltec)战争领袖却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将一名西班牙囚犯按在水下面,这名囚犯和其他人一样死了。来到太平洋地区的欧洲人被称为“库克人”,随库克船长(Captain Cook)而得名。这些“红毛、高鼻的外来野蛮人”,强行进入世界各部分的速度和强度,使我们不能不好好看一看欧洲。这是本书第4章要谈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