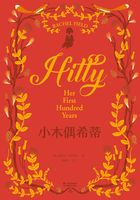
第3章 前往波士顿
因为乌鸦的抓挠、雨水的冲刷和树枝的刮擦,我的衣服已经破得不成样子。普雷布尔船长抽空为我做了一个精巧的小摇篮。经历了这些事后,能待在这样的小摇篮里,我真是无比感激。菲比的妈妈答应一有空就马上替我做几套新衣服。但那段时间,普雷布尔一家显然都很忙。因为普雷布尔船长很快又要远航了。这将是一次捕鲸之旅,他已经买下“戴安娜”号大半股份。此刻,这艘船正在波士顿接受检修和补给。
随后,九月悄然来临。海面、树叶和每一根草茎都闪闪发光,就连我这木头身子,都感到一阵奇异的春意。蟋蟀没日没夜地在枯草丛里鸣叫。它们叫得那般响亮持久,我真是头一次碰到。
“它们唱歌是为了驱走寒冷。”一天夜晚,我们三个坐在门阶上,看着那轮又红又大的秋月从海那边的岛后升起时,安迪这样对菲比说。
“真的可以吗?”菲比向来很好奇这种事情。“当然不行,”安迪肯定地说,“它们只是以为这样做可以。所以天气越冷,它们就唱得越大声,但最后还是会被秋霜冻死。等着瞧吧!”
“幸好我们不是蟋蟀。”菲比边说,边把我搂得更紧了,好像害怕我突然变成一只蟋蟀似的。
后来,所有人都上床睡觉了,整个屋子静悄悄的。躺在摇篮里,听着蟋蟀的鸣叫,想起安迪说过的那番话,我也不禁高兴起来——幸好我不是一只蟋蟀!
波特兰港和波士顿之间的邮件每周往来三次。普雷布尔船长经常骑马去波特兰港,看有没有关于“戴安娜”号的消息传来。那艘船的补给已经耽搁了不少日子,船长越来越不耐烦了。
“鲁本·索姆斯捕鲸是把好手,但修船的本事可不怎么样。”一天,普雷布尔船长对妻子说,“要想在十一月之前起航,看来我得乘下班驿车亲自去趟波士顿了。这是我最后一次从那出发,以后我都要从波特兰走!”
“哎呀,达内尔,就不能等我为你织完一打袜子再走吗?”他妻子哀求道,“一想到你可能要湿着脚在外奔波,我心里就挺不好受的。”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明天你可以跟我一起去波士顿啊!”他哈哈大笑,“你可以在路上织完它们,还能顺便给自己和菲比添置点儿时新的羊毛冬装。”
“老天,达内尔,你胡说什么呀!”她严肃地摇了摇头,“你总是这么浪费——海上都还没有船呢,就点两盏灯了!”
当时,我没听懂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这是捕鲸人妻子常说的一句话。意思是“钱还没到手就想花”。不久后,我听到了更多这样的海上行话。
不过,只要船长想做什么,总能找到办法如愿。因此,一个晴朗的秋日清晨,我们动身前往波士顿驿站。初升的朝阳中,马车“咔嗒咔嗒”,载着我们离开了普雷布尔家四四方方的白房子、红色的谷仓和那棵老松树。熟悉的景象渐渐远去,我压根没想到下个星期就看不见它们了。不,转上去往波特兰的大道时,我们谁都没想到这点。
真是个美丽的清晨啊!我永远都忘不了池塘和湿地边的那些红花槭,亮黄色的榆树和桦树,还有那火红铁线莲,仿佛把屋外的栅栏都点着了一般。去往波特兰的大道两旁,长满了麒麟草和紫苑。
“快看,凯特!”船长突然举起马鞭,“这是今年秋天,我瞧见的第一棵花楸树!”
果然,树林边缘,长着一株又高又细的花楸树,树上结满了橘红色的果子,宛如一个个闪亮的小球,把树都压弯了腰。
“那是希蒂的树,”菲比大叫,“那是魔法之树!”
“嘘,别吵,”妈妈责怪道,“不准说这种事!”
“但是妈妈,老货郎就是那么说的!”菲比坚持道,“难道你忘了,他做希蒂时,就说过这种树可以避邪!”
“这个呀,多半是他在吹牛吧!”看到妻子面露愠色,船长急忙插话进来,“好啦,管它是什么,总归是个好兆头!驾!查理,再晚我们就要错过驿车啦!”
其实,时间还很充裕。事实上,普雷布尔一家还在国会街的表亲罗宾逊家停留了片刻,吃了甜甜圈和姜饼,还喝了几杯苹果酒。再次出发时,他们把老马查理和马车都留在了那里。
现在已没有那样的驿车,也没有那般漂亮的马来拉动它们。我们乘坐的这辆红黄两色车由两匹灰色骏马和两匹栗色骏马拉着。车轮的辐条漆成了黑色。要是盯着飞转起来的轮子看,你肯定会头昏眼花。如果把脑袋伸出窗外往下看,准得晕过去。菲比可能就是这么晕车的。颠簸了大约一小时后,她便开始抱怨不舒服。普雷布尔船长、安迪、车夫和其他几个男人都爬到了车厢顶上。不过,还是有两三位女士跟我们一起坐在车厢里。她们都非常同情菲比,不住地提建议。有一位女士拿出胡椒薄荷糖,另一位掏出柠檬汁。我记得还有脱水的甘草根和家酿的云杉啤酒之类的东西。菲比把它们一一试了个遍,结果都不管用。她的脸色越来越苍白,即便马车已经平稳多了,还是只想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她恐怕脾胃弱。”她妈妈难过地摇摇头,冲其他几位女士说,“我们家的人都有这毛病。”。
真高兴我不用受此折磨。不过,当然,我也无法享用罗宾逊家的苹果酒和姜饼!我想,那些东西多少还是有点影响吧。
那天晚上,我们歇在朴次茅斯一家舒适的老客栈里,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又上路了。换上新的驿马后,车子很快便辘辘地朝塞勒姆驶去。
第二天,菲比感觉好多了。她妈妈一边跟新上车的两位女士聊天,一边继续飞快地为船长织袜子。穿过港口和海峡,农场和旷野,驶过榆树成荫的乡间公路,我们终于到达塞勒姆。这是一个停满船只的漂亮海港,有我从未见过的大房子。我们踏着淡淡的暮色,在城中漫步,看见好些砖砌的房子,屋顶的烟囱还带着个小小的方形阳台。菲比的爸爸说,那叫“船长之路”,因为站在那上面,就可以望见港口停泊的船只。一路上,菲比的妈妈都在感叹这些房子真大,门窗上的雕花那么精美,透过窗子,偶尔瞥见的漂亮家具也那么好看。
“他们买得起,”她丈夫解释道,“塞勒姆是这一带最富裕的港口。要是去码头,就能看见人们在卸下从印度、中国,还有不知道什么地方运来的货物。要是这次出海撞上大运,带回来六、七百桶鲸油的话,说不定我们也能住到这儿来。你觉得怎么样,凯特?”
他妻子却摇了摇头:“你是知道的,除了缅因州,我哪儿也不想去。可这并不影响我欣赏一下人家的大门和客厅里的窗帘呀,你说是吧?”
船长连忙点头称是。
第二天晚上,我们歇在了波士顿。一位船长打小就认识的老太太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邀我们住在她专门接待水手家庭的几间屋子里。大船都停在码头附近,透过她家楼上的窗户,我们可以看见那边一大片密密麻麻的桅杆。
船长立刻带上安迪去看他的船。等他回来时,菲比已经吃过晚饭,带着我上了床。听起来他有些担忧,不停念叨要是早些过来就好了。还说要是不想顶着秋天的大风出行,他们就必须尽快起航。几个他最得力的船员不是病了,就是跳槽去了别的船。不仅船到现在才装备好一半,他也没找到合适的厨子。看起来,最后一点最让他忧心。很显然,那一年的随船厨子很不好找。
又过了几天,船长在码头上越来越忙。我觉得,一定有什么事要发生。所以,有天晚上他回来跟菲比的妈妈长谈时,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奇怪。他俩把脑袋凑在一起,坐在桌旁的玻璃台灯边说话。因为和菲比躺在床上,所以我听到的并不多。普雷布尔船长在面前摊开几张海图和其他好些文件,一边说,一边用那根大大的食指在图上指指点点。他的妻子听得无比专注,连手中的针线活都丢在了膝头。
“好吧,达内尔,”最后,她说,“今晚我好好想想,明天早上答复你。我从没出过海,更没有在油腻肮脏的旧捕鲸船上,给一群饥肠辘辘的男人做过饭。”
“没你想得那么糟,”他对她说,“我们的船已经经过一次大整修,绝对比其他任何一艘船都好。你可以把船舱弄得像家一样舒适。至于做饭,完全可以找个帮手嘛!”
“可我只要一想到家里的厨房,”她叹了口气,“想到桌上那些果子冻,想到寄养在邻居家的奶牛,还有在波特兰大嚼燕麦的查理,就觉得自己干不了厨娘这个活儿。”
“那些事儿你不用操心。”他向她保证。
“好吧,如果非要我去,就得给船换个更像基督徒的名字。”她十分坚决地说。
“人们都说给船改名字不吉利,”船长对她说,“我倒不是非要信那些东西,但船员们信,总得照顾照顾他们的情绪吧。”对此,他的妻子却毫不让步。
“我才不管什么船员不船员,”她说,“任何取着异教徒名字的船,我都坚决不上!”
于是,船长答应再想想办法。第二天早饭时间,我们一起出海的事儿就定下来了。
这天的大部分时间,只有我和菲比一起玩,因为船长和他妻子在忙最后一次采买,以及出发前的最后准备。晚饭后,终于看见安迪让我们高兴不已。他穿着普雷布尔船长为他新买的水手短外套和海靴,忙着帮几个高大的水手搬箱子。看起来,他比一周前老成多了,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他十分看重自己船上侍者的新身份。但我觉得,对于我们也要同行的事儿,他并不是太高兴。
“人们都说船上没有女人的地儿,”他跟我们解释道,“而且他们也不会仅仅因为馅饼和甜甜圈,就想要带上你们。”
“好啦,我才不管他们怎么说。”菲比使劲摇着头,对他说,“反正我们要去。今天早上爸爸已经答应了。他是船长,他说了算!”
我们去码头时,太阳刚刚落山。但透过薄薄的秋暮和灯塔摇曳的微光,我们还是能依稀辨认出轮船、桅杆、水手和成堆的货箱。
“她在那儿!”船长突然大叫一声,指着码头边一个模糊的影子说,“菲比,那就是你的新家!你一定会喜欢她的!”
我们像一个个包裹般,摇摇晃晃地上了船。暗夜里,上方的桅顶灯发出一圈白色的微光。下方的吊索绑着个小凳子。一个男人正坐在上面,一边吹口哨,一边来回挥舞着手中的大刷子。
普雷布尔船长招呼我们过去。“这是吉姆,”他对妻子说,“正在完成您的吩咐。”见她一脸茫然的表情,他赶紧笑着解释,“他正在为这艘船刷上她的新名字!从现在开始,她就叫‘戴安娜·凯特’号!我想,你跟这位异教女神应该能彼此习惯吧?从现在开始,你们得朝夕相处差不多十一个月呢!”
就这样,我们的航行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