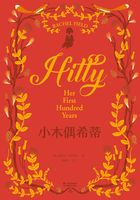
第2章 悲伤地上了天,愉快地落下地
那个夏天发生的事儿,我可以写满好多页纸。普雷布尔船长用他的轻便马车载着我们去了好多地方——波特兰、巴斯和附近的农庄。我们乘着橘黄色的旧帆船旅行,他还教安迪怎么用自制的帆布扬帆起航呢!天气很好,邻居和亲戚们也常常来家里做客,并且一玩就是一整天。北方的夏季短,那些湛蓝晴朗,白天很长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一时间,似乎所有花都开了。田野里的金凤花、雏菊和橘黄山柳菊还开得正艳,野蔷薇就已含苞待放。而当它们落下最后一片花瓣时,萝卜花和麒麟草又遍地都是。然后,我们便有数不清的浆果可采了。人们都说那年的浆果特别多,尤其是野树莓。的确,都是因为它们,我又差点被丢在外面的世界。
事情是这样的:普雷布尔太太让我们再去采一两夸脱野树莓回来做果酱。安迪和菲比打算去离家不远的一片草地,沿着路走大约一英里就到了。前几天,他们才去那采过树莓。安迪挎着一个薄木条底的大篮子,菲比则提了一个小篮子。我可以先在菲比的小篮子里坐一会儿,等采到树莓了再让位。那是七月下旬一个炎热的午后,菲比仔细地在篮子底部铺上了车前草叶,不仅让我坐得凉爽又舒适,还能避开路上的尘土和刺目的阳光。看来,当个木偶可真好啊!唉,可惜没过多久,我就不得不改变了想法。
到了那儿后,我们才发现有人已经捷足先登——灌木被踩得东倒西歪,几乎没剩下什么树莓了。
就在两人失望地准备转身离开时,安迪突然想起:“海岸那边还有个地儿!只要朝着贝克湾的方向,一直沿着海滩走,就能看到一片林中的开阔地。那儿的树莓差不多有我两个拇指那么大呢!”
“但妈妈说我们不能离开大路!”菲比提醒他道,“不管怎样,也不能去看不见大路的地方。”
“好啦,”安迪是个一旦打定主意,就不会轻易放弃的人,“是她让我们来采树莓的,不是吗?但这里已经没有树莓了呀!”
这句话的确没说错,所以安迪又催促了几句,就让菲比把妈妈的话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于是,没过多久,我们便踏上了那条通往贝克湾的羊肠小道,走在一片郁郁葱葱的云杉林里。
“昨天晚上,我听见阿布纳·霍克斯对你妈说,印第安人又开始在附近活动了,”安迪对菲比说,“他说他们是帕萨马瓜迪部落的,有好多人呢。阿布纳说他们卖篮子和其他东西,但他也说,他们全都不可信。我们最好小心点,别碰见他们。”
菲比吓得直哆嗦。
“我害怕印第安人。”她说。
“快点啦,”安迪催促道,“要去贝克湾,我们就要从这里转弯!接下来还要走一段石子路呢。”
路很难走,石头也因为长时间的暴晒而十分烫人。菲比穿着拖鞋都抱怨连连,安迪光着脚,更是一边大叫,一边跳向下一块石头。期间,他还时不时跑到岸边拍拍水,给脚降温。所以,他们折腾了好一会儿,才终于到达目的地。菲比在空地边找了棵盘根错节的老云杉树,把我放在树根中间。从这里望出去,我可以看见他们忙碌的身影。但他们要是走到树莓丛很高的地方,我就只看得见两个苹果一样的圆脑袋了,一红一黄,在绿叶间上下跳动。
这里宁静宜人。云杉树沿着山坡一直长到了水边,就像万千箭矢直指云天。湛蓝的海水闪着粼粼波光,扇贝一样的白色波浪轻轻拍打着远处牛岛的岸边。空气中传来蜜蜂和鸟儿的声音,海浪轻抚过岸边卵石的声音,还有安迪和菲比互相呼喊着采树莓的声音。我觉得,自己简直是世界上最满足的木偶!
接着,菲比突然毫无预兆地尖叫起来。
“印第安人,安迪,印第安人!”
我看见她指着我身后的树林,还看见他俩的眼睛都瞪得像门把手那么圆。我却因为无法转头,什么都看不见。安迪一把抓起菲比的手,拉着她转身就跑。他们在卵石滩上飞奔,踩得石子格格作响,篮子里的树莓也落了一地。然后,他们便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了树林里。起初,我还不相信他们就这样丢下了我,后来才发现这是真的。独自待在那儿真是可怕极了!身后传来树枝折断的“噼啪”声和一连串我听不懂的“叽里咕噜”声。靠感觉判断身后的东西,总是比亲眼看到更吓人。
结果,来的不过是五六个印第安妇女。她们穿着鹿皮鞋,挂着串珠,披着毯子,也是来采树莓的。没人注意到云杉树下的我。她们不停地往藤条篮里装着树莓,虽然黑了点,胖了些,头发也不怎么整洁,但看起来还是很友善的。有个人还背着个婴儿。小家伙眼睛亮晶晶的,像只土拨鼠一样从毯子下面探出头来,四下张望。太阳快落山时,她们才挎着装得满满的篮子离开了。
“现在,”我暗想,“安迪和菲比该回来接我了吧!”
然而,随着太阳一点一点地落下,我开始担心了。现在已是晚霞满天,海鸥成群结队地向牛岛飞去,落日的余晖洒在它们的翅膀上。要不是身处困境,我肯定会认为那画面美极了。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就像个被遗弃的小可怜。然而,和我即将遭遇的事相比,这一切就算不得什么了。
事情来得太快,我都没怎么反应过来。整个下午,我都听见远远的鸦叫声,也隐约感到附近树上有乌鸦。但我太熟悉乌鸦,普雷布尔家周围就有不少,所以压根儿没把它们嘶哑的叫声放在心上。突然,头顶传来一声刺耳的鸦叫。接着,一片黑影便向我罩了下来。不可能是夜幕降临!因为天空还是一片粉色,况且,这片黑影不仅有重量,还是暖的。没等我做出任何自救动作,一张尖利的鸟嘴就啄上我的脸,一双黄眼睛也恶狠狠地盯上了我。那简直是我见过最邪恶的眼睛。“呱!呱!呱!”
尽管我是块结实的花楸木,如此猛烈的攻击还是把我吓坏了。这次真的完蛋了。我把脸埋进清凉的苔藓,觉得或许这样,便看不到乌鸦脸上狰狞的表情。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乌鸦或许也不是真那么凶残。虽然无法改变天生的黑羽毛和尖利的嘴,但它们抓东西的确应该更小心一些。显然,这只乌鸦对吃掉我不感兴趣,因为它啄了几下后就放弃了。我能听见它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呱呱”叫得更大声。但它还挺固执,非要让我派上点儿用场不可。
突然,我感觉它叼住我的腰带,把我拦腰提了起来。我拼命想抓住苔藓和树根,却因为脚先离地,结果什么也没抓住。身下,贝克湾、云杉树林,还有那片树莓地都渐渐模糊起来。风把我的裙子吹得噼啪直响。但那时候,我也只能由着乌鸦的性子,任它抓着我,在空中忽上忽下地飞。
“这下死定了!”我这样想着,已经做好翻着跟斗,从天上掉下来的准备。
然而,天意就像乌鸦一样奇怪难测。
最终,我竟然被放了下来!好不容易回过神后,我四下一望,发现自己在松树顶一个乱糟糟的大鸟窝里。三只半大的小乌鸦正一脸惊奇地盯着我看。被一只乌鸦又盯又啄的已经够惨,三只又跳又叫地一齐朝我冲来,就更别提了。它们或许没有乌鸦妈妈那么大、那么凶,但争抢食物时尖利的叫声和大张着嘴,露出红红食道的样子,已经足以弥补上述缺憾。而且,它们总是张着嘴。看到乌鸦妈妈得不停地往那三个无底洞塞食物,我甚至都开始同情它了。然而,小乌鸦们刚把食物吞下肚,又开始“呱呱”地叫个不停。于是,乌鸦妈妈只得再飞出去觅食。我从没见过那么好的胃口,这次可算是看了个够,因为,我在那里待了整整两天两夜。
我从来没那般难受过。这鸟窝说起来一点也不小,但加上三只焦躁不安、就快长羽毛的小乌鸦,便不够用了。它们对我又推又挤,又戳又啄,似乎一点儿位置也不想留给我。乌鸦妈妈收起翅膀落了下来,不仅让鸟窝显得更加拥挤,还把窝底的我压得差点儿喘不过气。小乌鸦们在我身上又抓又挠,尖利的树枝也时不时地戳到我。真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第一个晚上的。
不过,天终于亮了,乌鸦妈妈又飞出去觅食了。坐在随风摇摆的乌鸦窝里,从松树顶上,而不是透过窗玻璃看日出,感觉真奇怪。不过,要是习惯了,其实也还不错。但窝的摇晃,加上小乌鸦不断地推搡,我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了。要是不想被挤出去,我的双脚就必须牢牢抓住窝底纵横交错的枝条。我慢慢知道了该如何变换位置,并一点一点地往高处挪,最后终于能扒着窝沿,看看外面的情况。从那么高的地方往外看,一开始可把我吓坏了。所以,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自己其实离家并不远。我估摸着,从鸟窝到我家前门,不过一段投石可及的距离。那只乌鸦刚好把我叼到普雷布尔家门外的那棵老松树上。再次看到袅袅炊烟从熟悉的烟囱里升起,看到老马查理在谷仓附近吃草,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起初,这一切还能给我带来安慰。但没过多久,我就更加难受了。眼睁睁地看着普雷布尔一家在我身下走来走去,听着安迪和菲比的声音,却没法引起他们的注意,真是太难熬。与此同时,身边的小乌鸦们仍然尖叫着推来搡去,争抢窝里的海贝和海胆。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也变得越来越难受,越来越孤单。
此刻,我看见太阳已经在松针间落了下去。一阵风吹过,激起一片松涛。如果安然坐在坚实的地上,而非危险的树梢,我一定会觉得这是片美妙的“沙沙”声。看着袅袅青烟从普雷布尔家的烟囱升起,我知道晚餐一定已经煮在锅里。很快,他们便会聚在桌旁一起吃,而我却不在。
“菲比要是知道我在这,一定会哭鼻子的。”我悲伤地想着。那只最不安分的小乌鸦又开始挤我,害我只得把胳膊从两根树杈间伸了出去。
我动作并不快,因为小乌鸦们越来越不安分,甚至连最后一点儿位置也不愿意留给我。看来,我在这儿待不长了。
夜幕降临。头上的星星又大又亮,就像落在黑幕上的晶莹雪花。我心中却涌起一股深深的绝望,比乌鸦的翅膀还沉,比这暗夜还黑。
“我再也受不了了,”终于,我对自己说,“就算被劈成柴火烧掉,也好过再受一晚上这样的折磨!”
我知道,要行动的话,就一定得赶在乌鸦妈妈觅食回来之前。于是,我开始一点一点地往外挪。必须承认,当我从窝边望出去,想着自己要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去时,确实害怕极了。那一刻,我还想起了树下那块灰色的大石头。以前,菲比和我经常坐在上面。想到这,我又一下子泄了气。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提醒自己。这是普雷布尔船长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我反复念叨了好几遍,终于做好准备。“毕竟,我可不是用一般木头做出来的!”
我要是能一步步地来,先抽出一只胳膊,再伸出一条腿,说不定这事儿还会容易些。但我的手脚都被钉子固定在了一起,要么一起动,要么就一动也别想动。
“呱!呱!呱!”
听见乌鸦妈妈的叫声,我知道再也耽误不得。幸运的是,小乌鸦们也听见了。它们在窝里又蹦又跳,动作激烈得就算我想待,也待不下去了。我举起双腿,胳膊往外一伸,“扑通”!我直直地跌了下去!
仿佛跌入一个黑色的无底洞,坚硬的松针和松果刮过我的脸,锋利的树枝接连戳在我身上。我不断地往下坠啊,坠啊,那时间恐怕比从月亮上掉下来都长。终于停下来时,我以为自己一定已经着地,可伸手一摸,周围还是松针和树枝,根本没有坚实的土地!
天亮后,我发现这个新地方总归比之前的鸟窝好点了。我没有如预想那样落到地上,而是被缠在一根比较靠外的树枝上,不仅头朝下地悬在半空,衬裙也翻了过来,真是太不淑女了!我难受极了,又羞又怒,却被紧紧卡住,一动也不能动。
然而,更难受的事还在后面。很快,我便发现,尽管能看见普雷布尔家的一举一动,但我还是像个松果一样,丝毫引不起他们的注意。松树很高,几乎到树干中部才开始有枝叶。所以,任何人站到树下,都不会产生抬头往上看的念头。于是,我就这样头朝下的在那挂了好多天,任凭风吹雨打。可最难熬的,还是必须眼睁睁地看着菲比·普雷布尔在我身下走来走去,或坐在那块大石头上。挂着我的这根树枝刚好把影子落到她的鬈发上,却无法使她抬起头来往上看。
我悲伤地想:“要是我的衣服都烂成碎片了还下不去怎么办?要是他们找到我时,菲比都已经长大,再也不玩娃娃了怎么办?”
我知道菲比很想我。我听见她这么跟安迪说过。安迪还答应要带她再去一次树莓地找我。后来,他们认定印第安人把我带走了。这想法让菲比十分难过。与此同时,我却只能像把倒扣着的伞一样,挂在他们头顶。
说来也怪,最后还是那窝乌鸦让我们得以重聚。我离开乌鸦窝后不久,小乌鸦们便开始学飞,成天嘎嘎叫着扑棱翅膀,那模样我真是从来都没见过。当然了,在那之前,我也没跟乌鸦这般亲近过。普雷布尔太太说她都快被乌鸦给吵死了,于是安迪成天举着弹弓,用鹅卵石打它们,却一只也没打中。不过,乌鸦们倒是哇哇大叫,好像真被打着了似的。一天早晨,他站在老松树下,举起弹弓瞄准时,终于看见了我。可能是我的黄裙子引起了他的注意,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花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我来。
“菲比!”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找到了什么,立刻大叫起来,“快来呀,快来看看这老松树上长出什么啦!”
他一把扔掉弹弓,向菲比跑去。很快,全家人都站到了树下,商量怎么把我弄下来。这可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树干太粗壮,就算普雷布尔船长将安迪扛到肩头,他还是够不着一根可供攀爬的树枝。因为我挂在高高的树枝上,所以也找不到足够长的梯子。看起来,似乎只有把树砍倒这一个办法了。但普雷布尔太太坚决反对这么干。她说这是棵古树,就像那个黄铜门把手,或松木梳妆台一样,是属于普雷布尔家的。安迪尝试着扔苹果,但我被卡得太紧,那样的撞击根本毫无用处。他们也不敢扔石头,怕把我砸坏。终于,我开始绝望了。
又过了一会儿,普雷布尔船长拿着一根刚削好的长桦木杆走了回来。这次他们成功够到了我,但不管杆头被削得多尖,他和安迪努力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能把我解救出来。最后,菲比的妈妈一手拿着把长长的煎叉,一手端着盘新炸好的甜甜圈,出现在厨房门口。这让船长灵光一闪。“把煎叉绑在杆子上试试,”他说,“这样我们就能勾住她了!”
他飞快地把煎叉绑在了桦木杆上。虽然离这个坚硬的铁叉子那么近怪吓人的,但我也顾不得抱怨了。当它插入我的背带时,虽然戳得比乌鸦爪子还疼,但我一点儿也没退缩。令人高兴的人,我感觉到自己真的从松枝间被提了起来!
“又多了个叉鲸鱼的办法!”他大笑着把我递到菲比手上。将煎叉交还给普雷布尔太太时,他又加了一句:“也多了种用甜甜圈煎叉的办法!”
“不用想,肯定是那些讨厌的乌鸦把她从贝克湾带回来的,”安迪对菲比说,“也不是没这可能!大家都说,它们是可恶的小偷!”
但失而复得让菲比太高兴了,她甚至没怎么为我破破烂烂的衣服难过。而我呢,只愿从此都能和菲比在一起,永远不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