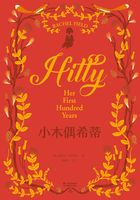
第1章 我开始写回忆录啦!
此刻,静悄悄的古董店里只剩下西奥博尔德和我,布谷鸟时钟已经在前天被人买走了。西奥博尔德最近一直都非常勤快,再也没有老鼠敢从木器后面溜出来捣蛋。西奥博尔德是一只猫,也是店里唯一的非卖品,这让他有时候表现得相当不可一世。我倒不是批评他,谁能没个缺点呢?再说,要不是他,我或许也没法在这写回忆录。话虽如此,但我知道,缺点是一回事,爪子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严格说来,西奥博尔德算不上是只坏猫,但他与“热心”也绝对沾不上边儿。还有,他不仅像鱼一样滑溜,爪子和尾巴也是我见过最厉害的。最近,他都喜欢把头搁在古董首饰盘里睡觉。前天夜里,他打个哈欠都差点儿吞掉一只石榴石耳环。亨特小姐要是看见这一幕,肯定会急得跳脚。不过,亨特小姐自从开了这家古董店,就养了西奥博尔德。而且,似乎正是因为他那些恼人的行为,亨特小姐才更器重他。亨特小姐自己就有很多怪癖,老是东戳戳、西戳戳,爱盯着别人看,还喜欢把每件东西都翻个底儿朝天。第一次看到这些怪癖时,用菲比·普雷布尔妈妈的话来说,我真觉得她有点神神叨叨的。虽然花点时间也可以适应,但按我一贯的教养来看,那些行为绝对有失礼貌。不过,亨特小姐心肠还是挺好,一旦认定你是件古董,就能为你做任何事。当她第三次在清晨发现我掉下椅子并摔了鼻子时,立刻表示每天晚上打烊前,都要把我从橱窗里拿出来。因为,她觉得自己再也不能让我这么珍贵的古董娃娃冒险。于是,我就坐到她这张乱糟糟的桌上来啦——背靠青灰色的墨水台,双腿耷拉在斑驳的绿色吸墨纸上。旁边堆得老高的账单和文件,就是一道完美的防雪堤!不远处还有一堆杂乱的文件,上面压着个老海螺壳。我曾见过比这漂亮得多的海螺壳,好吧,它只是勾起了我的回忆。看着洒在它上面的柔光,我就不禁想起南太平洋里的那座小岛和我们在那经历的一连串奇遇。店那头的壁炉架上,一只横帆的帆船模型静静地躺在玻璃罩里。不过,它的帆不够整齐,船身上的金箔也比不上我们驶出波士顿港时乘坐的“戴安娜·凯特”号。今晚,那个老瑞士音乐盒多半又要像往常那样,毫无征兆地放声高歌。坐在这里,听着它奏响熟悉的“玫瑰和木樨草”圆舞曲,感觉真是怪极了。要知道,在皮特斯先生为年轻女士和绅士们举办的那些沙龙上,伊莎贝拉·范·伦塞勒和其他人就是踏着这首欢快的曲子,翩翩起舞的。举办沙龙的地点离我现在待的地方不过一个街区,跨过华盛顿广场就是。不过,当时那儿还没有摩天大楼,也没有这种遍布小店的长街。
是什么让我生出了要写回忆录的念头呢?也许是玻璃罩里的那只船,或是那个八音盒,但更有可能是那支鹅毛笔。笔和那个青灰色的墨水台是一套的,但它早已过时,就像女士们的鲸骨裙撑和小女孩头上的阔边帽一样。不过,一个人很难忘记早年受过的教育,克拉丽莎拿鹅毛笔往她作业本上抄写的那些箴言,我可不是白看的!如果正如亨特小姐和那位老绅士所说,我是店里最珍贵的古董,那我干吗要放着鹅毛笔不用,而去用那些新发明的自来水笔呢?我可一点儿都不喜欢那些笔头尖利的铁家伙!所以,除了此刻握在手中的这支鹅毛笔,我是绝对不会用其他笔来书写回忆录的!好了,我要正式开始写啦!
据我所知,一百多年前的一个深冬,我诞生在缅因州。我自然是不记得这些的,但普雷布尔一家将这个故事翻来覆去地说了那么多遍,让我觉得当年那个老货郎用花楸木雕刻我时,我好像就在旁边观看似的。那块木头不大,就算是作为木头娃娃,我的个头也小了点儿。这木头是老货郎从爱尔兰漂洋过海带回来的,所以他很是珍惜。花楸木适合随身携带,它不仅能避邪,还能带来好运。因此,老货郎才会从沿街叫卖的第一天起,就一直把它塞在包底,走哪儿都带着。五月到十一月间他的生意最好,因为那时道路通畅,天气也不太冷。当他把货品摊开,农夫的妻子和女儿们都乐意出门来看看。然而,那一年他往北走了好远,比往年都远。最后,他被一场大雪困在了路上。当时,他已经走到一座树木繁茂的质朴村庄,再往前就是大海。寒风凛冽,转眼间,路上便积起一大堆雪,再也无法通行。无奈之下,他只得敲响了普雷布尔家厨房的门,因为那里面亮着灯。
普雷布尔太太说,如果没有老货郎,她和菲比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熬过那个冬天。因为就算加上小伙计安迪,要干的活儿还是太多——生火、打水、喂牛、喂马、喂鸡……甚至天放晴后,路还是堵了好些天。所有渔船都被暴风雪困在了波特兰港。考虑到普雷布尔船长还有几个月才能返航,老货郎决定待到明年春天,帮助他们干些零活。
那时,菲比·普雷布尔还是个七岁的小女孩,天真活泼,温和友善,一头柔顺的金色鬈发垂在脸旁。正是因为她,我才从一块六英寸半的花楸木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一个比月桂蜡烛还要矮点儿的组合木偶。于是,我最初的记忆就从这个快乐的房间开始。褐色的柔光洒满整个房间,方形洞穴似的大壁炉里,大块干柴噼里啪啦地燃烧着,旁边的活动吊钩上,挂着一只老旧的黑水壶。我平生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菲比呼唤她妈妈和安迪的声音:“快看啊,娃娃有脸了!”他们立刻围上来盯着我瞧。老货郎用拇指和食指夹起我,在炉火上来回翻转,好烤干我身上的颜料。现在,我都还能忆起菲比那张激动的小脸,以及她妈妈看到这个老头居然能在这么小的木头上雕出鼻子和愉快笑脸时,一脸惊喜的表情。当然,大家一致认为,再没有人能把水手刀用得如此娴熟。那晚,我被留在壁炉架上晾干,炉中摇曳的火苗投射出各种奇怪的影子,老鼠吱吱叫着在墙壁间钻来钻去。屋外,风从那棵大松树的枝丫间呼啸而过。后来,那声音我真是再熟悉不过了。
菲比的妈妈决定,得给我穿上合适的衣服,她才能跟我玩。菲比不是个喜欢针线活的姑娘,但妈妈的态度十分坚决。所以,不久后,她也只得拿起针线,套上顶针,翻找出各种布片,还为我量了尺寸。被选中的是一块缀着红色小花的浅黄色印花布,我觉得它真是好看极了。菲比的手艺不怎么样,而且每缝上十来分钟,她就开始不耐烦。不过,因为太想跟我玩,所以她的勤奋还是让我们都大吃一惊。我已经不太记得我的名字是怎么来的了。最初受洗时,我被取名为梅海塔布尔,但菲比实在受不了那么多音节,所以没过多久,全家人便都叫我希蒂了。而且,多亏普雷布尔太太的提议,这五个红色字母才被仔细地以十字针法,绣在了我的衬裙上。
“好啦!”绣完最后一针,菲比的妈妈说,“这下,不管发生什么事,她都不会忘记自己的名字了!”
“妈妈,她不会发生什么事的!”小女孩喊道,“她永远都是我的娃娃。”
如今再想起这句话,感觉可真奇怪。当时的我们,真是没有想过下一刻会发生什么啊!
几周后,我的小碎花裙终于做好。不幸的是,那天是星期六。按照当时的习俗,星期六太阳落山后,要到第二天晚上,孩子们才能再开始玩玩具。时值二月,太阳早早地就落到马路对面云杉覆盖的山头下了,这让菲比·普雷布尔很不高兴。她苦苦哀求,希望能跟我在炉火边再玩半小时,却被断然拒绝。她妈妈把我关进了老松木梳妆台的顶层抽屉,以免我们这位年轻的女士再受到诱惑。就这样,直到第二天早上大家都忙着准备去教堂时,我都和普雷布尔太太最好的佩斯利花呢围巾、菲比的海豹皮手筒,以及她爸爸上次从波士顿带回来的女士披肩待在一起。
对普雷布尔一家来说,每周日上教堂可是件大事。不过,他们家离教堂有好几英里,得坐很久的雪橇才能到。比起妈妈和安迪,菲比早早地就穿戴整齐了。她站上脚凳,拉开梳妆台的抽屉,很快便俯身看见了我。她原本是来拿皮手筒和披肩的,但一看见我,就再也忍不住了。可是,说句公道话,她真的努力抗拒过我的诱惑。
“不行,希蒂,”她说,“今天是星期天,太阳下山前,我都不能碰你!”
她叹了口气,仿佛在想这天有多么漫长。可没等我俩回过神来,她已经把我拿在手里了。
“不过,”她有些愧疚地说,“妈妈只说星期天不能跟你玩,但我就帮你理理裙子,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但接下来,她突然发现我刚好可以藏进皮手筒。这下,我就得跟她一起走啦。而一旦进入皮手筒,对于她接下来的计划,我便一点儿也不奇怪了。
“希蒂,没人会猜到你藏在我的皮手筒里!”她轻声说。她的声音让我觉得:这个早上,我是不会在松木梳妆台里度过了。就在那时,她妈妈急匆匆地走了进来,说得赶紧出发,否则就要赶不上赞美诗。那时,我虽然不知道赞美诗是什么,但普雷布尔太太万分焦急,从抽屉里拿披肩时,不仅没注意到里面少了我,也没注意到菲比通红的脸颊。
尽管菲比的两只手一塞进来,就没剩多少空间给我了,但待在海豹皮手筒里,还是非常温暖舒适的。当然,除了偶尔能看到几缕耀眼的亮光(我知道,那一定是反射在雪地上的阳光),其他的什么也都看不见。但我能感觉到马拉着我们赶路时,雪橇的颠簸,听得到马蹄踩在雪地上的“嘎吱”声、老货郎扬鞭的“噼啪”声和雪橇铃愉快的“叮当”声。普雷布尔太太不喜欢铃铛的声音,一路上都在责骂安迪,怪他忘记把铃铛从马具上卸下来。她说,去教堂还挂着铃铛有辱安息日的圣洁,而且,指不定邻居们会怎么想呢。安迪却说,铃铛就是铃铛,管它是挂在雪橇上,还是挂在教堂的尖塔上,不都一样吗!
结果,这话招来菲比妈妈更严厉的斥责。要不是雪橇已经停在教堂门口的台阶前,她肯定还会继续骂下去。一想到我已经来到教堂,踏进了这个任何木偶都不应该出现的地方,我就好奇得不得了。待在皮手筒里,尽管还是什么都看不见,但我能听到许多外面正在发生的事。即使已经过了这么多年,现在,我仿佛还是能听见周围人们起身时发出的“窸窸窣窣”声,以及他们的齐声歌唱:
“赞美上帝,保佑众生,
地上生灵,当赞主恩。”
听着这样的歌声,一股庄严肃穆之感顿时从头到脚,流遍我全身。
布道和祈祷实在太冗长,我终于还是听不下去了。至于菲比,她先是坐立不安,接着就倒在妈妈身上打起了盹儿。这下,我可倒霉了。我想,肯定是因为她睡着了,所以才抓不住皮手筒,让它一点一点地从手中滑了出去。然后,我便从这个温暖的藏身之地,一头摔到了地上。幸运的是,我掉下去时正好赶上人们起身做最后一次祈祷,所以谁都没听见我落地的声音。皮手筒滚到另一边,被安迪捡了起来。菲比则被一把拽起,跟其他人一起低头祷告。
我害怕极了,但在看见普雷布尔一家都起身走出去前,并未想过自己真的会被留在这里。听着门外的雪橇声和马儿的嘶鸣,我仍然盼着菲比会回来把我带走。但最终,我只绝望地听见了锁门关窗的声音。我知道,菲比的妈妈一定在催她赶紧走,而她又没胆子承认自己把我带到教堂的事。想想看,我竟然第一次出门,就落到了这般凄惨的境地。
我实在不想去回忆之后的那些日日夜夜,直到今天,我都没搞清楚自己到底在那儿待了多久。我只知道,我从来没有那般悲惨过,简直比后来遇上火灾和海难还惨。天冷得可怕,仿佛要把我的手脚都冻裂。外面寒风呼啸,吹得钉子噼啪作响,房梁“吱嘎吱嘎”地叫,还吹得门廊上的铃绳来回摆动,沉闷地响个不停。还有蝙蝠,我完全没料到竟会遇上它们!其中有一只的窝,就搭在普雷布尔一家坐过的靠背长凳下,那个角落离我只有几英寸。白天,它倒挂在一个灰球里。可一到晚上,他就会飞出来,四处俯冲,把我吓得够呛。有时他飞得低,翅膀甚至会碰到我。黑暗中,他黑色的小眼睛闪闪发光,爪子看起来也异常锋利。我真心希望,自己永远都不用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儿。此外,旁边摊开的那本插图版《圣经》也没有给我带来半点安慰。打开的那一页上,一条大鱼正把一个人吞进肚里。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真是跟他一样悲惨。
一天,我听到钥匙在锁眼里转动,顿时又燃起希望。是每周三都会来例行检查的教堂司事。我又一次充满希望——但是,如何才能引起他的注意呢?这会儿,我躺在长凳下面,被一个脚凳和一本《圣经》围在中间,连一根手指头都抬不起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老货郎觉得我每只手都只需要一根大拇指就够了。于是,我剩下的手掌便像连指手套一样,没有分开。看来,只能靠脚了。可我的脚是直接钉在腿上的,根本没有膝盖。不过,用尽全力,紧连着身体的大腿还是可以笨拙地动一动。看起来,这也是我唯一能做的事了。于是,我开始拼命地上下踢腿。
嗵!嗵!嗵!
就连我,也被自己的脚撞击旧地板的声音吓到了。这声音在教堂里可怕地回荡着。教堂司事一声闷哼,就“哐嘡”一下扔掉手中的扫帚,朝教堂后门狂奔而去,一路撞上好些长凳,还惊恐万状地咕哝个没完:
“是鬼吗?不是吧?是吗?不过,我才不要冒这个险!”
尽管很不舒服,我还是觉得十分得意——我的两条木腿,竟能把他吓成那样!
幸运的是,菲比不是个藏得住事儿的姑娘。还没到一周,她便坦白了把我带去教堂的事,并保证如果能把我找回来,她一定痛改前非。于是,她接受惩罚,坐下来绣一条特别长的花样时,安迪和老货郎便来到教堂,把我接了回去。
任何钢笔,甚至连最好的鹅毛笔,也无法写出我重返家园时的激动心情。就连普雷布尔家壁炉里的火焰,都比往常明亮了许多。能再次感受到它的温暖,看到那跳跃在锅碗瓢盆和菲比头上的明亮光线,真美好啊!当时,菲比正俯身在一块方形帆布上,用十字针法绣着这样一句箴言:
忠言逆耳利于行,
诤友不要轻放弃。
妈妈说,只有圆满地绣完最后一个字母,菲比才能跟我玩。所以,我俩能把这句话记得滚瓜烂熟,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期间,菲比哭过、线打过结,可还是过了好多好多天,完成了无数个进进出出的针脚后,菲比才终于绣完。
自从被遗弃到这个高高的架子,我就满心同情地看着下面发生的一切。对一个小女孩来说,这真是一场不小的教训。听着普雷布尔太太不停地唠叨要有良心,要小心谨慎之类的话,我真是庆幸木偶没这些规矩。从菲比放下绣样,不住叹气就可以看出,她多半也很想摆脱这一切吧。
那一年,缅因州的春天来得特别晚。直到三月中旬,雪才开始融化。之后的一个月,道路都泥泞不堪,车马几乎完全无法通行。柳树飘絮也比往年晚了好几个星期,所以安迪一直等到五月,才做成柳叶哨子。接着,突然有一天,普雷布尔家门口的紫丁香丛就冒出花蕾来了,街对面的树丛中也缀满姹紫嫣红的紫罗兰、雪花莲和獐耳细辛。当然,还有五月花,如果你知道哪里能找到它们的话。安迪和菲比就知道。在上一年的树叶和冷杉球果下,一簇簇粉白花朵开得遍地都是。从那以后,我也常常在花店的橱窗里看见它们,一小束一小束笔挺地扎在一起,一点儿都不像我们在对面树丛里采到的那些。
道路一畅通,老货郎就背起行李,带着普雷布尔太太为他准备的一大包食物出发了。菲比把我搂在怀里,和安迪一起把他送到了绿草茵茵的三角岛。在那个三条路分岔的地方,他们和老货郎道别,看着他渐渐消失在去往波特兰的那条路上。他走得有些跛,身子被沉重的包袱压得歪向一边,整个人活像大风区里那些歪脖子树。走到拐角处时,他停下来向我们招手。安迪和菲比也冲他挥手,直到再也看不见了为止。
要不是菲比的爸爸不久后便回来了,离开老货郎,我们肯定会感觉很孤单的。他事先谁都没通知,突然就大步流星地踏上了紫丁香丛中的那条小路。他是从波特兰赶着一辆轻便马车回来的。带回家的盒子、货物和航海箱把前厅堆得满满当当,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宝贝:丝绸、佩斯利细毛披巾、象牙、珊瑚制品、鸟儿标本和他从各个港口收集来的小玩意儿。我常常想,要是亨特小姐看见这些,会说什么呢?
普雷布尔船长身材魁梧,他太太总是骄傲地说,他光穿袜子,都有六英尺四英寸高。他有一双我见过最明亮的蓝眼睛,一笑起来就眯成一条缝儿,眼角的细纹也像老画片里的太阳光一样四散开来。他很爱笑,尤其听到菲比说的那些事,更是笑个不停。无论什么时候,他只要一笑,声音都像是从那双巨大的长筒靴里汇聚而来,然后“咕噜咕噜”地往上升,最后猛地一下从嘴里迸发出来,变成洪亮的“嗬嗬”声。
每当爸爸亲吻菲比,把她举过头顶两三次,看她又长大了多少时,菲比说的第一句话几乎都是:“这是我的新娃娃——希蒂!”接下来,他就得听她讲所有关于老货郎、花楸木和我如何在教堂长凳下度过了好几天的故事。尽管菲比的妈妈对此总是摇头,但那些故事还是让普雷布尔船长大笑不止。他笑得实在太厉害,结果外衣上的扣子都像海中的小船般,不停地上下摇晃起来。
“达内尔,这有什么好笑的,”她对他说,“还不到一个星期,你就把她惯成了一只鹦鹉。再这样下去,我干吗还要努力教导她。”
她这话我记得很清楚,因为直到今天,我都没弄明白鹦鹉到底是种什么样的鸟。如今,人们都不再提起这种鸟了。或许,它们很多年前就已经灭绝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