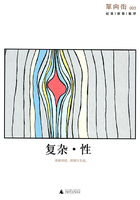
第5章 专题(5)
从性生活怎样、频率如何、是否有过性高潮、有没有主动要求过性生活、可不可以拒绝丈夫的性要求这些问题上看,男女平权的性关系在后村已经出现,大都在年轻一代的村民中:
学(29岁):性生活适当,有过性高潮,没有主动提出过性生活,但是可以拒绝丈夫的性要求。
洪(22岁):性生活好,一周两次,有高潮,有过主动提出性要求,可以拒绝他的性要求。
海(26岁):性生活很好,有主动要求过,可以拒绝他的要求。
连(44岁):稳定,一周两次,有过性高潮,有过主动要求,特殊情况下拒绝过丈夫的要求。
树(45岁):有过高潮,有了第一个孩子以后感觉过“好”。也可拒绝丈夫,不方便的时候。
灯(30岁):平时他不在家。过年他回家时,才在一起。有过高潮。可以主动地要求。一般不拒绝他。一年到头,就那么几天在一起。
44岁的中自称“老太太”(在后村,凡已婚女子无论老少,称为“老太太”、“老娘们儿”。——作者注),问她性的感觉,她说:
还行吧,年轻的十八九的闺女,让人拉拉手,都觉得怪好的。现在俺们这老太太们,老了,还能有嘛感觉?
[二]
调查还问及了后村女人的婚前贞节观念,问到了她们初次性行为是多大年龄,感觉如何。绝大多数被问到的女人没有过婚前性行为,尤其是年龄较大的。但是,在最年轻的女人中开始出现婚前性行为。对处女贞节的坚持随时代远去,已经显得不是那么坚定了。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伍尔夫这样谈到过贞节的问题:“因为贞节也许只是什么团体、组织为了不知什么理由而发明的一种偶像,但是贞节在那个时候,甚至现在,在女人的一生中有一种宗教的重要性,而且它被神经和本能紧紧包住,若想隔开把它拿到光天化日之下就需要绝大、难得的勇气。”这也是在后村调查中的印象:婚前贞节似乎有一种宗教的重要性和约束力。
根据资料,有七成左右的农村女性仍然认为贞操比生命还重要,只有三成上下不同意这种看法。但是,她们可能只是觉得跟生命相比,贞操重要性略低些,不见得不赞成婚前保持贞节的价值。最值得注意到是,这种观念从60岁到20岁的女人,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和变化。这一点让人觉得非常可悲。因为生命和贞操及其他个人品质相比,无疑是更加重要的价值,这是任何少有现代理性的人都会作出的判断。而有七成的农村妇女竟然认为贞操比生命还重要,令人感到传统社会的贞节牌坊不只是作为实物矗立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而且已经作为精神渗透到了传统中国女人的血液之中。
在后村,大多数女人正是这样做的,她们保持了婚前的贞节,而且认为当然应当这样做,不能想象其他的做法。还是有少数女人是在婚前就发生了性行为的,她们大都比较年轻。
在后村,婚前贞节仍然是一个被普遍遵循的道德规范,一旦违背,会造成人们的坏印象,带来不利后果。31岁的深,丈夫有4个姐姐,大姐远嫁他乡,四姐眼有残疾,另两个姐姐在少女时代即与有妇之夫有染,家风不好,导致丈夫二十大几娶不到媳妇。阎云翔所描述的东北村庄中“先有后嫁”的情况在后村还是比较少见的,个中原因恐怕还是地域文化的差异:在东北农村,男权制传统保留得比华北农村要少,在婚前贞节观念的灌输和渗透上,中原地区也比东北地区更加源远流长。
在贞节规范问题上,女性主义者麦金农的疑惑在于:男性有权多妻或不忠诚,而妇女却被要求忠诚;这样的事实使人疑惑妇女究竟从这种重新安排中赢得了什么。她认为,断言频繁多变的性交对妇女而言一定意味着羞耻和压迫,并不能解释一个本来如此的社会的起源。结果被表述为原因。对社会变化的解释是:贞节的妇女需要丈夫(不贞节的妇女或许正在和不忠诚的丈夫交往),男人却随时准备着迎接“事实上的群婚所带来的愉悦”。[1]
在众多女性主义的理论中,最值得注意到是关于什么是“自然”的讨论。有很多一般人看似天经地义的“自然”规则其实是由社会建构起来的,比如关于女人“自然”守贞、男人“自然”花心的说法。如果没有社会规则和习俗的塑造和压抑,也许女人会像男人一样的花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套用波伏瓦名言式的句式:贞节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
村里有一些女人的初次性行为是与其他女人不大一样的。荣是因为跟丈夫感情不好而一再拖延和丈夫同床的:
婚后三个多月才有第一次。因为当时不愿意嫁给他。感觉挺伤心。哭了一夜。
树则是因为换亲,对丈夫没好感,心里觉得委屈,一开始不愿意跟丈夫过性生活,她说:
第一次是19岁吧。有嘛(什么)说的呀,你这是问起来了。光记得结婚以后,过了好几天,才在一起。又赶上换亲,反正觉得挺委屈的,感觉被他欺负了,就自己哭,不说话。他吓坏了,给我擦眼泪,叫我“妹妹”。我想起俺哥也这样对他妹妹,就不哭了。
灯也是因为感情问题,一开始对性生活有抵触情绪,她对这个问题先是不回答,沉默许久后说:
俺俩没嘛(什么)感情。结婚前,他喜欢过他初中的一个同学,人家考上师范类,毕业又分到乡中学教书,非农业有工资,人家看不上他这个农民。他心里委屈。和我订婚也是家里逼着他去的。结婚过后好长时间,俺俩一直分居。后来公公病了,他不在家,是我伺候的。他回来时,俺们才在一起。就那样吧。农村人结婚前都没感情基础,结婚后现培养,想培养成嘛(什么)样就培养成嘛(什么)样,想培养多深就培养多深。
[三]
近几十年来,中国人生活在一种禁欲主义的社会气氛中,人们对性知识的学习和了解是比较艰难的。农村女性是如何获取性知识的?她们如何理解性行为?在对待性话题和性禁忌时,她们与男性的态度是否相同?她们是否遭遇过性侵犯?在观念保守、信息闭塞的农村,是否存在非主流的性现象(比如同性恋)?
在对性事的了解方面,农村孩子虽然信息渠道较城市孩子少,但并不比城市孩子了解得晚,了解得少。这是因为,几乎所有被访问到的后村女人,童年甚至少年时期都还和父母同睡一个大土炕。而这个给整个家庭带来温暖的大炕,就成为农村成年人完成性事和青少年了解性事的所在。
全家人同睡一个大土炕(少数是大床)的现象很普遍,这既和住房缺少有关,更和农村冬季取暖方式有关。冬天到来,一般家庭家里只生一个煤炉,做饭要靠这只炉子,冬季取暖也主要靠它。煤炉有一条烟道与一墙之隔的土炕相连,热气从煤炉出来,在土炕抗体中的暗道中回旋一圈,再经由墙体中的烟囱排到室外。一般一个核心家庭,冬季只有一个热炕,这个家庭自然而然的睡在一起。但被褥是有区别的:一般父母共用一条被子,子女(不分性别)共用一条被子。
孩子半夜醒来,偶尔会撞见父母夜间的“活动”,父母间不同于白日的声音或者奇怪的动作,给孩子一些朦胧而新奇的印象。这些印象,多多少少会使孩子联想到神秘的性事,而这些印象和信息,会很快在与同龄孩子们一起玩耍时得以交流。通过交流,孩子们验证并深化了自己最初的猜测。
所以许多农村女孩虽然不明白性是什么,但很早就知道,在夫妻之间存在一种神秘的仪式。这种仪式和生育有关,并且是隐秘的、见不得人的,但人们又乐此不疲地进行夜间活动。而她们对性知识的了解,正是通过夜间的发现和同侪们的交流、模仿获取的。
村妇燕,31岁,在了解到我们的调查情况后,她很认真地说起小时候和同伴们最爱玩的“过家家”游戏,她说:
玩过家家时,我们就是模仿大人们的行动。男孩当爸爸,女孩当妈妈。衣服里装进一整块砖,然后取出来,就说“生孩子”了。还有的时候,在场(指打麦场)里玩,有时候就到麦秸垛上玩,六七岁的男女小孩,一会儿男孩子把女孩压在身下,一会儿女孩把男孩压在身下。其实,只是模仿大人的姿势,不知道大人们究竟干了嘛(什么)事。小孩子们就是好奇这事,虽然谁压谁一会儿,没带来嘛(什么)好事,就是干这个事本身,让小孩子们心里很刺激、新鲜。
在后村,20岁以上的女子,几乎无一例外地童年与父母(或祖父母)同睡大炕,只有到一定年龄(一般是10~12岁),才自己独居一室,或者与同辈的姐妹、兄弟同睡一室。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供给宽裕的家庭陆续安装了土暖气,女孩结束与父母同睡大炕的年龄提前了几岁,但与长辈同睡大炕仍是童年必经的一个阶段,一个值得注意到现象是,女孩往往比男孩提前两三年结束与父母同睡大炕的经历,女孩比男孩早熟可能是原因之一。
农妇英说到她在少年时代最害怕的事情:
我们全家人睡在一张床上,我小时候看的书多,了解精子、卵子的事,我那时候最害怕的是,爸爸或者哥哥的精子会顺着被子爬到我身上,害怕它们钻进我肚子里。
后村人谈及性事,一般会顾忌女孩在场,但却忽略男孩。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后村学龄前的男孩,夏天几乎都是光屁股的,而女孩从出生就得至少穿个短裤。几乎每位妇女都有过拿自家和邻居家小男孩生殖器开玩笑的经历,但没有人对自家和邻居家女孩的生殖器官开玩笑,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女孩的家人会非常生气,会骂街,甚至引发更严重的后果。在西方基督伦理框架下,性总是正确和错误、正常和反常、善行和罪恶等评价联系在一起,性总是和罪联系在一起。而在中国农村,性却处于一个混沌自然的状态,它一般只同人品的高尚卑下、正派下流有关,人们对性的看法往往同羞耻感联系在一起。
性及性事,如果男孩了解得多,大人们会怀着善意甚至窃喜的心理呵斥这个男孩“真坏”,但并不影响大人们对男孩的印象,反而会高兴地认为,这个男孩已经长大成人了;如果同样年龄的女孩对性或性事了解得多一些,那么大人们会吓得变色,认为这个女孩思想不健康,并马上产生“作风不好”的联想。如果是自家女儿如此,父母会大骂她,并勒令她以后必须远离这些想法;如果是村里别人家女儿如此,就极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女孩未来的婚嫁,除非这女孩考上大学,远离后村,到城市中去生活。
村里的时尚女人永,回忆起自己何时变得与身边的人不同时是这样说的:
上初三时,发下课本,有《生理卫生》,我正翻着看,同桌大呼小叫地说,你看这个干吗,听说那书上讲小孩是怎么变出来的,还讲小孩在妈妈肚子里怎么长的——可真恶心死了!你怎么看这个!我一听她说这个就来气。我傻,坐在教室里看,她们聪明,嘴里说不看,背后比谁看得也多。
农妇军在提到自己少年时的一个同伴时,念念不忘这样一件事:
上小学时,邻居家的姐姐,大我一岁,在一起上学,我们常在一起玩,有天大人不让我和她玩了。因为大人们听说,那个姐姐有一次穿裙子,里面没有穿裤衩。人们认为她作风不好,也不让我跟她玩了,怕跟着学坏。(那个姐姐当时十二三岁。——作者注)
在这种男女双重标准的熏陶下,农村人认为,男孩是“皮实”的,不易受坏影响的,可以早些了解性事,而女孩是易受坏影响的,不该了解性事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农村女孩了解性事的过程要比同龄的男孩更为隐蔽,性事对她们来讲自然也成为具有更多神秘色彩的禁忌话题。
[四]
按照几率,只要存在一定数量的人群,就应当由一些性倾向异常的人存在。后村的女人里也有几位女同性恋者(自己认同女性,喜欢女性)或女易性者(自己认同男性,喜欢女性)。
一位是很T(女同性恋中的男角)很“锃”(方言,指有勇无谋、行动冒失的楞头青)的萍,萍的情形兼具同性恋和易性特质。
萍姓王,在村里算是大户。她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家里排行老三,从小就是那种很中性的女孩,短短的头发,身材矮胖,皮肤黑,性格偏执。小学五年级时,她到邻村读小学,认识了班主任琪。
琪那时三十来岁,性格爽快,身材高挑,教了萍两年。在萍到乡政府驻地读初中时,琪被借调到乡政府做干部。
琪开始收到萍的信。每封信都不称呼“老师”,而是称呼她“姐姐”,字里行间是思念、想念。琪读信时面目尴尬,她的同事们就抢过信,大声念,内容多是:“姐姐,我想你啊。我不想上学了,我想在乡政府前面摆个小摊卖东西,这样可以天天看到你。”“今天晚上我又一次骑着自行车来到你家附近徘徊,我多么希望你能恰好出门,能让我看到你的身影,听到你的声音……”“每天放了学,同学们都飞奔回家,只有我孤独地在路上,我骑车总是很慢很慢,多么希望你也下班回家,我们可以同路一会儿……”在同事的爆笑中,琪只好红着脸解释这是个女学生写的。琪不断地收到这些信,以致她不得不到学校,找到萍的班主任,委婉劝说萍“以后不要再这样了”。琪也曾很纳闷地问萍:“你想见我,都到我家门口了,为什么不进去?”萍低着头不说话。而让琪最不舒服,最不理解的是,每次站在琪面前,萍就站不稳,身体总是无意识地扭来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