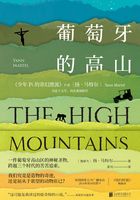
第3章 无家可归(3)
所有使用蜡烛和火炬以及在节庆假日焚香的教堂都面临失火的危险。卡马拉说这尊苦像会被送到“一座精致的古老教堂”。什么样的教堂能够赢得主教的如此赞誉呢?托马斯猜测那会是一座哥特式或罗马式教堂。这意味着教堂在十五世纪或更早的年代建成。布拉干萨的教区秘书并不是一位敏锐的教会历史学家。在托马斯的敦促引导下,他才勉强给出了五座教堂的名字——它们都失过火,也大致配得上卡马拉主教的赞誉。这五座教堂彼此相距甚远,分别位于圣儒里奥-德帕拉索斯、桑塔利亚、莫弗雷塔、瓜德拉米尔和埃斯皮尼奥塞拉。
托马斯给每座教堂的神父分别写了信。所有的回信都闪烁其词。每一位神父都盛赞自己的教堂,夸耀它久远的历史和壮丽的外观。那些溢美之辞让人误以为葡萄牙高山区遍布着可与圣彼得大教堂[5]比肩的圣殿。但是一旦说到教堂里的十字架苦像,神父们的话无一例外变得乏味。每个人都宣称那是一件能够唤醒信仰的作品,却无人知晓它的来历和年代。最终托马斯决定亲身探访。想要弄清楚乌利塞斯神父的十字架苦像是否如他想象中那样神奇,除了亲眼一睹之外别无他法。高山区位于葡萄牙偏僻的东北角,与世隔绝,但对他来说不是问题。用不了多久,那件作品就会呈现在他眼前。
他被一个声音吓了一跳。
“您好,托马斯先生。您是来拜访我们的,对吗?”
是年迈的看门人阿丰索。他已经开了门,低头看着托马斯。
他开门怎么这般悄无声息?
“是的,阿丰索。”
“您身体不舒服吗?”
“我很好。”
他略显慌乱地起身,一面把书塞回口袋。看门人拉响门铃。
铃声一响,他的神经也瞬间绷紧。他必须进去,别无选择。不仅是这个家——这个多拉和加斯帕尔死去的地方——每一个家都带给他同样的紧张感。爱是一座有许多房间的房子,一个房间供爱就餐,一个房间供爱娱乐,一个房间供爱沐浴,一个房间供爱更衣,一个房间供爱休息;每一个房间同时也可以用作欢笑的房间、聆听的房间、倾诉秘密的房间、生闷气的房间、道歉的房间,或者亲密相处的房间,当然,也可以是迎接家庭新成员的房间。爱是这样一座房子:每天清晨水管里汩汩涌出崭新的情感,下水道冲走昨日的争吵;推开明亮的窗户,清风扑面而来,满是友善的味道。爱是这样一座房子:它的根基不可撼动,它的屋顶坚不可摧。他曾经拥有一座这样的房子,直到它被摧毁。现在他已经没有家了,他在阿尔法马的公寓空空荡荡,像个僧侣的房间。每次走进别人的家,他只会想起自己已经无家可归。他明白自己最初为什么会对乌利塞斯神父感兴趣,只因为他们共同的对家的思念。托马斯联想到神父获悉圣多美总督夫人死讯时写下的文字。她是岛上唯一的欧洲女性。除她以外的欧洲女人住得最近的也在拉各斯,两地隔海相望,相距近八百公里。乌利塞斯神父其实从未与总督夫人谋面,只是远远见过她几次。
一个白人男子的死亡,倘若发生在这座瘟疫肆虐的岛上,远比死在里斯本更让人扼腕叹息。当死去的是个女人,我的上帝啊!她的离去是让人最难以承受的重负。恐怕从今往后,再无女性同胞的身影给我慰藉。美丽、高贵、优雅,都随之而去。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托马斯和阿丰索穿过铺着鹅卵石的院子。阿丰索恭敬地在他前面领路,他依旧习惯性地倒行,于是两人背对着背,步调一致。到了大门口,阿丰索侧身让到一旁,鞠躬示意。门前只剩几级台阶,托马斯仍然倒着走。没等来到门前,门已经开了,于是他倒着走进屋。他回过头,看见达米昂正等着他。他是伯父多年的管家,看着托马斯长大。他面带微笑,张开双臂。托马斯转过身。
“你好,达米昂。”
“托马斯,我的孩子,见到你真高兴。你还好吗?”
“我很好,谢谢。加布里埃拉伯母还好吗?”
“好极了。她像太阳一样照耀着我们。”
说到太阳,它正透过高大的窗户照耀着门厅里琳琅满目的陈列品。伯父靠买卖非洲货物发了大财,尤其是象牙和木材。一面墙上装饰着两支巨大的象牙。它们之间挂着一幅色彩艳丽、熠熠生辉的卡洛一世国王画像。国王陛下曾驾临伯父的府邸,当时他的眼前也是现在这番景象。其他几面墙上装饰着斑马皮和狮皮,上方挂着各种野生动物的头颅:狮子、斑马,还有非洲旋角大羚羊、河马、牛羚、长颈鹿。椅子和沙发也都以兽皮做饰面。壁龛和架子上陈列着非洲手工艺品:项链、原始的木质半身雕像、护身符、砍刀和长矛、五颜六色的纺织品、鼓,等等。此外,还有各式油画:风景画、葡萄牙领主和当地侍从的肖像画,还有一幅大尺寸的非洲地图,上面标明了葡萄牙殖民地。油画为大厅提供了背景,也多少透露出主人家的心性。右手边是精心布置的深草丛,有狮子标本潜伏其间。
在博物馆管理员的眼中,这个门厅简直乱成了一锅粥,或者说是文化的大杂烩,每件物品都从赋予它意义的环境中被强行拽了出来。但这个门厅曾点亮多拉的眼睛。她惊叹于殖民地的地大物博,这让她为葡萄牙帝国备感自豪。她触摸每一件自己够得到的物品,除了那头狮子。
“伯母身体好,我就放心了。伯父在办公室吗?”托马斯问。
“他正在院子里等你。请跟我来。”
托马斯背转身子,跟着达米昂穿过门厅,沿一条铺着地毯的走廊往里走,两侧都是油画与陈列柜。他们转弯步入另一条走廊。走在前面的达米昂打开两扇法式落地窗,侧身让到一旁。托马斯出了门,走上一个半圆形平台。他听见伯父热情洪亮的声音:“托马斯,看看这头‘伊比利亚犀牛’!”
托马斯转头,越过右肩向后看。他快步走下三级台阶,进入宽阔的庭院,到了伯父跟前才转过身来。他们握了握手。
“马蒂姆伯父,见到您真高兴。您还好吗?”
“怎么可能不好呢?见到我唯一的侄子,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托马斯本想再问候一下伯母,但伯父摆了摆手,叫他不必拘礼。“行了,行了。来,你觉得我的‘伊比利亚犀牛’怎么样?”他指着前方问,“它是我最骄傲的藏品。”
那头巨兽站在院子中央,不远处是它的管理员——瘦高个儿的萨比奥。托马斯注视着它。光线柔和、朦胧,轻纱一般落在它的身上,为它倍添光彩,但在托马斯眼里,它只是一头可笑的怪物。“它……太壮观了。”他回答。
伊比利亚犀牛曾漫步于葡萄牙的乡间。尽管它外形丑陋,他却总为它的命运感伤。这种动物最后的堡垒不正是葡萄牙高山区吗?这种动物以一种颇为奇特的方式存在于葡萄牙大众的想象中。人类的进步注定了这个物种的消亡。在某种意义上,它是被现代文明碾过的。它被追捕、猎杀,直到灭绝、消失,仿佛一种可笑的陈旧观念,直到消失的那一刻才激起人们的遗憾与怀恋。
如今它成了忧伤的葡萄牙民谣“法多”中的固定角色,演绎着这个民族独特的怀旧情绪——Saudade[6]。一想到这个消逝多年的物种,托马斯就难以抑制心里的Saudade。他的心情正如一句老话所说的:“犀牛般的甜蜜感伤”。
伯父对他的回答很满意。托马斯略带不安地望着他。他父亲的兄弟骨架结实,身上裹着财富的光环,大腹便便中透出一分略带滑稽的傲慢。他家住拉帕,锦衣玉食,把数额惊人的钱花在每一种新奇玩意儿上。几年前,他被自行车所吸引。那是一种以骑车人的双腿为动力的两轮交通工具。在里斯本高低起伏的鹅卵石街道上,自行车不仅不实用,而且十分危险。只有在公园的小径上骑行才安全,它也因此沦为周末的娱乐项目。骑车人沿着环形小径绕了一圈又一圈,行人不堪其扰,孩子们和狗也屡受惊吓。他的伯父收集了一屋子的法国标致牌自行车。之后他开始购置机动自行车。它的速度甚至比脚踏车还快,噪声也更大。此刻在他眼前的就是伯父昂贵藏品中的新宠。“不过,伯父,”他小心翼翼地说,“这只是一辆汽车。”
“只是,你说只是?”伯父应道,“这可是科技史上的奇迹,是我们的国家不朽灵魂的重生。”他抬起一只脚,踩在汽车侧面车轮之间的狭长踏板上。“我原本拿不定主意应该借给你哪辆车,我的达拉克,我的德·迪昂·布通,我的尤尼克,我的标致,我的戴姆勒,还是我那辆美国产的奥兹莫比尔?实在很难选择。最后,考虑到你是我亲爱的侄儿,也念在我朝思暮想的兄弟的情分上,我选定了藏品中的佼佼者。这是一辆全新的四缸雷诺,工程设计上的杰作。看看它!这件作品不仅闪耀着理性的光辉,还散发着诗歌的魅力。让我们摆脱那些把城市搞得污秽不堪的动物吧!汽车不需要睡觉——马能做到这一点吗?它们的输出功率也无法相提并论。测试结果显示,这辆雷诺的引擎有十四匹马力,这还只是严谨的保守估计。它的动力很可能达到二十匹马力。而且机械马力比牲口的力量更强劲,所以,想象一辆套了三十匹马的四轮马车吧。你看见了吗?三十匹马排成两列,迫不及待地踏着地面、咬紧衔铁。好吧,你不必想象,它就在你的眼前。那三十匹马已经被装进了前轮之间的金属箱里。多么惊人的性能!同时又多么经济!真没想到古老的火能以这种方式焕发新生。还有,汽车肚子里像马粪那样的肮脏玩意儿呢?根本不存在。只有一股烟雾飘散在空气里。汽车就像香烟一样无害。记住我的话,托马斯,这个世纪将因为这股烟雾的诞生而被铭记!”
伯父志得意满地看着他的高卢[7]玩具。托马斯仍旧一言不发。
他不像伯父对汽车那么痴迷。最近里斯本的街上已经出现了几辆这种新式机器。城市日常的牛马交通虽然热闹繁忙,却也不算太过嘈杂。如今这些机器如同巨大的昆虫嗡嗡掠过,声音震耳欲聋,模样古怪碍眼,气味刺鼻难忍。在它们身上他看不到一点儿美。伯父这辆酒红色的座驾也不例外。它算不上优雅,也不匀称。在他看来,和车厢下面那个挤了三十匹马的微型马厩相比,驾驶室实在是大得离谱。这玩意儿处处是金属,闪着刺眼、冰冷的光——用他的话说,简直毫无生气。
他情愿坐老式的马拉车前往目的地,不过他总共只有十天时间。他将在圣诞节前出发,这十天已经算上了他积攒的假期和从博物馆馆长那里苦苦求得的几天——他几乎要给他跪下了。路途遥远,时间宝贵。牲口是赶不及的。他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伯父慷慨相借的丑陋发明。
伴着咔嗒一声门响,达米昂托着盛有咖啡和无花果点心的餐盘走进院子。仆人搬来餐盘支架,随后是两把椅子。托马斯和伯父坐下来。仆人倒上热牛奶,搭配适量的糖。这种时候很适合闲聊,但托马斯直奔主题。“那么,汽车是怎么开的,伯父?”
他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不愿让自己的视线越过车顶,沿着伯父的院墙,顺着通往仆人住处的小径,落在那一排橘子树上。曾经,儿子常在那里等他。加斯帕尔会躲在一棵不够粗的树后面。一旦被爸爸发现,他就尖叫着跑开。托马斯追赶这个小鬼,佯装不知自己的伯母、伯父或是他们的众多眼线正看着他走上那条小径,就像仆人们佯装不知他踏入了他们的领地。是的,他宁可谈论汽车,也不愿看见那些橘子树。
“哈,问得好!我让你见识一下其中的奥妙。”伯父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托马斯跟着他来到车前。伯父松开车头的挂钩,把固定在铰链上的圆形小金属罩向前掀起。展现在他眼前的是纠缠的管道和闪耀着金属光泽的球状凸起。
“赞叹吧!”伯父敦促道,“3.054升排量的直列式四缸发动机。多么精美,多么伟大。注意到它们的排列顺序了吗:发动机、散热器、摩擦式离合器、滑动齿轮变速箱、后轮轴驱动器。未来就在这样的队列中产生。不过,还是让我先给你解释一下内燃引擎的奇妙之处。”
他伸出一根手指比画着,仿佛要把发动机不透光的外壳里发生的魔术凭空画出来。“在这里,化油器把汽油蒸汽喷进燃烧室。磁铁激活火花塞。蒸汽被点燃,然后急速膨胀。活塞——就在这儿——被往下一推,然后……”
托马斯听得云里雾里,木然看着眼前的一切。伯父得意扬扬地演讲完,探身从驾驶室的座椅上捡起一本厚厚的手册,递到托马斯手里。“这是汽车使用手册。那些你还没听懂的部分,上面都写得很清楚。”
托马斯扫了一眼手册:“这是法语的,伯父。”
“没错。雷诺兄弟是一家法国公司。”
“但是——”
“我已经在你的行李里面配了一本法葡字典。你必须尽心尽力保养这辆车,好好给它上机油。”
“机油?”这个词也令他一头雾水。
洛博先生没有理会他困惑的表情。“这些挡泥板很漂亮吧?猜猜是用什么做的?”他拍拍挡泥板,自问自答道,“大象耳朵!我的私人定制,从安哥拉带回来的纪念品。车厢外壁也一样,最精致的大象皮革。”
“这是什么?”托马斯问。
“喇叭。用来警告、提醒、催促、抱怨。”伯父捏了一下方向盘左边贴着车身的那只大橡皮球。与它相连的喇叭发出类似大号的响声,还略带颤音,声音洪亮,引人侧目。托马斯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位马背上的骑手,胳膊下面夹了一只鹅,像是抱了只风笛,每当危险临近就挤它一下,发出嘎嘎的叫声。他忍不住偷笑了一声。
“我可以试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