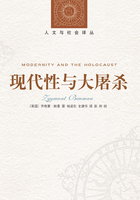
作为现代性之验证的大屠杀
几年前,《世界报》的一名记者采访了一些遭遇过绑架的受害者。他发现的最有趣的一件事是那些一同经历过人质磨难的夫妇有高得出奇的离婚率。出于好奇,他进一步研究了那些离异者做出分手决定的原因。大多数的受访人告诉他,在绑架发生之前他们从未想过离婚。但是,在恐怖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他们的眼睛被擦亮了”,“他们在一束新的光亮中看见了他们的伴侣”。平常的好丈夫“被证明是”自私的人,只顾自己的死活;大胆的生意人表现出令人厌恶的怯懦;而足智多谋的“男子汉”形如土灰,只有为他们即将到来的死亡而哀戚。这个记者自问:这些两面神明显拥有的两面化身中,哪一面是真实的,哪一面又是伪装? 他的结论是自己的问题提错了。哪一面也不比另一面“更真实”。这两面都是受害者所一直具有的品性——它们只是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环境下显露而已。“好的”一面之所以看起来正常只是因为正常环境使它覆盖于另一面之上。而另一面尽管通常看不见,却总是存在。而这个发现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如果不是绑架者的冒险,这“另一面”将可能永远隐藏下去。那些伴侣们将继续沉浸在他们婚姻的幸福之中,自以为了解他们的配偶,并喜欢他们所了解的配偶,而不知道一些不期而至或者异常的情况可能揭示的那些不讨人喜欢的品质。
我们上面从特克的研究中引述的段落的结尾是这样的:“要不是大屠杀,大多数救助者将继续行进于他们的独立道路之上,一些人从事慈善工作,一些人过着简单而不引人注目的生活。他们是潜在的英雄,常常无法把他们与身旁的人区分开来。”她的研究中一个得到最有力(也是最令人信服的)论证的结论就是,不可能“提前看出”个人为牺牲而做出准备或者个人在灾难面前会表现出懦弱的迹象、征兆或者暗示;也就是说,不可能在要求他们振作起来或者仅仅是“使他们醒悟”的情境之外来判断他们其后的表现。
J.K.罗斯提出了与我们的问题直接相关联的潜在性对现实性(前者是后者的一个尚未揭露的状态,后者是前者已经实现——并因此在经验上容易接近——的状态)的问题:
假如纳粹政权当道的话,那么裁定孰是孰非的权威就会发现,在大屠杀中没有自然法受到破坏,也没有犯下任何有悖于上帝和人性的罪恶。虽然应该继续、扩大、还是废止使用奴隶劳动是一个问题。但做出的选择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
大屠杀弥散于我们集体记忆中的那种无言恐怖(它时常让人们产生强烈的愿望,不要去面对那场记忆)就是要令人痛苦地去怀疑大屠杀可能远不仅仅是一次失常,远不仅仅是人类进步的坦途上的一次偏离,远不仅仅是文明社会健康机体的一次癌变;简而言之,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文明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事物(或者说我们喜欢这样想)的一个对立面。我们猜想(即使我们拒绝承认),大屠杀只是揭露了现代社会的另一面,而这个社会的我们更为熟悉的那一面是非常受我们崇拜的。现在这两面都很好地、协调地依附在同一实体之上。或许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它们不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且每一面都不能离开另外一面而单独存在。
而我们经常止步于可怕事实的门槛上。因此费恩戈尔德坚持认为大屠杀事件确实是漫长的、从总体上无可指责的现代社会历史中出现的一个新事物;这是一个我们不曾期望也无法预料的事物,就像一个据说已经被驯服了的病毒衍生出新的有害变体那样:
“最终解决” 标示出了欧洲工业体系走上歧途的那一点;走到了升华生命这个启蒙运动之夙愿的对立面,这个体系已开始自我损耗。而当初欧洲正是凭借其工业体系以及依附于它的精神才得以统治全世界的。
标示出了欧洲工业体系走上歧途的那一点;走到了升华生命这个启蒙运动之夙愿的对立面,这个体系已开始自我损耗。而当初欧洲正是凭借其工业体系以及依附于它的精神才得以统治全世界的。
表面上,统治世界所需要和利用的技术似乎与确保“最终解决”达到效果所需要和利用的技术在性质上有所不同。然而,费恩戈尔德直面真相:
[奥斯维辛]也是现代工厂体系在俗世的一个延伸。不同于生产商品的是:这里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终产品是死亡,因此,每天都有那么多单位量被仔细地标注在管理者的生产表上。而现代工厂体系的象征——烟囱——则将焚化人的躯体产生的浓烟滚滚排出。还有现代欧洲布局精密的铁路网向工厂输送着新的“原料”。这同运输其他货物没有什么两样。在毒气室里,受害者们吸入由氢氰酸小球放出的毒气,这种小球又是出自德国先进的化学工业。工程师们设计出了火葬场,管理者们设计了以落后国家可能会忌妒的热情与效率运转着的官僚制度体系。就连整个计划本身也是扭曲的现代科学精神的映射。我们目睹的一切的只不过是社会工程一个庞大的工作计划……
事实上大屠杀的每一个“因素”——即那些使大屠杀成为可能的所有条件——都是正常的;这种“正常”并非人们所熟悉的意思,也不是早就被充分描述、解释和接纳的一大类现象中的又一个标本(恰恰相反,大屠杀的经验是崭新而陌生的);“正常”所指的是完全符合我们所熟悉的文明、它的指导精神、它的精髓、它内在的世界观等等——“正常”还指追求人类幸福和完美社会的正确方式。用斯蒂尔曼和普法夫的话来说:
流水生产线应用的技术和与之相伴的物质普遍丰富的观念与集中营应用的技术和与之相伴的大量死亡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完全偶然的。我们或许希望能够否认这种联系,但布痕瓦尔德和底特律的里维罗格(River Rouge)一样是属于我们西方的——我们不能把布痕瓦尔德当做是本质上健全的西方世界的一次偶然失常而加以否认。
我们也想起了希尔博格对大屠杀之实施卓越而又具权威性的研究最终得到的结论:“就是说,毁灭机器与有组织的德国社会从整体上说在结构上是没有区别的。从它所扮演的那个特定角色来说,毁灭机器就是组织起来的社群。”
R.L.鲁本斯坦得出的结论在我看来则可以是大屠杀的终极教训。他写道:“它见证了文明的进步。”我们还可以补充说这是一个双重意义上的进步。在“最终解决”中,备受我们文明夸耀的工业潜能和技术知识在成功地完成一个史无前例的重要任务时达到了新的高度。并且,同样在“最终解决”中,我们的社会向我们展示了其至今无人怀疑的能力。由于我们一直被教育要尊重和崇尚技术效率和认真计划,因此我们只能承认,在赞扬我们的文明所带来的物质进步时,我们已经过分低估了它的真实潜力。
死亡集中营的世界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揭示出犹太教—基督教文明与日俱增的阴暗面。文明意味着奴隶制、战争、剥削和死亡集中营。它同时也意味着医疗卫生、庄严的宗教思想、动人的艺术和优雅的音乐。把文明和野蛮想像成对立面是个错误……当今时代,如同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其他方面一样,野蛮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有效的管理。它们还没有,同时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创造和毁灭同是我们所谓文明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希尔博格是历史学家,鲁本斯坦是神学家。而我曾急切地查找社会学家的著作,想在其中找到一些对大屠杀提出的任务的紧迫性有类似察觉的内容;想找到证据以表明跟其他的一些事物一样,大屠杀对作为一项职业和学术知识载体的社会学是一个挑战。而与历史学家和神学家所做的工作相比,大多数学院社会学所做的看起来更像是集体忘却和闭眼作瞎。总的来看,大屠杀教训在社会学常识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这些常识包括诸如理性压倒情感的益处、理性优越于(还有什么?)非理性行为,或者效率的需求与无可救药地充溢着“人际关系”的道德倾向之间的特有冲突等信念。无论对于这些信念的反对声有多高多刺耳,都无法穿透现有的社会学理论之墙。
我也知道,社会学家,以社会学家的身份,并没有太多的机会公然面对大屠杀的史实。1978年当代社会问题研究所召集的“大屠杀之后的西方社会”的座谈会曾提供了这样的一次机会(尽管规模较小)。 在座谈会期间,鲁本斯坦提出了一个富有想像力的、尽管可能过于感情化的尝试,即根据大屠杀的经验来重读韦伯对现代社会的趋势的一些人所皆知的诊断。鲁本斯坦希望发现,是否可以从韦伯所了解、察觉和加以理论化的事物中预见(由韦伯本人和他的读者)到我们知道而韦伯当然不知道的事情,或者至少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他认为他对上述问题已经找到了肯定的答案,或者至少他做出了这样的暗示:在韦伯阐述的现代官僚制度、理性精神、效率原则、科学思维、赋予主观世界以价值等理论中,并没有可以排除纳粹暴行的可能性的机制;而且,在韦伯的理想类型当中也没有任何东西将纳粹政权的活动必定地描述成暴行。举个例子来说,“德国的医学界或者技术专家所犯下的罪行没有一件不是秉承了价值具有内在的主观性、科学具有内在的工具性和价值中立这样的观点。”而研究韦伯的著名学者、具有高度威望且当之无愧的社会学家,G.罗斯(Guenther Roth)的不满溢于言表:“我完全不同意鲁本斯坦教授的观点。他发言里的任何一句话我都无法苟同。”或许鲁本斯坦的观点可能会导致对韦伯形象的损害,因而激怒了罗斯(正是在“预期”的观点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损害),他提醒与会人士韦伯是一个拥护宪法并且赞同工人阶级拥有选举权的自由主义者(因此,不应当把他与大屠杀这样可怕的事情联系起来)。但是,他却没有和鲁本斯坦的主张正面交锋。正是如此,他也丧失了一次机会,去认真思考被韦伯界定为现代性之本质特征并对之做出了最有价值的分析的日益增长的理性统治的那些“没有预料到的后果”。他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正视社会学传统的经典传承下来的富于启发性的观点的“另一面”;他也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思索,我们的那些令人悲伤的知识(那是经典作家们所不具有的)是否可以使我们能够以他们的洞见在事物中发现他们虽朦胧感知却无法确知的全部后果。
在座谈会期间,鲁本斯坦提出了一个富有想像力的、尽管可能过于感情化的尝试,即根据大屠杀的经验来重读韦伯对现代社会的趋势的一些人所皆知的诊断。鲁本斯坦希望发现,是否可以从韦伯所了解、察觉和加以理论化的事物中预见(由韦伯本人和他的读者)到我们知道而韦伯当然不知道的事情,或者至少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他认为他对上述问题已经找到了肯定的答案,或者至少他做出了这样的暗示:在韦伯阐述的现代官僚制度、理性精神、效率原则、科学思维、赋予主观世界以价值等理论中,并没有可以排除纳粹暴行的可能性的机制;而且,在韦伯的理想类型当中也没有任何东西将纳粹政权的活动必定地描述成暴行。举个例子来说,“德国的医学界或者技术专家所犯下的罪行没有一件不是秉承了价值具有内在的主观性、科学具有内在的工具性和价值中立这样的观点。”而研究韦伯的著名学者、具有高度威望且当之无愧的社会学家,G.罗斯(Guenther Roth)的不满溢于言表:“我完全不同意鲁本斯坦教授的观点。他发言里的任何一句话我都无法苟同。”或许鲁本斯坦的观点可能会导致对韦伯形象的损害,因而激怒了罗斯(正是在“预期”的观点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损害),他提醒与会人士韦伯是一个拥护宪法并且赞同工人阶级拥有选举权的自由主义者(因此,不应当把他与大屠杀这样可怕的事情联系起来)。但是,他却没有和鲁本斯坦的主张正面交锋。正是如此,他也丧失了一次机会,去认真思考被韦伯界定为现代性之本质特征并对之做出了最有价值的分析的日益增长的理性统治的那些“没有预料到的后果”。他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正视社会学传统的经典传承下来的富于启发性的观点的“另一面”;他也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思索,我们的那些令人悲伤的知识(那是经典作家们所不具有的)是否可以使我们能够以他们的洞见在事物中发现他们虽朦胧感知却无法确知的全部后果。
当然,罗斯并不是惟一一个宁愿以牺牲相反的证据为代价来积极捍卫我们共同传统中的神圣真理的人;这只是因为其他的多数社会学家没有被迫如此直接地来做这样的事情。总的来说,在日常的学术实践中我们没有必要为大屠杀的挑战而感到烦忧。作为一种职业,我们成功得几近于把它给抛到脑后,或者把它搁置在“专业兴趣”的领地,而在这个领地当中它没有可能与学术的主流搭上界。如果完全在社会学的文本中来讨论,那么最佳的情况就是,大屠杀会被视为一种人类内在的、未被驯化的侵略性可能造成的悲剧当中的一个,然后被当做一个借口来宣讲通过增加文明化压力和兴起又一个专家解决问题的热潮以驯服这种侵略性的好处。最坏的情况则是,大屠杀被回忆成犹太人特有的经历,以及犹太人与其仇恨者之间的事情(也就是不受末世论关怀引导的以色列国家的代言人们已经在上面下了很大工夫的一种“私有化”过程)。
这种情况之所以令人担忧并不仅仅也不主要是因为这些职业上的原因——尽管它对于社会学的认识能力和社会学的社会关切度有极大的损害。使这种状况更加让人坐立不安的是我们知道,如果“大屠杀能在其他地方大规模发生,那么它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它包含于人类可能性的范围之中,而不管你喜欢与否,奥斯维辛像人类登上月球一样扩展了全人类的意识领域” 。鉴于这样的事实,即让奥斯维辛成为可能的那些社会条件没有一个真正消失了,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消除产生类似于奥斯维辛这种浩劫的可能性和因果律,我们的忧虑是难以平静的;比如L.库佩尔近来还发现:“主权领土国家会以其主权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宣称有权利对在其统治下的民众实施种族灭绝或者有权利参与到种族灭绝的残害之中……而联合国从所有的现实目的考虑,竟对这个权利加以保护。”
。鉴于这样的事实,即让奥斯维辛成为可能的那些社会条件没有一个真正消失了,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消除产生类似于奥斯维辛这种浩劫的可能性和因果律,我们的忧虑是难以平静的;比如L.库佩尔近来还发现:“主权领土国家会以其主权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宣称有权利对在其统治下的民众实施种族灭绝或者有权利参与到种族灭绝的残害之中……而联合国从所有的现实目的考虑,竟对这个权利加以保护。”
大屠杀浩劫事后为我们提供了洞察在现代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各种社会原则那些本身尚未引起注意的“其他方面”的可能。这样说来,我认为已经被历史学家全面研究过的大屠杀的历史应当被看做一个社会学的“实验室”。而在“非实验室”的条件下无法被揭示并因此在经验上无法去接近的社会特征已经被大屠杀揭示和验证。换句话说,我打算将大屠杀看成是对现代社会具有的潜在可能性进行的一次罕见而又重要并且可靠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