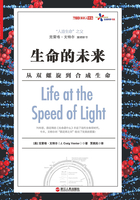
01 “合成生命”是可能的吗?
德国化学家维勒通过化学方法合成尿素,虽然并未对“活力论”造成实质性影响,却吹响了反击的号角。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用化学物质创造出一个人造生命。当我们创造第一个合成细胞时,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扮演了上帝的角色”。
这种类型的合成生物学,不仅对创造人造生命提出了巨大挑战,同时也对我们定义生命理论提出了重大难题。如果生命只不过是一个有能力进行达尔文式演化的、能够自我维持的化学系统,而且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理解化学是如何支撑演化的,那么我们就应该能够合成一个有能力进行达尔文式演化的人造化学系统。而如果我们真的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也就证明了支撑上述成功的这些理论实质上是“赋权性”的;相反,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努力创建一个化学系统来创造人造生命,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的生命理论是有缺陷的。
——史蒂芬·A.本尼尔
长期以来,人类一直痴迷于人造生命的概念。从中世纪帕拉塞尔苏斯的侏儒,到犹太民间传说中有生命的泥人,再到玛丽·雪莱创作的《弗兰肯斯坦》和《银翼杀手》中的“复制人”,各种神话、传说以及通俗文学作品中到处都充斥着合成生命以及机器人的故事。然而,如何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以便恰当地刻画出生命体和非生命体之间的差异以及生物生命和机器生命之间的区别,却依然是科学和哲学面临的一个重要的、不断被重新提起的难题。
几个世纪以来,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我们必须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理解生命,然后才是学会控制生命。出生于德国的美国生物学家雅克·洛布(Jacques Loeb,1859—1924)或许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生物工程师。洛布的实验室广泛分布于芝加哥、纽约、伍兹霍尔和马萨诸塞等地,在这些实验室里,他埋首于制造他在1906年出版的著作《生命物质动力学》(The Dynamics of Living Matter)中曾经提到过的“经久耐用的机器”。洛布创造出了双头蠕虫和其他许多东西,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没有受精的情况下使海胆卵子独自发育成为胚胎。洛布的探索给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885—1951)无穷的灵感,后者塑造了马克斯·戈特利布这个人物形象。马克斯·戈特利布是刘易斯于1925年出版的小说《阿罗史密斯》中的一个人物。这部小说为刘易斯赢得了普利策文学奖,它也是第一部理想化的纯科学研究巨著,里面特别提到了具有抗病毒能力的噬菌体。
菲利普·J.保利(Philip J.Pauly)在《控制生命:雅克·洛布和生物学工程理想》(Controlling Life:Jacques Loeb and the Engineering Ideal in Biology)一书中曾经引用过洛布写给奥地利物理学家兼哲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1838—1916)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洛布这样写道:“现在,有一个想法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盘旋:人类自身可以成为一个造物主,他们甚至能够依据自己的意愿创造出一个生物世界,人类至少能够掌握‘创造有生命的物质的技术’。”15年后,洛布在为自己的科学论文集作序时对这个想法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解释,他写道:“尽管主题各不相同,但是收集在这部论文集中的所有文章都渗透着一个主导思想,即我们有可能让生命处于我们的掌控之下。生物学的目的就是控制生命,别无其他。”
事实上,早在洛布与马赫通信的很多个世纪之前,洛布这种生命机械论思想的起源就能窥见一斑了。那就是与神创论生命理论形成了鲜明对照的“唯物主义”生命理论。(神创论生命理论是以某种“物质”本体之外的非物理过程和某种超自然的创造生命的方式为基础的。)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前490年—前430年)认为,所有东西——包括生命——都是由四种永恒的“元素”或“一切的根”所构成的,这四种元素是土、水、空气和火。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年—前322年)也是最早的“唯物主义者”之一,他把整个世界分为三大类:动物、植物和矿物。直到今天,我们的学校教育依然是这样进行分类的。1996年,我带领的研究团队完成了对第一个古生菌基因组的测序工作。这个序列被许多人赞誉为是代表生命的第三大分支的古生菌的重要证据之一——首次提出古生菌这个生命分支的人是美国微生物学家卡尔·乌斯(Carl Woese,1928—2012)。这个消息一传出去,电视节目主持人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便反问道:“我们已经有了动物、植物和矿物,那么新的分支还能是什么呢?”
随着理解的深入,思想家们变得更加雄心勃勃了。在古希腊时代,改变自然以满足人类欲望或试图控制自然的想法都被认为是极其荒谬的。但是,自从16世纪科学革命发生以来,科学的主要目标已经不仅限于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研究宇宙了,而是要控制宇宙。实际上,英国博物学家、经验主义创始人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早就阐述过“动手去做”胜于“坐而论道”这个道理了。他认为,希腊人“真的具有孩子的特征,他们敏于喋喋多言,却从来不可能动手去做出什么东西来;因为他们的智慧原本就是擅于文字而贫于行动的。……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从希腊人创造的任何一个体系中,以及从所有这些体系中衍生出来的各门学科中,竟然仍然找不到一个实验是用于改善人类境况或增进人类福祉的”。
培根在他1623年出版的乌托邦式小说《新亚特兰蒂斯》(New Atlantis)里描绘了他心目中未来社会的轮廓。这个想象中的世界充斥着人类的发明创造和发现成果,他甚至还设想了一个由国家支持的科研机构——所罗门学院。他写道,建立这个学院的目的是“取得自然界的统治权并且尽可能地去影响一切事物”。他还在这本小说里描述了一些对“野兽和鸟类”所做的实验。事实上,这些实验有点儿像是在进行基因改造。“使用人工手段我们能够使它们变得比正常品种更大或更小,也可以使它们侏儒化或停止生长;还可以使它们变得比普通品种更多地生育和繁衍,或者相反地,使它们不生育或失去传宗接代的能力;我们也可以使它们在颜色、外形、活动及其他诸多方面发生变异。”培根甚至提到了设计生命的能力:“这并非巧合,而是我们早已知道哪些生物可以混合和杂交,这种混合和杂交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新物种。”
而在这个试图征服自然的过程中,所有科学成果都要联合起来共同为人类服务。我们知道,勒奈·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是光学先驱,但在提到他的时候,我们更常想到的是“我思故我在”这句名言。在他的《方法论》(Discourse on the Method)一书中,笛卡尔期待着,终有一天,人类将会成为“自然界的掌控者和所有者”。笛卡尔和他的后继者们都把对自然现象的机械论解释拓展到了生物领域,并且探索了这种拓展的内在意蕴。然而,从这一类伟大的努力诞生之日起,批评者们就表达了一系列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在追求对自然更加高效的掌控过程中,人们有可能会忽略许多重要的道德问题和哲学问题。毫无疑问,随着这种浮士德式的现代科学精神的兴起,引发了一场有关人类“扮演上帝”这种做法的争论。
毫无疑问,对某些人来说,假设人类能够“扮演上帝”的最佳证明是,在实验室里创造出一些活的生命体。在《自然与生命的起源:源于新的知识》(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Life:In the Light of New Knowledge)一书中,法国生物学家和哲学家费利克斯·勒·当泰克(FeliXLe Dantec,1869—1917)曾经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现代物种是从早期的非常简单的有机体演化而来或者“变种”而来的。在达尔文主义盛行之前,法国学者经常用“种变论”(transformism)这一术语来讨论物种变化。勒·当泰克说,这种早期的非常简单的有机体是“具有最少的遗传特征的生命原生质”。在那本书中,他写道:“阿基米德说过一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起整个地球’。当然,阿基米德是在象征和比喻的意义上这样说的,因为如果只从字面上的意义来看,这句话无疑是相当荒谬的。类似地,今天的种变论者也完全有权力说:给我一个活的原生质,我就能再造一个完整的动物和植物王国。”当然,勒·当泰克清醒地意识到,这项任务极其艰巨,仅凭他自己所掌握的那个时代简单初步的方法是无法完成的:“我们对胶质物(大分子)的认识是如此粗浅和原始,以至于我们根本不应该指望自己能够快速而成功地制造出一个活的细胞。”但是,勒·当泰克非常坚定地确信,将来一定能够制造出一个合成细胞,而且他还指出:“随着新的科学知识不断积累,即使没有亲眼目睹原生质的构造过程,那些思想开明的学者也将会相信,在生物与非生物之间,既不存在本质的区别,也不存在绝对的不连续性。”
事实上,早在19世纪,许多杰出的化学家就已经对生命体与非生命体之间的界线问题进行过探索。这其中包括举世公认的现代化学伟大先驱之一、瑞典科学家琼斯·雅可比·贝采里乌斯(Jöns Jacob Berzelius,1779—1848)。贝采里乌斯在法国化学之父安托万—洛朗·拉瓦锡(Antoine-Laurent de Lavoisie,1743—1794)和其他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之上,开创了原子理论,并把它应用到了“活”的有机化学中。贝采里乌斯把化学的这两个主要分支定义为“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有机化合物指含有碳原子的化合物,它与其他的化学物质不同。在“有机”这个术语被广泛使用的第一个世纪里,“有机”指的是“来自生命”。贝采里乌斯在他出版于19世纪初的那本相当有影响力的化学教科书中对“有机”这个术语所做的定义,我们至今仍在使用。活力论者和新生代活力论者甚至从一个更为独特的视角去看待有机世界:“有机物质至少由三种成分组成……这些成分是无法通过人工制造的方式获得的……它们只能通过某种与生命力密切相关的方式才能获得。很显然,同样的法则并不适用于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生命力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合成尿素,一个对神秘生命力说“不”的故事
德国化学家弗里德里希·维勒(Friedrich Wohler,1800—1882)曾与贝采里乌斯短暂共同工作过一段时间。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维勒的一项重要发现证明了活力论者的观点是“虚假”的,那就是尿素的化学合成。你将会在现代的教科书、讲座以及文章里发现对维勒实验结果的引用。这个成就确实堪称科学发展史上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它标志着“生命必定是从古绵延至今的”这一观点的终结(而这一观点一度非常有影响力)。这种观点是说,存在着一种“生命的力量”,它能够区分有生命与无生命(生命与非生命),即存在着一个特别的“灵魂”,任何一个身体,只有在注入了“灵魂”之后,才能被赋予生命。与此不同,维勒的实验所涉及的是一种纯化学物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维勒似乎已经创造出了某种形式的生命。这确实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瞬间,它充满了所有的可能性。仅仅凭借一个实验,他就改变了整个化学的面貌——在那之前,化学被区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领域,一个领域研究有生命的分子,另一个领域研究无生命的物质。维勒打开了一个缺口,最终使化学这门学科彻底远离迷信,走向科学。值得一提的是,维勒这个伟大的成就是在玛丽·雪莱的哥特式小说《弗兰肯斯坦》发表10年之后取得的;另一个巧合是,这个重要事件还发生在乔凡尼·阿尔锹尼(Giovanni Aldini,1762—1834)试图通过电击方法让一个死囚“死而复生”之后没几年。
1828年1月12日,维勒给贝采里乌斯写了一封信,解释了他这个突破性实验。在这封信中,维勒细致地描述了他在柏林理工学院意外制造出尿素时的情景。在他得到这个成果之前,尿素一直因其为在哺乳动物的尿液里发现的最主要的氮化合物而广为人知。维勒一直试图利用氰和氨这两种化学物质来合成草酸(草酸是大黄含有的一种成分),但是最终制造出来的居然是一种白色的晶体物质。经过仔细的实验研究,维勒得到了天然尿素的精确分析结果,并且证明了他制造出来的晶体与天然尿素完全相同。在那之前,尿素一直只能从“动物资源”中分离出来。由于一直没有收到贝采里乌斯的回信,心急如焚的维勒在1828年2月22日又给贝采里乌斯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道:
我希望您已经收到了我于1月12日写给您的信。尽管我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希望看到您的回信,不过现在我已经等不及要给您再写一封信了,因为我不需要再隐瞒我发现了尿素这个事实了,我希望尽快把这一消息公布出去。我能够在不需要肾脏的情况下制造出尿素,无论是人的肾脏还是狗的肾脏都不需要了。我得到的这个氰酸铵盐就是尿素……只要把氰酸加入铵溶液中,让它们发生化学反应,就很容易获得这种人工合成的氰酸铵盐。让氰酸银和氯化铵溶液发生反应也可以得到同样好的结果。用这两种方法都可以获得这种四面直角的非常漂亮的棱状晶体物质。对它们用酸进行处理时,不会释放出氰酸;用碱进行处理时,也不会释放出氨气。但是如果用硝酸进行处理,则会产生一种容易结晶的泛着光泽的化合物,这种化合物拥有强酸的性质。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新的酸,因为它在加热时产生的既不是氮也不是亚硝酸,而是大量的氨气。我又发现,如果把它浸到碱溶液中,那么就会重新出现一种被称为氰酸铵的物质,利用酒精,就能够把这种东西提取出来。现在,突然之间,我明白了,所需要的只是对尿液中的尿素与氰酸盐中的尿素进行比较就可以了。
当然,贝采里乌斯最终还是对维勒的来信给出了回复,而且他的语气既幽默风趣又满腔热情:“当一个人已经决定用尿液这个东西来赢得自己的不朽名声时,他就毫无疑问有无数个理由去利用这个东西来完成这项伟业。真的,维勒博士确实已经设计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这个方法为他打开了通往真正不朽名声的道路……当然,这对未来的理论必定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事实的确如此。例如,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1803—1873)也对维勒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冯·李比希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在很多方面都对推动化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个例子是,他证明了氮是植物生长的重要营养成分。1837年9月,冯·李比希给利物浦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冯·李比希谈到,维勒“在没有任何生命机能的帮助下,制造出了这个非同寻常的、在某种程度上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尿素”。冯·李比希强调了这个成就的意义,并指出,“科学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维勒这个伟大的贡献很快就被写进了教科书和科学史著作中。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赫尔曼·弗朗兹·莫里茨·柯普(Hermann Franz Moritz Kopp)所著的《化学史》(History of Chemistry)一书。在这本书中,柯普描述了维勒的实验如何“摧毁了早先被广泛接受的关于有机体与无机体之间的区别的理论”。直到1854年,维勒关于尿素合成的重要意义仍然被学界广泛强调,例如,德国化学家赫尔曼·科尔伯(Hermann Kolbe,1818—1884)这样写到,人们一直认为存在于动物和植物体内的化合物的形成“应该归功于一种专属于生物界的非常神秘的固有力量,即所谓的生命的力量”。但是现在,随着维勒划时代的重大发现,有机化合物和无机化合物之间的鸿沟已经被填平了。
然而,与历史上一再经受重新考察的许多重大发现一样,维勒所完成的贡献也经历了一个重新解释的过程。“修正后的故事”带给我们的新见解甚至可能会使那些接受传统教科书解释的人感到惊讶——科学史学家彼得·兰贝格(Peter Ramberg)把这种传统解释称为“维勒神话”。这个神话在1937年达到顶峰,伯纳德·贾菲(Bernard Jaffe)在他所著的一本相当受欢迎的化学史著作《严酷的考验:伟大的化学家的生活和成就》(Crucibles:The Live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Great Chemists)中,细致生动地描写了维勒作为一个年轻的科学家在他那“神圣的庙宇”(实验室)中“辛苦劳作”,最终证伪了神秘生命力量的故事。
兰贝格指出,维勒做出的贡献当然是实验研究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维勒同时代的人对这一结果的反应究竟如何,为什么留下来的记录少到几乎没有。尽管贝采里乌斯显然对维勒的工作激动不已,但是这与其说是在活力论盛行的时代背景下的一种反应,还不如说是因为尿素的合成标志着可以把盐类化合物转变为非盐类物质。维勒证明,只要通过重新排列内部原子,就能够把氰酸铵变成尿素,而重量上既不增也不减,这也就意味着,他已经给出了被化学家称为“异构现象”(isomerism)的最重要的、最好的一个例子。维勒的做法无疑有助于破除原来的陈旧观念,即具有不同的物理和化学性质的两个物体不能由同样的成分构成。
历史学家现在普遍认为,仅凭一个实验不足以证明维勒发现了有机化学这个领域。维勒的尿素合成似乎并没有对活力论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贝采里乌斯本人认为,尿素只不过是一种废料:与其说尿素是一种有机化学物质,还不如说它“占领”了有机和无机之间的“中间地带”。此外,维勒的原料本身就来自有机物,而不是来自无机物。而且他这个成果也并非是独一无二的:早在四年前,他自己就已经利用水和氰人工制成了另一种有机化合物:草酸。科学史学家约翰·布鲁克(John Brooke)的最后结论是,维勒的合成尿素“只不过是试图阻碍活力论思想的河流滚滚向前的一小块儿鹅卵石而已”。
形形色色的“活力论”
活力论就像宗教一样,并不会随着新的科学发现不断涌现而轻易地自行消失。要实现信仰体系的更新换代,就必须从大量的实验中积累起足够厚实的证据。尽管不断进步的科学已经渐渐促使人们摆脱活力论的影响,但是这需要人们付出几百年的努力,甚至到了今天,扑灭这种神秘主义信仰的任务仍然没有最终完成。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如果能够有效地利用一系列关键成果,古老的活力论思想原本早该被摧毁了。这最早可以追溯到1665年,当时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1635—1703)开创性地使用了显微镜,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现了细胞。由于胡克以及其他一些发明家的努力,如荷兰人安东尼·范·列文虎克(Antonie van Leeuwenhoek,1632—1723),科学家们积累了许多“细胞演化为生命的主要生理结构”的证据。在16世纪和17世纪,随着现代科学的诞生,活力论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到了1839年,即维勒合成尿素十多年后,马蒂亚斯·雅各布·施莱登(Matthias Jakob Schleiden,1804—1881)和西奥多·施旺(Theodor Schwann,1810—1882)已经明确地写道:“所有活的生物都是由活的细胞构成的。”1855年,现代病理学之父鲁道夫·菲尔绍(Rudolf Virchow,1821—1902)提出了所谓的生物发生法则(Biogenic Law),即“一切细胞皆来源于细胞”或者“所有活细胞都来自已有的细胞”。这与自然发生说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然发生说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顾名思义,这种学说认为,生命能够从非生命的物质中自发地产生,比如说,蛆虫生自腐烂的肉、果蝇产自香蕉。
1859年,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完成了一个著名的实验,有力地反驳了通过简单的实验就能实现“自然发生”的观点。巴斯德分别对装在两个不同的瓶子里的肉汁进行了加热,一个是没有塞子的直颈瓶,让肉汁直接接触空气,另一个则是S型曲颈瓶,并且塞上了棉塞。当直接暴露在空气中的直颈瓶里的肉汁冷却后,里面长出了细菌,而在另一个塞了棉塞的曲颈瓶里却没有长出细菌。巴斯德认为,他自己这个实验足以证明微生物无处不在(包括存在于空气中)。然而,与维勒的实验一样,巴斯德的这个实验的具体细节无法让人确信不疑,因为许多明确的证据都是由一系列德国科学家的后续工作提供的。
以巴斯德的实验为先导,后来的一批科学家最终排除了“生命最初是由或者可能是由无机化学物质发展而来的”这种可能性。1906年,法国生物学家和哲学家勒·当泰克写道:“人们常说,在巴斯德之前,许多科学家竭尽全力在实验室里制造生命,但是巴斯德已经证明了,这种努力终将是没有用的。但是事实上,巴斯德只是表明了:通过采取适当的措施,我们可以让所有入侵物种确实存在于某些作为它们食物的物质之上。这就是全部。生物合成仍然是一个问题,并未解决。”
虽然巴斯德已经表明了怎样可以把特定的生命形式排除在无菌环境之外,但是他没有增进我们对“数十亿年以来,生命是如何在地球形成之初就已经奠定根本的”这一问题的理解。1880年,德国演化生物学家奥古斯特·魏斯曼(August Weismann,1834—1914)把一个重要的推论引进了生物发生法则,使生物发生法则回归到了最根本的起源。魏斯曼写道:“要对今天的活细胞进行追根溯源,就必须回到古代。”换句话说,今天的活细胞必定存在一个共同的祖先细胞。当然,这也就把我们带回到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名垂青史的进化论巨著《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上去了。达尔文与英国博物学家、探险家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一样,都认为存在于所有生物物种上的变化或变异特征都是代际相传的。有些变异产生了有利的结果,所以在每一代都能茁壮成长,因此它们——和它们的基因——变得更为普遍,这就是自然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新的变异不断积累,某一个世系可能已经演化到了一种程度,它不再与它的近亲交流基因。到这个时候,一个新的物种就诞生了。
尽管已经取得了上述科学进展,但是直到20世纪,活力论者仍然拥有许多热情的支持者。著名的德国胚胎学家汉斯·杜里舒(Hans Driesch,1867—1941)就是其中之一。由于身体形成于一个没有任何“模式”或“图案”的单细胞这个智力难题对他来说似乎是无法解决的,于是杜里舒转向求助于实体论(entelechy,这个单词源自希腊语entelécheia)的观念。这种理论要求有一个“灵魂”“组织现场”或“生命元素”来激活生命的物质。1952年,伟大的英国数学家艾伦·图灵(Alan Turing,1912—1954)向人们展示了如何从单一的一个胚胎开始,创造出一种新的模式。类似地,法国哲学家亨利—路易斯·柏格森(Henri-Louis Bergson,1859—1941)则提出,存在着能够克服活体内部物质的阻力的生命冲动。即使在今天,虽然大多数严肃的科学家都认为,活力论早已经被推翻了,但是还有一些人坚守这种信念,认为生命是建立在一些神秘力量的基础之上的。也许这并不令人惊讶:对于它的支持者来说,活力论这个术语拥有许多含义,不过,被广泛接受的有关生命的定义仍未出现。
在我们这个时代,一种新的活力论出现了。在这个更为精炼的活力论中,被强调的与其说是“生命的火花”,不如说是“其他理论的困难”,即现有的一切理论,无论还原主义,还是唯物主义,似乎都不足以解释生命的神秘。这种想法反映了这样一种信念:活细胞的出现极其复杂,它产生于能够形成相互连接的反馈循环的大量相互作用的化学过程中,仅仅根据这些构成过程和它们的构成反应是不足以描述整个过程的。因此,今天的活力论用改变过的中心观点把自己伪装了起来,它将重点从DNA转移到了细胞的“涌现性”上来。这里所谓的“涌现”,是指细胞大于组成它的所有分子的总和,而且在特定的环境有特定的表达形式。
这个精巧的新活力论无疑会导致一些人倾向于看轻甚至忽视DNA的重要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一点上,还原论并不能给我们任何帮助。细胞的复杂程度是如此之高,再加上大多数大学里的教学部门不断地对生物学进行细分,导致在许多人中间出现了蛋白质中心论和DNA中心论的观点之争。近年来,DNA中心论者越来越多地把重点放在了实验胚胎学上,“开关”系统会打开或关闭细胞中的基因,以应对诸如压力和营养这样的环境因素。从许多人现在的行为表现来看,就好像是实验胚胎学真的已经彻底从DNA驱动的生物学中分离出来了,或者已经成了一个完全独立于DNA驱动的生物学的一门独立学科了。当一个人把不可测因素加入到细胞质中去的时候,那么他在无意中就已经落入了活力论的陷井了。同样地,当一个人强调细胞的“高于DNA”的神秘的“涌现性”时,也是如此。强调这些,就相当于复兴“细胞产生细胞论”,即一切活的细胞都来自现有的细胞。
当然,细胞确实是所有目前已知的生命得以演化的最基本的生物基础。因此,对它们的结构和组成成分的理解是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新陈代谢这些重要的核心学科的基础。然而,正如我希望在本书中阐释清楚的那样,如果细胞缺乏遗传信息系统,那么它们很快就会死亡——通常来说,最短几分钟内,最长几天。最大的例外是人类红细胞,它的“半衰期”为120天。没有遗传信息的细胞无法造出蛋白质或者脂类分子膜,而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能够储存水性物质的细胞膜。这样一来,它们将不再演化、也不再复制,因此也就不能够存活下去了。
尽管我们承认,对维勒的尿素合成实验的神化掩盖了一些东西,使之无法精确地反映历史事实,但是维勒实验的基本逻辑仍然对科学方法造成了强大的、极具学科“合法性”的影响。在今天,证明化学结构正确性的标准做法仍是进行化学合成,并证明合成物质里包含了天然产品的所有属性。成千上万的科学论文都是从这个假设或者包含“合成的证据”这样的措辞开始的。我自己的研究也一直是在维勒写于1828年的那封信中所阐述的原理的指导下进行的。2010年5月,我自己创办的J.克雷格·文特尔研究所(J.Craig Venter Institute, JCVI)的研究团队通过计算机程序和四瓶化学物质合成了一个完整的细菌染色体,然后我们把这个染色体植入一个细胞中,创造出了第一个合成有机体。我们成功了!这是一个能够与维勒的工作和他的“合成的证据”相提并论的事件。
冯·诺依曼的“细胞自动机”
机械唯物主义生命观促使一些人试图利用机械系统和数学模型创造生物学之外的人造生命。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人们才终于承认DNA是一种遗传物质。在那之前,机械唯物主义的方法早已出现在科学文献当中了。根据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生命观,生命源自复杂的机械原理,而不是复杂的化学反应。1929年,年轻的爱尔兰晶体学家约翰·德斯蒙德·伯纳尔(John Des-mond Bernal,1901—1971)想象出机器有可能具有某种类似于生命的自我复制能力,他在《世界、众生和恶魔》(The World, the Flesh&the Devil)一书中描述,“在未来的后生物学时代,制造生命本身仅仅只是一个初级阶段。只有当我们打算让生命本身进行再次自我演化的时候,纯生命的制造才是重要的”。
在那之后的十年里,创造这类复杂“机械生命”的方法“合乎逻辑”地得到了发展。1936年,密码破译者和人工智能先驱艾伦·图灵描述了他那个众所周知的图灵机,它是写在磁带上的一组指令。图灵还定义了一个通用图灵机,它能够执行利用一个指令集写出来的任何计算命令。这是数字计算机的理论基础。
到了20世纪40年代,卓越的美国数学家和博学家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进一步发展了图灵的思想,构想出一个能够进行自我复制的机器。正如图灵设想出一个通用的计算机一样,冯·诺依曼构想出一个通用的构造器(构造函数)。在1948年于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的西克森举行的研讨会上,这个出生于匈牙利的天才概括了他的“自动机一般的且合乎逻辑的理论”。他指出,自然生物“一般来说比人工自动机更为复杂和精妙,因此也更让人难以精确理解其中的奥妙”。尽管如此,他坚持认为我们在自然生物身上观察到的规律对我们思考和设计人工自动机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从形式上看,冯·诺依曼的机器(冯·诺依曼细胞自动机)是一条由许多个细胞组成的“带子”,这些细胞编码了这台机器所要执行的“动作”序列。利用一个“写头”(也被称为“构造臂”),这台机器就能够打印(构造)出一个新的细胞模式,因此,它能够完整地复制出自身以及那条“带子”。从结构上看,冯·诺依曼这台能够自我复制的机器似乎有些笨拙,它由以下几部分构成:一个有80×400个方格的基本盒、一条“构造臂”和一个“图灵尾”,其中“图灵尾”本身也是一条编码指令的“长带子”,由15万个方格构成。(“图灵的自动机纯粹是一台计算的机器,”冯·诺依曼曾经这样解释,“而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制造出另一台自动机的自动机。”)总之,这个“生物”由大约20万个这样的“细胞”构成。为了进行复制,这台机器需要通过“神经元”来提供逻辑控制、利用传输细胞传送来自控制中心的信息、利用“肌肉”去改变周围的细胞。在“图灵尾”的指示下,这台机器会伸出它的“构造臂”,然后对它进行来回扫描,通过一系列的逻辑操作制造出一个自己的副本。这个复制品又能复制出另外一个副本,如此不断循环反复。
在我们这个数字世界和生物世界的科学进步并驾齐驱的时代,这些指令的性质变得更加清晰了。薛定谔提出了一些论述,似乎可以作为他的密码本的“第一参照”。他说:“正是这些染色体,或者可能是那些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真正看到的、被我们误认为是染色体的中枢骨骼纤维,携带了某种能够决定个体未来发展的完整模式和成熟后功能的密码本。”紧接着,薛定谔又继续指出,这个密码本可能就像二进制那样简单:“事实上,在这样一个结构中,原子的数量不需要非常大,原因是,为数不多的原子就能制造出几乎无限数量的可能物质。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试着考虑一下莫尔斯电码这个例子。莫尔斯电码由点和画这两种符号组成,它们之间的不同组合不超过4种,却可以表达出30种不同的意思。”
尽管冯·诺依曼构思他的自我复制自动机的时间要比双螺旋结构的DNA中真正的遗传密码被发现早好多年,但是他确实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到演化能力上了。在他的西克森演讲中,冯·诺依曼告诉听众,他这台机器执行的每条指令都“大致影响了基因功能”,他还继续描述,这台自动机中的错误是如何以像突变过程中会出现的某些典型特征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从规则的条件来看,这似乎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但是这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可能性:有可能以修改后的特征不断进行自我复制。”正如遗传学家悉尼·布伦纳曾经指出的那样,可以说,生物学为图灵和冯·诺依曼的机器提供了最好的真实世界的例子:“作为有机体的一种符合表征的基因——密码本这个概念所表达的含义,确实是生命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
在上述能够自我复制的机器的基础上,冯·诺依曼还进一步构思了一台纯粹基于逻辑的自动机。这台自动机并不需要一个“物理的身体”,也不需要海量的实体零件,相反,它是以一个网格中能够不断改变自身状态的细胞为基础的。对此,冯·诺依曼的同事,曾经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在那里他们一起为“曼哈顿计划”而工作)与他共事过的数学家斯塔尼斯拉夫·乌拉姆(Stanislaw Ulam,1909—1984)是这样解释的:冯·诺依曼利用一个抽象的数学工具来发展他的设计。乌拉姆自己过去研究晶体生长理论时也曾经利用过这个数学工具。1953年3月2日~5日,冯·诺依曼在位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发表了题目为《机器和生物》(Machines and Organisms)的瓦尼克桑演讲,他的“自我复制自动机”就是在这次系列演讲中公布于世的,它也是有史以来第一台细胞自动机。
正当这些科学家继续致力于研究“模型化的生命”时,1953年的4月25日,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核酸的分子结构: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Molecular Structure of Nucleic Acids:A Structure for Deoxyribose Nucleic Acid)这篇里程碑式的论文,至此,我们对真实生物的理解发生了改变。他们两人是在英国剑桥大学完成这项研究的,而他们提出的DNA双螺旋结构模型则是建立在由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1920—1958)和雷蒙德·高斯林(Raymond Gosling,1926—2015)所获得的X射线晶体数据的基础上的。沃森和克里克描述了“优雅”的双螺旋分子结构,解释了它的功能以及DNA是如何进行复制并将它的指令一代一代传递下去的。这是一台天然的自我复制自动机。
科学家努力创造另一种能够自我复制的自动机的开端,以及他们对人造生命研究的起步阶段,大体上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这也正是第一代现代计算机开始投入使用的时期。生命遗传信息系统密码特征的发现自然而然地促使人们将它与图灵机进行比较。图灵本人在他那篇有关人工智能的奠基性论文(发表于1950年)中也讨论了适者生存法则是一种有可能推进演化的“缓慢的方法”,这不仅仅是因为实验人员并不受限于随机的突变。许多人开始相信,人造生命将会在计算机内复杂的交互作用中出现。
各种各样的思想潮流都汇聚在这样一些焦点上:冯·诺依曼的理论以及他所做的关于早期计算机的研究和他提出的自我复制自动机的模型;图灵的理论以及他提出的有关人工智能机器的基本问题;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einer,1894—1964)在他于1948年出版的一本名为《控制论》(Cybernetics)的书中所描述的理论——他运用来自信息论和生命体的自我调节过程中的一系列思想,讨论控制论领域中的活的生命体问题。随后还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尝试,科学家试图在计算机中点燃生命之火。有关这方面最早的一个尝试出现在1953年,那是在位于新泽西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内,挪威裔意大利病毒遗传学家尼尔斯·奥尔·巴黎塞利(Nils Aall Barricelli,1912—1993)进行了一系列“旨在搞清楚发生在人造世界内的、类似于发生在活的生物体内的各种演化可能性”的实验。他报告了各种各样的“生物现象”,比如,在父母“生物体”之间进行成功的杂交,交配在进化演变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合作在演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等。
这个潮流一直没有停歇。几十年之后,即1990年所完成的那个人造生命实验或许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这一次,特拉华大学的托马斯·S.雷(Thomas S.Ray)进行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尝试,有史以来第一次,他以达尔文进化论为原理编制计算机程序。在他的人造生命中,“有机体”(即计算机编码片段)要在机器内部一个封闭的“自然保护区”内为内存(空间)和处理器能力(能量)而“战斗”。为此,他不得不克服的一个关键性障碍:编程的语言是“脆弱的”,在这个“有机体”内部,任何一个小小的变异——一行、一个字母甚至一个点放错了地方——都可能会导致程序停止运行。托马斯·雷设法进行了一些改进,以保证突变不那么容易会使他的程序停止运行。在这之后,又接着出现了一些其他版本的“进化计算机”,其中最突出的是阿维达(Avida),这个软件是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由加州理工学院一个研究自我复制计算机程序的演化生物学机制的团队设计的。研究者们相信,随着功能更强大、计算能力更高的计算机的出现,他们将能够制造出更为复杂的生物,因为按照常理,计算机的环境越丰富,人造生命的“日子”就能够过得更加“宽裕”,它们繁殖的速度也将更快。
即使在今天,仍有一些人认为,在巴黎塞利的世界中复制代码的原始程序碎片是今天的数字世界以及互联网和其他网络能够进行自我复制的多字节字符串的始祖。乔治·戴森(George Dyson)在他的《图灵的大教堂》(Turing’s Cathedral) 一书中就持有这个观点,他指出,现在存在着一个自我复制数字代码的宇宙,它正以每秒数万亿比特的速度不断膨胀,那是“一个有着自己的生命的宇宙”。这些虚拟的“景观”正以指数级速度在扩大,正如戴森自己所观察到的那样,它开始变成一个DNA的数字宇宙。
一书中就持有这个观点,他指出,现在存在着一个自我复制数字代码的宇宙,它正以每秒数万亿比特的速度不断膨胀,那是“一个有着自己的生命的宇宙”。这些虚拟的“景观”正以指数级速度在扩大,正如戴森自己所观察到的那样,它开始变成一个DNA的数字宇宙。
但是事实上,这些“虚拟牧场”总体上说还是比较贫瘠的。1953年,仅仅在巴黎塞利试图在一个人造世界中创造演化过程6个月之后,他就发现,任何在计算机中制造人造生命的尝试都有一些巨大的障碍需要克服。他报告说:“如果一个人解释说计算机中生物体的器官和能力的形成与那些活的有机体一样复杂,那么他必定没有看清楚某些东西……不管我们制造了多少突变,数字仍然还是那些数字,这些数字本身将永远不会变成有生命的物体!”
不过,最初构想的人造生命确实获得了新的虚拟生命,它们新的生命形式存在于游戏和电影当中,例如《2001: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yssey)中凶残的哈尔9000、电影《终结者》(Terminator)中进行种族灭绝的天网、《黑客帝国》(The Matrix)中恶毒的机器等。然而,现实情况仍然远远落后于此。在基于计算机的人造生命中,在被制造出来的有机体的基因序列或基因型与它的表型、基于这个序列的生理表达形式之间没有什么差别。在活的细胞里,DNA编码是以RNA、蛋白质和细胞的形式来表示的,它们形成了所有的生命物质。与此相反,人造生命系统则会迅速失去动力,这是因为,在计算机模型内的遗传潜能并不是开放式的,而是预先设定的。与生物世界不一样,计算机演化的结果已经被编进它的程序里了。
合成生命时代的到来
在我自己的“基因学”里,我把化学、生物学和计算机技术成功地融合到了一起。由DNA机器(人类)所设计的数字计算机现在被用来读取DNA内的代码指令,然后进行分析,并将新的代码指令写入DNA,以便创造出一种全新的DNA机器(合成生命)。当我们宣布创造了第一个合成细胞时,有些人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扮演了上帝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完成的这个实验恰恰表明了新生命的创造为什么是不需要上帝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我们确实“扮演了上帝的角色”。我还认为,在我们成功利用化学物质创造出了人造生命之后,我们最终将一劳永逸地终结所有活力论的残余观点。但是,我似乎还是低估了依然遍及现代科学思想各个领域的活力论信念的巨大影响。信仰是科学进步的天敌。例如,认为蛋白质是遗传物质这种信仰推迟了DNA作为遗传信息载体的发现时间,或许整整推迟了半个世纪之久。
一直到20世纪下半叶,我们才开始明白DNA便是薛定谔所说的“密码本”,并且破译了它所携带的复杂信息,进而开始精确无误地搞清楚了它是如决定生命进程的。在理解生命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史诗般的成就,它标志着一个新的科学时代的到来。是的,一个整合了生物学和科技的新的时代已经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