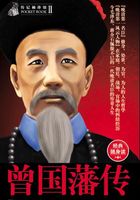
第4章 少年才子——曾国藩(2)
在京城学习期间,曾国藩曾经写信给弟弟们,很是自豪地向他们介绍自己结交的一些朋友。
曾国藩信中所提之人都非平庸之辈,他们都是北京的名流学士。这些人都是曾国藩在翰林学习时结交的,这些人是曾国藩在北京的主要交际对象,他们对曾国藩的影响可谓至深,有的是曾国藩一生的好友;有的是曾国藩事业上的指路人;有的对曾国藩的文学方面有很大的帮助;曾国藩一生的成就与他们的影响密不可分。以至于后来,曾国藩在教导子孙后代时也着重强调交友要慎重,不可大意,因为一位好友能给你带来无穷的益处,而不良的朋友带给你的一定是负面影响。
邵懿辰,字位西,清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久官于京师,熟悉朝章国政,朝廷不少大典、礼制、诰文均出其手,且博览典章,撰有《礼经通论》、《尚书传授同异考》、《杭谚诗》、《孝经通论》等。处理完繁忙的军机之事,他经常和唐鉴、梅柏言等人“以文章道义相往来”。曾国藩到京时,他任军机章京,曾国藩对这位老前辈格外尊敬。
刘传莹,字椒云,湖北汉阳人,官至国子监学政,专于古文经学。他是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养病期间结识的一位挚友。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曾国藩因病休养,趁此机会他阅读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有不明之处他便请教刘传莹,刘传莹也向曾国藩请教理学,二人互相学习,一来二去便成为挚友。
何绍基,字子贞,号东洲,别号东洲居士,晚号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晚清诗人、书法家,此人精通书法,尤精说文考订之学。曾国藩结识何绍基之后,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正是何绍基的长处,于是在写作方面他以何绍基为榜样。
吴廷栋,字彦甫,号竹如,安徽霍山人。吴廷栋爱好宋儒之学,入官极重视为官的品行,蹇蹇自靖。他与曾国藩无话不谈,一谈就是一天。谈论的话题都是修身治国的道理。从吴廷栋那里,曾国藩知道了窦兰泉,此人见识独特,非常不一般。
此外,曾国藩还认同子思与朱子的学习之道:学习就像是炖肉,先用猛火攻之,然后再用细火慢慢煨,这样,炖出的肉才会又香又嫩。曾国藩认为自己以前读书方法不对。所以他想搬进城去,改变自己的学习方法,摒除一切。但同时他也有所顾忌,城里有良师益友,唐鉴、倭仁、吴竹如、窦兰泉;城外也有一些像邵蕙西、吴子序、何子贞、陈岱云等曾国藩天天想见的人。
曾国藩一生交友无数,城内城外均有,他舍不得放弃任何一方,经常恨自己不能有分身之术。可以说,曾国藩是幸运的,因为他身边有那么多的挚友为他指引方向,给他带来光明。曾国藩曾言之:“与周瑜周公瑾交往,好像喝很甘醇甜美的酒一样舒服。”他在和邵蕙西的交往中就包含着这种感觉,两人自从见面就长谈不休,直到很晚也不愿分手,每次都是如此。对于子序,曾国藩也是十分佩服,此人见识远大,理论精辟,让曾国藩心生敬仰。特别是他对曾国藩所说的这番话:“用功好比掘井一样,与其掘了好几井而没有一口掘到地下的泉水,倒不如老是守着一口井掘,一定要掘到泉水为止。”曾国藩认为,此话正说出了自己的弱点,以后一定牢牢记住此话,专心掘一口井。
曾国藩曾写信告诉家人:“我等来到京城后,才开始有志学习写诗,写古文,并习字之法。但最初也没有良友,近年来得到一两位良友,才知道有所谓治学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才知道范仲淹、韩琦等贤臣可以通过学习做到;才知道司马迁、韩愈的文章水平通过学习也可以达到;程颐、朱熹也可以通过学习达到。”
起初曾国藩认为,京城里的那些成功人士、名流之辈都是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即的。两年之后,通过与一些朋友交流,他了解到自己以前的想法是错误的,“圣贤豪杰皆可为也”,不存在什么高不可攀。在曾国藩二十年后重回南京时,他还专程看望吴廷栋。当时的吴廷栋年事已高,腿上有病,但每天仍然校勘书籍,日理万机的曾国藩忙于国事之余,都会抽空看望这位老者,他们一起谈论时事,不亦乐乎。
实际上,曾国藩在不断结交新朋友的同时,也不忘联系旧朋友。他深知,人生路途离不开朋友,正是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才使自己有了一番成就。
5.若修其志,必先修其身
人若实现大志,必先修身养性,在这一点上,曾国藩是很好的榜样。他曾被人们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理学大师”,是晚清一代“儒学藩镇”。无论这些称谓是否合适,曾国藩都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曾国藩还在长沙岳麓书院学习期间,就接触了儒学。后来点翰林入院读庶吉士,满腔热情的他给家人写信,信中说自己要成为诸葛亮、陈平等人那样的“布衣之相”,学问方面要不断向孔、孟等人学习,争取做孔、孟那样的大儒。他写给弟弟的信中也体现了这一点:“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他还把“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作为他人生的座右铭,时刻提醒自己。又言:“自己以不为尧舜周公为忧,以学不讲德不修为忧。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
这无疑是曾国藩为自己立下的一个大目标——他想成为一个大儒,圣贤之人。有了这个目标之后,曾国藩就开始博览群书。什么样的书他都学,经、史、诗、文一样都不少,什么名家的著作他都读,司马迁、班固、李白、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方苞、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著作他都读过。直到后来,受到唐鉴、倭仁等一些理学家的影响,曾国藩读书就不再广泛了,而是有了一定的选择性,他开始专攻程朱理学,尤其专于朱熹。
对曾国藩思想与治学影响较大的有唐鉴和倭仁,这两人本是师生关系,曾国藩也是经唐鉴介绍结识了倭仁。曾国藩也是因为唐鉴才学习程朱的。
唐鉴,字镜海,号翕泽。湖南善化人,自幼就勤奋上进。嘉庆十二年(1807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十年(1840年),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蜚声京门。其实,曾国藩和唐鉴的相识也是出于偶然。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唐鉴调往京城,任太常寺卿,道光皇帝在乾清门迎接他,当时的曾国藩作为翰林院检讨,在一边侍驾。道光皇帝见到唐鉴之后,称赞他:“治朱子学有成就,并能按‘圣学’之教亲自去做,可谓朝廷的好官,读书人的榜样。”对于道光帝的这一番称赞,久经官场的唐鉴并未觉得有什么,可是曾国藩却非常羡慕,对唐鉴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曾国藩便打听到唐鉴的住址,以弟子之礼对这位功成名就的老乡进行拜访。
唐鉴一生爱惜人才,特别喜欢勤奋好学、聪明机智的人,而曾国藩正具备这些优点,他也知道曾国藩是自己同乡,所以对于曾国藩谦虚的态度很是满意。于是二人一见如故。
可以说,唐鉴跟曾国藩的第一次谈话,对曾国藩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次谈话让曾国藩在做事、修身、做学问方面都有了新的认识。
曾国藩向唐鉴请教了关于读书、修身方面的一些妙诀。唐鉴说:“读书要以《朱子全集》为根本。读该书时不能把它当做八股进阶之书,应该躬自实行,这是修身的典籍。修身的妙诀在于‘整齐严肃’、‘主一无适’,整齐表于外而主一持于内。读书要讲求方法,要‘在专一经’,只有一经通后,才能旁及诸经。所谓学问,只有义理、考核、文章三门,三者之要在义理统之。”唐鉴还说:“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不必他求。至于用功着力,应该从读史下手。因为历代治迹,典章昭然俱在;取法前贤以治当世,已经足够了。”
唐鉴告诉曾国藩,他一生读《朱子》,以其修身。修身检讨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每天记日记,一定要认真记录。不存在欺骗、隐瞒、作假之事,最丑的事要记下来,最丑的心也要记下来,对着圣贤天天检讨,时间久了自然就达到圣贤的境界了。圣贤就是不自欺,不欺人。在这方面,唐鉴向曾国藩介绍了倭仁,倭仁这方面做得不错,非圣贤莫属。
听了唐鉴的一席话,曾国藩可谓“胜读十年书”。三十年读书,却不知学问门径。多亏唐鉴指点,他才拨开迷雾,看到光明。于是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这句话:“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随后,曾国藩写信给家人。其中他写道:“我最初治学,不知根本,寻声逐响而已。自从认识了唐镜海先生,才从他那里窥见一点学问的门径。”
此后,曾国藩经常来到唐鉴住处,向他请教学问,与他讨论国事,同时向唐鉴学习朱子理义。唐鉴教导曾国藩立下“日课”:早起、主敬、静坐、读书、写日记、偶谈、做诗文、临帖、专读一经、谨言、保身、夜不出门等十二条规矩。除此之外,曾国藩自己还立下了《立志箴》、《居敬箴》、《主静箴》、《谨言箴》、《有恒箴》,挂在书房内,时刻提醒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为了督促曾国藩的进步,使其进步,唐鉴经常检查曾国藩的日记,有不妥之处马上指出,让曾国藩改正。对于曾国藩敢于揭发自己的隐患之处,唐鉴给予鼓励。另外,唐鉴还把自己编写的《畿辅水利备览》一书交给曾国藩,让他细细阅读。使他知道作为一个儒学家不仅要精通圣典,更要关心民事和经济,绝不可只会背圣贤书,不会治理国事,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名副其实的书呆子。从修身到治国,样样精通,这就是儒家“内圣外王”的真谛。
唐鉴向曾国藩介绍了倭仁,倭仁也是著名的理学家,他的读书修身也受教于唐鉴。倭仁对曾国藩颇有影响。倭仁,晚清大臣,乌齐格里氏,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九年(1839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考中进士后进入京师,历中允、侍讲、侍读、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同治帝之师。任副都统、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与李棠阶、王庆云、罗绕典等人进行“会课”,坚持长达十年之久,此“会课”有三步,第一步是写日课,每天都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有过改之,无过继续,属于修身养性;第二步,互相批改日课,有批评,有鼓励,有建议,以此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使人进步;第三步,当面指陈得失。这些人中只有倭仁能坚持下来,自始至终都“精进严密”,这一点让人佩服。
曾国藩认识了倭仁之后,就一心跟着倭仁学习,发现倭仁在实践中对自己的要求比唐鉴还严格。曾国藩稍一有念头,倭仁就会记下来,然后和自己辩解,哪怕是有一点点不合圣贤的想法倭仁都会将之消除在萌芽之中,让曾国藩的心术、学术、治术归之于一,这种克己的做法,近似于苛刻。在倭仁的要求下,曾国藩也开始一边读《朱子全集》,一边写日课,以便反省自己。
曾国藩在文、史、书法、考据方面皆有很深的造诣,但是思想宗旨一直没脱离儒学,在儒学方面,曾国藩又认宗朱熹的新儒学。在与太平天国的对抗中很明显地看到这一点,曾国藩和太平天国之间进行的是一场“宗教战争”,曾国藩打的是儒教的旗号,而洪秀全崇信的是拜上帝教,此说法是否准确姑且不谈,但说明曾国藩的确是一个儒家道统的继承与捍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