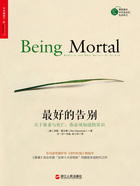
在我的早年生活中,从来没有目睹过严重疾病或者老年生活的种种难处。我的双亲都是医生,身体健康、强壮。他们从印度移民到美国,住在俄亥俄州的雅典(一个面积不大的大学城),在那里养育了我和妹妹。我的祖父母还在印度,并不与我们在一起生活。与我有交集的老人是一位女士,跟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我上中学时她曾教过我弹钢琴。后来她病了,不久就搬走了。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因此,老年生活的境遇完全不在我的感知范围以内。
在大学期间,我开始和凯瑟琳约会,她成了我的女友。1985年的圣诞节,我受邀去她家玩。她家住在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市。我认识了她的祖母爱丽丝·霍布森。老太太当时77岁。印象中,她热情、思想独立,从不刻意掩饰她的年龄。她一头自然的白发,梳成贝蒂·戴维斯风格的发型:直发,梳向头的一侧。她的手上缀满了老年斑,皮肤皱皱巴巴的。她穿着简约但熨烫得整整齐齐的衬衫和裙子,嘴唇上抹了一点点口红,鞋跟远远超过了旁人想象的高度。
我后来和凯瑟琳结婚了。我了解到,爱丽丝奶奶生长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以鲜花和蘑菇养殖闻名的乡镇。她的父亲是花农,在面积达数十亩的温室里培植康乃馨、万寿菊、大丽花。爱丽丝和她的兄弟姐妹是她家的第一批大学生。在特拉华大学读书期间,爱丽丝结识了土木工程系学生里奇·霍布森。由于碰上了大萧条,他们直到大学毕业6年后才有能力结婚成家。早先由于工作的原因,他们经常搬家。后来他们生育了两个孩子,其中的吉姆成了我的岳父。里奇供职于陆军工程兵团,是大型水坝和桥梁建设方面的专家。10年后,他得到升迁,在华盛顿特区郊外的司令部工作,并一直工作到退休。他们把家安在阿灵顿,买了一辆车,到处游玩,同时,换了一所更大的房子,送两个天资聪颖的孩子上了大学。做这些事,他们都是用自己积攒的钱,无须贷款。
在一次去西雅图出差的途中,里奇突发心脏病。他原本有心绞痛的病史,胸痛偶尔发作时,他会服用硝酸甘油片应急,但这一次没有奏效——1965年的时候,医生们没多少绝招对付心脏病。在爱丽丝赶到医院之前里奇就死了,只有60岁。当时爱丽丝56岁。
凭着陆军工程兵团的退休金,爱丽丝能够保住她在阿灵顿的房子。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一个人在格林城堡街的那所房子里生活了20年。我的岳父母吉姆和娜恩就住在附近,但是,爱丽丝完全独立生活。她自己修剪草坪,还会修理水管。她和她的朋友波莉一起上健身房。她喜欢缝纫和针织,为每位家人缝衣服、织围巾,还制作红红绿绿的圣诞袜子,袜筒上绣着有纽扣鼻子的圣诞老人和家人们各自的名字。她组织了一群人,认购了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全年度表演的票。她的座驾是体积庞大的雪佛兰羚羊。为便于查看仪表盘,她在座椅上放了一块垫子。她做些跑腿打杂的事,探望家人,开车接送朋友,给那些比她病痛更多的人送饭。
随着时光流逝,我不免会猜想,这样的生活她还能维持多久。她身材娇小,身高一米五几。虽然每次有人提起身高的问题,她都会发怒,但是,她一年比一年矮,体力也一年不如一年。我同她的孙女结婚的时候,爱丽丝喜笑颜开,把我拉到身边,告诉我婚礼让她多快乐,可惜严重的关节炎害得她不能与我共舞。但她仍然住在家里,独自打理生活。
当我父亲见到她,了解到她一个人生活的境况时,吃惊不小。他是泌尿外科医生,见过很多老年病人,发现他们大多独自生活,为此,他总是感到不安。老人随着身体功能的逐渐退化,许多基本生活需求都需要旁人的帮助,这一天总会到来,他为此深感担忧。作为印度移民,他联想到自己有责任把老家的老人安顿到美国的家中,抽时间陪伴他们,照顾他们。父亲是1963年来纽约做住院医师的,他逐渐接纳了美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他放弃了素食主义,约会了后来成为我母亲的女朋友——同样来自印度的儿科住院医师。虽然同属于印度移民,但她跟父亲说着不同的语言。他后来娶了她,而没让我祖父为他安排婚姻,为此使得家人遭到非议。他还是一位狂热的网球迷,做过当地扶轮社的主席,私密的朋友间还喜欢讲一些黄段子。1976年的7月4日,是美国建国200周年的纪念日,也是他最惬意的一天。这一天,在雅典县展览会的正面看台,在几百个欢呼雀跃的人的注视下,他宣誓成为美国公民。但是,有一个美国人的习俗他没有接纳,那就是对待老人和病弱者的方式——让他们独自生活,或者把他们丢给一系列无名的设备,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日子同几乎只知道他们名字的医生、护士一起度过。这是同他的祖国印度最不相同的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