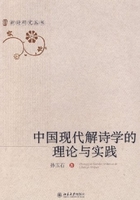
第4章 现代解诗学的理论内涵
现代解诗学的理论内涵,我以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解诗学是对作品本体复杂性的超越。解诗学对象是以象征派、现代派的作品为主,这些诗由于表现题材领域、审美意识追求和传达组织方式的特殊性,往往以复杂的形体出现,造成了人们理解和欣赏上的困难。一些批评家和读者往往称它们为“不懂”的“朦胧诗”、怪诞的“胡涂诗”。解诗学认为,由表现习惯的生活和感情世界转向表现生疏的感情和感觉世界,是新诗的一种进步。一些善于“从敏锐的感觉出发,在日常的境界里体味出精微的哲理的诗人”,在作品里“以敏锐的感觉为抒情的骨子”,又用暗示的方法来表现情调,便脱离了一般读者了解和欣赏的习惯,使得那些“只在常识里兜圈子”的一般读者,不免产生了“隔雾看花之憾”。朱自清先生解释了卞之琳难懂的短诗《距离的组织》之后说:“这篇诗是零乱的诗境,可又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将时间空间的远距离用联想组织在短短的午梦和小小的篇幅里。这是一种解放,一种自由,同时又是一种情思的操练,是艺术给我们的。”这种“复杂的有机体”是诗人用想象和智性创造的独特的艺术世界,就不能以“明了”和“晦涩”、“易懂”和“难懂”作为衡量的价值尺度。金克木认为,新诗一定可懂,“只不能是人人都懂而已。因为能懂的读诗者一定也要有和作诗者同样的智慧程度”。朱光潜先生进一步从心理上个别的差异来解释欣赏诗歌的审美距离。他认为“修养上的差别有时还可以用修养去消化”,而不容易消化的是“心理原型上的差别”,“创造诗和欣赏诗都是很繁复而也很精纯的心理活动,论诗者如果离开心理上的差别而在诗本身上寻求普遍的价值标准,总不免是隔靴搔痒”。河南一位中学教师写给胡适的信里,把卞之琳的《第一盏灯》、何其芳的《扇上的烟云》等称为谁也不懂的“糊涂诗”和“糊涂文”。胡适赞同他的“明白畅晓”的主张,却说“《第一盏灯》是看得懂的,虽然不能算是好诗。其余的两个例子,都是我们所谓应该哀怜的例子”。而沈从文先生却又说:“何其芳的散文,实在说不上难懂”,并称赞他是“近年来中国写抒情散文的高手”。一位读者认为《现代》刊载的杨予英的三首诗,读了“觉得无限神秘,奥妙,奇异之感”,使人“如入五里雾中,不得其解”,编者施蛰存先生却认为除一首《冬日之梦》“稍嫌模糊”外,其他两首却是“明白畅晓”的,问者的不解,“也许是故意”,也许是“不深思之故”。这些论述与争论,说明了现代诗本体的复杂性和可知性。解诗就是批评家对诗歌本体复杂性的认知和超越。闻一多说,在陌生的作品和诗人心理面前,人们有时“全不是你自己的主人”,“我们的障碍物乃是我们自己”,“你如何能摆开你的主见,去怪那完全和你生疏的‘诗人’的心理!”这也是“一切的文艺鉴赏的难关”。卞之琳先生在纪德作品译释序言的“附记”中也说:“解释的文字也应该尽于当钥匙的作用,因为纪德自己引导人也往往只引到门口为止,留下的都是被引导者自己的事情。现在如果这里既是一把没有铸错的钥匙,读者也应该超越它,而去追踪纪德,甚或进一步超越纪德。”解诗学的文字也就是以自身对作品复杂性的征服,给读者一把接近和鉴赏作品的钥匙。因为美就隐藏在这复杂的陌生里。对于复杂的陌生的征服和超越,是艺术鉴赏的准备,同时,我们鉴赏的愉快就包含在这理解和征服之中。
2.解诗学是对作品本体审美性的再造。一首现代诗即是一个独立的审美对象。解诗者在实践中缩短自身同审美对象之间的距离,因而理解的过程不是单纯的接受过程,而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艺术思维活动的实践。现代诗“远取譬”的想象、以象征和暗示曲折地表达情调等特征,使一首诗自身是一个艺术复杂的有机体,同时也在它的含蓄朦胧美中为读者和批评家留下了较大的创造空间。解诗学适应这种特点就产生了两个方面的规定性。
一方面,分析一首诗的意义,要从意象的联络和语言的传达入手,一层层挨着剥开去,弄清每一个意象、比喻(显喻和暗喻)的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每行诗句和每个词语的相互联系。诚如朱自清先生讲的,现代诗“意义是很复杂的”,如果“一个不留心便逗不拢来”,甚至与作品原意背谬,相差十万八千里。闻一多也讲,读一首诗要弄懂“每个字的意义”,“必须把那里每个字的意义都追问透彻,不许存下丝毫的疑惑”。例如朱自清先生解卞之琳的《距离的组织》一诗,把作者有意放在括弧里的一句诗“(醒来天欲暮,无聊,一访友人罢)”,与前面两行“报纸落。地图开,因想起远方的嘱咐/寄来的风景也暮色苍茫了”的含义弄错了。他没有分清“天欲暮”与“暮色苍茫”是一梦一真,括弧中的“友人”和末行“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的“友人”,是一我一他,主要就是因为把括弧中这句诗的主体与全诗的主体弄混淆了。而作者这点技巧的运用是艺术创造的权利。稍稍忽略了这种创造,解诗就会误入歧途,这是一个方面。解诗须遵从作者审美创造的逻辑性。
另一方面,解诗又是对于作品审美特性再创造的过程。强烈的参与创造意识使读者走进诗美的世界。朱自清先生讲的“细心看几遍”,“读者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搭起桥来”以完成对现代诗中省略的空间的填补,就是讲的读者再创造的过程。朱光潜先生更清楚地论述了这一再造的审美意义。他说:
读诗就是再做诗,一首诗的生命不是作者一个人所能维持住,也要读者帮忙才行。读者的想象和情感是生生不息的,一首诗的生命也就是生生不息的,它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一切艺术作品都是如此,没有创造就不能有欣赏。
这里从接受者的角度,说明了读者的想象和情感在作品审美再造中生生不息的作用。作品审美性的再造已经不是作者而是读者。解诗就包含了读者与批评家对这种审美再造能力的无限追求。从这个方面看,解诗学又是对作者审美创造能力的无限追求,也是对作者审美创造逻辑的补充和突破。
3.解诗学是对作品本体理解歧异性的互补。现代诗通过象征、意象、暗示、隐喻等种种艺术手段表现自己内心的感觉世界,追求在一种表现自己和隐藏自己的艺术效果中,吐露自己隐秘的灵魂。如金克木说的,一些“以智慧为主脑”的“新的智慧诗”,有“独特的对人生宇宙的见解”蕴蓄浸润其中。作品内涵的多义性和意象语言的朦胧性给解诗学带来了一个必然现象:对作品本体理解的歧异性和由此而产生的互补论。卞之琳的《鱼化石(一条鱼或一个女子说:)》只有四行:“我要有你的怀抱的形状,/我往往溶化于水的线条。/你真象镜子一样的爱我呢。/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作者在详细的注释和说明的文字中,都自认这首诗蕴蓄着多种意思,读者也可以作多种理解。诗的内涵表现了无限伸张的弹性。李广田先生评论说:“鱼化石,又岂止是鱼化石,这乃是一个代表,一种象征。”诗人在诗集的附录《鱼化石后记》中说:
诗中的“你”就代表石吗?就代表她的他吗?似不仅如此。还有什么呢?待我想想看,不想了,这样也够了。“这样也够了。”不错,作为诗,作为象征,这样就够了,就让读者们去“想想看”吧,你想到事业的完成,想到爱情的结合……你就只想到那“鱼化石”是可以的。纪德在其《纳蕤思解说》中说,一点神话本来就够了。这就是那从具体推到抽象,从有限推到无限的道理。
既然作者创作时就注入自己作品以多层次的内涵,也就更应该允许读者在作品中注入自己多层次的想象。朱光潜讲的读者的想象和一首诗的生命生生不息,施蛰存主张的“仿佛得之”为欣赏诗的极限,废名说明自己的《掐花》一诗,“有许多下意识”,容纳了童年“实在的经验”和佛教、古典诗词等多样文化,同他的《妆台》、《小园》一样,均可以作多种理解,都是这种理论的证明。现代诗的艺术创造也创造了读者再创造的权利。
读者和批评家的理解与作家的主观意图发生了歧异怎么办?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背谬的解释,应该以作者的本意为标准。前面讲的朱自清对《距离的组织》的误解,李健吾先生把《圆宝盒》理解为“圆宝”盒而不是圆的“宝盒”,从而误解了诗的意思,都是批评家与作者进行对话而后得到了正确的解释。另一种是合理的解释,它对作品理解的歧异没有超出象征派诗艺术的界定范围,即使作者出来说明他的本意,释义仍有存在的权利,与作者的一义成为互补的多义内涵之一。典型的例证可以举卞之琳的《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李健吾先生说:我贸然看做寓有无限的悲哀,着重在“装饰”两个字,而作者恰恰相反,着重在相对的关联。批评家的解释显然与诗人的本意出现了歧异。用正确和错误这两极可以概括两种意义的理解吗?不!批评家否定了这样简单的价值判断。他认为:“我的解释并不防害我首肯作者的自白。作者的自白也绝不防害我的解释。与其看做冲突,不如说做有相成之美。”关于《圆宝盒》,批评家李健吾和诗人卞之琳曾进行往返讨论。是不是诗人的自白就可抹煞批评家的理解了呢?也不!听听批评家聪慧的辩诘吧:“如今诗人自白了,我也答覆了,这首诗就没有其他‘小径通幽’吗?我的解释如若不和诗人的解释吻合,我的经验就算白了吗?诗人的解释可以撵掉我的或者任何其他的解释吗?不!一千个不!幸福的人是我,因为我有双重的经验,而经验的交错,做成我生活的深厚。诗人挡不住读者。这正是这首诗美丽的地方,也正是象征主义高妙的地方。这不是笨谜。一个谜,等你猜出来以后,除去那点儿小小得意的虚荣之外,只是一个限制好了的呆呆的对象。但是,一首诗,当你用尽了心力,即使徒然,你最后得到的不是一个名目,而是人生,宇宙,一切加上一切的无从说起的经验——诗的经验。”一首诗可以用错综的意象和读者的经验相结合,唤起“一座灵魂的海市蜃楼”。读者生活和诗的经验可以从自己的“视界”出发,与对象的“视界”相交融互补,形成一个新的再造的“视界”。这正是现代解诗学自身的特质给予批评家和读者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