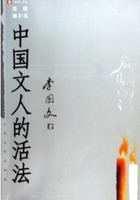
第7章 老弟弑兄该当何罪――文人笔下的“烛影摇红”疑案
汉字中的这个“弑”,专用于卑幼者对于尊长者的杀害。下属把皇帝杀掉了,子女把父母弄死了,要用准确的汉语来表达,就得用“弑”。由于我国有数千年封建史,登上龙位的帝王达三百多位,被“弑”掉的数量不少。因此,这个“弑”字,在汉语系统里,便和“朕”、“陛下”、“寡人”、“万寿无疆”、“万岁万万岁”一样,成了最高统治者的专属词汇。
当然,所有当皇帝的,都对这个“弑”字不感兴趣。相反,所有想当皇帝的人,对这个“弑”字,总是情有独钟。阿Q在未庄的大街上嚷嚷造反造反,要革这伙妈妈的命,心中也有这一个“弑”字在的。你别瞧不起他,他未必不敢当皇帝,他要坐在金銮殿上,照样人五人六。
英语中相当于这个意思的词汇,与汉语不尽相同,他们还加以弑君(regicide)和弑父(patricide)的区分。我一直不解,方块字难道会比英语粗疏吗?后来我悟出来了。原来西方历史中的封建统治时期,比我们短,帝王少,被弑者也少,出名的有英国的查理一世(Charles I),法国的路易十六(Louis XVI);不过,他们那里,逆伦者大概要比讲孝道的中国多得多,所以,弑皇帝和杀父母要分用两个词汇。
希腊神话中有位俄狄浦斯王,此人就是最出名的弑父者。杀了爹以后,还娶了自己的娘,居然生出来四个儿子,真是生猛得厉害,对比较古板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弗洛伊德的一本书,《梦的解析》,将“恋母情结”,称为“俄狄浦斯情结”,即由此而来。这个词汇,老外堂而皇之挂在嘴边,说出来不觉得不好意思。中国这块土壤,臣弑君,家常便饭,小事一桩,儿弑父,比较个别,甚为罕见。因为,不孝,或忤逆,是要被社会诅咒的,人神共弃的乱伦行为,更为天理难容。所以,汉字就无必要如英语那般精确,专门造一个类似patricide(弑父)的方块字,一个“弑”字,也就够用了。
所以,一提“弑”,在中国,专指皇帝脑袋搬家。被“弑”,很不快活,外国有断头台,喀嚓一刀,头颅跌落下来,即使痛苦,也是瞬间之事。而中国皇帝被弑,推翻者绝对不会让万岁爷死痛快的。勒死,淹死,毒死,闷死,吊死,烧死,不一而足。南唐后主李煜,就是被宋太宗赵炅,用其毒无比的鸩酒弑掉的。酒中下的鸩,史称“牵机药”,不知何种化学成分,不让你马上死,而是要你慢慢地死,不让你消消停停地死,而是要你手足相绞,前后扑,抽搐不止,在无穷痛苦的折磨中,耗到死透为止。真是残酷,鬼知道赵炅用的是一种什么药,估计已经失传了,要不然,元、明、清诸帝,会放过这样一种折磨文人的绝招?
李煜,作为诗人,是超一流的,赵光义若不杀他,至少有更多的佳作,留给后世,所以,遭遇这种其实是农民的君王,也是文学活该倒霉的一劫。但作为皇帝的李煜,三流都不及格。赵匡胤派大将曹彬,打到这位昏君的家门口,才想起抵抗。可抵抗派早被他听信谗言处置掉了。剩下的满朝文武,都是投降派,于是,我们这位诗人,白衣白褂,拱手纳土归顺。
宋太祖,要大度些,封他一个违命侯,羁押在开封府,至少还有写“最是仓皇辞庙日,挥泪对宫娥”的自由。宋太宗,心胸狭窄,毛泽东对他评价不高,说他“总不省”、“不知兵”、“无能”,所有无能的人都嫉能,所有无才的人都嫉才,所以,即位后第三年,就将其鸩死,够他妈狠。说句迷信的话,宋太宗最后不得好死,也是作恶多端的报应。“后主作小词,有‘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太宗恶之”,或说:“太宗使徐铉私见煜,煜太息称,当初悔杀潘佑(就是主张抵抗的将领)。及太宗问铉,铉不敢隐,因有牵机药之赐。”(近人陈登原《国史旧闻》)
赵炅堪称弑帝专家,不但弑掉了已经臣服的李煜、刘、钱?诸帝,还弑了自己的老哥大宋开国之君。此人特擅鸩毒之一道,是个恐怖杀手。中国封建社会的宫禁之中,诸如鸩酒、巫蛊、厌胜、符谶等等黑暗文化,是西方那些希腊、罗马、拜占庭、奥斯曼等庞大帝国的君主,望尘莫及的。他们的宫廷政变,无非行刺、暗杀、决斗、角力,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很小儿科的。
这位诗人,被虐杀的痛苦程度,在中国非正常死亡的文人中,大概要算头一份了。我至今弄不懂赵炅出于什么动机,要如此狠毒地收拾他?想来想去,一个原因大概就是女人了,谁教李煜有一个漂亮的小周后呢?偏偏被这位大兵出身的宋太宗相中了。也是时下一些新贵,粗粮吃腻了,换换胃口,想吃细粮,玩一玩具有文化品位的女人,来点情调什么的古代版。经常一顶小轿,将美艳的小周后抬进大内,一住好几天,玩个够,才放回来。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赵炅权力欲的恶性膨胀,所形成的赶尽杀绝的变态心理。你曾经当过皇帝,现在虽然不当了,但未必不想再当皇帝。所以,可怜的诗人,只好喝下这盏鸩酒,死得难看了。
皇帝其实不好当,觊觎他位置的人,也就是想“弑”他的人太多太多。但有史以来,还是有很多人想谋得这个有可能死得难看的可怕差使,尤其庄稼地里的农民兄弟。一部《二十四史》中数百次揭竿而起者,无一不是铤而走险的农民,因为横竖活不下去,还不如将皇帝弑掉,自己来当。一有无数金钱可用,二有无数女人可睡,何乐而不为?宣泄性欲和攫取财富,是为造反或革命的原动力,大致不错。
1927年,毛泽东勤工俭学不成,回到湖南老家考察农民运动,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句话,鼓动“痞子”起来造反。但他也看到这些“革命先锋”,是如何想在“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的性诉求。在那篇著名的调查报告中,这几句闲笔,倒是对农民革命家入骨三分、切中要害的心理描写。
农民穿上了龙袍,还是农民,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小农经济思想,像血型一样,至少他这一生,万难改变。巴尔扎克说过,不经三代的熏陶,成就不了一个贵族;同样,不经三代的蜕变,即使当上了皇帝,也还是换汤不换药,新鞋走老路的农民。试看近年来,因贪污而被枪毙的部级、副部级、以及大量司局级的案犯,一查,贫下中农甚多,而且,搞女人,搞票子,均为贪得无厌、永不满足的双搞好手,也证明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痞子精神”,是靠不住的,若不改造小农思想支配下的人生观,是决不能成器的。
赵匡胤、赵匡义(即赵光义,赵炅)兄弟,行伍世家,大兵出身,武装起来的农民,趁周世宗死后,孤儿寡母可欺,发动兵变,一举成功,赵老大得以披上了黄袍。大概权力这东西,如海洛因,上了瘾,无法自拔,尝到甜头的他,舍不得把龙椅交给其弟也来坐坐。赵老二在兵变中最卖力,没当上皇帝,本来窝火,等了十几年,不见动静,更急得五脊六兽。凡权力,皆诱惑,极大的权力,极大的诱惑,使得赵家老二,敢冒极大的危险,逼宫夺权,弑兄接位。这就是发生在公元976年(太祖开宝九年)冬天里那出悲剧的根本原因。
在多子女的家庭中,老大要宽厚一些,因为他出生时,没有竞争者,得到的是百分之百;老二来到人间,最多也只能得到百分之五十,纵使父母偏心,多也多不到哪里去,逼得他必须精明一些。因此,赵匡胤要憨厚些,赵匡义要刁蛮些,大概近乎事实。赵老大若及时发现其弟急不可待之心,主动礼让,也许不至于被赵老二“弑”掉。但赵匡胤最后说出“好做,好做”这句话,可以猜想做兄长的,终属厚道,还是做出让步,准备满足老二一心染指帝位的欲望。
从不足凭信的稗史演义,也能看出赵匡胤有这种大度的可能,这当然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愿有识者指教。记得旧时看过一部古装影片《千里送京娘》,赵匡胤为主人公,那汉子能够义不容辞,单骑匹马,千里迢迢,不避男女之嫌,护送一个毫无干系,只是被他搭救的异乡女子,回返家乡。我很钦佩,因为我做不到,尤其那样一个美丽的小姐。所以,我坚信,如此丈夫气概的赵匡胤,将帝位让出来,交给心急如焚的老弟,是做得出来的。
英雄救美,千里相送,本应是一则非常浪漫的故事,最后,由于赵老大的封建道德,江湖义气,导致一出香消玉殒的悲剧发生,真让人遗憾。这种假道学,肯定为今人所不取。但也看出赵匡胤的诚信,真朴,厚德载物的人格力量,与其急功近利的老弟,迥然相异之处。一路上,她骑马,他步行,晓行夜宿,朝夕相处,从太原到蒲州,一个极标致的女子,对这样一个极伟岸的男儿,又是如此倾心关注她的人,是无法不动情的。先是一再暗示,后是索性挑明,赵匡胤倒也诚实,承认自己绝非铁石心肠:“贤妹,非是俺胶柱鼓瑟,今日若就私情,一片真心化作假意,惹天下豪杰笑话。”拒绝了赵京娘的一片情。
明末冯梦龙的《警世通言》,描写赵匡胤为红脸汉子,赋予他强烈的性格特征。因为在国人的印象中,凡红脸汉,无不赤胆忠心,无不义薄云天,关云长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可惜那时的黑白电影,拍不出他那“面如?血”的精彩画面。但这部影片中,他那不为情动,坐怀不乱,一诺千金,不畏强恶的人品,在当时民族危亡关头,多少具有弘扬正气的作用,该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作品了。
现在,我已想不起是谁主演的了,也记不得影片中的插曲怎么一个旋律了。
赵老二就差点劲了,无名氏的《赵匡义智取符金锭》(见《全元戏曲》),一出场就是一个纨绔子弟形象,逛花园时,与符家小姐一见钟情,一拍即合,两相情愿,互订终身。而赵老大么,此公的感觉神经,实在迟钝。那赵京娘,为了使他明白自己说不出口的心意,“要公子扶她上马,又扶她下马,一上一下,将身偎贴公子,挽颈勾肩,万般旖旎。夜宿又嫌寒道热,央公子减被添衾,软香温玉,岂无动情之处?”尽管百般挑逗,赵老大兀自冥顽不化。“公子生性刚直,尽心服侍,全然不以为怪。”(见《警世通言》)
赵匡义不会犯这样的傻。当一个无赖,抢了赵匡义的彩球,强娶符金锭时,赵匡义岂能示弱,他是那种想得到什么,就必然要弄到手的强人,怎会甘心服输,召唤弟兄,附耳过来,口授妙计,三下五除二,一顶花轿坐着他的铁杆哥们,将这个求婚者打得屁滚尿流,另一顶便轿,用金蝉脱壳之计,抬着新娘子,洞房花烛,缔结良缘。所以,赵老二之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弑”兄以得帝位,也就不必奇怪了。
于是,他决定夺权了。
宋代文莹的野史笔记《续湘山野录》,描述了弑兄的整个过程:“急传宫钥开端门,召开封王,即太宗也。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女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寂然,无所闻,帝已崩矣。”
大雪天,急召开封王,显然不仅仅是邀他来宫里喝酒的,摒除一切闲杂人等,分明是有重要的话题交涉,不可能单是叙叙兄弟情谊。烛影下的历历镜头,很可能是赵匡胤从坚决拒绝交权,到终于在不情愿的状态下,同意退位的过程剪辑。让不耐再等的老弟,过皇帝的瘾,对赵匡胤来讲,是痛苦的割舍。所以才有在院子戳雪的动作,这是一种宣泄,表明他丧失掉最高权力,绝不是很开心的。然而,作为一个红脸汉子,还是勉励赵老二“好做好做”,终究肉烂在锅里,皇帝还是姓赵的在做。
但是,凡心黑者,无不手毒;凡手毒者,无不往死里整。赵老二懂得,在最高权力的争夺战中,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既然走出第一步,就没法止住脚。这世上哪有心甘情愿拱手让位的皇帝,要不将他“弑”掉,江山只怕坐不牢靠。万一他懊悔了呢?想到这里,一不做,二不休,将毒药下在他的酒杯里,只有让他彻底蒸发,方为上上之策。
那夜,开封城,下着好大的雪,被弑者很快鼾声如雷地睡死过去,弑兄者悄没声地离开了禁宫,脚印马上被厚雪覆盖住,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王府,这就是史书上的“烛影斧声”的千古疑案。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拥立新主的“苦迭打”,导演是赵匡义,不过字幕上没有打出来罢了。“受禅之事,本起仓卒,其实乃太宗与赵普主谋”(王鸣盛《蛾术编》),“是故太祖之有天下,太宗之力为多”(恽敬《续辨微论》)。大戏开场时,赵匡胤一下子进不了角色,颇有点被动。赵匡义,加上赵普那个村学究,加上石守信、王审琦等几个行伍弟兄,擐甲执兵,敲开他的门:“诸将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逼着他当这个皇帝。
宿酲未消的他,吓得跳下行军床,显然很狼狈,众人哪管这些,“即被以黄袍,罗拜,呼万岁,掖乘马南行”。懵里懵懂的他,被人劫持着,一路呼啸,从前线回到开封。周世宗柴荣的孀妻弱子,哪见过这种刀枪林立的兵变阵仗,早乱了方寸。即使到了此时,赵匡胤还没有找到当皇帝的感觉,认为自己依旧是周世宗的殿前都检点,一位应该秉承太后懿旨的军头。所以,一见到当朝宰相范质,腿软心慌,“呜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续资治通鉴》)
元人罗贯中有出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就写陈桥兵变中赵匡胤初当皇帝时的情景。到底不愧为《三国演义》的大手笔,简直小菜一碟,把赵匡胤捧着烫手山芋,不知如何当皇帝的尴尬,写得活灵活现。
这时候,柴荣的孤儿寡妻,已经拱手禅让,只求留条命在,可赵匡胤还是一口一声地“太后”、“幼主”,这场面,有点别扭,更有点滑稽,不过,情有可原,干什么行业都要有见习期,当皇帝也得有个熟练过程。罗贯中为他设计了一大段唱词,类似西方歌剧的咏叹调:“不争这老鸦占了凤凰巢,却不道君子不夺人之好?把柴家今日都属赵,惹万代史官笑。笑俺欺侮他寡妇孤儿老共小,强要了他周朝。”将这位天上掉馅儿饼,正巧砸在头上的幸运儿,心里面那一份不安和忐忑,侥幸和恐慌,快活和紧张,不知未来和手足无措的懵懂,都和盘托出来。
因此,赵匡义理直气壮地朝他讨这个皇帝当。公元959年,赵匡胤黄袍加身,某种程度上坐享其成,是他老弟给他披上的。因此,我想,这哥儿俩,早期可能有一个轮流坐庄的君子协定。等到坐上龙椅,享受到权力的盛宴以后,老兄欲罢不能,不想履行诺言。“太祖既与太宗同得天下,则太祖传子,自无以服太宗之心”(恽敬《续辨微论》)。于是,老弟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召他进宫时,那鸩药就揣在怀里了。
权力诱惑,常使人目迷五色,失态失常,罔顾一切体面尊严人格道德。在我熟悉的这个无足称道的文人圈子里,那狗屁大的一点权力,也让一班无聊之士,钻营竞逐,排挤角斗,厮杀争夺,咬啃得不可开交的。幸亏赵匡义的鸩药失传,不然,多少次的追悼会大概都开过了。
看来,赵老二在开封府肯定有一间秘密的鸩毒制造工厂,产品不止一种,他下在赵匡胤酒杯里的鸩药,更属尖端。不但死得没有痛苦,而且死出焕然一新之感,真是太神奇了。据《续湘山野录》:“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逮晓,登明堂,宣遗诏罢,声恸,引近臣环玉衣以瞻圣体,玉色温莹如出汤沐。”
如此看来,这是一个酝酿已久的阴谋,一切显然都按照早就拟定的脚本进行。
“癸丑,帝(赵匡胤)崩于万岁殿。时夜四鼓,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赵匡胤之子)。继恩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赵匡义),见左押衙程德元坐于府门与俱入见王,王大惊犹豫不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久不出。继恩促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矣。’时大雪,遂与王雪中步至宫。继恩止王于直庐,曰:‘王姑待此,继恩当先入言之。’德元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乃与王俱进至寝殿。(皇)后闻继恩至,问曰:‘德芳来邪?’继恩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勿忧也!’”
修正史者,多为名列庙堂的官员,对于人和事,褒和贬,一字着笔,往往思量再三,持极审慎的态度。他们对于家国的盛衰兴亡,人物的悲欢离合,也不是心如枯井,无动于衷的,但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主流意识,总是要约束个人感情的弛张。野史作者,多为藏身山林的文人,情绪用事,过犹不及,容易沸腾,容易爆炸,容易在笔墨中透露出爱憎分明的态度,所以,这种不受官方箝制的民间话语,或许比正史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即使从毕沅《续资治通鉴》以上这段文字,也有许多耐人寻味之处。王继恩,怎么说也应该是赵匡胤的嫡系心腹,不然不会让他当大内总管,现在却左袒赵匡义,显然早被收买,成了他埋伏在老哥身边的特工;程德元,似乎是赵匡义的私人医生,半夜三更,大雪纷飞,坐在王府门口等候,更是匪夷所思的行动。皇后不得不走当年柴荣孀妻的老路,只求饶命。近人陈登原在《国史旧闻》中案:“太祖病在壬子,次日癸丑即死,且不及医人一脉,又时当十月,亦无急性疫疠可能。李焘《长编》记太祖后,泣告太宗,母子之命,尽托官家。毕氏《续通鉴》,则记太祖后泣,见晋王至,愕然。何为而泣?何为愕然?事固不难言也。”
谁知是不是王继恩私开宫门?谁知程德元是不是制鸩专家?还有那个“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在这次政变中扮演什么角色,都是大有疑问的。
宫廷里的权力斗争,从来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赵匡义的政变,无论怎样掩人耳目,仍是疑窦丛生。尽管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在《涑水记闻》这部记载宋代早期史料的著作中,对这个“兄终弟及”的过程,采取了讳莫如深的态度,但《湘山野录》、《建隆遗事》、《东都事略》等野史,不持官方立场,就没有这种导向上的顾忌了,给后人留下了线索。即使以元代大臣脱脱主修的《宋史》说法:“太祖崩,帝遂即皇帝位”,《辽史》说法:“宋主匡胤殂,其弟炅自立”,一个“遂”,一个“自立”,字里行间,看得出正史也认为赵匡义取得帝位,并不是正常的继承。明代张燧说过:“艺祖舍子立弟,亘古未有,烛影斧声之疑,恐难置喙于后世也。”
赵翼《廿二史札记》认为:“角力而灭其国,角材而臣其人,未有不猜防疑忌而至于杀戮者,独宋实不然。”他认为,这是“宋太祖、太宗,并包天下之大度。”其实,这笔账算不至赵炅头上。
他在“斧声烛影”以后,登上帝位,南唐,吴越,南汉等周边割据政权的降服者,相继暴卒,死得十分蹊跷。据姚叔祥《见只编》:“李后主以七月七日生,七月七日毙,钱?以八月二十四日生,八月二十四日毙。各以其生辰死者,盖猜忌未消,皆借生辰赐酒,而毒毙之也。”那个生怕喝鸩酒的刘,何其警惧,结果还是进宫吃了御赐的宴席后,得急症而亡。西蜀的孟昶,据《国史旧闻》:“昶为惨死,但观其母不哭可知,与姚叔祥所记李煜、钱?之死,当为相同。”孟昶五月乙酉抵开封,六月庚戌卒,死得也飞快了一点,那时,赵匡胤尚在,估计负责慰劳这位降主的赵匡义,又请他喝了鸩酒。
赵炅对待已经降服的死老虎,尚不肯放过,必除之而后快;那么,对于活老虎,其弟廷美,其兄子德昭、德芳,这些有条件,有本钱,跟他也能玩一玩“苦迭打”游戏的血亲,从他弑掉老哥那一刻起,就不打算放过的。这一点,太祖后很清楚,她说母子之命,系于官家,赵炅还假惺惺地说共享富贵,其实,流出几滴鳄鱼泪的同时,也在生死簿上,给这三位画了勾。
这个消灭政敌的过程,真可怕。公元979年(太平兴国四年),德昭被迫自杀;公元981年(太平兴国六年),年仅二十三岁的德芳,突然夭亡;公元984年(雍熙元年),廷美在忧悸成疾中死去;还有一个廷俊,太宗根本不承认是兄弟,说是来历不明的带犊子,自然也就不知所终。由于他把所有可能危及他统治权力的亲属,分别用各种残忍手段,一一加以屠灭,赵氏皇族中间的白色恐怖,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以致他自己的亲生儿子元佐,也受不了频繁出现的惊吓,害了一场大病,最后成了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最后,这位权力狂人,箭创复发,五内俱焚,死于非命,似乎也有一点罪有应得的意思。
强烈的权欲,驱使人堕落,驱使人无恶不作,这对赵炅来说,是绝对应验了的。
康德曾经说过:“掌握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会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这是针对一般握权者的泛泛而言。而那些怀着私念、私心、私欲、私利的握权者,就更麻烦了。因为,即使是芝麻绿豆大小的权力,到了这些人的手中,也可能注入一份邪恶,而权力愈大,邪恶愈多,谁知道会制造出一个什么样的对人对己的灾难后果呢?
我想,历史所以成为一面镜子,就是能够给我们一点清醒。若是权力加上清醒,足够大的权力,有足够多的清醒,赵氏兄弟的悲剧,大概是不会发生的。
假设有人编一部《中国贪污史》,大概少不了赫赫有名的贪官严嵩,假如有人另编一部《中国廉政史》的话,大名鼎鼎的清官海瑞,则更是领衔主演的人物。无论前者和后者,巨贪和大廉,都出在明代嘉靖年间,我想,绝算不得是这位皇上的荣光。这两位文人的截然相反的活法,倒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挺特别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