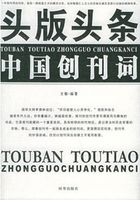
第5章 《时务报》
[创刊时间]1896年8月9日。
[创刊地点]上海。
[创办背景]
当“强学会”及其刊物被查封后,改良派力谋重振旗鼓,决定继续创办报刊以宣传其维新变法思想。1896年8月9日,黄遵宪、梁启超、汪康年等又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内粱雇超担任主笔,汪康年任总经理。麦茁华,徐勤、欧榘译、搴炳旗(太炎)等参加撰述和编辑工作。这是一份旬刊,形式如线装书,每期20余页。所刊登的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文章,深受思想开明的士大夫和新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欢迎,有些官员甚至封疆大吏也以订阕《时务报》为时髦。潮广总督张之澜还曾称赞《时务掇》“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并与湖南巡抚陈宝箴饬令所辖各府厅蝌县订购。给各级官员及书院学生阅读。该报销行量最多时高达17000余份,创造了当时图内报刊发行量之最高纪录。
1897年,《时务报》创始人之一的汪康年从内部排挤粱启超。在汪康年的控制下,该报言论迅速收敛并日趋保守,两《时报务》也因此而日益衰落。
康有为、梁启超于心不甘。1898年7月,他们为夺回这一重要舆论阵地,上书给光绪帝,请求将《时务报》改为官报,由粱启超专门负责。汪康年则迅速变招,在《时务报》出至第69期后,将其改名为《昌言报》,并于8月17日出版第1期。汪的这一举动遭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的抗议,但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康、梁逃往海外,《时务报》终未能恢复出版,而汪康年的《昌言报》在1898年11月也停刊了。
作者汪康年小传
汪康年(1860—1911),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字穰卿,晚号恢伯。光绪进士。张之洞幕僚,两湖书院史学斋分教。中日甲午战争后,愤励变法图存,欲化愚弱为明强。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参加上海强学会。次年与黄遵宪办《时务报》,自任经理,延梁启超主编。曾著文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力言中国宜伸民权,重公理,尚创作百贱安闲,尚改革而贱守常。后改办《昌言报》,不久停刊。1898年创《时务报》于上海,旋易名《中外日报》,拥护清政府实行“新政”。曾支持上海人民反对法人侵占四明公所公墓。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俄军久驻奉天(今沈阳)不撤,他愤然腾电中外,慷慨力争。1904年任内阁中书。1907年在北京办《京报》。1910年(宣统二年)办《刍言报》。有《汪穰卿遗著》、《汪穰卿笔记》等。
[创刊词译文]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根除闭塞求其通畅,这样便有利于发挥舆论阵地的作用而使天下清明。
国家的治国措施,老百姓不知道;老百姓的疾苦,统治者也不清楚。
本报为一些有识之士所办。对世界各国最近发生的事情,及时翻译成国文,让读者就可以知道国际当前的形势和一个国家兴衰的原因。就不至于坐井观天,夜郎自大;详录各省新的政见,可使读者了解到新法的好处。而反对者就会少一些;收集载录政府与各国交涉方面的事件,可使读者知道国家的政体不建立完善,就要受人欺辱,不懂得法律,就会被人愚弄;所以发愤学习吸纳新的知识,才能不忌以前因无知而受的耻辱;登载政治、艺术和一些学术方面的知识,可丰富读者的知识范围,使其耳聪目明。而不至于拖着八股文章或一味醉心于考据论证诗词典章而自得其乐,以至于空谈而自以为了不起了。
[焦点评析]
汪康年在创刊词中申明“去塞求通”之宗旨。列述西方国家报业的发达,“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认为“无耳目,无喉舌,是日废疾”。不了解世界形势,不闻不问国内大事,这是“有耳目”等于“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这是“有喉舌”等于“无喉舌”。起“废疾”,助“耳目喉舌”,就要依靠报馆。报馆是“去塞求通”的利器。文章还对报纸的体例作了说明:“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理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
汪康年大胆谋求“各省新政”,“奋励新学”,他的《中国自强策》和《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也写得大胆新颖。他批判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其治多禁防遏抑之制,而少开拓扩充之意”,他明确指出:“至今日而欲力反数千年之积弊,以求与西人相角,亦惟日复民权、崇公理而已。”其具体主张是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立法与行政分离,既立上下议院,又设相臣。下辖户部、刑部、商部、农部、外部、兵部、工部、民部、海部、教部、邮政等十一部,取代军机处行使政府职权,各部大臣及各省督抚的任免,均由议院投票裁决,做到职责分明,“在事之人,有治事之权;事外之人,有监察之权”,彻底治愈专制制度下的“官邪”习气。他还大谈实行民权有三大好处:一有助于行君权,二有助于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三可以民权抵御西方列强的要挟;论证实行君民共治,符合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不存在顽固派所说的“患权之下移”、“豪强横行,乱且未已”的问题;断言“天下之权势,出于一则弱,出于亿兆人则强,此理断断然者”。
《时务报》高举变法图存的大旗,态度鲜明,议论透彻,且文笔大多清新流畅,富有激情,因而大受读者欢迎,“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几十年后,有人对《时务报》的轰动效应仍记忆犹新。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追叙说:
《时务报》在上海出版了,这好像是开了一个大炮,惊醒了许多人的迷梦。……尤其像我们那样的青年,最喜欢读梁启超那样通畅的文章。当时最先是杨紫麟的老兄。寄到了一册,他宣布了这件事,大家都向他借阅,争以先睹为快。不但是梁启超的文章写得好。还好像是他所说的话。就是我们蕴藏在心中所欲说的一般。……一班青年学子,对于《时务报》上一言一词,都奉为圭臬。除了有几位老先生,对于新学不敢盲从,说他们用夏变夷,但究为少数,其余的青年人,全不免都喜新厌故了。
中国自有报以来,还没有那家报纸像《时务报》这样刊行不久就风靡全国,产生如此强烈的社会影响。变法运动的高涨和“诏定国是”的实现,《时务报》无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时务报》的创办,得到了封疆大吏张之洞的赞助。《时务报》最初的开办费,主要是移用上海强学会的余款(一千二百两),其中张之洞所捐占半数以上(七百两)。《时务报》发刊后,他又以湖广总督的名义,饬行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全省“文武大小衙门”,乃至“各局各书院各学堂”一体购阅,称誉《时务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士气……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但是,张之洞对《时务报》的支持不是毫无保留的,当《时务报》逾越他所认可的言论轨道时,便进行干涉和抑压。他一向不赞成康有为的“孔子改制”理论,认为称“圣人僭妄而又作伪,似不近情理”,及见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引称乃师的改制说,他大感不快。更令他不安的是,《时务报》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干犯时忌”的文字。第五册“有讥南京自强军语,及称满洲为彼族”;第八册指摘倭仁反对西学为“误人家国”:第二十三册谓“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这些言辞在张之洞看来是颇为“出格”的。梁启超在第四十册上发表的《知耻学会序》,尤其令他不能容忍的是“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接见西官,栗栗变色,听言若闻雷,睹颜若谈虎。其下焉者,饱食无事,趋衙听鼓,旅进旅退,濡濡若驱群豕,曾不为怪。士惟无耻,故一书不读,一物不知,出穿窬之技,以作搭题,甘囚虏之容,以受收检。”
张之洞认为此文“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恐招大祸”,立即电饬湖南巡抚陈宝箴“速告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禁止该期《时务报》在所辖地区发行。
张之洞对汪康年频频施压,要他对《时务报》上的言论严加“检对”。汪康年原系张之洞的幕僚,对张的督责不能无动于衷。1897年11月,梁启超应黄遵宪等人之邀,赴长沙主讲时务学堂(同时兼领《时务报》主笔)。汪康年在梁启超离沪后,只好“腰斩”了徐勤在《时务报》上连载的《中国除害议》,对梁启超寄来的文章也“改正”数处,他还打算请郑孝胥为总主笔(予梁启超正主笔之名),并且改变编辑方针,报中“论说”以选登外来稿件为主。汪、梁之间早有芥蒂,汪的行为使矛盾骤然激化。1898年3月,梁启超致函汪康年声明决裂,“非兄辞,则弟辞;非弟辞,则兄辞”。汪康年自然不肯辞去,梁启超也就从此辞去主笔一职,与《时务报》脱离了关系。
“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上奏朝廷,请将《时务报》改归官办,由梁启超办理,试图借官报名义,强收《时务报》。光绪帝下谕:准改《时务报》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但汪康年拒交报馆,并以“商款仍归商办”为理由,改《时务报》为《昌言报》,另行出版,只让出《时务报》“空名”给康有为的官报。康有为劾汪康年私改报名是违旨非法,张之洞则为汪辩解说:“《时务报》乃汪康年募捐集赀所创办,未领官款,天下皆知,事同商办。”“康自办官报,汪自办商报,自应另立名目,何得诬为抗旨?”与此同时,梁启超抓住汪康年在改《时务报》为《昌言报》所刊的启事中,有“康年于丙申秋创办《时务报》,延请新会梁卓如孝廉为主笔”等语,发表《创办时务报原委记》驳之,声明创办《时务报》非汪康年一人之功。汪康年据理力争,撰文相辩。双方大打笔墨官司,一时沸沸扬扬。未几,戊戌政变发生,这场争执乃不了了之。
汪康年由此也看清了康梁办报“实出于为清帝谋,亦为一身谋”。总的来说,汪康年等辈所办的《时务报》虽然流产了,然而,毕竟达到了让“阅者知新法实有利益”的目的,如今思来,“其日新月异之迹”,仍然可寻。仍然让人耳目一新。